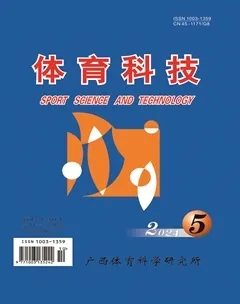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與創(chuàng)新機制





摘要: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大都是非正式制度,主要依賴“熟人社會”中的傳統(tǒng)要素,由民間信仰、宗族關系、族群認同、傳統(tǒng)節(jié)慶、習俗慣例等內在的傳統(tǒng)要素建構而成。文章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入手,明確制度文化以物質文化為基礎,以精神文化為反作用而發(fā)展變化,制度文化的邏輯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受到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制約和影響。基于這樣的邏輯推演,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同樣受到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制約和影響而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本文將由此分析和梳理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探究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創(chuàng)新機制。
關鍵詞: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 內生邏輯 "創(chuàng)新機制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諾思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guī)則,由正式的成文規(guī)則(正式制度)和作為正式規(guī)則基礎與補充的典型的非成文準則(非正式制度)組成[1]。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補充,共同構成社會的制度體系。非正式制度作為補充正式制度的非成文準則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產、生活和人際交往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是在一定范圍內或區(qū)域內約定俗成被社會認可的行為準則或行為規(guī)范。包括價值信念、風俗習慣、文化傳統(tǒng)、道德倫理、意識形態(tài)等”[2]。非正式制度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具有正式制度不可比擬的制度優(yōu)勢。作為非正式制度的一個方面,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經過幾千年歷史文化積淀和積累逐漸形成,對民族地區(qū)的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不竭的發(fā)展源泉。因此,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進一步完善,推動我國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
目前,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筆者以知網等文獻檢索工具進行成果檢索,首先以“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為主題進行文獻檢索,搜索的相關文獻資料成果約40余篇,主要成果有“全民健身視角下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的優(yōu)化”[3]“博弈論視角下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的主體分析”[4]等,提出目前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的表面現(xiàn)象是“上層形成、中層解釋、基層失效”,同時應用博弈理論分析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形成與發(fā)展,這些成果針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論述較少。筆者繼續(xù)以“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為主題進行文獻檢索,搜索到相關文獻資料只有3篇,主要成果為“少數(shù)民族村落傳統(tǒng)體育的非正式制度研究”[5]。通過實地調研桂西北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目,對不同民族的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進行梳理和研究,為后期的相關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郭瓊珠從鄉(xiāng)土社會的角度對鄉(xiāng)村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進行論述,提出非正式制度對鄉(xiāng)村傳統(tǒng)體育的影響以及鄉(xiāng)村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路徑[6]。筆者最后以“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與創(chuàng)新機制”為主題進行文獻檢索,沒有發(fā)現(xiàn)相關的文獻資料成果,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與創(chuàng)新機制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強,雖然缺乏相關的文獻資料,但民族體育制度的相關研究為本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源于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本身的發(fā)展,大多誕生于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村落。本課題針對桂西北、桂東南等民族傳統(tǒng)體育盛行的村落進行走訪和調研,這些村落包括壯族、瑤族、苗族、侗族等多個民族的聚居區(qū)域,涉及螞拐舞、搶花炮、長鼓舞、蘆笙踩堂、州佩功夫、十八路莊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tǒng)體育項目。本文主要運用觀察、訪談和收集資料等實地調研方法對這些區(qū)域的傳統(tǒng)活動進行調研,《社會學研究方法》作者風笑天認為,實地調研法是一種深入到研究現(xiàn)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參與觀察和非結構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并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定性分析來理解和解釋現(xiàn)象的社會研究方式。費孝通先生曾運用這樣的研究方法對江蘇省吳縣開弦弓村調研,著有《江村經濟》一書[7]。筆者通過這些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目的實地調研了解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從萌芽到成熟再到現(xiàn)在發(fā)展的過程,考究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內在的發(fā)生和形成邏輯,發(fā)掘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創(chuàng)新亮點,凝練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和創(chuàng)新機制。
1 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文化是社會發(fā)展的動力。馬克思曾指出,人類社會文化由三個層次構成:第一個層次是物質文化;第二個層次是制度文化;第三個層次是精神文化。其中,物質文化是基礎,制度文化是中介,精神文化是更高的上層建筑[8]。許蘇民先生在研究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的關系時認為:“三者是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物質文化中滲透著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為物質文化所決定,同時又以一定的精神文化觀念作為存在的前提,并在其中凝結著、沉淀著精神文化的因素。精神文化歸根到底為物質文化的發(fā)展水平所決定,但又反作用于制度文化和物質文化[9]。”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屬于社會制度文化的一類,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則是以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為基礎,又受到民族傳統(tǒng)體育精神文化反作用而逐漸演變與發(fā)展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之間的關系見圖1。
1.1 以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為基礎形成的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物質文化是指人類創(chuàng)造的物質產品體現(xiàn)出的文化,是人類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技術和物質產品的顯示存在和組合。依據物質文化本質屬性,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則包括民族傳統(tǒng)體育選定活動舉行時間、建設的運動場地、使用的器械物品、繪制的圖騰紋飾、穿著的民族服裝等,這些物質文化影響和制約著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1.1.1 以時間節(jié)氣文化為基礎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節(jié)氣是上古農耕文明的產物,最初是依據斗轉星移制定,是古代人民長期經驗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早在春秋時期就定有仲春、仲夏、中秋、仲冬等節(jié)氣,經過不斷改進成為指導農業(yè)活動的節(jié)氣文化。依據這種以自然形成為基礎的節(jié)氣文化,各少數(shù)民族根據本民族特點制定了不同的節(jié)慶日進行祭祖、慶祝和祈福等民族活動。廣西壯族、苗族、瑤族等在農歷三月三會舉辦大型的民族體育活動,這是一個隆重而盛大的節(jié)日。苗族古老的拉鼓節(jié)會在農歷九、十月?lián)袢张e行,而且有大小鼓之分,拉大鼓是十三年一次,為期十三天,拉小鼓是七年一次,為期七天。這些民族傳統(tǒng)體育活動舉行的時間規(guī)則節(jié)氣文化主要依據自然的節(jié)氣文化為內生邏輯產生并發(fā)展,節(jié)氣時間的內生邏輯較為清晰。
1.1.2 以場地建筑文化為基礎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活動的場所一般由自然地形改造而成。苗族的蘆笙坪是將一塊相對平坦的地方進行平整化的處理,場地中央建有七八米高的蘆笙柱,是苗族人民蘆笙踩堂、賽蘆笙的主要場所。蘆笙柱是每個苗寨蘆笙坪必不可少的建筑物,其用圓條杉木做主柱,用雕刻別致的石墩做柱腳來穩(wěn)固主柱,柱腳上刻有詩對和豎立日期,底層搭兩根十字架用來靠放大蘆笙、懸掛小蘆笙,象征四面八方來客的團結;中層一對水牛角,象征苗家人友好往來,互相贈送貴重的禮品;靠近頂端處是一只葫蘆,象征著苗家人生活富裕,有酒有肉;頂端是一只展翅的白錦雞,象征著苗家人的騰飛。整根柱子雕龍畫虎,形象逼真(見圖2)。整個蘆笙柱的物質文化孕育出蘆笙柱制作和使用的制度、規(guī)則文化,這種場地建筑文化催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又體現(xiàn)出苗族人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精神向往。
1.1.3 以器具紋飾文化為基礎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器具文化是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內容,器具的造型、飾紋和飾物的設計制作都有嚴格的規(guī)范。拉鼓節(jié)是苗族最為古老的傳統(tǒng)節(jié)日,也是苗族最隆重的祭祖活動。按照規(guī)范,拉鼓制作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要鼓主和鼓師帶族人上山砍伐“都花”樹作為制作拉鼓的材料;第二步是將“都花”樹量出三度三柞的長度,并將樹心鑿空,用牛皮將鼓的兩頭釘緊封住,做成中間粗兩端細的長鼓,還要在鼓桶上鉆兩個通氣眼,相傳是避免誤入鼓中的兒童因熟睡未被發(fā)現(xiàn)而窒息,這種制作拉鼓的規(guī)則依托于“都花”樹的材質和賦予在“都花”樹的物質文化;第三步是在拉鼓上裝配好水牛角,表達苗族人民對牛的崇拜和敬仰,體現(xiàn)了農耕時期耕牛對人民生產生活的重要性,賦予耕牛的物質文化已經融入人民的各類活動當中,影響著拉鼓節(jié)活動非正式制度文化的發(fā)展[10]。圖3為拉鼓實物圖。廣西三江侗族素有“三月三”搶花炮的傳統(tǒng)習俗。花炮一般分為頭炮、二炮和三炮,一般由傳承人盡心制作,每一炮都制作得非常漂亮(見圖4)。花炮漂亮的外表不僅體現(xiàn)了活動的喜慶氛圍,更體現(xiàn)出人們物質文化水平的提升。每一炮都有不同的含義,程陽大寨花炮,頭炮寓意福祿壽喜,第二炮寓意升官發(fā)財,第三炮寓意人丁興旺,這樣的規(guī)則寓意充分體現(xiàn)了侗族人民在當時物質文化基礎上對“求福、求財、求子”這種程序制度規(guī)則文化的訴求,有力地維護了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的傳承[5]。
1.1.4 以民族服裝文化為基礎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芒篙是儺文化的體現(xiàn)。在苗語中,“芒”意為古老、往昔,“篙”意為舊。“芒篙”即指古舊的東西,被苗族人們視為溝通人與神陰陽兩界的媒介。苗族祖先根據直接所說或觀察到人死后變得扭曲、猙獰、可怕的面目,這樣的物質文化基礎催生出芒篙齜牙咧嘴、表情怪誕面具的設計和制作規(guī)則,再配以芒篙藤制成的蓑衣,嫣然成為一個丑陋、恐怖、怪誕人物形象(見圖5),通過揮動具有神力的竹棍和蹲、跳、翻、躺等動作驅魔壓邪、禳災去禍,保護村寨平安。納洞村螞拐舞的傳統(tǒng)服飾通常裸露上身,皮膚繪有蛙紋,下穿印有蛙紋的綠色短裙(見圖6),另外,“毛人”(代表田里的毛蟲)則穿戴用棕桐皮制作的衣帽,模擬毛蟲形象。納洞村人通過對青蛙和毛蟲的觀察和理解所形成的服裝文化深刻影響著螞拐舞的制度文化,作為物質與精神的文化載體,民族體育服飾所蘊含的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已經成為體育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1]。
1.2 以民族傳統(tǒng)體育精神文化為反作用力形成的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精神文化是人類在從事物質文化基礎生產上產生的一種人類所特有的意識形態(tài),是人類各種意識觀念形態(tài)的集合,屬于精神、思想、觀念范疇的文化,代表一定民族的特點反映其理論思維水平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觀念、心理狀態(tài)、理想人格、審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總和[12]。民族傳統(tǒng)體育精神文化應包括價值、道德、禁忌、禮儀、獎懲等方面,這些精神文化反作用影響和制約著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1.2.1 以價值文化為導向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非正式制度的價值是“約定社會行為的動機、目的和價值訴求”,處于制度系統(tǒng)的核心層次,它決定著制度的性質和演變的方向[13]。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也有相同的價值。在對民族體育行為的約束方面,民族體育非正式制度較政府的法律和政令更有效。搶花炮活動就是運用民間非正式制度來約束人體動作行為的比賽,搶花炮可以通過擠、抱、扳、鉆、傳、攔、奪等手段取勝,但禁止使用打人、踢人等惡意的動作,也不允許攜帶任何器械參加搶花炮的活動,避免發(fā)生傷害性事故[14]。首先,這種非正式制度體現(xiàn)出侗族人民對公平、公正、安全、健康活動的精神訴求,成為相互約定的社會行為規(guī)則,這種精神訴求反作用于非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執(zhí)行。其次,民族傳統(tǒng)體育活動大都伴有民間信仰成分。壯族螞拐舞的文化源頭是螞拐崇拜,這種價值訴求就是通過祭祀本土神靈獲得太平安康的生活,在這樣的價值訴求下形成愛護、敬畏青蛙的非正式制度文化。
1.2.2 以道德文化為導向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道德通過社會的或一定階級的輿論對社會生活起約束作用[15]。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對參賽人的選擇上往往使用一定的道德標志來衡量,壯族舞春牛挑選遵規(guī)守法、敬重長輩、頭腦靈活且能歌善舞的村民作為隊員;程陽大寨搶花炮規(guī)定在“還炮”時,只有那些有福氣、家境好,不賭博、不犯罪、不違紀違法的才可以拿炮歸還;芒篙扮演者也是選擇人品正直、有威信、樂于助人、身體健壯的苗族男性青壯年擔當,模擬攙扶、過橋等生活化的動作,表現(xiàn)苗族對人際間互助信任、友善關系的贊美以及對和諧社會的頌揚。這些規(guī)定折射出村落重德敬賢的體育道德文化,也是在這樣道德文化的導向下催生出相應非正式制度文化。
1.2.3 以禁忌文化為導向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禁忌是指在一些特定的文化或是在生活起居中被禁止的行為和思想,目的在于促使人們約束自己的言行[16]。在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村落體育中,禁忌是非常多的,壯族舞春牛規(guī)定,入戶表演時不可將春牛臀部對著主家祭臺,避免對戶主祖先的不敬,同樣退出廳堂時須臀部在前倒退出門;由于對花炮的崇拜和敬仰,侗族在“游炮”時任何人都不能擋路,否則碰壞的東西不予賠償;苗族拉鼓節(jié)“忌鼓”期間,外出的媳婦則要接回來參加活動,但已嫁出的本寨女子一律不準回娘家;侗族在斗牛比賽的前一天禁止在牛欄周邊出現(xiàn)“打擊性”行為,男人不準放槍,以免因為驚嚇到牛傷害牛的銳氣。這些民族體育禁忌規(guī)則的本質是少數(shù)民族人們在長期的社會交往中所積累的經驗以及形成的社會規(guī)范,是禁忌文化促進規(guī)則文化的內生演變,對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行為具有很強的約束力。
1.2.4 以禮儀文化為導向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宋代理學家朱熹曾說儀、式、刑,皆法也,禮儀在詞典里解釋為典禮的秩序形式。在少數(shù)民族體育中往往有著嚴格的禮儀規(guī)范。螞拐舞中找螞拐、祭螞拐、葬螞拐和拉鼓節(jié)中卜鼓、祭祖、箍鼓、唱鼓、拉鼓、忌鼓等一系列的禮儀程式都具有類似的文化內涵[10]。此外,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往往具有一定的動作儀式文化。舞春牛,其動作程式包括賀年、開耕、戲牛、豐收等,具體動作有吃草、犁田、播種、牛鳴叫、牛轉身、牛洗澡、牛公摸牛頭、牛公趕牛等。這些動作,歷經數(shù)代傳承人的凝練而程式化,這樣的動作禮儀程式文化充分表達出壯鄉(xiāng)人民崇敬和愛憐耕牛的樸素情感。這些秩序規(guī)則制度文化往往隱含著人民對禮儀程序的需求,通過這樣的儀式文化來強化民族傳統(tǒng)活動的規(guī)則意識。
1.2.5 以獎懲文化為導向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內生邏輯
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一般都有獎懲規(guī)則,這些獎懲規(guī)則也是基于當時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觀念。程陽搶花炮獲勝方會得到花炮臺、紅豬、米酒等獎勵;平流村斗牛的獎品一般為電風扇、水鞋、水壺、鐮刀等;有些傳統(tǒng)體育活動沒有物質獎勵,觀眾的掌聲、喝彩、贊譽就是最好的獎勵,納洞村的螞拐舞就是用實際的掌聲和喝彩聲給予演員們精神上的獎勵。
在懲罰方面,有些傳統(tǒng)體育活動就有明確的處罰規(guī)則。侗族斗牛規(guī)定:組織斗牛的村寨必須在約定的時間將牛牽到比賽現(xiàn)場,否則就要賠禮道歉請吃吃飯,或者取消斗牛比賽資格;各村寨之間如果因為斗牛比賽發(fā)生爭執(zhí)或動手打人的都要受到罰款的處罰[17]。這些處罰雖然在實際生活中的約束力不夠強大,但在村寨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人際關系中卻極為重要。受到處罰的人會失去個人信譽和友誼,這對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對受處罰者的生存狀態(tài)有非常重要的負面影響,從而起到懲罰的效果。因此,這樣的獎懲規(guī)則制度文化是基于人們生產關系和人際交往意識產生的。獎懲文化不僅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得以發(fā)展傳統(tǒng)的需要,更是激勵和督促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順利開展的需要。這種獎懲意識反饋到規(guī)則當中逐步演化成獎懲制度文化。
2 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制式制度文化的創(chuàng)新機制
機制,最早源于希臘文,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現(xiàn)在多指有機體各要素之間的結構關系和運行規(guī)律。基于物質文化基礎性和精神文化反作用性,制度文化創(chuàng)新機制源于物質文化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兩者之間各自的內在關系和運行規(guī)律。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的創(chuàng)新機制取決于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兩者各自的內在關系和運行規(guī)律。
2.1 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要素催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創(chuàng)新機制
環(huán)境變化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目非正式制度文化具有一定創(chuàng)新作用,高山瑤的長鼓舞,動作多具有山地攀行的特點,講究“蹲騰立跳,屈腿弓腰”,動作粗獷靈活,沉穩(wěn)有力,這跟高山瑤族居住環(huán)境息息相關,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催生出不同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目及非正式制度文化[5]。隨著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社會環(huán)境在推動少數(shù)民族生活方式轉變的同時,也促進民族傳統(tǒng)體育活動方式不斷變化,體育非正式制度也得到創(chuàng)新。隨著社會發(fā)展,電視、無線通訊等大眾媒體這樣的物質文化不斷融入到少數(shù)民族生活,人民對現(xiàn)代舞蹈審美產生認同感。基于這樣的文化發(fā)展,在文體局專家指導和幫助下,黃泥鼓傳承人以原有的走、跑、蹲、挫、旋、轉等動作為基礎,融入了跳躍、俯沖、托舉、奔跑等現(xiàn)代舞蹈動作元素,這些動作符合當?shù)噩幾迦藗兇肢E奔放的性格,獲得當?shù)厝藗兊恼J可,有力地推動了黃泥鼓舞非正式制度文化創(chuàng)新。
2.2 民族傳統(tǒng)體育精神文化要素催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創(chuàng)新機制
(1)價值觀念影響。價值觀念屬于精神文化范疇,處于文化的核心層次,精神文化對制度文化的反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價值觀念對制度文化的反作用。李志清學者認為,侗族搶花炮的精神文化源于清代廣東漢人的影響[18]。清代廣東漢族商人逆江西上,將搶花炮的“求財”價值觀一起帶到了桂西北的侗鄉(xiāng)。所以,侗族搶花炮“求財”的價值觀念是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產生的,這種價值觀念的創(chuàng)新也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融合。
(2)社會觀念影響。社會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的發(fā)展。富祿搶花炮在傳統(tǒng)上具有“求福、求子、求財”三方面非正式制度的儀式程序,但解放后受社會觀念的影響,其儀式程序被調整為“團結炮、勝利炮、幸福炮”,這樣的制度創(chuàng)新發(fā)展是被當時社會觀念深刻影響的。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在民族傳統(tǒng)文化政策方面變得相對寬松,富祿搶花炮又回歸到“求福、求財、求子”非正式制度儀式程序,這充分體現(xiàn)出社會觀念對非正式制度文化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影響。
(3)宗教信仰影響。宗教信仰是精神文化的重要內容,是人類所具有的普遍文化特征,具有神秘神話色彩,它是人類精神的階段性體現(xiàn)。宗教信仰一旦形成,便具有“制度原則”的功能,并引導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這個方面發(fā)展。螞拐舞就是壯族人民對螞拐(青蛙)的崇拜和信仰,在這樣的精神支配下,創(chuàng)造和形成了找螞拐、祭螞拐、葬螞拐、跳螞拐的非正式制度文化;苗族拉鼓主要是祭祀祖先、追懷先人,在這種精神信仰的引導下,苗族人民也創(chuàng)造了以卜鼓、祭祖、箍鼓、唱鼓、拉鼓、忌鼓等追懷祖先的非正式制度文化。
2.3 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精神文化要素催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創(chuàng)新機制
壯族拋繡球這項民族傳統(tǒng)體育活動的非正式制度文化的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一個典型案列。學者韋曉康、李霞的研究表明[19]:拋繡球運動的形成最早得益于壯族傳統(tǒng)狩獵文化,在狩獵采集的過程中利用繡球的雛形“飛砣”對獵物進行擊打和捕殺,這時使用飛砣的規(guī)則都是基于如何擊中獵物為目的;進入農耕時代,“飛砣”文化又受到壯族傳統(tǒng)的稻作文化影響,“飛砣”成為裝有稻、豆、粟、谷等谷物繡球,這些谷物繡球被注入了五谷豐登的內涵與對豐收的渴望;之后繡球又受益于壯族傳統(tǒng)的婚姻文化,成為塑造男女定情信物的象征,同時賦予繡球運動的愛情涵義;接著,拋繡球又受益于歌圩文化,一項民族傳統(tǒng)體育比賽項目,需要按照規(guī)則將繡球拋過由一根長桿支撐的一個環(huán)狀物。拋繡球這一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不斷創(chuàng)新基于“飛砣繡球”“谷物繡球”(圖7)的物質文化發(fā)展,同時也受到“愛情繡球”“對歌繡球”“比賽繡球”(圖8)這樣的精神文化的反作用,兩種文化共同作用促進拋繡球制度文化創(chuàng)新機制的不斷發(fā)展。
3結語
我們要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高度重視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發(fā)展過程中,其內生的邏輯主要源于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內容和要素的發(fā)展,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的基礎作用和精神文化的反作用共同結果。民族傳統(tǒng)體育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創(chuàng)新機制在于民族傳統(tǒng)體育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要素創(chuàng)新,文化要素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規(guī)律形成創(chuàng)新機制,這個規(guī)律就是能夠沿著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向著更好的方向去發(fā)展,能夠產生良性社會效應進行創(chuàng)新,能夠產生正向功能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創(chuàng)新,只有這樣才符合民族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社會訴求,才能推動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的進一步繁榮。
參考文獻
[1]道格拉斯·C 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4.
[2]葉國平.論和諧社會中的非正式制度建設[J].社科縱橫,2007(5):10-12.
[3]吳秋來,謝小龍,張揚,等.全民健身視角下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的優(yōu)化[J].四川體育科學,2013,32(5):94-97.
[4]劉利容,吳秋來,唐麗君,等.博弈論視角下民族傳統(tǒng)體育制度的主體分析[J].當代體育科技,2014,4(12):152+154.
[5]孫慶彬,吳光遠,周家金,等.少數(shù)民族村落傳統(tǒng)體育的非正式制度研究:以壯、侗、苗、瑤等少數(shù)民族古村落為例[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4,31(1):64-69.
[6]郭瓊珠.非正式制度與鄉(xiāng)村傳統(tǒng)體育的發(fā)展:鄉(xiāng)土社會的視角[J].體育與科學,2009,30(3):12-15.
[7]楊丹.民族學實地調查法探析—以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為例[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
49-51.
[8]田旭明,沈其新.文化強國與當代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升華:馬克思主義文化結構論視角下的分析[J].理論導刊,2012(4):77-79.
[9]許蘇民.文化哲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08-109.
[10]錢應華,楊海晨.融水苗族拉鼓節(jié)的淵源、現(xiàn)狀及發(fā)展對策研究[J].體育研究與教育,2012,27(6):69-74.
[11]孫光芹,崔國文.試析中國民族體育服飾的文化特征[J].才智,2009(1):189-190.
[12]曾麗雅.關于建構中華民族當代精神文化的思考[J].江西社會科學,2002(10):83-88.
[13]蒯正明.制度系統(tǒng)的構成、層次架構與有效運作[J].南都學壇,2010(6):96-100.
[14]富祿129屆花炮節(jié)組委會.“三月三”搶花炮項目規(guī)則[S].2013.
[15]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xiàn)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259.
[16]李靈.體育禁忌研究[J].體育文化導刊,2010(4):151-154.
[17]徐曉光.“圣枯”與“牛籍”—侗族斗牛活動中的儀式與習慣法規(guī)則[J].原生態(tài)民族文化學刊,2010,2(3):75-80.
[18]李志清.儀式性少數(shù)民族體育在鄉(xiāng)土社會的存在與意義:以搶花炮為個案的研究(一)[J].體育科研,2006(4):17-25.
[19]韋曉康,李霞.論壯族繡球運動的文化淵源[J].體育文化導刊,2003(8):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