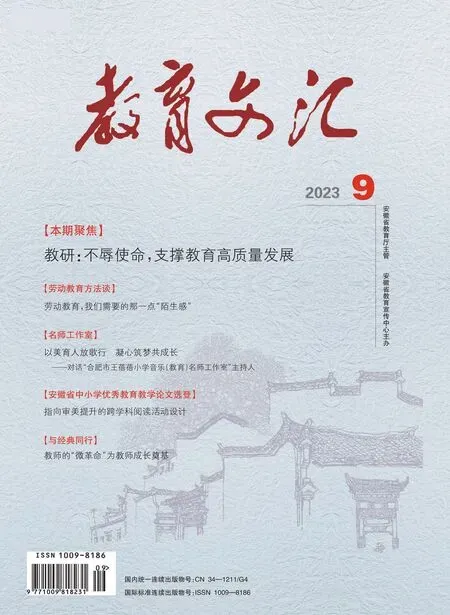勞動教育,我們需要的那一點“陌生感”
安徽藝術學院/柳友榮
大學時讀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感覺其中的“For what is time?”(何為時間)特別引人沉思。有關“時間”,沒人會問你這么個似乎“淺顯而笨拙”的問題,你毫無疑問內心澄明;可真當被問到“究竟什么是時間”時,你一時間會陷入混沌而無法梳理出清晰的結論。其實,類似于“時間”這樣的概念,我們身邊還有很多,即使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的教育領域,也會有我們熟視無睹、自以為是的熟悉的“陌生物”,譬如,“教育質量”。教育質量是什么?是知識的增加,抑或行為的改變?教育的本質是“人的發展”,從一開始教育的發生就是伴隨著人的不斷完善的需求的,是人全面發展的價值追求使然。然而,當教育越來越多地走進社會,接受社會資源、分享社會進步的同時,必然地履行了更多的社會責任。這些“工具理性”日趨強勢,就必然地規制了教育原初的“價值理性”的實現。當知識的增長和行為的優化過程,已經異化為人的發展的消極因素時,還能實現教育質量嗎?也正因為如此,德國教育家、哲學家雅思貝爾斯才不無憂慮地警告:教育是對靈魂的喚醒,而不是知識的堆砌。
其實,我們又何止是對“教育質量”應該保有一份“陌生感”,勞動教育呢?現在,我們的身邊,一談到勞動教育,腦海里閃現“農田”“插秧”“播種”“植樹”“割草”等等勞動場景,幾乎天經地義,把這些簡單地看作是勞動教育,生活中也絕對不會鮮見,甚至一些教育管理人員,也會不假思索地把勞動教育視同如此。“農田”“插秧”“播種”“植樹”“割草”是構成勞動教育的必然場景、充要條件嗎?很顯然,我們犯了主觀經驗主義錯誤。這種錯誤的產生,往往是因為我們對事理似乎過于熟悉,而想當然地“習以為常”,這叫“熟悉性遺忘”。為什么我們對幼兒常識性的“十萬個為什么”,很多時候會無能為力、緘默不語?因為我們對這個世界似乎太過于諳熟,念茲在茲、耳熟能詳,其實,我們經不起“追問”,難以應對打破砂鍋的執蓍。這不僅僅是因為“插秧”“播種”“植樹”“割草”本身只能代表傳統的農耕勞動,無法囊括更多形式的復雜勞動、綜合勞動等新時代的智慧勞動。而且,即便這些傳統的農耕“勞動”過程中也有天然并存的“教育”元素,比如傳授植樹技術、播種技巧等,但這絕對不等于我們就可以將這些勞動簡單地視同“勞動教育”。
一、“陌生感”的勞動教育
哲學家周國平先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女兒問媽媽:云的后面是什么呀?
媽媽答:是星星啊。
女兒又問:那星星后面呢?
媽媽接著答:還是星星。
女兒堅持:我問最后的是什么?
媽媽:……
這個故事中媽媽的“無語”和女兒的“懵圈”都給我們展示了一個面對無比熟悉世界的“陌生感”。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需要將我們習以為常的環境“陌生化”。“陌生化”究其本質就是有意識地去“解構”(deconstruction)思維中已有知識圖式系統,反思身在其中的生活世界。很多時候,這反而會給我們呈現一個不一樣的、絢麗多彩的“陌生世界”。我們需要“解構”“重構”勞動教育,是因為我們對傳統的“勞動教育”認識是那么的駕輕就熟、那么的無可厚非,甚至沒有一丁點兒“違和感”。我們都似乎習慣于把勞動看成勞動教育,把勞動資源看成勞動教育資源,把勞動成果看成勞動教育成果。
回想20 世紀50 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小學生勞動教育,勞動何嘗不是勞動教育的全部合法表達。那個時候,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大批人才,我們身處的世界簡單到“所學”就是“所用”,“所用”必有“所成”。我們在勞動中教會學生“種植”技術、“收割”技能、“編織”手藝……學生獲得這些生活本領后,就能面對現實生活,增強生活和生產的信心。
今天,如果我們依然一成不變地用這些已經被高度固著的、傳統的、“被建構”的知識來面對我們復雜而充滿未知的世界時,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勞動教育在當下,與勞動相去甚遠。就像一個會烹飪技術的年輕人,壓根兒就不愿意進廚房一樣。因為,勞動教育的目的,并不止于勞動技能的習得,否則,職業技術教育或者綜合技術教育就足夠了,何勞再開展“勞動教育”而多此一舉呢?按照2020 年3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中對“勞動教育總體目標”的概括:“使學生能夠理解和形成馬克思主義勞動觀,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體會勞動創造美好生活,體認勞動不分貴賤,熱愛勞動,尊重普通勞動者,培養勤儉、奮斗、創新、奉獻的勞動精神;具備滿足生存發展需要的基本勞動能力,形成良好勞動習慣。”可見,形成馬克思主義勞動觀念和良好的勞動習慣,熱愛勞動、尊重勞動,才是勞動教育的真正目的所在。很明顯,勞動教育不是職業教育,不啻勞動技術的習得,更傾向于勞動觀念的確立和勞動情感的養成。我們既不能把勞動與勞動教育畫上等號,更不能將勞動技能的傳授視為勞動教育的全部目標。
因此,面對我們近在咫尺的真實世界,我們需要帶著種種“質疑”和“反思”,審視“常識”,解構“真實”,才能在“陌生世界”撥云見日,心智洞明。
二、在教育邏輯里釋讀勞動教育“陌生感”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視角來看,重視勞動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的本質特征,承認勞動和勞動者的價值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最本質訴求。很顯然,在社會主義國度里談勞動教育,與資本主義社會里講勞動教育不能簡單地概而論之,更不能等而視之。即使從教育邏輯里去審視勞動教育,似曾相識的“勞動教育”讓我們“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情況還是相當程度地存在著。
(一)理論“陌生感”:在“五育融合”的體系中看勞動教育
在教育現實活動中,我們常常聽聞:雖然開展了勞動教育,但教育效果不盡人意,甚至還有“抵消育人效果”的論調。究其原因,我們不難得出,勞動教育效果不理想,源自對勞動教育的本質認識不清。一些中小學教師和學生家長把勞動教育看成是新增加的“額外”的負擔,學校也覺得每周得“多”出來“1 節課”需要安排,教師也認為是出于應對“檢查”而不得已為之……對勞動教育既沒有科學規范的認識,也沒有科學嚴謹的設計,更缺乏科學有效的推進。
一切教育活動,本質上從來就不是“碎片式”“分離式”的課程。它之所以以“學科”“課程”形式表現出來,是便于實踐操作。就像德智體美勞“五育”一樣,沒有孤零零的“智育”、孑然一身的“德育”、充滿物性的“體育”,也不存在“只見樹木”的“美育”,更沒有純粹“出力、流汗”的“勞育”。
勞動教育效果不好,是因為我們常常“窄化”勞動教育,就像把勞動“窄化”為生產勞動一樣,孤立地把“勞動課”視作勞動教育,自然取得不了很好的育人效果。其實,德育也不局限于那幾門德育課,班主任、輔導員、政教處(學生處)、團委、少先隊等,甚至包括校園文化、潛在課程,都是德育的有機組成內容;體育當然也不限于體育課,運動會、早鍛煉、課外活動等都是體育的必不可少的組成內容。因此,我們既不能無視“勞動課”的存在,也不能夸大“勞動課”的作用。
最近,還聽說了一個悖論:強調“勞育”與其他“四育”的融合,是不是就可以用德智體美“四育”替代“勞育”了。馬卡連柯說過,在任何情況下,勞動如果沒有與其并行的知識教育——沒有與其并行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教育,就不會帶來教育的好處,會成為不起作用的一種過程。[1]以勞樹德、以勞增智、以勞強體、以勞育美,不等于“勞育”沒有獨立性,可以被取而代之。其實,其他“四育”同樣要走“融合”之道。體育里沒有美育嗎?那種運動美、力量美因何而來?體育里沒有德育嗎?那些團結、拼搏、集體主義因何存在?“五育”原本就不是獨立的客觀存在,只是為了方便在人的教育活動中,思考和把握有關人的教育的“抓手”和“著力點”而涉及的同一個整體的五個方面。我們不能割裂其間的整體性,只從片段的、片面的角度看教育過程,這樣做只能是形同“盲人摸象”,令人啼笑皆非。
(二)現實“陌生感”:在資源缺失中看勞動教育
前段時間,在“學生接待日”中,學生向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宿舍的陽臺上落滿了各種殘枝敗葉,問怎么辦?一個宿舍里,住著4 位血氣方剛的新時代大學生,面對陽臺上的落葉,問校長怎么辦。這樣的匪夷所思的問題當時確實令我詫異。你說,是同學們缺少清除雜物的勞動技術,還是沒有勞動觀念和養成良好的勞動習慣?
誠然,勞動教育中“教”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勞動基本技能,還是幫助他們端正勞動觀念和形成勞動情感?現實中,不少學生缺少正確的勞動觀念和良好的勞動習慣,這可能還不僅僅是有沒有開設勞動教育課的問題。雖然,在2020年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文件下達之后,教育部又相繼頒行了《大中小學勞動教育指導綱要(試行)》和《義務教育勞動課程標準(2022 年版)》,但是,各地大中小學在落實和實施勞動教育時,除了有些學校還存在認識不到位的問題之外,還顯而易見地存在著師資隊伍專業化水平低、勞動教育教研活動匱乏、勞動教育組織不專業、勞動教育推進不科學等勞動教育資源缺失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催生了勞動教育現實“陌生感”,制約了勞動教育本質目標的達成,影響了勞動教育實施的科學性、規范性、增值性。
德國教育家凱興斯泰納說過,勞動教育本質上是一種人格教育,他以尊重別人的勞動果實、熱愛勞動、形成勞動習慣作為目標。所以說,勞動教育追求的并不是技能上的進步,而是道德和精神上的發展。勞動教育讓學生學會用“肢體”丈量物理和心靈的世界,樹立正確的勞動觀點和勞動態度,熱愛勞動和勞動人民,養成勞動習慣的教育,達成內在人格。由此可見,形成勞動觀念、勞動精神、勞動習慣才是勞動教育目的內涵。[2]
三、在歷史邏輯里釋讀勞動教育“陌生感”
勞動教育之所以重要,還是因為勞動與教育的關聯與結合自古有之。在原始社會里,成人的勞作與兒童教育過程幾乎完全融為一體,互為主輔。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積累不斷增加,就分離出專門的學校來完成教育下一代的任務,進而教育與生產勞動發生了分離。到了資本主義的大機器生產時代,“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重要形式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從“原始統一”,到“現代結合”,再進一步發展到當今社會的“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因此,勞動的形態發生了嬗變,有生產勞動也有消費勞動,有體力勞動也有腦力勞動,有生活勞動也有服務性勞動。“在民主主義的社會,凡是關于體力勞動、商業工作以及對社會所做的明確服務逐漸受人尊重”“勞動受人推崇,為社會服務是很受人贊賞的道德理想”。[3]
(一)勞動教育等于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嗎
綜上所述,簡單地把勞動教育歸結為“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是一種直觀錯誤。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是我們黨的教育方針,這種結合從今天來看,至少有兩個方面的結合形式:
一方面是校內的結合,即各種生產的實踐,比方說在校內打掃教室衛生、除雜草、植樹等相關活動,還包括我們校內各種專業的實踐活動;另一方面還有校外的勞動,包括我們的專業實習、志愿服務和社會實踐。教育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通過校內校外這兩方面的勞動,看起來好像我們已經開展勞動教育了,但其實這僅僅是我們的一種勞動實踐,跟勞動教育不是一回事。勞動教育本身是把勞動融于教育當中,通過科學的課程設計來使勞動本身融入教育元素。換一句話說,勞動只有與有關勞動課程設計相結合,才有可能稱為勞動教育。
就像我們去植樹,植樹本身是一種勞動,如果我們運用得好,學生會愛上植樹、愿意去植樹;如果運用得不好,學生在植樹過程當中會厭惡勞動,植完樹以后根本沒有對這個勞動過程的體悟,不珍惜這樣一種勞動的機會。不珍惜別人的勞動成果,也不熱愛勞動,那就不是勞動教育。也就說有勞動不一定就是教育。
勞動和教育、勞動和勞動教育之間不是一回事。如果簡簡單單就把勞動當成是勞動教育的話,顯然是不科學的。所以,勞動教育不等于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二)勞動教育是我們的教育理想還是對現實的一種妥協
當今社會,很多年輕人越來越遠離體力勞動。因為一般意義上的體力勞動在現代社會中已被機器人、人工智能替代了,那么我們現在再強調勞動教育,是不是把勞動教育看成是對現實的一種妥協呢?其實不是這樣。
在新時代,強調勞動教育是我們的一種教育理想,因為新時代離不開勞動教育,更加需要勞動教育。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勞動教育在現實生活當中很容易被理解成為勞動技能教育,于是我們教學生如何植樹、如何烹飪、如何收納,更加強調一些技能,卻忽略了勞動教育本身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一種通識教育,培養學生熱愛勞動、形成勞動習慣、尊重別人勞動果實這樣一種內在的品質。所以說勞動教育注重的是勞動觀點、勞動態度和勞動習慣的形成,解決的是我們一些通識性知識的形成。也因此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教育實際上是一種綜合的教育。
大家都知道,現代社會,閑暇時間越來越多。當物質更加豐富的社會到來時,更多的人已經不需要付出太多勞動就可以維持生活了。在(生活)衣食無憂的情況下,我們就特別需要用勞動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讓自己的閑暇生活變得更加有品質,學會享受閑暇生活。這樣,形成一些勞動的品質、掌握一些勞動的技能,就有助于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否則,我們的閑暇,就會變成簡單地追求一種像凡勃倫那句話所說的,有閑階層的這種生活方式,僅僅是為了炫耀。當我們有了一定的勞動技能,學會用勞動來享受生活的時候,我們就有更豐富的勞動手段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所以說,勞動應該是一種通識教育,是提升自己生活品質的一種方式。
四、在時代邏輯里釋讀勞動教育“陌生感”
馬克思肯定了勞動是人成為人的本質力量,同時也承認勞動的消極性。因而,本質上,勞動有屬人性和非屬人性兩種。[4]但是,在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足的新時代,勞動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讓學生學會勞動、熱愛勞動,還要引導學生追求勞動“屬人性”的幸福,把勞動看成美好生活之一部分,在屬人的勞動中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這樣一個命題: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快樂,還是周六和周日“閑暇”快樂?如果是周六和周日“閑暇”快樂,那為什么還有很多人在閑暇里選擇“種花養草”“釣魚種菜”的勞動?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給自己一個假設,如果沒有周一到周五的“工作”,還會有“閑暇”的快樂嗎?這樣結論就顯而易見了——“勞動是快樂的”。那么,人為什么還是本能地覺得“閑暇”快樂呢?這是因為在“工作”日里是有些“約束感”的,也正是在勞動所創造的“人與人之間的”“規制的”關系世界,人和外部世界的關系才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原來自在意義上的自然世界逐漸成為意義上的人類世界。[5]
那么,為什么“閑暇”里,人們還要自主地選擇“工作”“勞動”呢?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個時候的勞動屬于“自由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言,“我的勞動是自由的生命體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6]
隨著物質生活相對富裕,我們的教育會發生一些改變。就是當我們衣食無憂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到用更多豐富的生活方式來改善和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這樣我們會發現自由勞動離我們越來越近。掌握豐富的勞動技能是自由勞動的基礎。比如,當我們用幾天的勞動就能維持我們很多物質生活需要的時候,我們會有更多閑暇時間。周末,我們就希望帶著家人到郊外踏踏青,也希望租一小塊農田,種上蔬菜,一家人在融融親情中體驗勞動的快樂。其實,那些種的蔬菜、收獲的果實的價值,根本不抵往返路途中所消耗的汽油費用。那么,為什么大家要以勞動方式來換取這種勞動成果呢?其實,今天很多的勞動正在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植入我們普通人的生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表達和個人生活品質的提升。換句話說,未來真正的快樂,并不是簡單的“閑暇”享受,而是“一個能夠擁有勞動意義感的勞動者可以更愉快地生活在這個世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