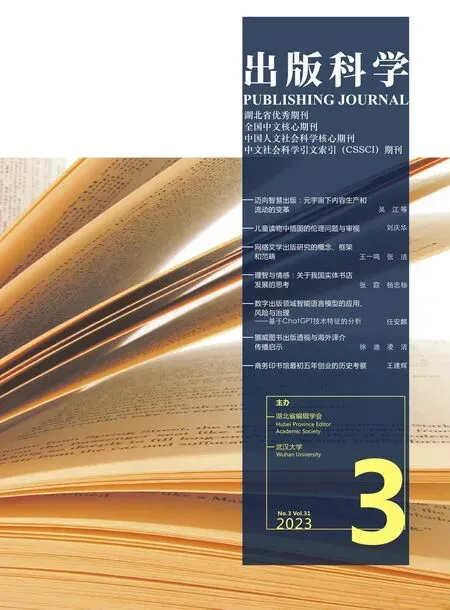出版的價(jià)值訴求“一元性”與“多元性”
徐華亮
(湖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長(zhǎng)沙,410003)
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在布局“推進(jìn)文化自信自強(qiáng),鑄就社會(huì)主義文化新輝煌”戰(zhàn)略任務(wù)時(shí)指出,“要堅(jiān)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指導(dǎo)地位的根本制度,堅(jiān)持為人民服務(wù)、為社會(huì)主義服務(wù),堅(jiān)持百花齊放、百家爭(zhēng)鳴,堅(jiān)持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1],這體現(xiàn)了國(guó)家宣傳思想工作價(jià)值訴求的兩個(gè)方面: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上要求牢牢堅(jiān)持馬克思主義的“一元性”,文化建設(shè)要承認(rèn)和尊重“多元性”。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作為聯(lián)通意識(shí)形態(tài)集群“同心圓”的媒介和紐帶,已成為當(dāng)下中國(guó)新聞出版場(chǎng)域的主流話語(yǔ),這一話語(yǔ)經(jīng)由多年實(shí)踐和理論積淀的“一元性”,形成了一套內(nèi)涵豐富的概念與觀念集群[2]。另一方面,中華文化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中國(guó)正著力推動(dòng)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構(gòu)建,通過(guò)開(kāi)展領(lǐng)域廣泛、形式多樣的文化交流形成文化紐帶,增強(qiáng)了中國(guó)在國(guó)際舞臺(tái)的話語(yǔ)權(quán)。出版工作是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所當(dāng)然,其價(jià)值訴求也包括含“一元性”的意識(shí)形態(tài)訴求和“多元性”的文化精神訴求。
目前,國(guó)內(nèi)學(xué)界對(duì)出版價(jià)值訴求的研究大多側(cè)重于靜態(tài)化的訴求主體、對(duì)象、方式、邏輯。然而,出版價(jià)值訴求意味著對(duì)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一個(gè)“塑造”過(guò)程,從本質(zhì)上可以看作是出版對(d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再生產(chǎn)”過(guò)程[3]。由此可知,出版的價(jià)值訴求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只有把出版活動(dòng)放置在不同時(shí)空語(yǔ)境下進(jìn)行動(dòng)態(tài)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價(jià)值訴求的本質(zhì)。在此背景下,本文試從價(jià)值關(guān)系、功能、邏輯三個(gè)維度動(dòng)態(tài)考察出版價(jià)值訴求的“一元性”與“多元性”本質(zhì)屬性。
1 價(jià)值關(guān)系面向:對(duì)立統(tǒng)一
意識(shí)形態(tài)并非空中樓閣、虛無(wú)縹緲,而是根植于多元化的社會(huì)情境之中。政治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思想文化領(lǐng)域、日常生活領(lǐng)域以及國(guó)際交往領(lǐng)域都成為意識(shí)形態(tài)爭(zhēng)奪戰(zhàn)中最為敏感和尖銳的場(chǎng)域。例如,面對(duì)中國(guó)的崛起,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精心包裝“修昔底德”話語(yǔ)陷阱,到處渲染“中國(guó)威脅論”,極易挑撥有關(guān)國(guó)家同中國(guó)關(guān)系。作為意識(shí)形態(tài)傳播的重要載體,出版業(yè)如何在多元文化語(yǔ)境中堅(jiān)持馬克思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指導(dǎo)地位成為新時(shí)代重要的研究課題。
馬克思指出,“人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jué)的活動(dòng)”[4]。在出版實(shí)踐過(guò)程中,有人認(rèn)為精神文化的訴求要成為人們生活世界的一種操縱力量,要超越一切之上,包括意識(shí)形態(tài),這明顯是對(duì)出版價(jià)值關(guān)系面向的認(rèn)識(shí)出現(xiàn)了偏差。政治訴求的形成及發(fā)展雖然離不開(kāi)所處文化的精神滋養(yǎng)[5],但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作為出版的文化價(jià)值訴求根植于國(guó)家、社會(huì)和國(guó)民等層面,具有公共性、真實(shí)性和異質(zhì)性,其產(chǎn)生和發(fā)展是“多元”的;而作為出版的政治價(jià)值訴求根植于意識(shí)、思想、信念等層面,具有權(quán)威性、傾向性和話語(yǔ)性,導(dǎo)向是“一元”的,兩者具有“對(duì)立性”。但是,多元文化是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產(chǎn)生的基礎(chǔ)和內(nèi)容的豐富,而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則為多元文化提供指導(dǎo)方向,兩者又具有“統(tǒng)一性”。
1.1 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的公共性與政治價(jià)值訴求的權(quán)威性
出版文化價(jià)值作為價(jià)值觀念、活動(dòng)目標(biāo)、行為規(guī)范及其載體的總和,伴隨著識(shí)記、整理、轉(zhuǎn)化和再創(chuàng)造的出版活動(dòng),存在于共同的普遍交往形式之中,它具有特定的擴(kuò)散功能和社會(huì)化趨勢(shì),通過(guò)不同要素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作用、相互促進(jìn),成為人類共有的東西,所以價(jià)值訴求具有公共性。政治價(jià)值訴求是為了將自身所包含的思想觀念、價(jià)值體系傳播給社會(huì)群體,促使社會(huì)群體對(duì)其專屬成果的綜合收益不被破壞,維系現(xiàn)存政治體系。同樣,出版文化自由價(jià)值訴求不能是超越階級(jí)和利益之上的抽象自由,作為一個(gè)社會(huì)的精神生產(chǎn)方式,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的表現(xiàn)[6]。顯而易見(jiàn),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的公共性與政治價(jià)值訴求的權(quán)威性矛盾就產(chǎn)生了,這實(shí)際上是出版文化上“道德契約”和意識(shí)形態(tài)上“政治契約”的矛盾。目前,微信、微博、博客、網(wǎng)絡(luò)論壇、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等自媒體中“去中心化”與“碎片化”的出版行為,降低了主流出版的權(quán)威性與認(rèn)同度,這正是由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和政治價(jià)值訴求的矛盾屬性決定的。因此,需要認(rèn)識(shí)到兩者矛盾的客觀存在并著力解決。
但是,在統(tǒng)一性上,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的公共性是政治系統(tǒng)運(yùn)行的一個(gè)重要手段,它服從于、服務(wù)于政治價(jià)值訴求的權(quán)威意志、路線、方針、政策。出版的公共性體現(xiàn)在為全社會(huì)公眾服務(wù)上,其對(duì)權(quán)威性價(jià)值訴求實(shí)現(xiàn)起到“催化劑”的作用。我國(guó)出版工作“擔(dān)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wù)”就是將兩者很好融合的最好例證。
1.2 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的真實(shí)性與政治價(jià)值訴求的傾向性
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是基于發(fā)展傳承人類文化理想、文化精神、社會(huì)責(zé)任而產(chǎn)生的,是一種精神活動(dòng),不斷地向社會(huì)提供有價(jià)值的信息,承擔(dān)著價(jià)值導(dǎo)向、精神傳遞、文化塑造的社會(huì)責(zé)任,以此構(gòu)建反思性的“內(nèi)向世界”[7],催生有價(jià)值的思想和真理,成為現(xiàn)實(shí)中可以遵循的標(biāo)準(zhǔn),并確保“標(biāo)準(zhǔn)”不僅成為紙面上的東西,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即是“真實(shí)性”。在這種條件下,出版承擔(dān)著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實(shí)踐者和推動(dòng)者的角色。由于政治在國(guó)家中占有絕對(duì)的優(yōu)勢(shì),出版?zhèn)鞑檎蝺r(jià)值訴求服務(wù),擴(kuò)展了政治的空間,而作為政治的對(duì)立面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的真實(shí)性空間自然縮小,這樣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便站在了政治訴求的對(duì)立面。
然而,出版的實(shí)踐活動(dòng)具有客觀真實(shí)性,而且是自覺(jué)的、有目的的能動(dòng)性活動(dòng)。出版發(fā)行客觀事實(shí)并不是出版活動(dòng)本身,而是通過(guò)人的加工改造過(guò)的反映出來(lái)的客觀事實(shí),出版發(fā)行真實(shí)性與政治傾向性的統(tǒng)一是通過(guò)人的主觀意識(shí)與客觀事實(shí)的相統(tǒng)一編輯(實(shí)踐)而實(shí)現(xiàn)的。在出版過(guò)程中編輯根據(jù)自己意圖、目的、計(jì)劃對(duì)出版內(nèi)容選擇、分析、取舍材料、提煉主題思想等,但編輯這種主觀意識(shí)是建立在客觀真實(shí)事物基礎(chǔ)上的,由此可知,出版客觀真實(shí)性與政治傾向性是辯證統(tǒng)一的。
1.3 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的異質(zhì)性與政治價(jià)值訴求的話語(yǔ)性
文化是分享關(guān)于彼此之間以及生活之意義的場(chǎng)所[8],即差序格局社會(huì)生活的場(chǎng)所。出版的文化訴求在差序格局中突顯出來(lái)的價(jià)值就是異質(zhì)性意義的分享。出版文化價(jià)值訴求的異質(zhì)性,應(yīng)該放置到兩個(gè)系統(tǒng)中。一是從連續(xù)性和繼承性上考察對(duì)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和升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拋棄傳統(tǒng)、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9]。出版文化保護(hù)的是民族“魂”、民族的“根”。尤其我們中華民族正在朝著偉大復(fù)興宏偉目標(biāo)前行,更要讓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共鑄海內(nèi)外中華兒女的魂。二是從創(chuàng)新性和融合性考察對(duì)外來(lái)文化的發(fā)展和包容。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堅(jiān)決守護(hù)好我們的文化根脈基礎(chǔ)上,需要與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這樣才能為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提供養(yǎng)料和活力。當(dāng)前,我國(guó)的“一帶一路”建設(shè)更要植根于“美美與共”的異質(zhì)性文化對(duì)話與交流之中,這樣才能不斷推動(dòng)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政治話語(yǔ)是國(guó)家軟實(sh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guó)家意識(shí)、意志、價(jià)值等在對(duì)外交往中的表達(dá),擔(dān)負(fù)著陳述自身政治訴求和目標(biāo)的歷史使命[10]。政治話語(yǔ)權(quán)作為上層建筑,必然要為統(tǒng)治階級(jí)服務(wù),是一元的[11]。隨著全球化進(jìn)程和新媒體傳播場(chǎng)域的嬗變,馬克思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yǔ)在面對(duì)國(guó)內(nèi)外各種思潮沖擊時(shí)出現(xiàn)的失語(yǔ)、失聲情況,嚴(yán)重?fù)p害馬克思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yǔ)的主導(dǎo)性地位[12]。出版文化的異質(zhì)性訴求與政治話語(yǔ)的主導(dǎo)性訴求沖突在所難免。
然而,在政治話語(yǔ)一元主導(dǎo)和異質(zhì)文化多元發(fā)展這對(duì)矛盾中,出版工作最主要的任務(wù)是正確理解和化解這一沖突。出版在“異質(zhì)性”上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guó)具體實(shí)際相結(jié)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不斷推動(dòng)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與時(shí)代化,推進(jìn)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13];在“話語(yǔ)性”上要“加快構(gòu)建中國(guó)話語(yǔ)和中國(guó)敘事體系,用中國(guó)理論闡釋中國(guó)實(shí)踐,用中國(guó)實(shí)踐升華中國(guó)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xiàn)中國(guó)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4]
2 價(jià)值功能面向:社會(huì)性價(jià)值、媒介性價(jià)值、公共性價(jià)值
出版的價(jià)值功能也可稱之為內(nèi)在價(jià)值,是指出版所內(nèi)含的、客觀上具有的功能和作用[17]。新時(shí)代中國(guó)出版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內(nèi)在價(jià)值立足于新時(shí)代社會(huì)發(fā)展新理念以及新時(shí)代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的時(shí)代性表達(dá)[16]。一方面,“新時(shí)代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的時(shí)代性表達(dá)”意蘊(yùn)出版活動(dòng)與意識(shí)形態(tài)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出版活動(dòng)應(yīng)該審視意識(shí)形態(tài),因?yàn)樯鐣?huì)中的總體意識(shí)形態(tài)有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非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和反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之分[17]。由于多元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存在,多種意識(shí)形態(tài)的影響和滲透于社會(huì)群體之中已不可避免,但是,統(tǒng)治層面的政治導(dǎo)向要求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一元化,于是就產(chǎn)生了社會(huì)統(tǒng)治階級(jí)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一元導(dǎo)向與非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反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多元導(dǎo)向之間的“張力”。在此背景之下,出版活動(dòng)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去把握好這種“張力”。
另一方面,“新時(shí)代社會(huì)發(fā)展新理念的時(shí)代性表達(dá)”意蘊(yùn)出版需要提供既能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強(qiáng)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產(chǎn)品[18]。出版新理念兼具“事業(yè)”和“產(chǎn)業(yè)”的屬性。在新媒時(shí)代,出版“產(chǎn)業(yè)”利益追求和“事業(yè)”文化使命之間的博弈日益激烈:一方面,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為導(dǎo)向的出版活動(dòng)中,一些出版企業(yè)一味追求經(jīng)濟(jì)收益而罔顧出版的最高價(jià)值,摻雜大量暴力、色情、低俗內(nèi)容,導(dǎo)致低俗、過(guò)度娛樂(lè)等現(xiàn)象產(chǎn)生;另一方面,出版在弘揚(yáng)中華傳統(tǒng)文化、凸顯主流價(jià)值等方面成效顯著。簡(jiǎn)而言之,出版活動(dòng)總是會(huì)遇到文化使命和經(jīng)濟(jì)利益沖突的困境[19]。
綜上,在“新時(shí)代社會(huì)發(fā)展新理念以及新時(shí)代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的時(shí)代性表達(dá)”中存在困境是由于對(duì)出版的價(jià)值功能認(rèn)識(shí)不清導(dǎo)致,需要進(jìn)一步從出版的社會(huì)性價(jià)值功能、媒介性價(jià)值功能、公共性價(jià)值功能視角洞察導(dǎo)向的“一元性”與取向的“多元性”的關(guān)系。
2.1 社會(huì)性價(jià)值功能
對(duì)于出版活動(dòng)來(lái)說(shuō),社會(huì)性價(jià)值維度有效地界定了“一元性”與“多元性”的邊界,主要體現(xiàn)為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與文化價(jià)值的邊界、出版自由與意識(shí)形態(tài)的邊界、個(gè)體效益與社會(huì)效益的邊界。首先,出版的本質(zhì)是文化[20],經(jīng)濟(jì)只是作為出版手段。出版文化價(jià)值具有正外部性,決定著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范疇。其次,法律秩序社會(huì),出版自由與承擔(dān)義務(wù)辯證統(tǒng)一[21],因此,出版的自由是法律框架下的自由,服從一元意識(shí)形態(tài)。再次,“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是我國(guó)出版活動(dòng)的基本前提。出版社會(huì)效益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jià)值導(dǎo)向。所以,企業(yè)在追求個(gè)體利益的同時(shí),也應(yīng)時(shí)刻警醒不要跨過(guò)社會(huì)效益的邊界,一味追逐經(jīng)濟(jì)效率而罔顧公平、正義、責(zé)任。
社會(huì)性出版和社會(huì)性生產(chǎn)雖有聯(lián)系,但又有區(qū)別,需要辯證看待。社會(huì)性生產(chǎn),按使用性質(zhì)分,分為私有性生產(chǎn)與公共性生產(chǎn)兩種模式,只有公共性的出版物生產(chǎn),才可稱之為社會(huì)出版活動(dòng)。私有性生產(chǎn)是根據(jù)微觀個(gè)體意愿與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出版物生產(chǎn),例如單位的內(nèi)部資料、個(gè)人手寫(xiě)詩(shī)集、未發(fā)表的科研成果集等都不是面向社會(huì)需求進(jìn)行生產(chǎn)行為。公共性生產(chǎn)是以商品銷售方式將其推向社會(huì),進(jìn)入眾多需求者手中,以產(chǎn)生較大的、較直接的社會(huì)影響,并在這一過(guò)程中,實(shí)現(xiàn)出版物生產(chǎn)機(jī)構(gòu)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目的,包括政治的、經(jīng)濟(jì)的和文化的目的[22]。在概念層面中,出版物的私有性生產(chǎn)與社會(huì)性出版的界限是非常明顯的,但在實(shí)踐層面中,界限比較模糊,難以區(qū)分,因?yàn)樗接行陨a(chǎn)既是把自身的知識(shí)、觀念、理論外在化的過(guò)程,也具社會(huì)性出版特征。但總體上還能找出一條界限來(lái)區(qū)分私有性生產(chǎn)與社會(huì)性生產(chǎn),即是否適應(yīng)社會(huì)需要,并且以商品交換為目的。所以說(shuō)沒(méi)有永遠(yuǎn)完全自用的私有性生產(chǎn),一旦有了適當(dāng)條件,就從中演化出公共性出版活動(dòng)。即使極具個(gè)人私密性、機(jī)密性的私有生產(chǎn),為適應(yīng)社會(huì)需求將其公開(kāi)出版發(fā)表便成為了社會(huì)性出版。
2.2 媒介性價(jià)值功能
隨著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和技術(shù)條件日新月異的變化,媒介形態(tài)趨向融合,媒介、媒介形態(tài)及其自身的嬗變對(duì)人類表達(dá)傳播和文化出版方式的影響十分巨大[23]。社會(huì)出版形態(tài)既具有由書(shū)寫(xiě)媒介時(shí)代向機(jī)器印刷媒介時(shí)代轉(zhuǎn)化的特征,又具有機(jī)器印刷媒介時(shí)代向電子媒介時(shí)代過(guò)渡的特征,在社會(huì)科技日益進(jìn)步的條件下,傳統(tǒng)的出版形態(tài)正在發(fā)生自覺(jué)的變革,呈現(xiàn)出不斷解構(gòu)與重構(gòu)的“兩重性”特征。解構(gòu)方面,信息技術(shù)對(duì)出版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進(jìn)行了重構(gòu)。一方面,信息導(dǎo)致原有出版體系內(nèi)部熵流增加,出版生態(tài)系統(tǒng)為快速適應(yīng)新的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流程和銷售模式,開(kāi)始進(jìn)入新的演化階段,出版的核心價(jià)值觀和文化權(quán)威地位逐漸地被多元商業(yè)文化挑戰(zhàn);另一方面,信息技術(shù)本身所固有的離散化價(jià)值觀念日漸強(qiáng)化,無(wú)序化的網(wǎng)絡(luò)語(yǔ)言符號(hào)無(wú)限增長(zhǎng)和擴(kuò)張,造成表達(dá)文本邏輯的弱化,解構(gòu)了傳統(tǒng)表達(dá)所追尋的美好人類精神歸宿和雋永價(jià)值,顛覆了傳統(tǒng)價(jià)值觀。因此,在技術(shù)變革之中的出版文化也同時(shí)在各樣文化沖突和融合中,呈現(xiàn)出形態(tài)的嬗變或者說(shuō)混沌特征,傳統(tǒng)出版的全面、立體的等級(jí)秩序日漸消弭,作者、出版者、傳播者、接受者等之間的主客體界限日益模糊。
信息技術(shù)重塑了出版的形態(tài)和方式。作為信息重要載體的電子媒介從多個(gè)層面對(duì)出版活動(dòng)進(jìn)行了重構(gòu),使其呈現(xiàn)出有秩序、有規(guī)律運(yùn)行的“負(fù)熵”狀態(tài)。“冷媒介”傳達(dá)的信息量少而模糊[24],只是對(duì)出版文字符號(hào)的抽象表達(dá),缺乏形象生動(dòng)闡述;作為“熱媒介”的電子媒介正是在不同的語(yǔ)境下,對(duì)符號(hào)進(jìn)行多重含義的解讀,使得人們得以高度自由化和自主性地表達(dá),立體式、多維度地平衡了出版系統(tǒng)內(nèi)部各要素之間沖突。一方面,各要素都會(huì)找準(zhǔn)自己的定位,順應(yīng)出版活動(dòng)的信息化趨勢(shì),提高配置和整合效率,釋放出版活動(dòng)本身的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政治和社會(huì)潛力。另一方面,要素都有自己的本質(zhì)特征,反映不同利益群體的多元思想,在自主有序流動(dòng)中,孕育著新的思想意識(shí)和觀念。
2.3 公共性價(jià)值功能
公共性是出版的本質(zhì)屬性。一方面表現(xiàn)為政治形態(tài)的公共性。作為政治的“公共性”表現(xiàn)形式就是“公共輿論”。公共輿論場(chǎng)域是介于多元性私人場(chǎng)域與一元性政治場(chǎng)域之間的場(chǎng)域空間,以及通過(guò)這個(gè)場(chǎng)域呈現(xiàn)出來(lái)的共同傾向性的看法或意見(jiàn)[25]。首先,公共輿論場(chǎng)域不是單個(gè)的利益?zhèn)€體。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出版雖然追求利益,但并不是本質(zhì)和核心。如果出版一味追求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背離履行文化使命為最高價(jià)值要求,其后果是商業(yè)供給旺盛和文化需求資源匱乏并存。為平衡市場(chǎng)需求,最終結(jié)果還是利益追求和文化使命之間博弈以最終達(dá)到相對(duì)均衡。其次,公共輿論必須對(duì)社會(huì)和公眾承擔(dān)相應(yīng)的責(zé)任和義務(wù)。盡管出版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且擁有自己的經(jīng)營(yíng)目標(biāo),但作為公共傳播資源的受托使用者,與單純的商業(yè)營(yíng)利活動(dòng)不同,出版活動(dòng)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制約。公共傳播媒介既具有對(duì)公共領(lǐng)域的批判功能,同時(shí)也具有形塑社會(huì)的功能[26]。再次,經(jīng)濟(jì)個(gè)人主義、價(jià)值通約主義和物質(zhì)主義的泛在使出版市場(chǎng)魚(yú)龍混雜,出版?zhèn)惱硎艿酵{[27]。由于出版涉及政治責(zé)任、法律責(zé)任、經(jīng)濟(jì)責(zé)任、道德責(zé)任,為維護(hù)出版活動(dòng)的正常運(yùn)行,必然需要道德資源。如果否認(rèn)出版?zhèn)惱淼墓残裕捅厝粫?huì)切斷出版與社會(huì)公共價(jià)值認(rèn)同的聯(lián)系,在出版活動(dòng)中就會(huì)出現(xiàn)道德失范現(xiàn)象。最后,公共輿論使個(gè)人思想找到了存在的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是各主體間思想文化進(jìn)行平等交流、交匯、交鋒領(lǐng)域。尤其在虛擬公共場(chǎng)域中,個(gè)體特殊的 “認(rèn)知圖式”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存在,還獲得了充分自由成長(zhǎng)的“土壤”。個(gè)人交流、傳播的過(guò)程和權(quán)利進(jìn)一步被放大,由于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具有的便捷、海量空間、低技術(shù)成本等特征,人們?cè)诠差I(lǐng)域可自由地交流個(gè)人的思想。
另一方面表現(xiàn)為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的公共性。普遍聯(lián)系和公共價(jià)值是經(jīng)濟(jì)形態(tài)公共性的兩個(gè)方面[28]。從供需兩側(cè)看,出版供給決定消費(fèi),消費(fèi)誘導(dǎo)出版供給,經(jīng)濟(jì)效益成為最大化的實(shí)踐框架。市場(chǎng)邏輯下的政治性組織、非營(yíng)利性組織同樣存在逐利性[29],其普遍聯(lián)系的集體行動(dòng)邏輯是各主體收益最大化。這種以普遍聯(lián)系形式出現(xiàn)的集體行動(dòng),使出版活動(dòng)進(jìn)入到公共邏輯的運(yùn)行架構(gòu)。出版是商業(yè),但卻是以特殊的形式,即公共價(jià)值出現(xiàn)。在合理追求利益的同時(shí),出版主體不應(yīng)該跨過(guò)公共價(jià)值的邊界,要肩負(fù)起強(qiáng)化思想引領(lǐng)、堅(jiān)定文化自信與塑造國(guó)家形象的重要使命[30]。
3 價(jià)值邏輯面向:統(tǒng)一——遞進(jìn)——融合
出版價(jià)值訴求離不開(kāi)社會(huì)體制背景,它關(guān)系到權(quán)力地位在社會(huì)階層中的權(quán)威性分配;出版價(jià)值訴求也離不開(kāi)社會(huì)實(shí)踐,它關(guān)系到社會(huì)個(gè)體的根本人格特征;出版價(jià)值訴求更離不開(kāi)對(duì)執(zhí)行過(guò)程及其實(shí)施結(jié)果進(jìn)行的動(dòng)態(tài)監(jiān)督和反饋,它直接關(guān)系到社會(huì)公平和公眾福祉。
3.1 “階級(jí)性——人民性”統(tǒng)一價(jià)值
在馬克思哲學(xué)思想中,出版自由主題是其展開(kāi)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批判和構(gòu)建理想維度的重要理論基石[31]。意識(shí)形態(tài)具有階級(jí)屬性,同樣出版自由也具有階級(jí)性,并服務(wù)于政治統(tǒng)治的階級(jí)屬性。毛澤東指出,“階級(jí)消滅之前,不管通訊社或報(bào)紙的新聞,都有階級(jí)性”[32],階級(jí)性是分析政治意義上的出版自由的基石。出版自由的階級(jí)性與人民性如何實(shí)現(xiàn)內(nèi)在統(tǒng)一呢?出版自由首先使人呈現(xiàn)了獨(dú)立和自主的精神內(nèi)核。馬克思認(rèn)為,構(gòu)成人民報(bào)刊的機(jī)體是由各自顯著特征的分子組成,每個(gè)報(bào)刊的關(guān)注側(cè)重點(diǎn)也不同,這樣人民報(bào)刊恰好反映了本階級(jí)的特殊利益要求,每個(gè)需求集合即是人民需要。那時(shí),每家報(bào)紙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發(fā)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現(xiàn)出玫瑰的特質(zhì)一樣。”[33]新時(shí)期,“黨的新聞?shì)浾摴ぷ鞯穆氊?zé)和使命是:高舉旗幟、引領(lǐng)導(dǎo)向,圍繞中心、服務(wù)大局,團(tuán)結(jié)人民、鼓舞士氣、成風(fēng)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謬誤、明辨是非,聯(lián)接中外、溝通世界”[34]。新時(shí)期我國(guó)出版?zhèn)鞑サ幕纠砟罡叨绕鹾狭笋R克思主義的“階級(jí)性——人民性”統(tǒng)一的價(jià)值要求,是后者在新歷史時(shí)期堅(jiān)持、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亦是推進(jìn)我國(guó)新聞出版工作自我完善和發(fā)展的強(qiáng)大理論武器。
3.2 “群體符號(hào)——個(gè)體自覺(jué)”遞進(jìn)價(jià)值
出版是傳播人類文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傳播人類文化的必要媒介。出版的過(guò)程就是對(duì)事物認(rèn)知的過(guò)程,通過(guò)思考、選擇、加工然后把對(duì)事物的認(rèn)知傳播出去,把自己的價(jià)值觀、意愿和要求作用于世界,成為人類的“群體符號(hào)”,變成人類共有文化。出版作為社會(huì)文化活動(dòng),被認(rèn)為是“群體符號(hào)”,但這并非意味著對(duì)其個(gè)體性特征加以否定,相反,文化形成過(guò)程是一個(gè)敞開(kāi)的、微觀個(gè)體參與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而出版對(duì)文化認(rèn)知的最佳路徑就是通過(guò)對(duì)個(gè)體在微觀意義上文化創(chuàng)造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xué)把握。因此,文化既是對(duì)整個(gè)人類實(shí)踐成果的抽象化總結(jié),又是對(duì)具體個(gè)體勞動(dòng)經(jīng)驗(yàn)概括,其背后隱藏著具體抽象化的過(guò)程。文化既是個(gè)體生命活動(dòng)的直接表征,也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直接證據(jù)[35]。出版過(guò)程是有意識(shí)的文化傳播過(guò)程,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個(gè)體對(duì)文化的自覺(jué)。毋庸諱言,出版能自覺(jué)地在對(duì)象上表征自我的本質(zhì),即能夠表達(dá)作為微觀個(gè)體意義存在的價(jià)值,而非作為整體的群體“符號(hào)”。出版活動(dòng)體現(xiàn)出社會(huì)個(gè)體的根本人格特征就是其作為實(shí)踐主體的自覺(jué)能動(dòng)性,這一過(guò)程是群體符號(hào)到個(gè)體自覺(jué)進(jìn)階價(jià)值轉(zhuǎn)換。
3.3 “監(jiān)督權(quán)——自由權(quán)”融合價(jià)值
出版價(jià)值訴求的最終目的是推動(dòng)社會(huì)的進(jìn)步。由于大眾傳播是一種信息傳播方式,而信息是以真實(shí)的形象出現(xiàn)的,這就確定了信息的嚴(yán)肅性和出版的嚴(yán)肅性。出版起到了對(duì)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作用,成為改造社會(huì)的有力工具。正如馬克思指出,“報(bào)刊按其使命來(lái)說(shuō),是熱情維護(hù)自己自由的千呼萬(wàn)應(yīng)的喉舌”[36]。報(bào)刊充當(dāng)人民的耳目喉舌,是人民權(quán)利的捍衛(wèi)者,毫不動(dòng)搖地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chǎng)上,“直面社會(huì)丑惡現(xiàn)象,激濁揚(yáng)清、針砭時(shí)弊,同時(shí)發(fā)表批評(píng)性報(bào)道要事實(shí)準(zhǔn)確、分析客觀”[37]。我們黨歷年來(lái)重視對(duì)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指出,“完善權(quán)力監(jiān)督制約機(jī)制,以黨內(nèi)監(jiān)督為主導(dǎo),促進(jìn)各類監(jiān)督貫通協(xié)調(diào),讓權(quán)力在陽(yáng)光下運(yùn)行”[38]。新聞出版有監(jiān)督權(quán)力的自由,那么它的自由怎么被監(jiān)督呢?出版要反映和傳播信息與文化,形成一種無(wú)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定位就是要站在人民“善”的一邊,走向出版自由。出版不可能獨(dú)自在真空狀態(tài)下存在,必然作為一個(gè)“群落”存在于生態(tài)系統(tǒng)之中,所以就必須以不侵害他人的自由權(quán)利為前提[39]。否則,在人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權(quán)利過(guò)大的情況下,當(dāng)個(gè)人可以隨意侵害他人的自由權(quán)利時(shí),自由就是不穩(wěn)定的,正常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乃至社會(huì)秩序也就無(wú)法維持,這正是行使出版自由權(quán)時(shí)要有所制約的原因。總之,出版的邏輯是既要有“批判的武器”,又要有“武器的批判”,使之成為改造社會(huì)的有力工具。
綜上,統(tǒng)一價(jià)值是根本價(jià)值、是價(jià)值基礎(chǔ),當(dāng)其他價(jià)值與統(tǒng)一價(jià)值相沖突時(shí),其他價(jià)值存在無(wú)意義;遞進(jìn)價(jià)值是核心價(jià)值,對(duì)自我生命本質(zhì)的還原與復(fù)歸,是人之為人所特有的存在特征[40];融合價(jià)值是負(fù)荷價(jià)值,是促使現(xiàn)統(tǒng)一價(jià)值、遞進(jìn)價(jià)值及其他價(jià)值體系之間融合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