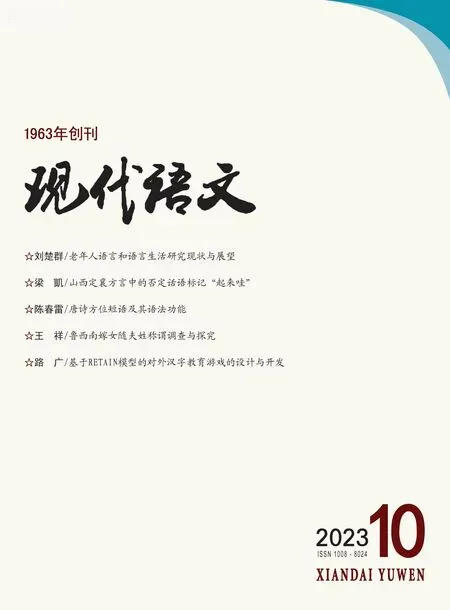魯西南嫁女隨夫姓稱謂調查與探究
王 祥
(濟寧學院 人文與傳播學院,山東 曲阜 273155)
親屬稱謂是對有親屬關系的人的稱呼,其社會基礎是家庭和親屬關系。本文討論的“隨夫姓稱謂”屬于“從他親屬稱謂”之一,是親屬稱謂中比較特殊的一種,簡稱“從他稱”“從他稱謂”。有學者認為,這屬于一種稱謂借用現象,即借用他人稱謂供自己使用,如從兒稱謂等。隨夫姓稱謂,亦稱“從夫姓稱謂”“含夫姓稱謂”。嫁女隨夫姓稱謂是傳統農耕社會的部分地區,專門用于“嫁女”的稱謂現象。對于傳統農耕社會的嫁女來說,她出嫁前的生活環境里,最常用的人際關系有兩種:親屬關系和鄰里關系。其中,前者按照原有的親屬關系稱呼她,就形成親屬稱謂;后者按照鄰里關系稱呼她,則形成擬親屬稱謂。這種稱謂系統,由于傳統農耕生產方式的穩定而長期保持不變。嫁女是相對特殊的一類人,她從原有的、穩定的人際關系圈里走出去,進入另一個新的、穩定的人際關系圈。這時,傳統農耕社會為嫁女重新創造了一種稱謂方式,即以丈夫家姓氏稱呼她,故稱“隨夫姓稱謂”。同時,原有人際關系圈里的非親屬關系者(如鄰居等),也采取和親屬關系相同的稱謂,原有的親屬關系稱謂和擬親屬關系稱謂遂合二為一。
嫁女隨夫姓稱謂方式經過漫長的發展歷程,已經成為固定的語言習慣,它是存在于現代漢語詞匯系統中的一種重要的語言現象,也是一種重要的語言民俗文化現象。隨夫姓稱謂可用于面稱和背稱。其表現形式主要為:“老+夫姓(兒化)”“老+夫姓”“老+夫姓+家”等,其中,“老”為前綴。
一、魯西南嫁女隨夫姓稱謂現象調查
魯西南地區地處黃河下游,地形主要為平原,屬于典型的農耕文明區域。這一地區的農耕民俗文化特色鮮明,保存至今的傳統民俗事象和民俗文化豐富多樣。嫁女的隨夫姓稱謂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一)隨夫姓稱謂是嫁女的重要特征
從稱謂者的角度來說,使用這一稱謂的人是嫁女的娘家兄嫂、父母和其他長輩。這一稱謂不區分親疏,因此,這里的“其他長輩”包括嫁女的親伯父親伯母、親叔父親嬸母、親姑姑,也包括同姓或不同姓的、同村的長輩們。
從被稱謂者的角度來說,它使用的時間起點是出嫁后回門這一民俗環節。此后,無論嫁女的年齡多大,從道理上講,都適用隨夫姓稱謂。可見,這一稱謂是由姑娘到嫁女的區別性特征之一。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女子剛剛出嫁時,這種稱謂方式使用較少,而大多用于嫁女年長之后。
(二)嫁女隨夫姓稱謂存在諸多變式
總的來看,魯西南地區嫁女隨夫姓稱謂存在兩種基本格式。第一種格式是“老+夫姓”,這種格式又可以細分為兩種情況:兒化和不兒化。以嫁女夫家姓王為例,該稱謂的兒化形式即為“老王兒[lɑu44w?r41]”,他姓類推。如:“老王兒來了,沒抱孩子來啊?”該稱謂的不兒化形式即為“老王[lɑu44w?41]”,他姓類推。第二種格式是“老+夫姓+家(輕聲)”。以嫁女夫家姓王為例,該稱謂即為“老王家[lɑu44w?41t?i?]”,他姓類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年齡、輩分等關系,此類稱謂又有其他諸多變式。“老×”可以后接其他親屬稱謂,兒化現象亦隨之消失。如果姊妹倆夫家都姓王,長輩和兄嫂面稱均為“老王兒”,背稱則以“大老王兒”“小老王兒”區分。如:“大老王兒昨天來給她娘送節禮了嗎?”晚輩亦然,如“大王姑”“小王姑”。也可借用夫家所在村莊加以區別,如“張莊的(那個)王姑”。如果是獨生女,則出嫁后用夫姓作姊妹間區分的語境也就不存在了。
與此同時,弟弟或晚輩對于嫁女的稱謂也很復雜。傳統社會的宗法制度使得漢語的親屬稱謂非常復雜。如果是親弟弟或親侄子,女子出嫁前后都稱“姐姐”“姑”或“大姐姐”“二姐姐”“大姑”“二姑”等,不必改口,也不必區分面稱和背稱。反之,則面稱和親弟弟一樣,背稱則多為老王姐姐、老李姐姐、老王姑、老李姑等。對姑奶奶的稱謂規則與此相同。此外,因關系較疏遠或出嫁既久,諸姐、姑、姑奶奶的排行大小有時已不易區分,或者不必區分。
(三)調查區域嫁女隨夫姓稱謂使用情況
本文以魯西南的濟寧地區為調查的核心區域,擴大到魯西南的菏澤地區部分縣市區。同時,亦涉及魯西、魯南、魯北、蘇北和河南東部、南部等區域。
1.該稱謂在這些地區的整體使用情況非常復雜
嫁女隨夫姓稱謂的使用范圍主要集中在魯西南和魯西、魯南的部分縣域。其中,魯西南梁山東部鄉鎮至今使用,相對其他區域,適用人群的年齡偏小,在55歲左右。可見,某些小范圍地區的民俗事象演變比較緩慢。
濟寧朝東北方向至寧陽縣境內,隨夫姓稱謂不再使用,基本上是直呼嫁女之名。從濟寧地區的曲阜市域繼續向東,如臨沂地區西部平邑等縣域和濟寧地區的泗水縣接壤,仍然存在該稱謂。60歲以上的嫁女回娘家,當地就以隨夫姓稱謂稱呼她,但不使用兒化音。如夫家姓季,則稱嫁女為“老季”。從平邑縣繼續向東,至臨沂地區的東部,隨夫姓稱謂現象則不再出現。
菏澤地區位于濟寧地區西南方向,大部分縣域都使用過或仍在使用嫁女隨夫姓稱謂。至最西南方的東明縣即消失。
濟寧地區向南,至江蘇北部豐縣一帶,仍然存在這一稱謂,但沒有兒化現象。
魯西如聊城地區的陽谷縣域內,也存在著這種隨夫姓稱謂,但不使用兒化。
從濟寧向西、向西南方向,進入河南信陽地區和洛陽地區等,均不使用嫁女隨夫姓稱謂,而是直呼其名,或在嫁女年長之后,以“嫁女孩子名+娘”稱呼她。
2.濟寧地區普遍存在嫁女隨夫姓稱謂現象
整個濟寧地區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城市和農村,典型的嫁女隨夫姓稱謂主要是在農村使用,城市則使用頻率較低。以下例證均以夫姓“王”為例,不加特別說明的區域均指農村地區。
任城區,即濟寧市區。有隨夫姓稱謂。情況比較特殊,在夫姓后加輕聲“家”。以嫁女夫家姓王為例,該稱謂即為“老王家[lɑu44w?41t?i?]”,他姓類推。
兗州區,屬于濟寧市的一個區。有隨夫姓稱謂。長輩均稱呼嫁女為“老王兒”,嫁女現已70歲左右。
金鄉縣。有隨夫姓稱謂。目前能這樣叫的老者,最低年齡也超過66歲了。城市里沒有隨夫姓稱謂。即使嫁女年齡已經很大,也是直呼其名或以親屬稱謂、擬親屬稱謂稱之。
嘉祥縣。有隨夫姓稱謂。不到70歲的人,仍稱呼嫁女為老黃姐姐、老李妹妹等。一般情況下,長輩稱呼嫁女為“老王兒”,使用兒化音;平輩則稱呼嫁女為“老王姐姐/妹妹”。晚輩稱呼長輩是“老王姑”“老王姑奶奶”等。
微山縣。位于濟寧地區的最南邊,南接蘇北地區。有隨夫姓稱謂。年齡超過60歲的稱呼嫁女為“老王”,不使用兒化音。
魚臺縣。有隨夫姓稱謂。老年人稱呼自己已出嫁的女兒為“老王兒”,稱女婿為“老王兒家”,感情色彩不濃。
梁山縣。位于濟寧地區最西北角,與魯西聊城地區的陽谷縣、河南省濮陽地區的臺前縣隔黃河相望。有隨夫姓稱謂。該縣東部的館驛鎮,55歲左右的人仍使用這種稱謂方式,并且使用兒化音。晚輩則稱呼“老王兒姑”或“(嫁女名字最后一個字)+姑”等。當地人認為這樣稱呼比較親切,不生硬。背稱且與晚輩對話時,長輩會稱呼嫁女為“你老王姑”等。稱呼姑父時不使用兒化音。面稱時稱之為“恁姑父”,這里的“恁”并不含敬意;背稱且與晚輩對話時,就是“恁老王姑父”。單純背稱大多稱“老王家”。
鄒城市。有隨夫姓稱謂。不使用兒化音。使用這種稱謂的人和嫁女均在55歲以上。
曲阜市。70歲以上的老人仍在使用隨夫姓稱謂,被稱呼的嫁女也在這個年齡階段。當地稱呼嫁女有這樣幾種情況:自家父母、親伯父母、親叔父母等稱呼嫁女,或者按照排行稱“大妮兒”“二妮兒”等,或稱乳名,或稱“嫁女孩子名+娘”。村里鄰居長輩稱“老王”,沒有兒化現象,這種稱謂的感情色彩并不濃厚。平輩之間的哥哥姐姐,或稱其小名,或從兒稱為“某某他三姑”或“他三姑”等。這里的“某某”是指嫁女的娘家侄女或侄子。
泗水縣的情況則比較復雜。南部有隨夫姓稱謂,但不加兒化音。同時,不僅有“老王”這樣的稱謂,還有和任城區一樣的“老王家”。其他鄉鎮,有些沒有隨夫姓稱謂。嫁女回娘家,沒有孩子的稱呼嫁女乳名;有了孩子的稱呼她為“孩子乳名+(他)娘”;如果孩子不止一個,一般以老大的乳名稱呼,如“小偉他娘”“偉他娘”等。
二、隨夫姓稱謂的歷時與共時考察
上文描述的主要是魯西南地區的嫁女隨夫姓稱謂現象,基本上限于嫁女娘家人(含嫁女娘家的母系親友)使用。實際上,這種稱謂只是隨夫姓稱謂之一類。目前,中國其他地區以及世界很多國家,都存在著女性隨夫姓稱謂現象。這種稱謂現象具有顯著的社會屬性,其本質也是“妻隨夫姓”風俗的反映,是傳統女性社會地位從屬性的典型表現。
(一)歷時考察
根據已有研究,已婚婦女從夫姓稱謂方式自古有之,大約興起于漢魏之際。中國傳統社會妻隨夫姓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登記機關簡化了妻子的姓名,以減輕登記工作的難度;二是夫妻之間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中國古代,“妻的人格被夫所吸收”[1](P109)。孫兆華、王子今指出,在里耶秦簡戶籍文書中,存在很多“妻不書姓”“妻從夫姓”的現象。“秦代遷陵縣南陽里戶版所見的妻不書姓現象,即在書寫時可能是默認妻子從戶人(戶主)之姓而加以省寫,這或許反映了當時妻從夫姓的社會情形”[2](P43)。至近代,隨夫姓稱謂仍很普遍。如著名湘劇名伶饒福美(1885—?),長沙人,本姓黃,系名丑黃元和胞姐,福祿坤班第一科出身。嫁人后即從夫姓饒,世傳其名即為“饒福美”。這又是一種完全更換成夫姓的“隨夫姓”方式。
張學軍指出,中國夫妻的稱姓習慣、法律規范可以分為三個階段[3](P5-14)。第一階段為自秦漢至清。在公文書和契約書中,對未婚的女性稱呼姓名或只稱呼名字。對已婚的女性習慣上有三種稱呼:以娘家姓稱為“某氏”,以娘家姓稱為“阿某”,在“某氏”或“阿某”之前冠以夫姓。
第二階段為北洋政府至國民黨政府時期。1925年,《民國民律草案》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條規定:“妻于本姓之上冠稱夫家之姓,并取得與夫同一身份待遇。”至此,妻隨夫姓不再是民俗習慣,而成為法定義務。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民法》第一千條規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贅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4](P536)至此又有進步,妻隨夫姓這一義務,既可以約定,也可以不約定。
第三階段為1950年至今。1950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一條規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權利。”該規定并未明確允許夫妻雙方約定一方冠以對方的姓氏。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指出:“同時,這種規定,當然也毫不妨礙夫妻關于除本姓之外互相冠姓的自愿約定。”[5](P65-66)這一規定在法學上被稱為“夫妻約定冠姓制”。1980年9月,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權利。”同年,《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改草案)〉的說明》中,亦未涉及“夫妻約定冠姓制”的廢除。2001年以后的多次婚姻法修改中,都沒有提及廢除“夫妻約定冠姓制”這一問題[6](P4-21)。因此,“夫妻約定冠姓制”仍然是夫妻稱姓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共時考察
目前,不僅內地法律沒有明文禁止已婚婦女從夫姓稱謂,而且中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也存在著妻姓前冠以夫姓現象。它往往以四字格姓名格式呈現,如“林鄭月娥”“范徐麗泰”“陳馮富珍”等。同時,中國的少數民族也有這種現象。如苗族婦女的姓名和稱謂講究避諱,不允許稱呼婦女的原名。她們的姓名和稱謂都是一成不變的格式:夫姓加“咪(媽)”加長子或長女名。比如,丈夫姓為“榮”,長子名為“兩”,那么,這個婦女的姓名就叫“榮咪兩”。苗族婦女從夫姓從長子/女名的習俗,體現了苗族家庭結構中血緣關系與姻緣關系之間的矛盾,以及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
已婚婦女從夫姓稱謂方式不僅中國存在,世界上其他國家亦有保留。美國、英國等國家存在著相同的現象,比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克林頓即其夫姓;又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是以夫姓名世。目前,發達國家的“夫妻稱姓制”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強制變更。夫妻必須選擇丈夫或妻子的本姓作為雙方的姓氏,如日本、瑞士、土耳其等。二是允許變更。夫妻均可改隨對方姓氏,如英國、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加拿大(魁北克省除外)。三是禁止變更。夫妻必須保持本姓。不過,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盡管立法完全實現或基本實現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但絕大多數夫妻仍采用丈夫的姓氏,如日本大約將近97%的夫妻選擇夫姓[7](P34)。
三、隨夫姓稱謂的學術價值
從以上考察到的情況來看,“妻隨夫姓”在全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從本質上講,除了風俗的巨大慣性作用以外,更深層次的原因仍在于女性的社會地位不高,男女性別平等并未真正實現。正因如此,這類稱謂具有重要的語言學價值、民俗學價值和社會學價值。當下魯西南地區的嫁女隨夫姓稱謂方式,雖然正隨著傳統農業社會的衰退而逐步消失,但是仍然具有這三方面的價值,值得深入探究。
(一)語言學價值
根據我們的調查,嫁女隨夫姓稱謂可謂是語言和民俗相結合的重要現象與例證。
首先,對嫁女隨夫姓稱謂的基本格式及其變體進行分析。它的基本格式是“老+夫姓(+兒化)”,這與“夫姓+父姓+氏”有所不同。前者突出的是夫姓,“老”屬于前綴,無實際意義;后者則夫姓、父姓順序有先后之別,如“王張氏”。前者存在變體,即“老+夫姓”“老+夫姓+家”,因地而異,用法相同。
其次,對嫁女隨夫姓所含“擬親屬稱謂”特征進行分析。就其本質而言,擬親屬稱謂是親屬稱謂的泛化現象,它是指非親屬關系的交際雙方,比照親屬之間的年齡、輩分特點,借用親屬稱謂語稱呼對方,是對親屬關系的一種模擬。擬親屬稱謂在漢語世界中普遍使用,其深層結構反映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家族意識的擴大和延伸,是傳統禮俗對人們的交際行為加以規范的結果。
嫁女隨夫姓稱謂主要適用于嫁女的娘家哥嫂和長輩。這里的哥嫂和長輩主要是指同宗同族,也可以指外村同宗同族者,還可以指同村異姓者。嫁女娘家的非親屬、非同族的鄰居、朋友等,也都以親屬稱謂稱呼嫁女。如本村異姓也可以采用嫁女隨夫姓稱謂,像“老王兒”“老劉”“老李家”等。當然,也可以稱呼嫁女為姐姐、妹妹、姑姑、姑奶奶等。還可以采用從兒稱謂“他姑”“他姑奶奶”,或者“恁姑”“恁姑奶奶”等。這些都可以歸為擬親屬稱謂。
(二)民俗學和社會學價值
可以說,嫁女隨夫姓稱謂是一種具有鮮明特色的農耕文化民俗現象。盡管農耕文化正在更新換代,傳統的農耕民俗文化逐漸消失,但是這種稱謂現象仍在一定范圍內頑強存在著,依然具有重要的民俗學和社會學價值。魯西南地區把男青年找對象稱為“尋([?in41])①《廣韻》中,“尋”的古音是徐林切,本為開口呼;按照語音發展規律,今應讀為[?in41]而不是[?yn41]。可見,山東方言保留了這個音的古讀。媳婦”,而女子找對象則稱為“尋主兒”,女子找到了婆家稱為“有主兒”了。“主”的發音在當地接近于[t?u?r44]。可見,這種稱謂中隱含著傳統女性“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的身份附屬性。隨夫姓稱謂也反映出女性的社會地位不高,在家庭生活和夫妻關系中具有附屬性的特征。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實際上,從娘家人的角度來看,嫁女隨夫姓稱謂亦反映出原生家族對于嫁女身份的認可和尊重。
1.娘家人對嫁女身份的認可
所謂“嫁女的身份”,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她組建了新的家庭,成為這個家庭的新成員,將來還可能會擁有主婦的身份;二是她已經脫離了原生家庭,開始具有“客人”的身份。但是這個“客”和其他的客人不一樣,嫁女與原生家庭有著血緣關系,原生家庭里有她必須養老送終的父母。娘家人在面對嫁女夫妻倆時,把“客[khe24]”這個稱呼給了女婿。對于嫁女不能直接稱之為“客[khe24]”,而是在娘家和婆家之間尋求到一種平衡性稱謂,并使這個稱謂聯結雙方的家庭,實現了最重要的家庭親情和最重要的法律關系(夫妻)之間的相互聯結,如站在娘家人的角度稱呼嫁女為“老王兒”等。這個稱謂本來專屬于娘家人,本族人和本村鄰居們使用時,則屬于擬親屬稱謂。
2.娘家人對嫁女身份的尊重
民間常說“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它主要是指嫁女沒有財產繼承權。不過,血肉親情畢竟是割不斷的,在嫁女身份轉換、組建新的家庭后,娘家人確實需要給她一個“獨特的稱謂”。在這個意義上說,嫁女隨夫姓稱謂既體現了“別內外”,也顯示了對嫁女的尊重。魯西南地區,嫁女隨夫姓稱謂在實際使用時,語氣、語調上都帶有嚴肅的、尊重的意味。盡管這一稱謂仍然帶有夫姓,但是嫁女畢竟成家立業了,已成為獨立的個體。就此而言,嫁女隨夫姓稱謂是對她獨立、成家的認可和尊重。
從娘家人的特有稱謂這個角度來看,如果稱謂方(年長平輩或長輩)和嫁女既同屬一個家族,又有其他親屬關系,比如,嫁女嫁給了稱謂方的姑姑家、舅舅家、朋友家等,稱謂方也需要主動站在嫁女原有家族的角度來稱呼嫁女,即選擇嫁女隨夫姓稱謂,而不是稱之為弟媳婦、表嫂等,除非雙方重新商定、重新選擇。這就說明嫁女隨夫姓稱謂的使用是嚴肅認真的。從這個意義上看,說它含有對嫁女身份的尊重色彩,是毫不為過的。同時,這種稱謂的改變,也是在提醒嫁女的哥哥嫂子或者弟弟弟妹,嫁女已是客人身份,她再回娘家時,要加以特殊尊重,不能再像以前那樣隨便了。當下社會,嫁女回娘家的次數明顯增多,稱謂詞語“別內外”的功用就不那么顯著了。不過,在一些重大事項上仍然會有明顯的體現。如娘家侄子結婚,作為姑姑,嫁女拿出的禮金要遠遠高于其他親友。
可以說,嫁女隨夫姓稱謂是從“既嫁從夫”的舊道德而來,隨著社會的進步,農村新型人際關系、婚嫁觀念等逐步形成,此類稱謂有關舊道德的作用和意味已經淡化,而對于嫁女角色轉換的標記和區分作用,正是其積極的民俗和社會價值所在。
四、嫁女隨夫姓稱謂正走向消失
隨著時代的發展,女性地位不斷提升,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技能也有大幅提高,嫁女隨夫姓稱謂正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現代社會的女性更希望長輩像未嫁時那樣稱呼她們的名字。當代女性普遍認為,名字是屬于我自己的,不愿意將別的姓氏的稱謂加在自己身上。同時,很多已婚女子表示,自己在聽到嫁女隨夫姓稱謂“老王兒”時,會更關注前綴“老”,這自然會給人帶來不舒服的感覺,因為誰也不想“老”。時代的進步,社會的變遷,催生著人們觀念的更新,一些傳統的婚姻觀念、婚嫁禮俗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如傳統社會中的嫁女,無論多大年紀,從結婚那天開始,就要“凈面”“絞臉”,把頭發挽成髻狀,穿衣也要向中老年女性靠近。如今,這些行為方式都已煙消云散。
同時,傳統的養老方式正在發生改變,新型的養老觀念、養老模式已在農村廣泛形成,這也影響到嫁女隨夫姓稱謂的延續。傳統社會中的女性是“潑出去的水”,因此,既不能繼承原生家庭的財產,也不參與親生父母的養老分攤。這雖然在傳統農耕社會行之有效,卻不符合當今社會的實際情形。現在的法律明確規定,女子也要對自己的親生父母盡贍養義務,和自己的兄弟一樣給父母養老送終。今天的魯西南地區,嫁女在養老問題上已經基本做到了這一點。如果一個老人身體健康,嫁女會經常到家看望。如果老人不能生活自理,需要輪流照顧,嫁女往往比自家兄弟做得更好。如果老人去世,嫁女還要拿出一大筆錢用于喪事,也算是對娘家兄弟的支持和幫助,甚至不管嫁女自家的生活如何。既然養老觀念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嫁女來往娘家的次數大大增加,那么,對于嫁女的稱謂也就不再強調其“別內外”的作用了。
可以說,魯西南地區嫁女隨夫姓稱謂的演變,折射出婚嫁觀念、人際關系、法律制度、養老模式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反映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巨大進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雖然在法律層面并未廢除“夫妻約定冠姓制”,但與之相比,“夫妻雙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權利”更能順應時代潮流的發展與廣大民眾的心聲,已婚女子仍使用婚前姓名已成為社會的常態。新時代以來,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促進男女平等和婦女兒童全面發展,更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在這一背景下,女性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廣大婦女充分發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精神,積極投身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去,努力實現人生價值,不斷創造美好生活。嫁女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轉變,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破除陳規陋習,弘揚文明新風,已成為新時代新女性的新選擇、新作為。當然,對于嫁女隨夫姓稱謂現象,我們應該秉持平等尊重的理念,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以理性平和的態度來關注這一課題。同時,通過這一個案研究,也帶給我們深刻的啟示:在農耕文明日益凋零的今天,人們應立足于新時代新征程,積極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努力走好鄉村文化振興之路。我們要守護好農耕文明,深入挖掘其蘊含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范,主動探尋農耕文明元素與當前社會運行方式融合的新路徑,不斷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真正“活起來”“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