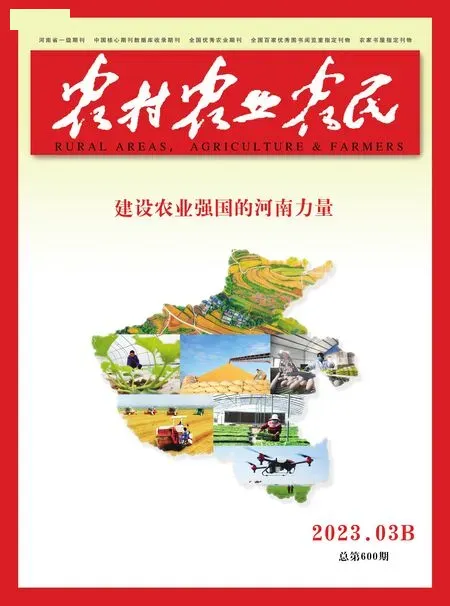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夯實農業強國建設根基
賈小虎
(河南農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農業資本存量,是影響農業發展乃至國民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份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有所論述。特別是從“十二五”至今,中央一號文件關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內容持續擴展、力度不斷加大。與之對應的是,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進展顯著,取得了矚目的發展成就。以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為例,相應投資規模從2006年的518億元增加到2021年的14275億元,增長了26.6倍,投資規模顯著擴大。但就目前來看,單純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加已不能完全應對當前農業農村現代化乃至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要求。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既要適應新的工農城鄉關系,也要適應新的生態發展目標,還要適應多變國際形勢的沖擊等。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實際上是基于當前面臨的一些新挑戰。
第一,在“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全球氣候變化等各種因素相互疊加,使我國耕地保護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在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近年來每年減少的耕地面積均高于增加的耕地面積,導致我國耕地面積呈剛性遞減趨勢。截至2021年年底,全國耕地面積為19.18億畝。從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看,第二次調查以來的10年間,全國耕地減少了1.13億畝,年均減少面積略有擴大,主要原因是農業結構調整和國土綠化。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占用的多是優質耕地,而補充的耕地往往質量較差,導致耕地整體質量下降。同時,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無論是鄉村產業發展,還是生態宜居美麗鄉村建設,都需要土地提供支撐,由此可能導致農村新型建設用地需求的增長進一步擠壓耕地空間。從耕地質量角度看,當前存在明顯的“低”與“污”兩個問題。“低”主要是指耕地的基礎地力低,“污”即耕地土壤的污染問題。《2021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數據顯示,全國耕地質量平均等級為4.76等,較2014年提升了0.35個等級,耕地地力年均提升0.7%。其中,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積為6.32億畝,占耕地總面積的 31.24%,四至十等的中低等耕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68.76%,表明全國耕地以中低等耕地為主,耕地土壤地力有限。此外,在鄉村振興背景下,一些地方將鄉村產業振興作為主要抓手,大面積發展設施農業,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益;或以全域旅游理念為引領,在縣域范圍內大力發展旅游業。然而,這兩種產業選擇方向都容易導致耕地的“非糧化”趨勢。
糧食生產根本在耕地。在對耕地保護的部署方面,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加強耕地保護和用途管控,嚴格耕地占補平衡管理,嚴格控制耕地轉為其他農用地,探索建立耕地種植用途管控機制,加大撂荒耕地利用力度。
第二,受自然因素、技術因素、制度因素的影響,我國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尚存在一些問題。從自然因素來看,高標準農田建設方向及規劃設計內容,受地形坡度、水資源情況及土地結構類型的影響較大。比如,在“梯田”環境中,僅能夠通過“截水”等少數工程措施優化水資源分配,服務于高標準農田建設的方法較為有限。從技術因素來看,高標準農田建設是一個年度任務,各地每年都有新建設任務,除前期項目區選址、可行性摸查、地形測量和后期項目實施招投標、施工、驗收等,留給項目開展規劃設計的時間往往不足,同時面臨地形測量精度不夠等問題,且規劃設計涉及諸多環節,很難做到科學全面。如果后期施工中遇到復雜施工點,無法按計劃完成施工,就只能先行開展技術性設計變更,對施工效率及進度造成影響。從制度因素來看,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通過驗收后,建設單位會與項目所在地村委會及村民小組簽訂三方管護協議,將建成的基礎設施全部移交村民管護。這種管護方式雖然明確了管護主體,但由于沒有安排專項管護資金用于設施維修,村委會及村民小組雖有管護之責,卻無配套資金可用,最終影響整個項目效益的發揮。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區各部門高質量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截至2022年年底,全國累計建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穩定保障1萬億斤以上糧食產能,19.18億畝耕地超過一半是高標準農田。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完成高標準農田新建和改造提升年度任務,重點補上土壤改良、農田灌排設施等短板,統籌推進高效節水灌溉,健全長效管護機制。制訂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的實施方案。
第三,在投資建設與后期管護環節,農田水利建設均存在治理失靈問題。一些地區在農田水利設施供給實踐中存在著諸如“集體水利廢弛、小微水利遍地”“灌溉工程成擺設”“被遺忘的抗旱井”等現象。從目前灌溉水利的基本狀況來講,灌溉水利設備與農業進展情況脫節,灌溉水利設備對農業生產的支撐不足,很難適應現代農業生產需要。比如,部分區域耕地灌溉仍以老式灌溉手段為主,使用老式澆灌裝備會造成水資源的嚴重損耗,不利于農業的順利平穩進步。從投資建設來看,盡管政府逐步增加在小型水利項目方面的投資,但是資金仍然較為短缺。此外,長期投資水利制度亟待完善,資金短缺已成為各地興修水利的主要障礙。由于計劃和單位規模較小,所以一般采用先傳達命令再施行補貼的方案,使得部分項目呈報很高效。水利建設在引進資金方面沒有充分利用社會上各類資金資源以及當地農民的支持,影響了農民參與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意愿。從后期管護來看,農村稅制改革撤銷了“兩工”制度后,村民進行修筑投資需通過“一事一議”來實現,而基層團隊和村民在落實“一事一議”方面經驗匱乏,導致相關工作難以順利推進。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村民渙散的管理形式與小規模灌溉設備全體利用和節約用水之間的沖突加劇,水費很難按成本收取,導致鄉鎮水務部門的管治經費欠缺,不足以支持水利工程運行。除此之外,村民用水協會組織治理規模有限。這些都是造成農田水利設施管護職責不夠清晰的關鍵原因。
糧食生產命脈在水利。在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扎實推進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加快大中型灌區建設和現代化改造,加強田間地頭渠系與灌區骨干工程連接等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推進黃河流域農業深度節水控水,在干旱半干旱地區發展高效節水旱作農業,深入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
第四,我國是世界上受自然災害影響嚴重的國家之一,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防災減災抗災工作。雖然我國減災抗災措施最突出的優勢是能夠充分發揮國家權力的效力,集中調配資源,集中力量減災抗災,應急機制反應較為迅速,但從農業防災減災工作來看,一些農業防災減災投入產出效率不高,存在防災減災資源未得到高效利用的現象。主要有下列表現。一是救災資金到位周期長。由于程序和長鏈條的審批機制,從資金批復到下撥周期較長,易導致農業災害的救援滯后,進而可能延誤農業生產的最佳時機。二是農業生產恢復資金投入不足。目前農業抗災減災資金主要用于災害損失減少和基礎設施維護,用于農業生產恢復的資金投入還有待進一步加大。三是中央和地方權責失衡,縣鄉應急指揮技術系統尚未成熟。對于農業災害救助政策,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權,未發揮主觀能動性,基層工作人員主要職責以監測和上報為主,未充分利用和發揮地方政府基本職能。四是農民抗災救災意識和能力不強。農民缺乏實施自我保障措施的意識、動力和能力,不注重自我抗災救災,對政府抗災救災具有較大依賴性,對于救災資金使用存在不合理現象。五是社會組織力量利用不夠充分。目前抗災救災還是政府主導為主、非政府組織參與為輔的局面,且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不夠獨立,處于被動地位。
在強化農業防災減災能力建設方面,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研究開展新一輪農業氣候資源普查和農業氣候區劃工作,加強旱澇災害防御體系建設和農業生產防災救災保障,提升重點區域森林草原火災綜合防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