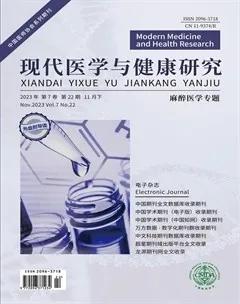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對行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外周血T 淋巴亞群細胞因子的影響
夏 穎 ,沈 磊,楊 軍
(長江航運總醫院麻醉科,湖北 武漢 430000)
膝關節骨折是一種常見的損傷性疾病,臨床表現為疼痛、膝關節活動受限等,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目前全膝關節置換術為膝關節疾病治療的常用術式,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疼痛,促進關節功能恢復,但部分患者年齡較大,身體機體功能差,對于手術耐受力較低,從而導致手術風險增加,因此術中配合有效麻醉方案至關重要。以往主要采取全身麻醉方法,但由于多數高齡患者生理功能逐漸降低,再加之伴有基礎疾病,導致臨床麻醉難度增加;同時全膝關節置換術后疼痛和免疫抑制直接影響膝關節功能康復,由于單獨全身麻醉術后患者疼痛、應激及手術創傷等均會對患者免疫功能造成較大影響[1],因此,臨床急需找到一種減輕對患者免疫功能抑制的麻醉方法。近年來,超聲引導下神經阻滯麻醉被廣泛應用于臨床中,該方法具有顯著鎮痛效果,且不良反應發生率低,深受臨床麻醉醫師和手術醫師的青睞;同時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對于術后疼痛及藥物用量的減少有顯著效果,且對于患者免疫功能的提升有良好效果,可減輕患者手術的應激反應,減少兒茶酚胺的釋放,進而保持外周血T 淋巴亞群細胞因子的平衡狀態[2]。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對行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麻醉效果及T 淋巴亞群細胞因子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以隨機數字表法將2021 年5 月至2022年12 月長江航運總醫院收治的76 例行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分為兩組。對照組(38 例)患者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SA)[3]分級:Ⅰ級28 例,Ⅱ級10 例;其中男、女患者分別為23、15 例;年齡61~88 歲,平均(78.62±4.13)歲;文化水平:初中及初中以下19 例,高中及高中以上19 例。觀察組(38 例)患者ASA 分級:Ⅰ級25 例,Ⅱ級13 例;其中男、女患者分別為21、17 例;年齡60~86歲,平均(77.95±3.98)歲;文化水平:初中及初中以下22 例,高中及高中以上16 例。兩組患者ASA 分級、性別、年齡及文化程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可比。納入標準:①參考《骨科疾病診療指南(第3 版)》[4]中膝關節骨折的診斷標準,且符合全膝關節置換術手術指征;②單側擇期實施膝關節置換術;③意識清楚,具備良好依從性。排除標準:①具有手術禁忌證;②伴有腎、心、肝等嚴重器質性病變;③藥物濫用,或具有本次研究所用藥物過敏史;④伴有嚴重凝血功能障礙、血液系統疾病;合并惡性腫瘤。長江航運總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已批準本研究,且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麻醉方法對照組患者使用全身麻醉,麻醉誘導:靜脈推注0.15~0.2 mg/kg 體質量注射用苯磺順阿曲庫銨[浙江仙琚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90202,規格:5 mg/支],0.3~0.5 μg/kg 體質量枸櫞酸舒芬太尼注射液(宜昌人福藥業有限責任公司,國藥準字H20054171,規格:1 mL∶50 μg),0.03~0.05 mg/kg 體質量咪達唑侖注射液(江蘇恩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43222,規格:10 mL∶50 mg),1.5~2.5 mg/kg 體質量丙泊酚乳狀注射液(四川國瑞藥業有限責任公司,國藥準字H20030114,規格:50 mL∶0.5 g);麻醉誘導后采取氣管插管,術中予以丙泊酚4.0~8.0 mg/(kg·h)和注射用鹽酸瑞芬太尼(江蘇恩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43314,規格:1 mg)0.2~0.5 μg/(kg·min)靜脈滴注,靜脈復合維持麻醉,間斷予以順阿曲庫銨,確保肌肉處于放松狀態,調節腦電雙頻指數為40~60。
在上述基礎上,觀察組患者采用超聲引導下腰叢坐骨神經阻滯麻醉 :取膝胸側臥體位,患側向上,超聲探頭長軸與脊柱平行,同時在脊柱與雙側髂肌最高連線點交叉位置患側旁邊進行掃描,明確L2~5橫突,發現橫突下緣伴有亮回聲,即腰大肌,通過超聲在L3~4橫突間隙到腰大肌部位行穿刺,進針到腰叢神經周圍,回抽無血后,靜脈滴注0.25%鹽酸羅哌卡因注射液(江蘇恒瑞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60137,規格:10 mL ∶100 mg)20 mL。坐骨神經阻滯:仰臥體位,屈曲膝關節及髖關節,經大腿后側移動探頭到近端,采用髂脛束后緣進行穿刺,回抽神經鞘周圍無血后,予以15 mL 0.25%羅哌卡因。神經阻滯成功20 min 后,行全身麻醉,方法同對照組,間斷予以順阿曲庫銨,確保肌肉處于放松狀態,根據患者實際情況調節全麻藥物劑量及滴速,維持腦電雙頻指數為40~60。術后,兩組患者均采取自控靜脈鎮痛方法,予以鹽酸托烷司瓊注射液(杭州民生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52664,規格:5 mL ∶5 mg)5 mg、枸櫞酸舒芬太尼100 μg 與生理鹽水混合液,按2 mL/h 的速率輸注。
1.3 觀察指標①血流動力學指標,通過心電血壓監護儀(深圳市施博瑞科技實業有限公司,型號:SPR9000A)檢測麻醉前、插管時、拔管時心率(HR)、平均動脈壓(MAP),采用血氧飽和度檢測儀(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型號:PM-60)檢測麻醉前、插管時、拔管時血氧飽和度(SpO2)。②疼痛評分,術后6~72 h 采用視覺模擬量表(VAS)疼痛評分[5]評估患者疼痛情況,分值0~10 分,分值越高,疼痛越劇烈。③T 淋巴細胞亞群指標,分別于術前及術后24、48 h 采集患者空腹靜脈血(5 mL),用流式細胞儀(上海土森視覺科技有限公司,型號:BD FACSAria Ⅲ)檢測全血CD8+、CD4+百分比,并計算CD4+/CD8+比值。④不良反應發生情況,統計患者嗜睡、惡心嘔吐、皮膚瘙癢等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0.0 統計學軟件分析數據,血流動力學指標、疼痛評分、T 淋巴細胞亞群指標為計量資料,經S-W 法檢驗符合正態分布,以(±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多時間點間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SNK-q檢驗;嗜睡、惡心嘔吐、皮膚瘙癢等為計數資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血流動力學指標比較與麻醉前比,插管時、拔管時對照組患者HR、 MAP 逐漸升高,兩組患者的SpO2逐漸降低,且不同時間點觀察組HR、 MAP 低于對照組, SpO2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觀察組患者的HR、 MAP 各時間點組內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血流動力學指標比較(±s )

表1 兩組患者血流動力學指標比較(±s )
注:與麻醉前比,*P<0.05;與插管時比,#P<0.05。HR:心率;MAP:平均動脈壓;SpO2:血氧飽和度。1 mmHg=0.133 kPa。
組別例數HR(次/min)MAP(mmHg)SpO2(%)麻醉前插管時拔管時麻醉前插管時拔管時麻醉前插管時拔管時對照組3880.85±4.96 87.12±6.95* 91.58±7.74*# 91.95±7.74 95.56±6.84* 107.45±8.13*# 98.55±0.28 96.78±0.44* 95.83±0.41*#觀察組3881.02±5.13 81.36±5.6881.67±6.64 91.82±8.03 87.52±7.73 100.51±6.97 98.56±0.23 97.02±0.15* 96.58±0.42*#t 值0.1473.9565.9900.0724.8023.9950.1703.1837.877 P 值>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
2.2 兩組患者VAS 疼痛評分比較與對照組比,觀察組患者術后各時間點VAS 疼痛評分更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VAS 疼痛評分比較(分,±s )

表2 兩組患者VAS 疼痛評分比較(分,±s )
注:與術后6 h 比,△P<0.05;與術后24 h 比,▲P<0.05;與術后48 h 比,□P<0.05。VAS:視覺模擬量表。
組別例數術后6 h術后24 h術后48 h術后72 h對照組383.47±0.523.23±0.56△1.86±0.21△▲1.26±0.24△▲□觀察組382.51±0.452.03±0.39△0.98±0.19△▲0.52±0.15△▲□t 值8.60610.83919.15516.118 P 值<0.05<0.05<0.05<0.05
2.3 兩組患者T 淋巴細胞亞群指標比較術后24、48 h兩組患者CD8+百分比先升高后降低, CD4+百分比及CD4+/CD8+比值先降低后升高,且不同時間點觀察組CD8+百分比均低于對照組, CD4+百分比及CD4+/CD8+比值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T 淋巴細胞亞群指標比較(±s )

表3 兩組患者T 淋巴細胞亞群指標比較(±s )
注:與術前比,P<0.05;與術后24 h 比,▲P<0.05。
組別例數CD8+(%)CD4+(%)CD4+/CD8+術前術后24 h術后48 h術前術后24 h術后48 h術前術后24 h術后48 h對照組3825.49±4.47 28.94±3.61images/BZ_59_717_457_758_509.png 26.98±1.32▲ 34.59±2.13 23.09±0.89images/BZ_59_717_457_758_509.png 35.15±0.77▲ 1.20±0.48 0.80±0.25images/BZ_59_717_457_758_509.png 1.30±0.58▲觀察組3825.52±4.32 26.53±3.12 24.67±1.46▲ 35.12±2.98 33.98±0.98images/BZ_59_717_457_758_509.png 40.23±0.91images/BZ_59_717_457_758_509.png▲ 1.39±0.69 1.28±0.31 1.64±0.62images/BZ_59_717_457_758_509.png▲t 值0.0303.1147.2350.89250.71026.2701.3937.4302.469 P 值>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
2.4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對照組[13.16%(5/38)]與觀察組[7.89%(3/38)]患者不良反應總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例(%)]
3 討論
膝關節是承重關節,勞損及骨質疏松等均可能引起膝關節疾病,多發于老年人群,且患者通常具有活動受限、關節疼痛癥狀。臨床上主要采取手術治療,全膝關節置換術為常用手術方法,該術式治療的重點在于緩解膝關節疼痛,及早恢復膝關節功能,具有操作便捷,清除全面、定位準確等優勢,被廣泛應用于臨床中。盡管全膝關節置換術具有一定治療效果,但由于部分患者年齡較大,或者合并基礎疾病,則會增加手術麻醉難度。全身麻醉是全膝關節置換術中常用的一種方法,但老年患者由于年齡大、代謝延緩,采用全身麻醉藥物很可能導致蘇醒延遲,故其應用受到限制。
超聲引導下的神經阻滯麻醉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的作用主要是減少成功阻滯的局部麻醉面積,該方法在超聲引導下進行操作,對呼吸、循環系統無明顯影響,對全身影響小,鎮痛效果更好,并且肌松效果良好。同時,超聲引導也可以精確地定位組織,使神經阻滯得以精確控制,準確觀察麻醉的蔓延范圍,并對其進行評估,從而提升麻醉效果。此外,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阻斷手術操作向中樞神經系統的疼痛傳導,阻斷外周傷害性刺激引起的應激反應,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6]。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采用超聲引導下股神經阻滯聯合浸潤麻醉具有良好的血流動力學穩定性和高安全性[7]。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時間點觀察組HR、MAP 及VAS 疼痛評分均低于對照組,SpO2高于對照組,說明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應用效果顯著,可以平穩患者血流動力學指標,減輕術后疼痛。
手術應激及鎮痛藥物的使用均能夠加重患者免疫功能紊亂,T 淋巴亞群細胞因子在機體免疫調節中至關重要,CD4+、CD8+百分比兩者平衡是維持機體免疫調節功能的關鍵,外周血CD4+降低或CD8+升高均提示機體免疫調節紊亂,存在一定的免疫抑制[8]。在全身麻醉基礎上聯合神經阻滯麻醉,結果顯示,與術前比,術后24、48 h 兩組患者CD8+百分比先升高后降低,且不同時間點觀察組均低于對照組;兩組患者CD4+百分比及CD4+/CD8+比值均先降低后升高,且觀察組更高,說明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應用效果顯著,能夠改善外周血T 淋巴亞群細胞,提高免疫功能。究其原因,單純全身麻醉有可能促進皮質醇與受體的結合,導致機體免疫功能下調。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減少了全身麻醉藥物的用量,減輕了麻醉藥物本身帶來的對免疫系統的抑制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免疫功能;此外,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應用于全膝關節置換術中,能夠強化鎮痛效果,減輕機體應激反應,從而減輕機體免疫抑制程度[9-10]。另外,本研究在全身麻醉的基礎上聯合神經阻滯麻醉,通過觀察兩組安全性發現,對照組與觀察組患者不良反應總發生率經過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進一步說明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應用安全性良好。分析原因可能為,與單獨全身麻醉相比,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能夠減少術中全麻藥物的用量,減輕免疫抑制,直接影響了患者術后精神狀態的恢復,減少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此外,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麻醉不僅可以確保手術的安全性,還能提高患者的舒適度,且不同麻醉方法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從而避免不良反應的發生,因此麻醉安全性良好。
綜上,全身麻醉復合神經阻滯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應用效果顯著,不僅可以平穩患者血流動力學指標,減輕術后疼痛,且能夠改善外周血T 淋巴亞群細胞,提高免疫功能,安全性良好。但本研究樣本量較少,且未對麻醉藥物用量的結果進行分析,結果可能存在偏倚,后期需增加樣本量及研究考察指標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