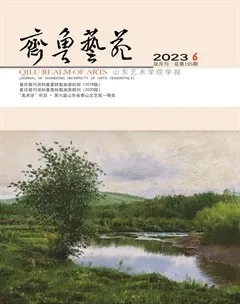社會空間中的藝術干預
——以山東藝術學院美術學院國家一流課程《社會考察》為例
邢士強
(山東藝術學院美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隨著學科建設與專業發展的推進,美術專業的教學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學分制教學改革、一流專業評選、高水平學科競爭、學科評估等等都為美術教學的變化規定了尺度與方法,以師徒技術語言傳承的傳統模式漸漸被以科學孕育方法建構為框架的現代模式所取代。山東藝術學院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專業的《社會考察》課程通過借鑒優秀高等院校的成功案例以及結合山東地域文化特點和學院自身發展定位,經過多年打磨,逐漸成為有特色創新的、符合當前時代教育要求的優秀課程。在遵循藝術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以關注當下的大文化價值取向、具備思想性的反映人類生存狀態與文明,尤其是精神層面上的民族精神為核心價值觀,把敏銳的藝術視角伸進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的土壤中,在遵循社會倫理道德規律、藝術生成規律的同時,追求高等教育的高要求,培養學生使之成為具有人文理想的倡導者和踐行者。《社會考察》課程以鄉土為學院,通過社會現場的教學,聯動鄉村和高校的關系,引導學生建立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感、勇立潮頭的時代感、關注家國情懷的責任感,回應藝術教學以人民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探索以鄉土為學院的扎根中華大地的藝術教育實踐,制定圍繞時代命題的育人方案,推進藝術教育與鄉土社會、藝術教育與思政教育雙向聯動的教學改革方案,形成從校內課堂到社會鄉村的藝術育人新現場,催生了文化傳承、藝術教育、思政育人、社會服務、四位一體的育人新機制。課程體系架構從每一個具體的環節(教學環節、調研課題環節、傳播交流推廣環節等)出發,探討新形勢、新境遇下美術教學。藝術、人與社會是相互關聯的幾個支柱,它們共同作用,藝術和社會行動緊密結合。在藝術與鄉村、田野、人文境遇、社會的關系之間,我們從不同的思考角度,進行探索、挖掘并轉換。
藝術干預的概念從20世紀就有了更明確的定義,意大利先鋒派藝術家團體“未來者”把自己形容為“干預者”。國際情境主義中的新先鋒派——一群以法國藝術家蓋·德波為核心的20世紀60年代藝術家——也使用“干預”一詞。德波受他的導師亨利·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生成”理論的影響,在藝術實踐中開創了多個具有影響力的策略,構建了多種情形,并促進了公共空間和社會互動關系這一理念的發展。在今天藝術家們經常嘗試與政府、企業、鄉村和其他社會空間合作,發起空間藝術項目、藝術節活動等。高等院校也通過校企合作、校村合作探索藝術與鄉村振興的發展。事實上,我們的社會考察課程就屬于一種集體的、高等教育理念下的、教學與實踐相結合的、與社會鄉村空間合作的藝術項目。《社會考察》課程作為一種特殊的走出校園的實踐性課程,本身就帶著一種多重屬性,它既是高校教學的課程,又是社會鄉村美育的踐行體現。從場域的角度來說,它又是一個復雜的行為事件,顯而易見,這樣一隊人馬駐扎在一個特定鄉間村落,用藝術的多元形態在這樣一個空間內形成有效反映,無論是行為性的、視覺性、過程性、傳播性的,過程的點點滴滴、成果的字里行間,都是一種藝術介入下的干預活動。這種干預活動的指向包括精神文明形態(比如優秀傳統思想),也包含視覺審美形態(比如大眾視覺、民俗民藝、文創方向),甚至隱含相關的健康與治療形態(比如心理學方向)以及社會美育的傳播與引導。“干預作為刺激或激化的工具,要取得成功,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將相應的溝通形式視為創造的不同之處。”[1](P76)藝術干預通常基于項目靈活性基礎,也可以包括臨時行動或表演,以及非正式和顛覆性的藝術策略,相對于長期而言的雕塑等藝術形式,它們大多數具有短暫和臨時性的特點。干預包括室內或室外空間的現有條件,同時按主題解決該地點特定的社交、社會、文化、功能、空間和物質等方面。藝術干預意味著特定場所和空間是一種介入和反思的必備條件,考現學作為其中一種方法,有助于我們的課程在實施之前展開相應的調查,通過鄉村考現,之后進入到創作轉換過程,并介入藝術干預的理念。本身從這種教學行動而言,已經進入了藝術干預性活動中的鄉村,成為近幾年我們課程實施的重要場域。例如我們經常到的威海榮成煙墩角村(連續三年課程建設中均為我們的教學實施地點),它是集海洋農牧及鄉村旅游為主導的山東沿海村落,在當下新農村發展大潮中,它是走在前列的,在這里有幾個關鍵詞是這個村的重點:天鵝(它的生態保護下,是天鵝過冬的聚集地),漁業(遠洋捕撈、近海養殖),海草房(當地特色民居)、古老村落(民俗文化)等,這為我們的藝術項目介入提供了寶貴的基礎因素。“考”是以類似田野調查的方式,“現”則是過去的總和集合于當下,這使得我們的視點從風景與物件開始,轉移到民居、公共空間、村民和日常生活,包括對本土知識的學習與開掘,以及對地理、人文、生態、歷史、風物獨特性的體察與再現,并在其中發現鄉村生活的特殊審美。“鄉村考現”隨風土情境而轉移,其所記錄的物質與精神形態也具有了更為深遠的意義。
任何一種材料,無論是時間、光線、聲音和空間中的運動,都可用于藝術干預。藝術干預還像地景藝術,可以看作是公共空間的藝術。公共空間不總是默認為向所有人開放的空間,可以是一個不同用途的綜合空間,同時不僅僅是物理空間,還是集體、社交和社會意識的精神構建處。將藝術干預判斷為孤立的審美評判,未免太過簡單。藝術家作為文藝工作者,以解放教育的使命和戒律為指導,要創造超越面前事件的互動和溝通的創意綠洲。藝術干預要考慮日常生活和公共社會文化的社會方面,通過活動家、干預者或參與戰略,直接介入普遍的社會進程和狀態。在福柯·蘇曼的研究成果《公共空間的美學干預》一文中,他的空間與藝術介入的觀點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有關干預的美學問題。他對美學干預和藝術干預的意圖做了區分:“美學干預不代表反對其所干預地域主流秩序。在負面反映這種秩序方面,不算作與之對立,其目的并非要反對現有,而是通過更多復雜因素的集結,形成有效力量。因此可以認為這種介入不存在于批評意見之中,或試圖形成煽動性角色,也不存在于反對所謂意見或者呼吁重置。因此這種美學干預在不違背普遍秩序中為創意行動開辟更多新的可能,甚至有些‘格格不入’。那么創造和再創造,以及改變現狀,成為這一美學介入的大膽嘗試。”[2](P24)
在我們社會考察的村落中,煙墩角村具有居住村落與旅游村落的雙重屬性,那么在這樣一個空間里,居民、游客構成了屋子以內和屋子以外的兩大類別。在公共空間內,這兩大全體共同占有和使用這些空間,從居民角度來說,這些公共空間在很大程度上以單一用途為特征,甚至由于生活環境的問題和缺陷,居民經常疏遠一些公共空間。因此,人民會感受到內心的分裂,與城市周圍的環境喪失聯系。在這里,藝術和文化可以充當社會凝聚力的媒介,給居民以生活的歸屬感。但是這種潛力不應該用于制造太多的娛樂文化,而應用于更多地促進參與人文構建。我們在教學過程中,盡可能地結合這些復雜的因素,以專業的審美素養與人文境界去捕捉那些敏感點,并盡可能避開大眾審美下的娛樂文化,我們甚至采用批評的方法和矛盾的力量,去激活和干預。而這種介入,恰恰也是我們所倡導的一種教學與實踐相結合的體現。我門的這種藝術介入可以幫助挖掘村落的潛在文化價值,繼而轉化為新型生產力并帶來直接效益;還可以有力地作用于那些在歷史行進中被忽略的村落文化基因,重塑村落的文化凝聚力,用文化與創意更新知識和技術、升級理念和經驗,積極發揮優秀基因在當代社會建設中的作用。通過干預和介入到煙墩角村的生活與空間,同學們提出一系列卓越的新奇計劃,形成一種跨地域、跨學科的對話,并直接與他鄉形成對話。
從本文社會空間中的藝術干預角度,我們在此框架中提出了諸多問題:以干預形式的藝術活動如何產生長期或階段性的影響?如何衡量它們在這些領域的影響,以及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將此類研究成果納入藝術教育?眾多的項目和目前為止與我們課程相關聯的項目模塊的長期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項目經驗和豐富的優質成果,那么在這個提倡前沿交叉學科的時代背景下,造型藝術如何與應用學科(景觀學、社會學、農學等等)搭建這種學科交叉的新模塊?如前文所述我們的社會考察課程經過多年的打磨,基本確立了以前沿交叉學科為背景下的優質精品課程定位。接下來我分享幾個社會考察課程實施的項目案例。
1.數字孿生—— “記憶的留存”
每個時代都有著不同的審美經驗所面臨的新問題和挑戰,數字時代的到來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藝術表達與形式。借用數字語言的方式進行藝術創作,一方面符合我們培養方案中的方向要求(造型與新媒體),另一方面也是藝術與科技這個大的交叉學科的內容要求。借助數字孿生、數字虛擬的方式,可以模擬現實世界中的物理系統和進程,也可以對已逝物品的追溯與闡釋,進而更好地進行運算、管理以及決策甚至存儲留檔等方面的應用。
“記憶的留存”是這一項關于記憶的裝置作品,也歸類于數字人文的前沿交叉探索。有同學通過對本區域的調查后認為,隨著物質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很多老物件已經在逐步過度老化的過程中喪失其使用功能,還沒有被丟掉的也僅靠其“視覺審美”的光環生存,于是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問題:老物件的前世今生所囊括的內容,是可以引領觀看者通過物品進入到一個更龐大的關于這個村子的故事。因此,這個由五個大三同學組成的群體,在煙墩角村的居民私人空間展開了搜集,力求尋找到更多的代表性的、背后有故事的物品,例如一個作為勞動獎品的搪瓷缸,一個現在的大叔小時候雕刻的手工玩具,一個早已淘汰的陶瓷水漂等等。各種主題脈絡與本地收集的經驗相結合,產生一個多層的整體概念,并使用化學膠水把物品封存,凝固之前附帶二維碼鑲嵌其中。當觀看者掃描二維碼時,數字端所呈現的就是關于這件物品的物主訪談,從而把我們引領到這件物品的故事中去。由此匯集的所有物品組合在一起,形成一件裝置作品擺放在廣場中,以膨脹的“彈出”現象發生著它的藝術作用,把背后的故事遷移到村落的公共區域,并在給定的數字平臺內運行。具體而言將帶有記憶屬性的物品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予以整合,視覺審美成為前奏,掃描進入數字呈現開辟進一步的互動,最后,這些記憶樹立了標簽,用一個個故事串聯出了村落的歷史與人情。在此情景境遇下,我們可以推測,這樣發起交際的過程和培養新的社會交流關系有助于加強村落和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心理溝通,以及我們提倡的對于社會美育功能下的心靈塑造。這種藝術干預通過線上與線下結合的方式,形成了共振式的影響。
2.場域圍筑——“遺失的寶劍”
從古典藝術到現代藝術再到當代藝術的轉化過程,伴隨著一種觀看方式〈或體驗方式〉的變化,即從靜觀,到劇場,再到沉浸的演變。審美靜觀帶有強烈的宗教內涵,它要求觀眾駐足凝神,像膜拜偶像那樣直面一件偉大的藝術杰作。這種觀看方式在20世紀60年代發生分裂。隨著極簡主義的到來,藝術家通過場面調度,將一種極簡物〈通常還是現成品〉作為藝術品展出,從而將觀眾帶入劇場般的藝術現場。觀看者像參與者一樣,進入到空間系統,并與物形成共振。當代藝術的晚近趨勢呈現為越來越強烈的虛擬現實特征,使觀眾產生懸置了幻覺的那種沉浸感。這一觀看之道的演化與哲學和世界觀的變化相關:即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再到具身性的轉向。自杜尚開始興起,場域的概念在當代藝術中占據著新創作領域的重要位置,利用特殊地域的本土性,總是可以激發更多的創造性,以及這種借力之后的發酵。
“遺失的寶劍”是一場戶外劇場類的藝術項目嘗試,首先同學們選定了一個當地的民間傳說故事為題材進行改變,并尋找到一處有多重意義的場地,從神話故事內容來說符合的場域,從布局上看,前景、中景、遠景都是他們加以利用的內容,前景他們選擇了舞臺劇場式的搭建,包括處理后的廢船和其他道具、幕布等,都是他們作品的一部分。中景的海灘,他們選擇了雇傭人群的介入,在看似偶然的機械式運動的人,恰恰是作品的刻意安排,無論是打太極劍的老人,還是打鬧的孩童。遠景自然變化的天空就當成了瞬息萬變的自然背景。整個的項目以循環的方式進行,仿佛村里的社戲,這是一出觀看者可以無意間參與其中的戲,故此觀看者也是作品的參與者。而同學們只是從當地的一則民間傳說進行演繹,展開了這部場域概念的劇場藝術,它顛覆了大家的對藝術的理解(1)每日勞作的村民,進入到同學們安排的角色中,當他們看到之后的視頻,從笑容之中感受到他們的融入,一種被認定和跳出的力量內含其中,他成為了一名“角色”。這與他們一直以來的固定身份之間形成了一種沖突,藝術干預下的影響,軟化了疲憊的身軀,對精神、對人性的尊重與光芒進而呈現。。現代藝術的教條或意識、意識形態從來沒有停止過在這兩種目的之間的撕扯,一種是內在的目的,一種是超越的目的。而藝術本身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無論是單一式還是交叉式,都從未停止過想要將兩種目的的彼此割裂,跨界的方式是如此充滿趣味,藝術與藝術之間的、藝術與非藝術之間的等等。這項計劃的方式是創造性的集合,連同作為合作演員參與其中的“觀眾”,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儀式化的一部分,并引導當代生活藝術概念的解題。雖然他們“拙劣的表演”僅是稚嫩的嘗試,但從藝術干預的角度,他們獲得了內容的填充與釋放。
3.傳統轉換——“補船”
傳統是從歷史上延續下來的,包括思想、道德、風尚、文化、制度、禮儀、藝術等方式。它們通常作為歷史文化財富而傳承,而文化是一個圍繞著不同國家和民族,沿著時間單向運行的矛盾復合體。何為轉換?轉換是在不同的語言系統中對于意義的更迭表達,是生命體的編碼轉譯形成新的生命體。而對于文化的當代性轉換,更不是簡單的元素照搬和淺顯的挪用和嫁接,轉換的核心意味著對母體內在結構、意義認知的重新生成,是對母體內在價值的再創造。
船,對于一個漁村自然有著特殊的意義,漁網亦是如此,一船一網一人構建了早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方式。在煙墩角村里隨處可見的廢舊老船,以及碼頭對面的三星造船廠交相呼應,現代文明、科技進步與傳統手工的舊式勞作之間有意思的話題是這幫同學思考和研究的。他們決定用一種烏托邦式的勞動——補船(用漁網線去修復殘破的漁船)來實施這項計劃,并選定煙墩角村社空間中的群眾廣場附近區域進行藝術干預的嘗試。在廣場區域是大眾形態的雕塑作品和日常的現成品擺放地,而正是如此,多種因素匯集才有效地以不同的呈現方式介入到這樣一個常規形態下的鄉村廣場空間。在這里面,藝術不再是一個特定或固定的對象,民間的、大眾的、這樣的介入性的轉換作品,形成有效的互動干預空間,居民、游客在看懂與非懂之間、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依照他們自己的知識庫對藝術作品評頭論足,或沉思琢磨。這一背景下開展的藝術干預項目讓事情不再一成不變,通過它們混合在一起的作用,甚至被認為是破壞性的元素和刺激源而成為辯論和溝通的催化劑。藝術由此變得更加的可見、可爭論、可反思,無論是對既定認知的再認知,還是對他們暫時懸置后的新認可,等等,都可歸納為藝術干預社會空間后的有效能動性。
4.農村與城市——展覽
如果說以上的分組作品是課程中不同方式、視角的對于藝術空間干預性介入的體現,那么對于每次課程結束之前的在地性的展覽,則成為一種集體事件式的藝術干預,我們依舊從行為方式的角度去分析這種在地傳播所帶來的影響。在地展是一種促進文化流動、激發對話的實踐機制,它薈集了本地營造的精粹部分,扎根于鄉村的展覽并巡回至城市文化空間,使我們的敘事置于不同的語境之中,形成相應的互文關系。這體現了我們用藝術“往鄉村導入城市資源,向城市輸出鄉村價值”的“藝鄉建”路徑。當村民、游客進入到展覽中,他們通過作品去思考、追問,了解村落、民俗、藝術、同學們所想所思,而回到城市中的二次展覽,作為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紐帶,把傳播的空間放大,把藝術干預與影響放大。它通過我們的活動、干預者或參與戰略,直接介入普遍的社會空間(日常生活和公共社會文化)進程中去。
在遵循藝術發展規律的學科發展中,只有那些表達人類共同關注下的優秀化價值取向、具備思想性的反映人類生存狀態與文明,同時具備創造性的藝術方式,才能獲得強大的生命力,而這種生命力的根本,就是民族優秀文化的滋養。未來課程的發展和建設需要我們更加具體的樹立國家、民族、時代特征的通識教育理念,體現新文科背景下的藝術教育新要求,更多的體現紅色革命精神與傳統,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新鄉村建設成果,體現和諧社會下的人文湖山,并在執行過程中進一步做好深入性、系統性和分類分層的細化,這需要我們在未來更加強調課程的應用性、實踐性、以教學育人為前提的基礎上的科學性,在教學過程中、藝術介入鄉村的形式之下,讓教學成果、人才培養彰顯教學能力的同時,更多角度地反哺人民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