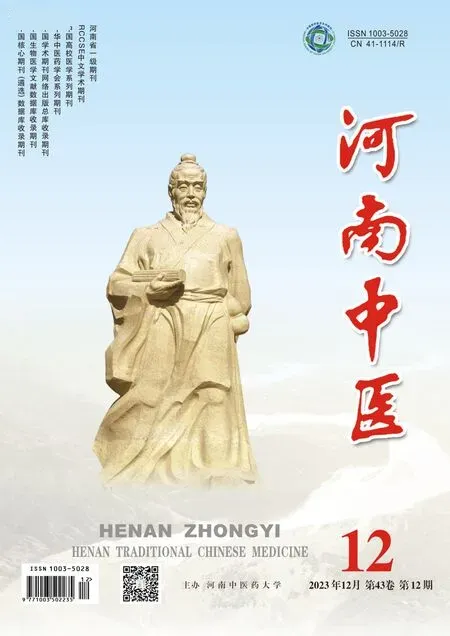《傷寒雜病論》舌診芻議*
郭倩,李榮科,張磊,魏昭暉,馬欣欣,萬生芳
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1 《傷寒雜病論》舌診
《傷寒雜病論》中,涉及舌診的條文共有32條,包括《傷寒論》[2]中的24條和《金匱要略》[3]中的8條。關于舌診,主要包括察舌體、舌苔、舌態等,且首察舌苔[4]。張仲景認為,三陽病及六腑病,重在察舌苔變化,因為三陽病及六腑病多為外邪侵襲,病位表淺,正氣尚未衰,舌質變化不明顯;三陰病及五臟病,重在察舌質形態,因為三陰病及五臟病病位在里,舌質變化較顯著。
1.1 論舌苔
1.1.1 上寒下熱之苔《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治》云:“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這是濕病誤下的變證,“寒”是指濕邪,濕困熱邪,誤用下法,形成上寒下熱之證,下熱當舌燥,而又有上濕,舌象表現當是苔厚膩,現上下寒熱不調、濕熱不當則見似苔非苔之象。
1.1.2 黃疸、肝寒之苔《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言:“腹滿,舌痿黃,燥不得睡,屬黃家。”《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曰:“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可以看出,張仲景將“舌痿黃”“舌本燥”視為診斷“黃疸病”“肝中寒”的主要指征之一,體現了舍證從舌的辨證思想。
1.1.3 臟結之苔“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說明小柴胡湯可以調節三焦氣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臟結是虛寒之證;結胸是實熱之證,所以臟結的舌象是舌上白苔滑。
1.1.4 大、小柴胡湯證之苔《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言:“腹滿,口干舌燥,此腸間有水氣,己椒藶黃丸主之”。“腹滿”而現“口干舌燥”,非津虧液耗,實則水氣過盛,停留腸間,阻滯氣機,氣不化津、化液。“陽明病,脅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此處“舌上白苔者”可作為大、小柴胡湯證的鑒別點:大柴胡湯證為陽明熱盛,故見舌苔黃,“白苔”自然區別于大柴胡湯證;“不大便而見白苔”,未用攻下之法,而用小柴胡湯,說明小柴胡湯可以治療大便不通。
1.2 論舌體
1.2.1 舌青主瘀《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言:“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為有瘀血。”“舌青”即青舌,主血瘀,是脈絡阻滯于舌下,血流不暢的表現,而“胸滿”“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等均為患者的自覺癥狀,無法準確判斷瘀血證,而“唇痿舌青”能客觀反映瘀血狀態,故此條文明確了舌青與瘀血的辨證關系。
現階段,頭頸部腫瘤在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惡性腫瘤中占有一定比例,傳統的治療方法對頭頸部腫瘤有許多不良影響,嚴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質量。因此,突破傳統探索新的低細胞毒性的治療至關重要。這不僅是頭頸部腫瘤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所有惡性腫瘤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其次,傳統的抗腫瘤藥物存在嚴重的耐藥性,探索新的藥物,將大大豐富聯合用藥的方案。二甲雙胍最早應用于臨床有賴于它的降糖作用,后來的研究和應用中發現,二甲雙胍的作用不只針對糖尿病,在多囊卵巢綜合征、代謝綜合征和糖尿病預防也有突出表現,尤其是當前提出的二甲雙胍可能作為一種新型的多方位的藥物來預防和治療腫瘤,將二甲雙胍的研究又推向了新的高潮。
1.2.2 熱厥之舌“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指出熱厥的治療原則是下之,若誤用辛溫發汗之品,助熱傷津則口舌生瘡。
1.3 論舌態
1.3.1 舌痿《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言:“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舌痿’疑作身痿。”此黃疸為寒濕陰盛之陰黃。
1.3.2 舌難言《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言:“邪在于絡,肌膚不仁;邪在于經,即重不勝;邪入于腑,即不識人;邪入于臟,舌即難言,口吐涎。”“舌即難言”為邪入臟,舌失滋養,舌體運動失靈而出現語言障礙。
1.3.3 舌不仁“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于轉側,口不仁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口不仁面垢”是味覺失常,黏膩不爽,言語不利。陽明熱盛則見“腹滿”,熱盛上攻,則見“口不仁面垢”。
2 舌診意義
張仲景運用舌診不只是單純說明一個癥狀,更是說明一個病因病機、一種預后、一種臨床用藥方法。因此,根據舌診變化可以推求病因、論述病機、確立治則、指導治療、判斷預后等。
2.1 推求病因《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言:“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腹滿”可有虛實之分,以手按之無壓痛者是虛證,有壓痛者是實證。若下法后舌黃消退,則可推斷其病因為實熱之邪。此條文論述了腹滿的虛實辨證,并提出實證的治療原則。尤在涇言:“腹滿按之不痛者,無形之氣,散而不收,其滿為虛;按之而痛者,有形之邪,結而不行,其滿為實。實者可下,虛者不可下也。舌黃者熱之證,下之實去,則黃亦去[5]”。

2.3 確立治則《傷寒論》第129條言:“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臟結沒有發熱、口渴之里熱表現,也沒有往來寒熱之癥,而舌上苔滑,更是陽氣大虛的表現可知該證屬三陰病。“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成無己言:“臟結于法當下,無陽證為表無熱,不往來寒熱為半表半里無熱,其人反靜為里無熱”[6]。柯韻伯言:“結胸是陽邪下陷,尚有陽證見于外,故脈雖沉緊,有可下之理。臟結是積漸凝結而為陰,五臟之陽已竭也。外無煩躁潮熱之陽,舌無黃黑芒刺之胎,雖有硬滿之癥,慎不可攻。理中、四逆輩溫之,尚有可生之義”[7]。
2.4 指導治療《傷寒論》第137條言:“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哺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第168條言:“傷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熱結在里,表里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干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兩條文中均有“舌上燥”,前者是邪熱內結,熱盛津虧,予大陷胸湯瀉熱逐水。后者是失治誤治導致的表里俱熱,表邪入里,津虧氣耗,則予以清里熱、益氣津之白虎加人參湯。
2.5 判斷預后《傷寒論·辨脈法》言:“脈陰陽俱緊者,口中氣出,唇口干燥,蜷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舌上胎滑”是陽虛里寒之征,“陰陽俱緊”表示寒邪郁閉,陽虛寒盛,病情危重,治療當謹慎。
3 張仲景對舌診的貢獻
3.1 首創舌苔概念,明確舌診內容《黃帝內經》中雖有“舌上黃”“舌焦”等舌象變化的記載,但未對“舌苔”做準確的描述。張仲景《傷寒論》言:“何謂臟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最早提出“舌苔”概念[8-10]。明確舌診內容包含舌質、舌苔、舌態等,舌體變化有:舌痿、口傷爛赤、舌不得前、舌青;舌苔變化有:舌上苔滑、舌燥、舌上白苔、舌上白苔滑;舌覺變化有:口中辟辟燥、口苦、口中和、口噉蒜狀、口不仁等;舌司語言功能變化有:舌即難言等。通過舌質、舌苔的形態、色澤、潤燥等判斷病邪性質、正邪盛衰、病情預后等。
3.2 通過舌診辨表里、寒熱、虛實《傷寒論》第230條言:“陽明病,脅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此“舌上白苔”證明邪尚未入里,脅下硬滿進一步說明病位在半表半里之少陽,予小柴胡湯和解。《金匱要略》言:“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舌上如胎”指舌白滑潤澤,結合原文“胸滿”“渴欲得飲水不能飲”可以推斷患者胸中有寒。《傷寒論》中白虎湯證與白虎加人參湯證的鑒別點為“舌上干燥而煩”,前者為陽明熱盛,但未傷津,屬實證;后者舌燥煩,口大渴表明已傷津耗液,加人參補氣生津,屬虛實夾雜證。
3.3 同病異舌,同舌異治“舌上燥而渴……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腹滿,口舌干燥……己椒藶黃丸主之”“若渴欲飲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三條文均記載有口舌干燥之癥,但大陷胸湯證病機是熱結胸脅;己椒藶黃丸證病機是水飲停留腸道;白虎加人參湯證病機是熱盛津傷。雖然舌象相似,但病機各異,則治法不同。第221條之梔子豉湯證與第168條之白虎加人參湯證雖同為陽明病證,但兩者舌象不同,病機不同,故分別用梔子豉湯與白虎加人參湯治療。
4 小結
《傷寒雜病論》舌診內容豐富,不但繼承《黃帝內經》之內容,又加以補充。張仲景既重視舌象變化,又強調四診合參,既有舍癥從舌,又有舍舌從癥,既有同病異治,又有異病同治,同一舌象,病機不同,治療亦不同;同一病證,舌象不同,治療也各具差異,總以辨證論治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