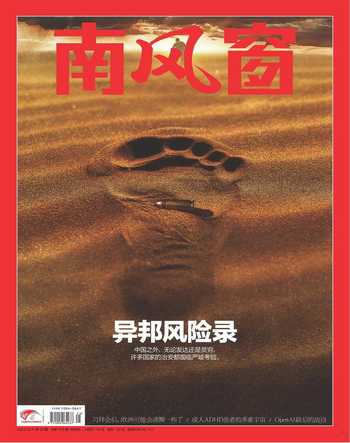歐洲治安,一言難盡
范一驥

2023年10月16日當地時間19時15分左右,兩名瑞典人在布魯塞爾被槍擊身亡,當時正進行的歐洲杯預選賽比利時和瑞典間的比賽也被迫取消。第二天,作為西歐樞紐之一的安特衛普火車站,一度因為發現可疑物而停用。
事后警方發現,恐襲主謀名叫阿卜杜薩勒姆·拉蘇德(Abdesalem Lassoued),來自突尼斯。他申請政治庇護未果之后就“黑”在了比利時,之后一邊打黑工,一邊和恐怖組織取得聯系。
就在槍擊案幾周前,兩名巴勒斯坦難民因綁架謀殺一名9歲兒童,被判處30年監禁。面對盜竊、搶劫、恐怖襲擊,惴惴不安中,歐洲人迎來了安全感稀缺的灰色時代。
當然,歐洲人自己也并非一副“如臨大敵”的態度。可以說,要從放松、悠閑的生活方式轉變到安全優先,恐怕還要一段時間。
歐洲治安城鄉有別
2023年11月,巴以沖突以來歐洲受到了中東武裝分子揚言的恐襲威脅,布魯塞爾國際機場宣布加強安檢,入關的行李要被挨個檢查,這也讓國際旅客的入關時間延長至一個多小時。相比很多地區,入境歐洲特別是入境申根國,是一件十分快捷的事情。1小時的安檢入境,已經是布魯塞爾能做的最大“努力”了。
2021年我首次入境歐洲,彼時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即便如此,我從下飛機到進入比利時境內也只用了20分鐘。而入境申根區后,你會發現,除了進入大型場館以及搭乘飛機,幾乎沒有地方需要安檢。地鐵、火車可以直接進入,商場和超市也很少安裝攝像頭。用身份證買車票或者要靠實名制進行遷徙的事情,在歐洲人看來幾乎是天方夜譚。
在歐洲,警察可以是一份非常輕松的職業。我經常看到他們慢悠悠去打卡,然后等待下班。旅歐期間,我少有的幾次和警察碰面,都是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當然,如果遇到大事,你也不太容易找到警察。
有一次,我邊騎自行車邊看手機導航,這時身后鳴笛,回頭一看竟是警車。車上的警察一邊鳴笛,一邊告訴我專心騎自行車,不要玩手機。當然,歐洲各國的警察主要干的事情也有所差別。比利時的警察喜歡查騎車玩手機,以及騎行中的頭盔佩戴問題;法國警察喜歡罷工;德國警察的任務較為繁重,他們喜歡蹲在邊境火車站去檢查乘客們是否攜有合法居留證明,盡管按照申根協議這并不是必需的。
在歐洲傳統里,社會治安不依賴警察,而靠自治。歐洲本地人甚至對警察搜查外來人口,表現出了一定的反感。“移民局的警察很煩人,沒人喜歡他們。”室友魯本對我說。長期以來,地方自治維系著歐洲的社會治安。你覺得鄰居鬼鬼祟祟可以舉報,你覺得餐館偷稅漏稅也可以舉報,看到不軌你可以見義勇為,然后警察和法院照章辦事來解決問題。
由于歐洲普遍是小國寡民,因此除了個別大都會城市,比如巴黎、布魯塞爾、柏林,其他城市在很多時候都是“街坊”們“雞犬相聞”的狀態。一旦發生公共事件全城人會第一時間知道,警方才跟在后頭按照蛛絲馬跡找到線索。因此,歐洲的安全感來自地方自治,原本并不需要太多的公共安全投入。但由于移民向大城市的聚攏,這套辦法在大城市根本行不通,人流量越大的地方安全感也就越差了。
小偷小摸習以為常
曾經的歐洲安靜祥和:危險發生,有市民見義勇為,有智者尋求真相。今天,取而代之的是公眾的疲倦、困惑、不安以及荒誕。
我曾在安特衛普一家咖啡店上班,一天早晨我發現店里的咖啡機失竊了。咖啡店在市中心的一家商場里,和歐洲大多數的地方一樣,商場沒有監視器。因此,我們對于找回咖啡機不抱任何希望。警察在接案后四小時,慢悠悠來到現場。在了解基本情況后,一位警察本來準備打卡下班,這時他的同事發現,臉書二手市場上正在賣一個和我們失竊的咖啡機型號一模一樣的機器。
歐洲的安全感來自地方自治,原本并不需要太多的公共安全投入。但由于移民向大城市的聚攏,這套辦法在大城市根本行不通,人流量越大的地方安全感也就越差了。
就這樣,在事發當天下午,偷咖啡機的賊被人贓并獲,咖啡機也回到了店里。竊賊之所以敢明目張膽銷贓,是因為在歐洲,人們對于丟失東西已經習以為常,一旦丟失他們也并不打算找回。因此,歐洲人都要給自己的自行車買保險,萬一丟了好歹還有些補償,反正自行車肯定找不回來。
對于家中失竊,近年來歐洲人也見怪不怪,遇到小偷小摸,大家也只能自認倒霉。在巴黎的地鐵上,我曾看到一個7歲上下的小孩偷了別人的錢包被當場抓了現行,車廂里的人在對小孩一番教育后便讓孩子離開了。“我的東西沒關系,但我自己的時間很寶貴。”丟東西的乘客這樣說。
比起丟東西,刑事犯罪才是讓歐洲人自感日益不安的主要因素。Asmara來自印度尼西亞,和我曾住在同一公寓。剛來比利時的她對于生活環境非常滿意,她說這里的北非移民非常友善,還贈送給她很多肉類。但一周以后,她就問我安特衛普哪個地段的房子更安全。
“每天晚上,下課回家路上都有人尾隨我,還有人和我搭訕并且騷擾我,我感到很害怕。”她說。
比起安特衛普,布魯塞爾的情況更惡劣。2015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巴黎恐怖襲擊,參與襲擊的恐怖分子,最終在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被警方發現。而在恐怖襲擊之前,莫倫貝克區和旁邊的斯哈爾貝克,就在歐洲以高犯罪率而臭名昭著了。今天,我依然可以看到莫倫貝克的橋洞下面睡著很多難民。在這些區域,女性夜間單獨出行是十分危險的。我的一位比利時朋友曾是布魯塞爾的警察,他在目睹了接二連三的案子而領導又無動于衷后,最終心灰意冷離開了自己的崗位。
在歐洲,警察用處有限,遇到危險主要靠自救。巴黎的媽媽們教育自己的孩子:放學以后如果獨自回家,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因為在歐洲,人多的地方會有一些“正義之士”管閑事,而大城市的死胡同,往往是惡性事件的高發地。巴黎的18區到20區是傳統危險區,那里是移民聚集、街道稠密、缺少曝光度的公共活動區域。
除了盜竊和刑事犯罪,毒品走私在海關松弛的歐洲也很常見。在巴塞羅那,吸白粉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在安特衛普,一走出火車站你就能聞到濃厚的大麻味。作為亞洲人,這種風貌實在是讓我感到詫異和惶恐。我的波蘭女朋友也很震驚于我從來沒有吸過毒品。她說:“在我們歐洲,幾乎人人都或多或少服用過毒品。”
毒品走私離不開毒販子們的貢獻。據說,多年前摩洛哥黑幫曾經因利益分配問題,在安特衛普唐人街展開過激烈的槍戰。但正所謂“盜亦有道”,他們在開戰之前,通知了周圍的商戶晚上不要出門,通知了救護車何時收尸,告訴了警方何時來調查。我一位曾參加過這場巷戰的鄰居還向我“細說當年勇”。
日益嚴峻的社會治安,讓歐洲人走在街上不是那么踏實,而國際局勢的不明朗,又讓他們回到家里看完新聞又會害怕。中東局勢一緊張,歐洲街頭的行人也開始感到神經緊繃。在“愛與和平”教育中的歐洲新一代人長大后,發現世界并不如學校老師宣傳的那么美好,如今他們一部分人開始高呼“童話里都是騙人的”。
停不下來的難民潮
長期以來,北美大陸一直是歐洲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但進入2020年前后,大西洋兩岸卻見證了一股反向潮流:根據歐盟的統計,在過去十年歐盟國家接到的美國移民申請逐年遞增。
根據《經濟學人》的分析,政治撕裂導致尖銳的社會和族群矛盾,以及難以遏抑的槍支暴力事件,是美國人選擇背井離鄉重新在“舊大陸”安居的主要原因。
在這些美國人的想象中,歐洲可能是這樣一幅景象:從歐洲之都布魯塞爾的機場到國際都會巴黎的盧浮宮,人們普遍過著節奏緩慢乃至閑散的生活。人們慢悠悠地去上班,坐在太陽下品嘗午間咖啡,觀看著藝術家們在火車站前表演歌劇選段……
寧靜與祥和在很長一段時期,是歐洲社會的真實寫照,然而2004年的一聲爆炸改變了這一切。2004年馬德里發生了震驚世界的“3·11連環爆炸案”,2005年倫敦又發生“7·7爆炸案”,潘多拉魔盒被打開。法國、比利時、德國、西班牙,這些曾經安靜祥和的世外桃源,如今烏云密布。
安全失序的背后是難民問題。進入本世紀,越來越多的有著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風俗的人為了生存,選擇來到歐洲。僅僅2019年,比利時就接納了超過2000名巴勒斯坦難民。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歐盟國家的公眾民意開始扭轉。
巴黎的媽媽們教育自己的孩子:放學以后如果獨自回家,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因為在歐洲,人多的地方會有一些“正義之士”管閑事,而大城市的死胡同,往往是惡性事件的高發地。
如今,波蘭人吐槽他們的國家被烏克蘭人“占領”了;而5年前,比利時人就吐槽自己國家被摩洛哥人“占領”了;10年前,法國人開始吐槽自己國家被非洲法語國家移民“占領”了。
移民數量眾多,他們有的誠實勞動并且過著合法生活,甚至成為了國家標榜的社會融入的楷模。我們社區的門診大夫,就是當年持假護照偷渡入境被警方發現,有關部門思考再三才給他難民身份。依靠難民身份,他在比利時免費學醫,最終成為了今天的醫生。
有的人則是打黑工、靠救濟勉強活著。還有一些人來自極端組織,或者從小就接受極端主義思想的教育。參與2015年和2016年發生在法國和比利時的4場襲擊的很多恐怖分子,都是在歐洲長大的。
在默克爾擔任德國總理期間,歐盟可以說是對非法移民態度最寬容的。隨著歐洲周邊地緣局勢緊張,再加上中東族群的生育率連年跑贏歐洲本土白人,歐盟多國政府收緊難民政策、簡化難民遣返程序,也是可以理解的。
非法難民的滯留,讓歐洲社會不斷撕裂,矛盾叢生。“穆罕默德”一度是被使用最多的布魯塞爾新生兒的名字。阿富汗人、敘利亞人、土耳其人、摩洛哥人、阿爾及利亞人……有時候,布魯塞爾變成了一個小中東。我曾路過一個比利時小鎮,那里有一家人,他們家窗戶上貼著標語:要比利時,不要比利斯坦。
在“政治正確”的西歐社會,這樣的言論也只能在小鎮里展示一下了。我的室友瓦特是比利時人,他熱衷于討論時事政治。有一次,他這樣跟我說:“我們歐盟團結在一起是為了保護彼此,但如今越來越多歐盟之外的人跑到我們這里尋求庇護,他們拿歷史綁架我們,這可不是歐盟成立的初衷。我們的社會生病了。”最后他補充道:“這些話我也只敢在家里說,很多歐洲人都像我一樣,如果在外面說這樣的話,我會被看作種族歧視。”
除了難民潮,能源危機、全球疫情、經濟危機、戰爭等因素,也讓歐洲當地人的生活水平日漸下降。生活的困苦,也讓更多人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我的波蘭女友在俄烏戰爭前,可以靠工資養貓、旅游、過小康生活,如今同樣的工資只夠她交房租。在東歐,更是有一些極端組織專門針對外國人進行暴力襲擊,他們認為外國移民拿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然而,這些極端組織的行為加深了本國人對于安全的恐慌。
比起20年前、10年前乃至5年前,更多歐洲人處在冷戰結束后未有的惶恐和不安中。

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美國地緣戰略學家彼得·扎安認為,歐洲和周邊地區生育率的落差,決定了歐洲將要長期面臨難民潮的沖擊。加上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范圍內供應鏈被重塑,缺少能源資源的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會面臨通脹壓力。
難民和通脹兩重壓力疊加,讓歐盟多國的政治面貌發生改變。2022年9月,由焦爾吉婭·梅洛尼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贏得大選,梅洛尼成為意大利歷史上首任女總理。就在她執政100天里,梅洛尼的支持率維持在52%上下。直到如今,她依然是歐盟成員國里支持率最高的政府首腦。在頻頻更換總理的意大利,梅洛尼跟公眾的“蜜月期”之長,可以說鮮有。
由于一直反對過于寬容移民,被一部分西方媒體稱作“女版墨索里尼”的梅洛尼,其高企的支持率也給歐洲其他一些國家帶來啟發。進入11月,德國“三黨聯盟”政府在移民問題上擺出了跟去年競選時期完全不同的態度。在會見完各個聯邦州的州長后,總理朔爾茨表示,德國需要開始“大規模”驅逐那些無權留在德國的移民,并稱來到德國的非正常移民“已經太多了”。
“歐洲正在自殺。”他斷言,今時今日許多歐洲人到了生命終點,也許會給子孫留下一個面目全非的,甚至不能稱得上是“歐洲”的歐洲。
溫和左翼的朔爾茨這次擺出“強硬”態度,算是歐洲總體民意的一道分水嶺。
面對越境移民,長久以來歐洲人的處理方式是施以“懷柔”。他們會傾聽這些移民的訴求,給他們開設免費融入課程,讓他們免費學習語言、免費接受職業培訓,如果因為宗教信仰原因無法在規定的日期參加考試,甚至可以為他們單獨開小灶進行測試。老師也會告訴這些移民如何“占便宜”去領取各類津貼。在過去,即使對于非法移民,左翼勢力和很多民眾也會高呼要給他們生存的權利和留在歐洲發展的機會。
然而,多年來的懷柔政策并沒能有效減少惡性事件的發生。在卡塔爾世界杯舉辦期間,每當摩洛哥取得勝利,他們的移民就會走上街頭狂歡慶祝乃至打砸破壞一番。法國和摩洛哥之間的半決賽,更是給巴黎帶來了巨大的騷亂。而這些摩洛哥球迷,很多早已是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移民了。面對著“吃飯砸鍋”的問題,沉默的大多數也漸漸不再沉默,歐洲各國的右翼乃至極右政黨,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民眾支持。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高福利支出讓政府無力更多砸錢提高社會安全感,自治傳統也讓他們不想構建一個完全依賴國家力量并且追求極度安全的社會模式。英國作家道格拉斯·穆里在《歐洲的奇怪消亡》開篇寫道:“歐洲正在自殺。”他斷言,今時今日許多歐洲人到了生命終點,也許會給子孫留下一個面目全非的,甚至不能稱得上是“歐洲”的歐洲。而這個社會面貌轉變的過程,即使用歐洲的標準來看,也是漫長的。
今時今日,歐洲人還可以拿著咖啡慢悠悠去上班,但面對遙遠的未來,心中卻充滿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