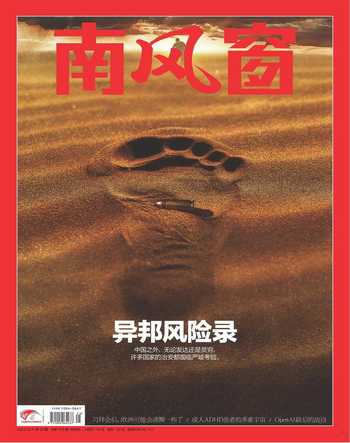APEC峰會三十載:重塑供應鏈之惑
于英紅

2023年11月中旬,舊金山上演“APEC周”,一系列高官會、部長會舉行后,便是眾所矚目的兩天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由于聚攏了亞太地區大大小小21個成員經濟體,因“地緣”而聚的特色,使得成員之間淡化政治差異,在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數字經濟、清潔能源和氣候、健康、性別平等以及反腐敗和糧食安全等廣泛的政策議題上,各抒己見。
今年峰會的三個優先事項為:互聯互通、創新和包容。盡管有人說,當下APEC的經濟合作功能正處于歷史上的暗淡時期,但從低谷往上走,不被戰爭和大國競爭這些話題帶偏,APEC峰會在走過30年風風雨雨后,仍能發揮獨到的黏合劑作用。
危機在于,經貿領域“去風險”和“脫鉤”的鼓噪,給原本就在重塑中的區域供應鏈帶來困惑。“印太”概念橫空殺出,讓原本被視為21世紀引領者的亞太地區,被提及的次數明顯減少;關于 “亞太自貿區”的憧憬,也開始讓位于CPTPP這種強調“跨太平洋”而虛化“亞洲”的伙伴關系協定。
回望過往榮光,APEC需要尋找新動能,重振該組織成立初期制定的自由開放的長期目標。僅僅是規劃更具可持續性、包容性的貿易政策,可能已經不夠了。
區域開放貿易的緣起
稍微檢索便知,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誕生于1989年,是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鮑勃·霍克促成的。但很少人知道,創設該組織的靈感,來自1980年代中期東盟發起的一系列部長級會議。
這些部長級會議,后來涵蓋東盟的6個成員(泰國、文萊、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及其6個對話伙伴(澳大利亞、日本、美國、加拿大、韓國、新西蘭)。這12個國家,也正是APEC的12個創始成員。所以,別看文萊國家小,但人家是創始成員。再有,因為東盟這層關系,APEC的秘書處是放在新加坡的。
東盟本來拿了一手好牌,但命名權卻給了澳大利亞,這就要說到霍克總理的前瞻性眼光。當時他訪問韓國,從前一年剛舉辦奧運會并在金牌榜列第四的韓國身上,看到東亞國家的銳氣,就提出“漢城倡議”,建議召開“亞洲—太平洋圈”的APEC部長級會議,首屆在堪培拉開,第二屆在新加坡開,第三屆在韓國開。這相當于澳大利亞、韓國聯手,把東盟組的局給“反客為主”了。
而今APEC有21個成員,比當初多了9個成員。其中,中國、中國臺北和香港都是在第三屆APEC部長級會議上接到擴員邀請的,算是韓國作為1991年東道主的一個明智決斷—第二年,中韓就正式建交了。
另外增加的6個成員,分別是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智利和秘魯(不包括哥倫比亞),大洋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歐洲的俄羅斯,以及東盟的越南(不包括柬埔寨、朝向印度洋的緬甸、位處內陸的老撾)。它們在1993年到1998年間陸續加入。
在APEC建立的第五個年頭(1993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誕生于美國華盛頓州,即媒體上俗稱的APEC峰會。中美領導人借此機會實現了會晤,顯示APEC峰會不僅僅具有經貿功能。
當然,APEC的初衷還是消除壁壘、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過去34年里,APEC最輝煌期還是在前半部分,也就是G20峰會(2008年金融危機后召開第一屆)還沒有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
從1989年到2021年,在營商便利化方面,APEC的工作成效卓著:不僅大幅減少貿易壁壘、消除法規差異,使得成員之間平均關稅稅率從17%下降到5.3%,還使得APEC地區的商品貿易總額增長9倍多,其中2/3以上的貿易發生在成員經濟體之間。
APEC的初衷還是消除壁壘、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過去34年里,APEC最輝煌期還是在前半部分,也就是G20峰會還沒有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在印尼爪哇名城茂物召開的APEC峰會,承諾到2020年實現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此后,各成員經濟體為實現這一目標付出了諸多努力,包括簡化海關程序、實施可預測和透明的監管措施等,也取得了可衡量的進展。
2009年的新加坡峰會是另一里程碑,推動了此后4年內將亞太地區的營商便利度提高11.3%。例如,加快了施工許可證的發放速度,便于在亞太地區創辦公司。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峰會發布了《供應鏈互聯互通框架》,計劃到2015年將各經濟體間的供應鏈在時間、成本方面的績效提高10%。根據APEC政策支持單位的評估,2009—2013年,該地區的進口商品交貨時間平均下降了25%,出貨時間下降了21%。
轉向掛靠“包容性增長”
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全球敲響了警鐘:經濟增長并不惠及所有人,很可能會將一部分人的福祉置于危險之中,最終累及所有人。于是,一邊是救銀行,一邊是反思。
這年11月中旬,此前名聲不大的G20在美國首都舉行第一次峰會,一本正經地討論救經濟。幾天后,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才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此時距離首屆APEC峰會已過去15年,貿易自由化也開始在一些國家內部暴露出問題。各成員開始認識到有必要超越GDP,讓更多的人從發展中受益,于是參考了聯合國在2000年設定的千年發展目標—可持續性的包容性增長。
為響應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APEC鼓勵提高能效和為環保產品開綠燈。如2011年,各成員承諾到2030年將該地區的能源強度降低45%;2012年海參崴峰會同意在2015年底前,將54種環保產品的關稅稅率降至5%或更低;2014年,各成員同意到2030年將該地區可再生能源的份額翻一番。
而從2015年馬尼拉峰會提出“打造包容性經濟”開始,所謂“確保所有人參與其中享受發展紅利”的包容性增長,成為APEC宣傳的高頻詞。馬尼拉峰會呼吁為中等及小微企業融入區域和全球市場制定政策;2016年利馬峰會提出“高質量增長和人類發展”,重申對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以及實現中小微企業現代化的承諾;2018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莫爾茲比港)召開的APEC峰會,則提出“把握包容性機遇,擁抱數字化未來”。
原定2019年在智利圣地亞哥舉行的APEC峰會,因當地陷入嚴重騷亂而被提前取消。該屆峰會原本強調“人、環境與包容性增長”,提出要提高婦女在經濟中的作用,制定與海洋有關的可持續發展路線圖。但這些合作動議,都隨著一場首都騷亂,而被挪到新加坡APEC秘書處降格處理。
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連續兩屆APEC峰會都以視頻形式舉行。在馬來西亞召開的峰會,提出“實現共享繁榮的未來”,希冀建設一個開放、有活力、有韌性、有包容性的亞太共同體。新西蘭還在2021年11月第二十八次非正式會議召開前,于德爾塔毒株肆虐全球的2021年7月,增開了一場臨時應對疫情的視頻特別峰會。
等到疫情進入尾聲的2022年11月,曼谷APEC峰會重申以包容和可持續的復蘇,共同應對疫情后的重建與氣候變化等環境挑戰。然后,這次舊金山峰會也把“包容”列為三個優先事項之一;明年第三次在秘魯舉行的該峰會,預計也會響應這一主題。
“包容性增長”并非包羅萬象,APEC作為主打經貿功能的組織,沒必要像聯合國那樣為窮國兜底;“包容”的核心所指,是各成員經濟體培養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及其參與全球供應鏈的能力。
多年來,亞太經合組織發起了各種各樣的中小企業發展倡議。比如,APEC中小企業創新中心2005年在韓國成立,實地開展咨詢業務;2011—2014年,APEC倡議使來自亞太地區19個經濟體的約60個生物制藥和醫療器械行業協會及其成員公司,通過并實施了道德準則;2013年,APEC啟動了創業加速器網絡,旨在將科技初創企業與資金和導師協同起來。
舊結構能否應對新挑戰?
時隔12年,APEC峰會再次回到美國。但從1993年首次領導人會晤到2011年夏威夷峰會,再到2023年舊金山峰會,APEC的基調出現不小變化。
在1993年前后,冷戰時代的劍拔弩張已經結束,全球化如箭在弦上,蓬勃發展的亞洲時代已經到來,“窮則關稅壁壘、達則貿易天下”的觀念漸入人心,互聯互通的價值成為不言自明的共識。
亞太經合組織創設之初,追尋的貿易理念是開放的區域主義。在1998年吉隆坡峰會上,參會國家在APEC確定的領域,承諾“盡早和自愿”放開貿易壁壘。彼時,亞洲剛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掙扎出來,宣布去除壁壘,無疑是一個標志性的關鍵跨越。
近年來,非關稅的限制性措施有所增加,對新型服務的限制越來越普遍,例如對跨境數據流動的限制。這些隱性的貿易壁壘,對APEC的監管實踐提出了更多挑戰。
然而,APEC設定的自由貿易目標是自愿的,不具有約束力。APEC的工作是提供說服。就在吉隆坡峰會期間,日本拒絕削減對森林和漁業部門的保護,理由是這個問題在國內非常敏感。事實上,從此時開始,盡管開放日程仍在不斷向其他領域蔓延,創始初期開放的區域合作愿景卻被靜悄悄地窄化了。特別是近年來,非關稅的限制性措施有所增加,對新型服務的限制越來越普遍,例如對跨境數據流動的限制。這些隱性的貿易壁壘,對APEC的監管實踐提出了更多挑戰。
而且,今昔對比,最大的不同是美國在APEC中的角色發生了巨大變化。30年前,華盛頓在其中發揮著主導地位,而今美國在貿易談判中的貢獻明顯不足,在區域一體化的新努力中美國主動邊緣化了,甚至在尋求建立平行的合作框架,試圖重振昔日霸權。《經濟學人》將美國有選擇性的退出總結為“它將提供更少的經濟胡蘿卜”。
喧囂一時的印太戰略,以及2015年美國主導聯合日本、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12國草簽的TPP協定,都在嘗試新路徑。TPP的開放愿景與APEC類似,希望建立類似于歐盟的以零關稅為主要特征的新的跨太平洋單一市場,但在2017年初,特朗普就任總統伊始便宣布退出TPP。
華盛頓放棄了TPP,但是壯志未泯,美國轉入一個以保護主義的產業政策為主導特征、選擇性擁抱全球化的時代。其他國家在去壁壘和走向開放的道路上,也不同程度地面臨各種適應的問題,比如在知識產權保護、數字貿易壁壘和勞工權利等領域。
在這種新的背景下,舊金山峰會提出“為所有人創造一個有韌性和可持續的未來”。就像華盛頓州和夏威夷州一樣,舊金山所在的加州也比美國中東部地區更認同“亞太”這個概念。但是,作為亞太地區歷史最為悠久的區域合作框架,APEC這一舊的架構需要進行怎樣的調整,才能應對“克服大國分道、提高組織效率”的新挑戰?
回到供應鏈問題,像越南一類的中小國家,在貿易中能發揮與其經濟體量不成比例的角色,但其供應鏈網絡仍脫離不了地緣因素。事實證明重塑亞太供應鏈不能基于陣營思維,而APEC不同于“印太經濟框架”、CPTPP等的長處就是超越陣營,從地緣出發推動貿易開放進程,即便某個階段停滯不前,但在復蘇區域經濟和推動更持久的經濟增長方面,它的韌性仍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