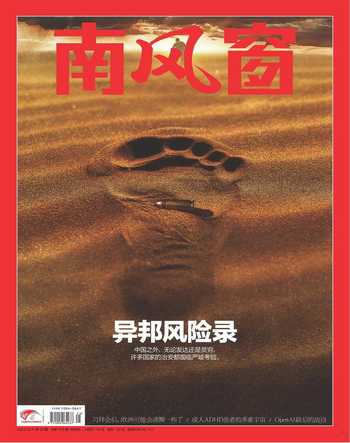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吶喊》100年,“阿Q”為自己而活
魏含聿

1923年,魯迅小說集《吶喊》出版,一個個代表彼時中國社會中典型人群的角色,躍然紙上,生動形象,堪稱民族群體畫像的寓言。
《狂人日記》中的狂人,聲嘶力竭地吶喊出“從來如此便對嗎?”是在向固有的傳統(tǒng)思想宣戰(zhàn),同時也是在試圖喚醒書中其他人物—全面展現(xiàn)舊時國民劣根性的阿Q,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潦倒代表的孔乙己,吃著人血饅頭的愚昧民眾。
整整百年后的今天,當“精神勝利法”和“吃人血饅頭”被賦予新的時代性解讀,啟蒙者般的狂人成功了嗎?面對生存困境的阿Q該何去何從?他們是否擁有更多的使命和選擇?
在今年烏鎮(zhèn)戲劇節(jié)的舞臺上,先鋒戲劇導(dǎo)演李建軍用新作《阿Q正傳》的首演,回應(yīng)了魯迅筆下經(jīng)典人物在跨越百年后具有時代性的發(fā)問。
面向當下的觀眾,李建軍版本的《阿Q正傳》從阿Q的死亡講到狂人的消逝,重構(gòu)了“精神勝利法”和“吃人血饅頭”的當代存在形式。
戲劇《阿Q正傳》的宣傳頁上印著:“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而在戲劇中,改編后的文本不停地啟發(fā)觀眾思考:今天阿Q還活著嗎?如果活著他是誰?穿越了100年的阿Q與從前有何不同?他會不會想要換一種活法?
在接受南風(fēng)窗專訪時,李建軍表示,時代主題變了,“精神勝利法”的內(nèi)涵也變了,從“荒唐的借口”變成了現(xiàn)代人的一種“安慰劑”。但無論如何,“精神勝利法”還普遍存在于當今社會,因為集體的文化基因會遺傳,所以今天的我們?nèi)匀恍枰斞浮?h3>阿Q終于“勝利”了?
從2011年的《狂人日記》,到2012年的《影喻》,再到今年的《阿Q正傳》,李建軍三度改編魯迅的作品,并將之搬上戲劇舞臺。而這一次的創(chuàng)作沖動,早在10年前就萌芽了。
2013年時,李建軍就想做《阿Q正傳》,但“改編魯迅的作品是很難的一件事”,他當時讀魯迅的作品讀得越多,心里越覺得“魯迅變成了山一樣沉重的存在”,因為讀不完。
對魯迅的闡釋要超出文學(xué)的范疇,要去讀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基于種種,李建軍暫時放下了創(chuàng)作《阿Q正傳》的念頭。
在之后的近10年里,李建軍連著做了3個西方經(jīng)典文本的改編,卡夫卡的《變形記》、法斯賓德的《世界旦夕之間》,以及俄國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
在準備今年的烏鎮(zhèn)戲劇節(jié)演出作品時,他想給自己的創(chuàng)作注入一些新鮮的話題,便計劃選一個中國的文本。“我想,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文學(xué)形象就是阿Q,再找不出第二個,所以我決定改編《阿Q正傳》。”
《阿Q正傳》發(fā)表于100多年前,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和舊中國人的麻木,可以說,阿Q滿身的缺點是時代塑造的。若非置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故事的內(nèi)容很難被完全理解。同時,阿Q這個角色在中國文學(xué)史、思想史,甚至在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中,都被賦予了太多文學(xué)之外的意義,而這些都是改編創(chuàng)作時需要面對的內(nèi)容。
“過去我們對阿Q的批判,來自魯迅對社會的批判。那時候的時代主題是生死與存亡,‘精神勝利法是負面的、消極的。但在我們活下來以后,我們就要去思考,‘精神勝利法與當下我們面對的社會問題之間有什么聯(lián)系。”李建軍對南風(fēng)窗說。
歷經(jīng)百年,我們早已步入現(xiàn)代化社會,生存危機解除了,可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影響力未減,有所變化,卻不曾消失。在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上,“精神勝利法”是熱搜詞,不少網(wǎng)友對阿Q充滿同情。我們現(xiàn)在對“精神勝利法”的批判,更多的是針對它背后的機制,例如消費主義、階層固化、底層生活壓力等。
“改編魯迅的作品是很難的一件事”,對魯迅的闡釋要超出文學(xué)的范疇,要去讀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
因此,李建軍改編創(chuàng)作的思路是:用當代話語把阿Q的故事講給今天的觀眾,去呈現(xiàn)從100年前的阿Q到今天的阿Q,有什么變化。對當下的思考使得這一版的《阿Q正傳》具有濃厚的現(xiàn)代性,也自然而然地與當今社會現(xiàn)狀形成映照關(guān)系。
改編后的文本,阿Q的故事是倒敘,小說中的結(jié)尾,成了劇目中的開頭。舞臺上的阿Q是個鬼魂,通過即時影像的藝術(shù)手法,穿越到100年前,回顧了他的前世經(jīng)歷;又通過影像片段的敘事方式,穿越到100年后,開始他在今世的生存之旅。
從當下的歷史維度與現(xiàn)實視角去理解阿Q,讓李建軍終于可以在改編的層面上“平視魯迅”—撥開壓在文本上的政治、歷史、思想的大山,褪去附在阿Q身上的角色標簽與時代符號。在戲劇的舞臺上,李建軍帶領(lǐng)阿Q穿越百年時空,在當代尋找活下去的方法,尋求更自我的意義和價值。
100年后,阿Q是誰?
1921年,小說《阿Q正傳》首發(fā)于北京《晨報副刊》上。刊發(fā)后,報社編輯陸續(xù)收到很多封讀者來信,其中不少來信認為《阿Q正傳》是在諷刺自己,甚至有人請魯迅不要那么尖銳地攻擊他們。這件趣事恰恰說明了魯迅的洞察力和阿Q的影響力。
到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駐華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采訪魯迅時問到:“阿Q的時代是否已經(jīng)過去?”魯迅聽了就笑了,說并沒有。“你看,阿Q都當上總統(tǒng)了,所以阿Q的時代并沒有過去。”
1981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將《阿Q正傳》改編成電影,影片的最后是一個講述者說,阿Q沒有斷子絕孫,阿Q的子孫有很多,到處都有。
百年后的今天,“阿Q到底是誰?”也是李建軍在做改編創(chuàng)作時最糾結(jié)的問題。在他看來,魯迅寫出這篇文章時,對當時國民的劣根性作出了批判,但這個話題在今天產(chǎn)生了偏移。“我看到網(wǎng)上人們對阿Q這個人物形象,更多地是套用底層人物的視角去理解他,也就對他多了一份認同和同情。所以我在做這個戲時,想要試著把魯迅100年前創(chuàng)作的人物拉到我們今天的生活中,并且和他做一個對話。”

對話從阿Q被槍斃后變成鬼魂開始,這一設(shè)計源于魯迅對“阿Q”的設(shè)定與解讀。
原著的序中,作者提到,因為不知道gui的讀音應(yīng)該是“阿貴”還是“阿桂”,所以用了一個Q代替。恰巧,Q也是“鬼”的諧音。后來,魯迅亦在自序中提起,他覺得自己給阿Q這樣一個并不成名的人物做傳,仿佛心里有鬼似的。
實際上,隨著阿Q這個角色逐漸符號化,他已不是某個人,而成了人們心中的“鬼”,也正因如此,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阿Q。李建軍直言,他認為自己就是阿Q。“我們都是阿Q,他還活在我們身上。他抽象而具體,既是某一個人,又是每一個人。”
李建軍導(dǎo)演的戲劇版《阿Q正傳》中有一段說唱,其中一句臺詞反響強烈:“ABCDEFG,Q的前面就是個P。”這句臺詞,是主演這部戲的青年演員們創(chuàng)作的。
李建軍導(dǎo)演的戲劇版《阿Q正傳》中有一段說唱,其中一句臺詞反響強烈:“ABCDEFG,Q的前面就是個P。”這句臺詞,是主演這部戲的青年演員們創(chuàng)作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強勁有力的魯迅式表達。阿Q得罪了人,所以活不下去了,Q的前面就是個P,這是100年前魯迅想表達的。在今天青年演員的臺詞中,這是一種更加現(xiàn)代、更加清楚的表達。”李建軍認為,在理解并重構(gòu)阿Q的故事時,就是要把自己的經(jīng)驗帶入進去,找到創(chuàng)造的原動力,這也是做藝術(shù)創(chuàng)作時最重要的核心。
阿Q在100年之后有了一些變化,阿Q要找一種別的活法,他就像一個魂,如果是作為底層、被壓迫、被侮辱的那個人、那個魂,一直活到了現(xiàn)在,那么他為什么要活著?他要打破這樣一個邏輯,尋找一種偶發(fā)。“所以必須把阿Q放到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中、對社會和歷史的閱讀中,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找到當下大家普遍關(guān)注的真問題。魯迅塑造的角色是抽象的,但如果不能轉(zhuǎn)化成一種創(chuàng)作者的解讀,便也創(chuàng)作不出任何東西來。”
除了對阿Q的當代性思考,劇中還加入了狂人吶喊的情節(jié),與阿Q形成雙故事線。這是李建軍在這個戲中隱喻時代變化的重要寄托—狂人在今天怎樣?
“在魯迅的文學(xué)系列里,《狂人日記》充滿了一種對于環(huán)境的吶喊,所以10年前的那部《狂人日記》在表演和精神內(nèi)核方面,很像是年輕人的搖滾樂,充滿了我們對當時現(xiàn)實的回應(yīng),充滿了要去改變現(xiàn)實的動能。但是今天的我們會對這種動能產(chǎn)生懷疑,我們想要的改變靠某些啟蒙者的吶喊就可以實現(xiàn)嗎?那樣一個對美好世界的想象,在今天顯得非常無力,甚至有些滑稽。”
所以,與10年前李建軍創(chuàng)作的《狂人日記》不同,這次的戲里,狂人死了,他的吶喊終成一場幻滅。“我覺得這可能就是后人對魯迅文本中提出的問題的回答或體驗,就是把一種個體經(jīng)驗放到了這個故事中。”
在這個版本的戲里,阿Q作為一個鬼魂,從100年前穿越到了現(xiàn)代,戲的結(jié)尾和開始之間就有了線索。在最后一幕里,狂人和阿Q出現(xiàn)時,狂人死掉了,變成了軀殼,總之不再是一個啟蒙者;阿Q變成了想找到自己活法的一位現(xiàn)代年輕人,基礎(chǔ)態(tài)度就是“我不跟你們玩了”。這些設(shè)定都是按照最初的人物穿越100年的歷史時空的象征性的理念去構(gòu)思的。
魯迅看了也不會失望
20世紀30年代時,一位朋友問魯迅,是否可以將《阿Q正傳》做成話劇。魯迅答應(yīng)了,但在回信中補充了一句話:其實我很擔(dān)心這個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或話劇,所剩下的只不過是滑稽。
對于戲劇創(chuàng)作來說,比藝術(shù)形式重要的是對文本內(nèi)容的表達。而在魯迅的文本里,最重要的是對中國的思考、對中國人生存的思考、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思考,以及站在東亞立場上對中國歷史的思考。這種思考,離戲劇藝術(shù)本身很遠。因此,魯迅并不主張把《阿Q正傳》改編成戲劇。
在李建軍看來,改編一部作品或者說這個作品中的一個人物,是需要創(chuàng)作者打開那些在現(xiàn)實中被隱藏起來的內(nèi)容;那些潛藏在文本下面的和現(xiàn)實對應(yīng)的內(nèi)容,是需要被創(chuàng)作者激活的。“沒有核心,沒有創(chuàng)新,就很沒意思。因為100年前魯迅就這么寫了,到現(xiàn)在還只是把小說中的人和事兒簡單地演出來,是不行的。”
看過李建軍導(dǎo)演的戲劇《阿Q正傳》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魯迅研究專家寇致銘表示,這個版本的戲劇,是在受到魯迅文本的啟發(fā)和影響后,生發(fā)出的全新的創(chuàng)作,這反而是本質(zhì)上的忠于原作,貢獻非常大。“我認為,魯迅看了都會覺得非常有意思,不會因為只剩滑稽而感到失望。”
談到李建軍的創(chuàng)新,影像在舞臺上的運用是讓人無法忽視的一點。有觀眾評價說,李建軍導(dǎo)演的戲,隨便抽出來一幀做劇照,都帶有他獨特的藝術(shù)特征。無論是演員的服化道,還是舞臺和影像的交替呈現(xiàn),都帶有他鮮明的個人創(chuàng)作標簽。
100年前魯迅就這么寫了,到現(xiàn)在還只是把小說中的人和事兒簡單地演出來,是不行的。”
傳統(tǒng)的戲劇舞臺上沒有影像,但若是應(yīng)用得當,影像會帶來很多便利。在李建軍版的《阿Q正傳》中,運用了一段在現(xiàn)代背景下錄好的影像來表現(xiàn)阿Q穿越到了當代的情節(jié)。這種影像手段,能讓觀眾更直觀地體會到了阿Q穿越的親歷感。
這部戲有兩條故事線,一條是阿Q的故事,主要是在舞臺上,另一條是狂人的故事,基本在影像里。“因為影像技術(shù)在戲劇舞臺上的普及,我們可以把關(guān)押狂人的房間封閉起來,讓狂人在房間里表演。影像技術(shù)帶來的藝術(shù)擴展,對敘述是一種便利。”
但對李建軍來說,所有敘述方式的選擇,最終都要回到如何用有效的藝術(shù)語言去講述主題和展現(xiàn)人物,如何恰當?shù)孛鎸裉斓挠^眾的基本問題上。
他認為,在一個作品中應(yīng)該展現(xiàn)一種視角,這個視角是打開經(jīng)典文本的核心,即為什么要打開這個經(jīng)典文本,然后回應(yīng)我們現(xiàn)實中的很多問題。例如,在這個版本的戲劇中,百年前的阿Q在那樣一個主流邏輯里活得很痛苦,他就用精神勝利法麻痹自己。穿越到百年后的今天,他有可能逃出這樣的邏輯從而找到一種新的活法嗎?
這是魯迅提出的問題,也是每個讀者、每個觀眾都應(yīng)該去回答這個問題,或者他們還會提出他們自己的問題。李建軍很難從他自己的角度來給觀眾答案。“所有這些是要在創(chuàng)作中一層一層打開的,很難直接講我要告訴人們一個什么答案,因為如果那個答案能夠被講出來,我想我們就不用在今天再做《阿Q正傳》了,甚至魯迅當年也不用去寫《阿Q正傳》了。”
在李建軍看來,他自己就是阿Q,還活在一個困境之中,那個答案是什么,作為創(chuàng)作者的他也不知道,又怎么會給觀眾一個確定的答案呢。“所以這個版本的戲里‘狂人這個角色的意義,更多的就是給阿Q一個答案,可是這個答案又好像是一種很虛幻的答案。”
藝術(shù)作品可能會激活觀眾對生活的一種思考,提供一種看待問題的角度,還有精神的鼓舞、情感的慰藉、人性的溫暖,但很難直接獲得答案去解決現(xiàn)實的問題,也不能指望誰在藝術(shù)作品中給出一種答案。“即便給了,我覺得都是假的。”
而李建軍的作品,不說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