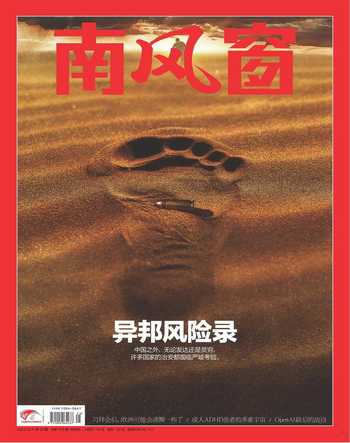長治久安,秘訣在哪里?
譚保羅

如果要列舉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國家,那么中國一定是首屈一指的。很多人均GDP高于中國的國家,甚至是西方一些高度發達的工業國,社會治安的水平也遠遠不如中國。到這些國家旅游或者商務考察,旅行者基本不敢“露富”,不敢把自己的新款手機放在顯眼處,更不敢把名牌包輕松地挎在肩上。
更夸張的是,在一些特定城區,你都不敢穿好一點的運動鞋。因為,當地年輕人癡迷于搜集某些特定品牌的運動鞋,特別是那些100美元以上的款式。然而,他們沒有工作,只有一身發達的肌肉和無處發泄的荷爾蒙。為了一雙鞋,他們可能突然對你發起襲擊。
也就是說,治安這個問題,它和社會整體經濟的發展水平并非是一種完全的對應關系。那么,治安好不好的關鍵,到底是什么?
因素有很多。從大的層面來說,國家治理的良好,特別強大的財政能力帶來對社會治安支出的慷慨投入,以及科層治理的嚴密性和社會管理的高效率,必然是社會治安良好最容易被理解的原因。
文化傳統也很重要。比如,巴西的人均GDP早已達到9000美元的水平,遠遠高于絕大多數中亞國家,然而在中亞的城市旅行,安全系數肯定要比在里約熱內盧高得多。很多中亞國家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還經歷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時代,這使得它們的社會文化傳統截然不同,也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行為模式。
從文化的角度來講,中國的治安水平全球頂尖也不難理解。比如,在中國的文化中,“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一直被視為社會安定的理想狀態,這其實代表了社會的一種價值取向。穩定和寧靜的狀態,是對社會治理狀態的評判標準,也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人們所遵循的行為準則。
國家治理和文化傳統,無疑是決定治安水平高低的關鍵因素。但這一問題也可以換個角度,從經濟的角度來解釋,畢竟大多數人的行為,最終都是靠著經濟激勵,而收益和成本的權衡則是最現實的心理約束。
窮人和通脹
不少人對國外一些地方治安較差的印象,多半來自三個途徑:一是傳媒,二是出國旅行的感同身受,另外一個則是影視作品的影響。
通過這些途徑獲取的印象,可能會讓人對社會治安水平較差的原因形成理解偏差。比如,某些國家雖然科技和經濟高度發達,但貧富差距大,社會治理失敗,政客只關心選票,而根本不關心非票倉地帶的治安問題;或者,在旅游景點的“犯罪分子”都是外來移民,其他地方還好。
影視作品帶來的理解偏差更需要糾正。“黑幫火并”和“打劫銀行”是影視作品中最常見的兩種名場面。為了增加可看性,這樣的場面被設計得極其火爆,參與者都一表人才,有的還是科技怪杰或者退役特工。總之,情節設計得讓人印象深刻,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很多人對國外治安問題的理解。它讓人誤以為,治安問題的表征充滿了極端現象。
貨幣快速而劇烈的貶值,會讓很多人無法安排明天的生活,當生活資料的獲取失去了可掌控性和可預期性,那么實施“超短期行為”—搶劫或盜竊就具有了吸引力。
實際上,在一些國家最常見的治安問題,并不是“打劫銀行”那種極端事件,而是一些看似日常的行為,比如搶劫或者行竊。換句話說,這些行為并不是要挑戰現任政府權威,或者通過非法手段實現一夜暴富,而不過是一位青壯年要維持日常基本物質生活所致。讓人鋌而走險,通脹可能難辭其咎。
在國外一些地區,窮人的身份意味著他們沒有抵抗通脹的資產,比如房產、優質的債券和股票,以及家里存放著的美元和黃金。窮人不但沒有好的資產,可能都沒有穩定的工作,即使有臨時性的體力工作,老板也并不會根據通脹指數進行定期漲薪,這意味著他們對物價變化的敏感程度超乎想象。
巴西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從 1980年代開始,巴西的里約熱內盧貧民窟成為了“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槍戰、販毒、搶劫每天都在發生。如果衣著華麗,尤其是帶著高端相機希望拍照的外國游客,一定要到此一游的話,那么必須在警察的陪同下才敢深入這些充滿暴力和毒品的地帶。
里約熱內盧貧民窟的故事被全世界知曉,但很少有人注意,貧民窟治安的惡化和巴西的通脹大爆發,在時間上是高度重合的。1981年開始,巴西爆發了史上最嚴重的通脹。
1981年,由于債務危機爆發,巴西的GDP增速從接近10%,降到了負數,即經濟出現了負增長。與此同時,國內通貨膨脹率開始飆升,整個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都是巴西的高通脹時代。這一時期,每年的通脹率經常高達1000%以上,這意味著如果薪酬提升不和通脹率掛鉤,那么很多白領的物質生活保障都成問題,更不要說貧民窟的底層家庭。
另一個因為治安問題而被人熟知的地帶是非洲。非洲一些國家被全球的經濟學家視為主權貨幣失敗的典型,比如,津巴布韋就以超級通脹聞名。實際上,如果仔細觀察,很容易發現但凡那些治安較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多半都有嚴重的通脹問題,窮人往往朝不保夕。
在非洲投資的一些企業家發現一個有趣的觀察:一些地方的經濟活動如果放棄當地的主權貨幣,在交易中使用歐元、美元或者人民幣計價和結算,那么當地的經濟往往發展更好,普通人的生活也更穩定。因為,這些強勢的國際性貨幣不會導致嚴重通脹,會讓企業家和普通人對手中現金的價值,以及對未來生產生活都有明確的預期。
通脹對窮人的殺傷力是驚人的。從常識來說,貨幣快速而劇烈的貶值,會讓很多人無法安排明天的生活,當生活資料的獲取失去了可掌控性和可預期性,那么實施“超短期行為”—搶劫或盜竊就具有了吸引力。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這種行為也并不算是某些人在高通脹之下的最壞選擇。于是,治安問題便擁有了一種社會心理結構上的內生機制。
對任何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來說,治理通脹都是一個難題。一方面,要發展就容易經濟過熱,當需求增加超過了供給,那么通脹就上來了。但一個成功的例子是中國。中國的高速發展,并沒有伴隨長期的高通脹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那么,中國的秘訣在哪里?
城市化和工業化
近年來,中國的通脹率長期保持在低于3%的這一合理水平。合理的通脹,意味著適度的產品和服務價格上漲會推動企業家擴大再生產,而消費者或者說工薪一族,也可以理性地預測自己的財務前景。
但不能忽略,在1980年代末期,中國也出現過比較突出的通脹問題,最嚴重的時候,通脹率超過了20%。雖然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高通脹相比,這一水平并不算高,但也對當時企業和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了不小影響,也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擴大開放,通脹率降了下來。
縱貫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通脹,給中國的經濟治理帶來了一些教訓,也是經驗。之后,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和金融監管部門一直都將CPI視為極為重要的指標,時刻保持緊盯這一數據。某種意義上講,必須將通脹控制在合理范圍,早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金融紀律。
一般而言,當通脹率超過5%,那么消費者在購買生活必需品的過程中,就會出現明顯的現金貶值“痛感”。這也是很多后發經濟體因為無法控制通脹,給國民生活帶來嚴重沖擊,進而給社會治安帶來困擾的原因。在這方面,中國無疑值得很多后發國家參考。
實事求是地說,除了房子這種特殊“商品”之外,如果拉長時間到改革開放的40多年來看,中國人的收入增速是高于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增速的。這一點,從普通人的肉類、奶制品攝入量一直在增長,就可以得到印證。
那么,中國是如何解決通脹問題的呢?這必須和影響社會治安水平的另一因素—城市化,結合起來分析才行。
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平衡,帶來城市就業崗位的增速大大低于人口集聚的速度,必然導致地理空間上犯罪行為的易生性和集聚性。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基本上所有以黑幫和犯罪組織為題材的影視作品,發生地多半都是位于城市的特定區域,比如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貧民窟,還有就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特定街區,比如紐約意大利裔集中的地方。簡單來說,就是居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很多都沒有就業機會,要么游手好閑,要么做起了影響治安的那些行當。
換句話說,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平衡,帶來城市就業崗位的增速大大低于人口集聚的速度,必然導致地理空間上犯罪行為的易生性和集聚性。一些數據讓人吃驚。比如,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了85%,而早在1990年,巴西的這個數字就已經是70%,達到了發達國家水準。在非洲,很多國家的城市化水平也超過了中國(2022年我國城鎮化率為65.22%)。比如,利比亞城市化率是80%,而南非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國家,也達到了68%。
城市化率的計算,以城市常住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比為基準,并不體現居住質量,更不體現背后的就業質量。因此,在很多特定情形下,這個數據可能并非一個正向的指標。
2022年,我國的工業增加值突破40萬億元大關,占GDP比重達33.2%。而拉美和一些非洲國家,盡管其城市化率高于中國,但這一指標卻遠遠低于我國。比如,巴西近年就穩定在20%的水平,并且還出現了下行趨勢。
城市化必須和工業化同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治安問題。除了日本等少數對農業實行貿易保護的國家和經濟體,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地方,作為一個規模報酬遞減的行業,農業都是收入最低的行業。因此,一旦人口流動管制解除,農業人口就有天然的進城訴求。無論拉美、非洲,還是東亞,都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通過工業發展來創造就業機會,讓進城人口得到足夠就業機會,讓更多的人放棄“超短期行為”,而是選擇“長期行為”,通過計酬的正當工作來改善人生和家庭。
如果城市化大大超前于工業化,再疊加金融治理失誤帶來的通脹,那么治安問題就是一種無法根治的病。經濟治理的邏輯十分簡單,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這片土地所發生的奇跡,并不只是經濟意義上的成功,同時,也是社會治理領域的非凡事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間通道中,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成功破解通脹難題,最終實現了社會的長治久安。這無疑為很多后發經濟體提供了極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