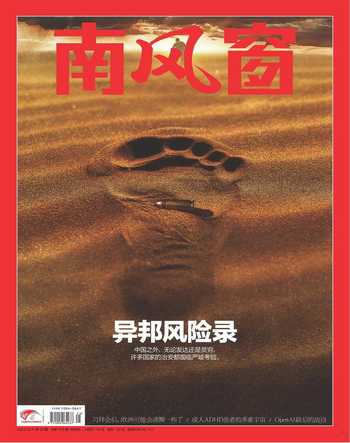州長憑什么限制迪士尼
近年來,嚴肅出版物長篇累牘地哀嘆、慶祝或冷靜分析新自由主義的消亡。你可能認為潮流已經逆轉,“自由市場”福音的社會民主主義替代方案,已經獲得了足夠的知識和立法基礎,成為傳統智慧。
當然,左派似乎已經贏得了意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說的“陣地戰”,即通過“常識”的語言改變世界的體驗方式,從而改變政治現實。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黑人的命也是命、#MeToo、伯尼·桑德斯、“大辭職”、產業政策的復興,以及新工會主義,確實改變了美國人對市場作用的看法。
同樣,在新冠大流行期間,不平等問題以收入再分配的形式找到了答案,而關于就業和教育的新觀念,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主流思維。在過去的十年里,破碎的醫療保健系統和勞動力市場,使得全民醫保和巨額基礎設施政府支出或綠色新政,成為絕大多數美國人眼中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最高法院對生殖權利的攻擊、州級監管之手,以及公民身份范圍,產生了意識形態反彈,使“進步主義”重新煥發活力,挽救了民主黨在州一級的地位。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證實,年輕選民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嘗試生計和生活兩不誤時,并沒有倒向右派:工會和社會主義從未如此受歡迎,即使在傳說中的1930年代也要相形見絀。
總而言之,這些意識形態趨勢(至少我們可以通過民意調查和投票來衡量它們),既解釋了右翼對美國社會主義顯然降臨的歇斯底里言論,也解釋了《經濟學人》對自由市場即將消亡的清醒反思。我們似乎確實處于徹底變革的邊緣。
但是,如果左翼贏得了陣地戰,那么“機動戰”—爭奪國家機器控制權的競爭—不會像“自由市場”思想那樣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相反,保守的、公開反動的社會運動—大多是出于恢復父權制的愿望,并且非常清楚他們正在背水一戰—利用他們獲得國家權力的機會來控制公眾輿論。
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利用州立法機關,對文化產業領域的私營公司(位于佛州中部奧蘭多市的主題游樂公園“迪士尼世界”)和公共部門進行正面攻擊,只是這種做法中最令人震驚的例子。在其他地方,“選區劃分”和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求立法將“保守”政策推廣到多數統治、司法裁決或行政否決權的范圍之外,已被證明足以完成少數人統治的任務。
如果民主信條從來都不是新自由主義者所關心的,我們就不能指望這一信條的不守規矩的后代會害怕或羞于以少數人的名義進行統治。新自由主義大廈的右翼建筑師,總是將美國對自由和平等的傳統承諾視為矛盾。對他們來說,自由是契約的自由,它以自由市場為前提,任何以機會平等的名義規范市場的企圖都是對契約自由的威脅,必須予以反對或禁止。
因此,利用國家權力來規范最私人的企業—比如在監督女性身體或決定宗教信仰方面—并不能用來證明以新自由主義論點武裝起來的右翼立法者 “虛偽”。他們竭盡全力限制平等獲得選票和阻止工會化,也不能作為這種證據。我們中間派的新自由主義者知道,市場從來都不是自由的,美式民主總是受制于某些人,他們通過將私有財產保護列為法律最高優先事項,來創造、鞏固和管理民主。
在美國,財產權一直優先于人的權利,盡管開國元勛們在設計一個長青的共和國時,努力平衡財產權的影響。這就是為什么罷工可以通過向法官請愿來禁止,但資本外逃卻不能:前者威脅到法律現在指定的財產價值,而后者則沒有。
詹姆斯·利文斯通是美國羅格斯大歷史學教授,著有六本書,包括《聯邦儲備系統的起源》和即將出版的《思想地震:實用主義如何改變世界》。本文已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