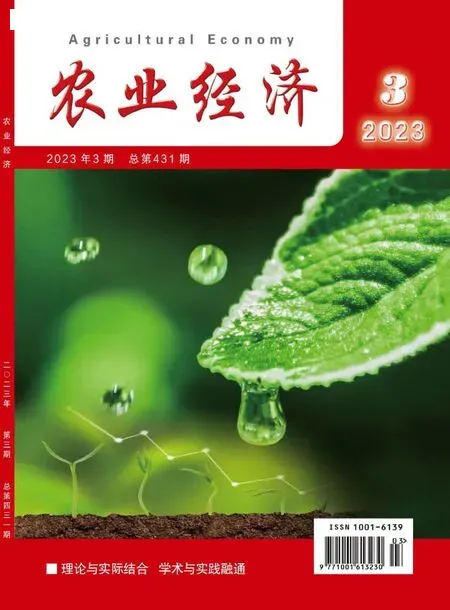差別化農業生產的成因、應對及省思
◎王舵
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農戶的農業生產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然經濟成分,除了進行市場交換也具有自給自足屬性,這就決定了農戶兼具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作為生產者,農戶勢必會爭取利益的最大化;作為消費者,農戶要確保自身的食品安全。如此一來,導致了農戶生產行為的差別化,為了提高農作物的產量,他們存在著過度使用農藥、化肥(甚至包括禁用農藥和抗生素等)的動機。同時,以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另起爐灶”,生產供自己、家人和朋友等食用的農產品。人類生存的基本前提是食物的攝取,即使消費者意識到食品安全問題的嚴重性,最終也只能選擇被動消費,許多化學投入品無法輕易發現也不易徹底清洗,最終在不知不覺之中被消費者內化,引發農產品交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檸檬市場效應。
一、差別化農業生產的成因
(一)生產者的“多元理性”。在現有的食品交換體系中,農戶的生產行為對食品質量的高低具有先導性影響。由于生產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農戶缺乏議價能力,只能依靠產量增加來獲取經濟收益,兼之食品交換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農戶大多會依據經濟理性原則,傾向于選擇以資本替代勞動力的工業化農業,而對這種生產模式所帶來的負外部性則考慮甚少,大量施用化肥造成農作物中硝酸鹽含量的嚴重超標、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死亡,造成了食品污染和環境退化等,嚴重威脅到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如此一來,農戶形成了事實上的“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加劇了食品安全領域“飛去來器”效應。面對食品安全威脅,在生存理性主導下大多數農戶首先考慮的是為家庭成員提供安全的食物,根據家計原則以及親緣互惠原則,選擇小部分農田用于家庭內部生產,并在種子選擇、田間管理和采摘存儲等諸多環節,以遠高于經濟理性的標準進行投入。同時,農戶在鄉村熟人社會中也體現出一定的社會理性,如果自家生產的安全農產品有富余,則會在鄰里之間相互饋贈。
(二)消費者的觀念失當。在經濟全球化、市場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一味追求“物美價廉”會存在一定的誤區。任正非曾經說過,物美價廉的東西靠不住。產品質量與生產成本是相輔相成的,“便宜”和“優質”類似于魚和熊掌之間的關系不可兼得。而很多消費者是以農產品的“賣相”作為決策依據,這就向農戶傳遞了一個錯誤的信號,導致農戶使用相應的化學投入品以確保“賣相好”,近些年來在海產品、蔬菜和菌類中檢測出甲醛(俗稱“福爾馬林”)的新聞報道屢見不鮮,究其原因在于經甲醛浸泡過的農產品外觀漂亮、色澤艷麗,而甲醛作為一種無色的強刺激性氣體,早已被世界衛生組織確認為致癌和致畸性物質,是公認的變態反應源和強致突變物。
二、差別化農業生產的應對
(一)提升農戶安全生產的積極性。確保化學投入品使用量的零增長是我國農業發展的長期國策,而目標的達成關鍵在于提升農戶進行安全生產的積極性。誠然,在農產品市場信息不完全對稱的大背景下,差別化生產是農戶權衡經濟收益和人際關系之后的一種“理性”選擇,不過這種農業生產機制并不能保證所有家庭成員的食品安全,無法實現“集體共保”,因為有很多家庭成員外出務工、遠嫁他鄉或異地就學等,他們消費的大多是市場上銷售的而非自家出產的農產品。此外,受資源條件和環境條件的影響,農戶不可能對其所需的蔬菜、水果、肉、禽、蛋和奶等均進行差別化生產,有些生活必需品需要進行市場采購,這也意味著農戶自身也面臨著食品安全威脅。因此,農戶向市場提供安全農產品責無旁貸,片面追求自我保護只能使全社會陷入更加嚴峻的食品安全危機。同時,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非農就業數量的不斷增多,意味著農村經濟的發展面臨著“劉易斯拐點”,更多農戶追求的是家庭收益的最大化而非農業收入的最大化,如此一來采取粗放式的農業經營策略也就變得順理成章,因而政府應為農戶的安全生產提供補貼資金和生物農藥等,以充分發揮政策規制在低采用概率新技術上的促進作用,確保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二)降低消費者逆向選擇行為出現的概率。消費者也需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應將消費者責任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從法律層面規范其消費行為,促其成為有道德的、負責任的消費者,使其清楚一味追求“質優價廉”不利于“劣幣驅逐良幣”問題的解決。因此,政府應積極引導消費者樹立理性的消費觀念,為優質農產品支付與其價值相匹配的市場價格,以激發農戶從事生態種養的積極性,促進農產品安全生產模式的社會化。同時,在傳統的農產品供應鏈體系中,消費者對生產環節、流通環節及加工環節等缺乏深入的了解,即使在產品包裝上注明了產地信息并附有檢測機構的相關證明,但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消費者仍然會對其心存疑慮,這是消費者逆向選擇行為出現的根本原因,而構建替代性食物體系可以有效化解橫亙在農戶和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危機。目前,替代性食物體系以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和短鏈農業為主,且在供應渠道上有所創新,如社區支持農業、農夫市集、共同購買、巢狀市場、社區菜園、“從農場到校園”項目等新型渠道的拓展,有助于解決農戶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在產消對接過程中消弭誤解,供需之間由基于算計的博弈走向基于信任的合作,且壓縮了參與利益分配的其他環節,使利益回歸小農戶,進而由個體自保走向社會共保,消費者也實現了從“外人”到“自家人”的轉變。
(三)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加大政府監管力度是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重要前提,當前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看似涵蓋了從生產到銷售等諸多環節,但實際上存在一定的盲區,如運輸和存儲這兩個環節就難以細分。同時,監管針對的主要是不合格農產品,監管措施以查處市場上的不合格農產品為主,這種監管手段的被動性、盲目性和滯后性明顯,而預見性、預防性則有所欠缺,事中的管控和事后的危機處理誠然重要,不過事前預防更為關鍵,“亡羊補牢”模式不適合對農產品質量安全進行長期的、有效的監管。因此,要構建長效的、科學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預防為主、防控結合,并將其貫穿于農產品的產前、產中和產后全過程。具體而言,一是加強基層檢測隊伍建設。錄用檢測人員時應嚴格把關,并不定期地開展業務培訓與技能測試,以優化檢測人員的知識結構,保證檢測技術的先進性和成熟性,且制訂科學的獎懲機制,依據相關的法律制度對瀆職失職的檢測人員依法問責;二是統籌整合職能部門。從生產到銷售涉及多個政府管理部門,這種環節化管理模式很容易出現職權交叉問題并造成“權威碎片化”,因而應對這些職能部門進行統籌整合,以實現農產品安全檢測的一體化,實現監管資源的科學配置和有效利用。
三、對差別化農業生產研究的省思
有些學者將農戶的自留地(包括庭院種植在內)也納入差別化農業生產的研究范疇,本文認為這不太符合自留地的功能定位,因為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絕大多數農戶只是認為這既方便又劃算,并未在潛意識里將其與食品安全相關聯。因此,將沒有或較少使用化學投入品的自留地作為判斷農戶進行差別化農業生產的關鍵依據在邏輯上難以自洽,因為這種研究模式的前提,是將農戶滿足“自給自足”需要的自留地納入統一的市場環境當中進行審視。當前,自留地仍是農戶獲取必需農產品的生產資料,能夠一定程度上滿足農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自留地的存在不應定位為農戶的“個體自保”,也就是說自留地主要是為了滿足農副產品特別是蔬菜的供應,基于種養結合的傳統農作方式,人畜糞便等可以為自留地供給足夠的肥料,且自留地靠近村莊的空間布局便于農戶的高頻次采摘,也使得農戶能夠發現病蟲害并及時予以清除。因此,以自留地來保障食品安全只是一種“意外”,而非農戶的主動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