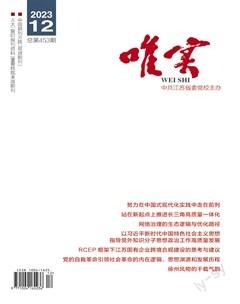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的理論探頤及其當代啟示
顏苗苗
面對19世紀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恩格斯從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實踐出發,以宏大的世界歷史視野審視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高屋建瓴地預測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形成并發展了世界歷史觀。恩格斯的世界歷史觀雖受馬克思影響較大,但仍有其獨特的思想成果。通過分析《共產主義原理》(以下簡稱《原理》)文本中的世界歷史思想,探討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的主要內容、基本特點及現實意義,有助于樹立正確的世界歷史觀,辯證審視世界歷史發展大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為解決國內發展問題和國際發展難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一、批判與革新:恩格斯早期
世界史觀誕生的客觀必然性
16世紀以來,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推動下,人類文明逐步由封閉走向開放,由民族的、區域的逐步走向世界一體化。恩格斯的早期世界歷史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開辟翻開了世界歷史新篇章,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不可調和成為世界歷史的發展推力,生產力發展潮流不可逆性成為世界歷史的發展動力,人的全面發展是世界歷史的發展途徑,共產主義社會是世界歷史的未來走向。
世界歷史翻開新篇章: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開辟。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的形成,也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密切相關。16世紀尤其是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歷史出現前所未有的急劇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打破了民族和區域的封閉狀態,促使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從而推動了生產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重大變革。其一,生產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在生產領域,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工廠制度代替了手工作坊,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模式使社會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同時,資產階級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使生產交往具有了開放性與世界性。在這種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隨著世界市場的建立而向全球擴展。其二,資本主義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資產階級開始謀求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于是“資產階級都取得了政治權力,并擠掉了以前的統治階級——貴族、行會師傅和代表他們的專制王朝”[1]。建立在高度發達社會生產力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創建了一套較封建制度更為先進的上層建筑體系,有效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面具有重要歷史貢獻。其三,世界歷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大工業使世界文明趨向一體,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實現了“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和“交通的極其便利”,迫使一切不想滅亡的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參與到文明中去。[1]資產階級迫使世界各民族采用他們的生產方式、接受他們的文明,并通過商業貿易和殖民擴張開拓國際市場,使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占據統治地位。由此造成的直接結果是,“使未開化或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1]。從這個意義上講,整個世界由此進入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時代。
世界歷史的發展推力: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可調和。作為取代落后封建制度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在建立初期體現出巨大優越性,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1]。一方面,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及其自由競爭模式,既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又為社會化大生產和科學技術廣泛應用開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建立在高度發達社會生產力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在法律和意識形態等領域也有一定建樹。資本主義制度盡管有其積極、進步和文明的一面,但也有消極、落后和野蠻的一面。恩格斯指出,大資本家階級在“所有文明國家里現在已經幾乎獨占了一切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1],而無產者為換得生活資料不得不屈從于資產者提出的苛刻條件,甚至他們連農奴都不如。“農奴生活有保障,無產者生活無保障”[1]。資本主義制度不僅造成了無產階級的物質貧困,更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其精神貧瘠。在對無產階級貧困化進行論述的基礎上,《原理》對產業革命及其危機進行中觀分析。恩格斯認為,“競爭和個人經營工業生產已經變成大工業的枷鎖,大工業必須粉碎它”,由商業危機導致的雜沓局面,“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將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1],這些弊病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制度走向滅亡。恩格斯在《原理》中對現實世界進行了深刻批判,并將矛頭直指資本主義私有制制度。他指出,“可以把所有這些弊病完全歸咎于已經不適應當前情況的社會制度”,而消除這些貧困和災難,可建立新社會制度的辦法來徹底鏟除。[1]無產者只有“通過消滅競爭、私有制和一切階級差別才能獲得解放”[1],只有共產主義革命才能真正同傳統所有制關系進行最徹底的決裂,即同以往的一切私有制生產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世界歷史的發展途徑: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價值目標,也是實現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重要途徑。恩格斯指出:“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將創造出這種人來。”[1]這表明,作為衡量社會歷史發展尺度的生產力的發展與人的發展有著內在聯系,人的不斷發展是推動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途徑。其一,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人的發展。恩格斯指出,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1]可見,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在這一條件下,人必須全面發展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從而推動人由“單一”向“更全面”轉變。其二,人的發展離不開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的大工業生產,導致了社會分工的明確化、固定化,“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1],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在物質層面、行為層面乃至精神層面的發展受到束縛。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部分人逐漸被“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所取代,這在客觀上能夠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既表現為生產的新發展需要更加“全面發展的人”的參與,又表現為生產力的發展為實現人的發展而創造出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條件。
世界歷史的未來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世界歷史與共產主義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共產主義必須在世界歷史范疇上才能實現。世界歷史的發展為共產主義的實現提供物質基礎、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沒有世界歷史的發展便不會有共產主義的實現。同時,共產主義只有在世界歷史層面才有可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1]因此,共產主義必然是世界歷史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世界歷史的未來走向是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推動人類社會由歷史轉向世界歷史,但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其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盡管資本主義開啟了世界歷史新篇章,但世界歷史的邏輯走向卻是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世界歷史的真正發展也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有通過共產主義革命,歷史才能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只有共產主義革命才能使單個人“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1]。因此,世界歷史與共產主義是相輔而行的,共產主義須依靠世界歷史才能勝利,世界歷史的未來圖景也必然是共產主義。
二、設想與建構:恩格斯早期世界史觀的基本特征
任何一種思想的形成都是循序漸進的,恩格斯世界歷史觀的形成也是如此。隨著客觀世界的不斷變化,恩格斯的思想認知不斷走向成熟。盡管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尚未成熟,但作為恩格斯世界歷史觀成熟道路上的“鋪路石”,其早期世界歷史觀的地位不容忽視,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統一。任何一種有價值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都不是憑空產生的,離不開人類思想文明發展中的優秀成果,也離不開特定的時代背景。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既是對前人優秀成果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其所處政治、經濟環境的實踐總結。一方面,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具有自成一派的理論體系,是對近代歐洲哲學、歷史、經濟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選擇性繼承和發展,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早期共產主義思想對其產生了深遠影響。19世紀初,面對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們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深刻揭露與批判,并對未來社會進行設想和描繪,這為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提供了思想來源。馬克思作為親密戰友,對恩格斯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嘗試用經濟學相關理論論述未來社會形態,第一次系統闡述了共產主義理論;《德意志意識形態》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歷史任務,為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奠定了初步的理論基礎。可以說,這些思想是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形成的重要理論來源。另一方面,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具有植根于理論的實踐基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根本特征在于實踐性,實踐性貫穿世界歷史發展始終。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在充分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結合19世紀的政治、經濟環境進行現實考量和實踐探尋,再一次論證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推力,強調人的不斷發展是世界歷史的發展途徑,論證了資本主義被共產主義所替代的必然性,論證了共產主義革命的階段性,描繪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大致輪廓。可以說,恩格斯世界歷史觀的形成體現了理論性和實踐性的高度統一,并對共產主義運動具有指導意義。當然,這些理論只是階段性思想成果,恩格斯并未停滯不前,而是在實踐發展中推動世界歷史理論日臻完善,以期更好地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長期性與斗爭性相統一。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進程,恩格斯在《原理》中闡明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從以農業為中心的中世紀到手工業發展鼎盛的17—18世紀,再到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19世紀,人類文明逐步由封閉走向開放,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擴張,社會進步和世界整體化趨勢日益顯著。這既肯定了資本主義對世界歷史的推動作用,又充分證明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進程。同時,恩格斯還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指出資產階級社會制度對無產者的壓迫是無產階級斗爭的根本原因。要擺脫壓迫和剝削、破除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發展桎梏,斗爭是唯一的選擇和途徑;只要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存在,無產階級的斗爭就不會停止,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將私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1]。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要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原理》較為具體地列出了12項廢除私有制的主要措施,為實現共產主義提供了方法和依據。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私有制會隨著國家對資本、生產以及交換的集中而以一種最穩妥的方式自行走向消亡。這也表明,恩格斯在早期就已深刻認識到,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必然是一個長期且充滿斗爭性的歷史進程。
民族性與世界性相統一。世界歷史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突破地域和文化限制,由原始、孤立、分散的歷史發展為相互交流融合、普遍聯系的歷史。恩格斯在《原理》中闡述民族問題時指出,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按照公有原則結合起來的各個民族的民族特點,由于這種結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從而也就自行消失”[2]。恩格斯不僅指出了民族消亡的時間、前提、途徑和特征,即民族消亡的時間在共產主義階段,前提是廢除民族剝削壓迫制度,途徑是通過民族融合而消亡,民族消亡是一個自然、自覺的進化歷程而非通過人為因素去消除民族特征、民族差別來實現,而且指出了世界歷史與民族特性間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辯證關系。一方面,世界歷史離不開民族特性,世界歷史的世界性是融合各民族特性的集合體。民族特性既是世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重要因素。即使到了共產主義階段,民族實現自然消亡,世界共同體依舊是各民族個體的集合體,共同的世界性離不開各民族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民族特性只有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才能獲得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和影響范圍。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進程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脫離世界而單獨存在,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民族特性,從而使其包含和體現某些世界性的因素,為民族跨越式發展和民族性的延續提供現實可能。因此,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認為,世界歷史既有民族性也有世界性,是民族性與世界性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雙向互動,具有民族性與世界性相統一的特征。
三、實踐與啟示:恩格斯早期世界史觀的當代價值
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盡管有其時代局限性,但在新時代仍具有深刻預見性,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辯證客觀地闡發和運用恩格斯早期世界歷史觀,用以指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探索國內發展問題和解決國際發展難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重視“人”的作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世界歷史發展的本質特征是人的發展。恩格斯的世界歷史觀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并將人的發展與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聯系起來。其一,關注“人”的生存境遇。恩格斯十分重視“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并對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受壓迫、受剝削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報以同情和擔憂。他指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下,不僅勞動時間逐漸增多,獨立性也逐漸被資本家所剝奪,就業形勢也不容樂觀;除來自同伴間的競爭與排斥,還受到機器的壓制與威脅。同時,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肆虐,使無產階級經常陷入極度貧困狀態。其二,肯定“人”的價值。一方面,肯定人的自在存在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這表明“人”的存在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沒有“人”就沒有人類社會,更沒有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歷程。肯定“人”的存在價值,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最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肯定“人”的歷史存在價值。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恩格斯看到并肯定了“人”對世界歷史轉變的推動作用。“人”創造了社會物質財富,如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發展離不開工人的勞動;“人”創造了社會精神財富,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勞動實踐是精神財富形成的源泉;“人”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如奴隸可以通過廢除奴隸制獲得解放,無產階級可以通過消滅競爭、私有制和一切階級差別等以獲得解放。
對當下而言,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關注人民群眾的生存境遇,重視人民群眾的社會價值,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強調“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唯一選擇就是為人民群眾做好事,為人民群眾幸福生活拼搏、奉獻、服務”[3],為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不懈奮斗。
發展先進生產力:堅持改革開放。世界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是一個客觀、必然的歷史進程,其中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其一,生產力的發展是廢除私有制的必要手段。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產生了空前大規模的資本和生產力,并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這些生產力的手段”[1];資本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裂縫加深,“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私有制和資產者遠遠不能駕馭的程度,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蕩”[1]。因此,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必須加快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其二,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要前提。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實現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必須重視生產力的高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其三,生產力的發展是全球化的根本動力,也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核心推力。恩格斯較早意識到生產力發展對全球化的重要作用,他立足資本主義發展實際,從歷史發展和全球視野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進行考察,頗具先見性地從經濟、文化等方面論及全球化問題。
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正加速重構與演變,全球化的發展方式和形勢也有了深刻變化,大力發展先進生產力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立足時代方位和現實坐標提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抉擇。新的歷史階段,必須堅定歷史自信、把握歷史主動,既要科學研判形勢打響改革攻堅戰,又要與時俱進實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在改革創新、開放合作中不斷增強發展動力活力,為實現民族復興偉業添磚加瓦。
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文明交流互鑒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與文明交流互鑒貢獻了中國方案。對于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等問題,恩格斯在《原理》中作了相關闡述。其一,文明多樣性是世界歷史發展趨勢,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是世界歷史進步的必然要求。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世界市場的建立推動著世界歷史的加速演變,各民族、國家間的交往范圍不斷拓展,“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系起來”[1]。恩格斯既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特征,肯定了各種文明樣態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又極大肯定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建立對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積極作用,認為世界市場的建立與發展“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1]。其二,和諧交往范式是世界歷史進步的必然選擇,也是構建和諧國際關系的必由之路。在恩格斯看來,和諧交往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生成和發展的動態過程,其表現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消解現實沖突為主的和諧交往范式。通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人與集體、人與社會、人與國家、國家與國家間的不和諧現實,表明現實社會對和諧的需求與渴望,同時論證了只有通過變革資本主義社會才能構建和諧的共產主義社會。另一種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物質支撐的和諧交往范式。在恩格斯看來,世界是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特別是生產力的發展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恩格斯看到了生產力發展與交往形式間的關聯,指出生產力在國際范圍內的發展帶動了各民族、國家間交往形態的轉變,“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后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1]。
和諧世界的構建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愿,但和諧世界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各國需要同舟共濟,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在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中積極構建和諧的國際交往關系,把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共產黨人基于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發展理論,理性分析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問題、全球性治理難題等問題作出的現實選擇,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繼承、創新和發展,是黨帶領人民運用中國智慧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這一理念推動了世界歷史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對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無疑具有重大歷史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本文系連云港市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媒介融合視域下統戰宣傳工作體制機制創新研究”(23LKT018)、江蘇海洋大學重點項目“中國式現代化話語建構的‘道與‘術”(ESD20231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蘇海洋大學副教授)
責任編輯:劉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