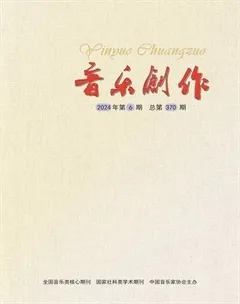“二維奏鳴曲式”與勛伯格《第一弦樂四重奏》







摘要:勛伯格《第一弦樂四重奏》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作品在結構上融合了奏鳴曲式和奏鳴套曲的特征,成為“二維奏鳴曲式”的典型例證。本文闡述了二維奏鳴曲式的內涵,并通過對勛伯格《第一弦樂四重奏》的結構分析,揭示了這一理論在該作品中的具體應用。
關鍵詞:二維奏鳴曲式;勛伯格;《第一弦樂四重奏》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大型器樂作品中呈現出在單樂章奏鳴曲式中結合多樂章奏鳴套曲的特征,西方理論家對這類作品的分析研究取得諸多重要研究成果。阿爾多夫·伯恩哈德·馬克斯和胡戈·里曼都提出奏鳴套曲的核心由“第一樂章、內部樂章和終曲”這三個樂章構成,并認為這種三樂章的奏鳴套曲與單樂章奏鳴曲式的呈示部、展開部和再現部之間存在相似性。威廉·S·紐曼提出“雙功能曲式(double-function form)”的理論主張,即這種作品中的所有曲式單元都具有曲式和套曲的雙重功能,且奏鳴曲式的各部分與奏鳴套曲的各樂章完全重合。詹姆斯·赫珀科斯基提出“對話法(dialogue)”,即將1850年后的大型奏鳴曲式視為與古典奏鳴曲式進行的一種“對話”,側重于將多樂章奏鳴套曲中第一樂章常用的奏鳴曲式結構作為分析這類單樂章作品的基礎。
雖然這些理論為分析這類大型單樂章作品提供了新的理論和分析方法,但這些研究仍在傳統曲式理論的框架內進行探索。史蒂文·萬德·莫特勒則認為,在研究1850年后的曲式時,需要超越傳統的曲式理論框架,考慮單樂章作品獨特的語境和慣例,因此,用多樂章作品中的某一樂章為標準來衡量單樂章作品,忽視了單樂章曲式結構模式的獨特性。
基于這一觀點,莫特勒在吸收這些理論家部分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二維奏鳴曲式(two-dimensional sonata form)”這一新理論。以下將對二維奏鳴曲式的理論內涵進行闡釋,并通過分析勛伯格的《第一弦樂四重奏》(Op.7),探討該作品是如何體現奏鳴曲式和奏鳴套曲這兩個維度,以及如何將奏鳴套曲的各樂章與奏鳴曲式的各部分相融合。
一、“二維奏鳴曲式”之理論內涵
莫特勒在其著作《二維奏鳴曲式:李斯特、施特勞斯、勛伯格、策姆林斯基單樂章器樂作品中的曲式與套曲》中為二維奏鳴曲式進行了類型上的定義,他這樣寫道:“‘二維奏鳴曲式’是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些大型器樂作品中使用的一種曲式組織原則。在這些作品中,奏鳴套曲中的不同樂章結合在一個單樂章奏鳴曲式中。”他進一步指出,在二維奏鳴曲式中,單樂章的奏鳴曲式和多樂章的奏鳴套曲位于相同的層次上,因此,二維奏鳴曲式是“奏鳴套曲的各樂章與奏鳴曲式的各部分在單樂章作品中同一層次上的結合”。這種結構既包括奏鳴曲式的所有基本部分,也包括奏鳴套曲的所有樂章,其中各部分和各樂章能夠以多種方式相互作用。莫特勒將貫穿整個作品的奏鳴曲式稱為“總體奏鳴曲式(overarchingsonata form)”,將構成奏鳴套曲中第一樂章的奏鳴曲式稱為“局部奏鳴曲式(local sonataform)”。事實上,這類作品并不完全遵循紐曼所闡釋的觀點,即奏鳴曲式的各部分與奏鳴套曲的各樂章完全重合,相反,在二維奏鳴曲式中,奏鳴曲式的各部分與奏鳴套曲的各樂章可能但不必須重合;每個二維奏鳴曲式都存在僅屬于套曲維度的樂章;同時,作品中也存在只在曲式維度中有效而在套曲維度中不起作用的單元。
莫特勒借鑒了卡爾·達爾豪斯在分析李斯特的《b小調鋼琴奏鳴曲》時提出的“共享單元(identification)”和“插部(interpolation)”兩個概念。此外,他引入了“套曲外(exocyclic)”曲式單元的概念,以補充和豐富對二維奏鳴曲式的理解。在二維奏鳴曲式的結構中,曲式維度與套曲維度可能會發生重合或不重合這兩種情況。在兩個維度不重合的情況下,套曲外曲式單元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套曲樂章插入總體奏鳴曲式時,這兩個維度并不重合,而是彼此相鄰。在穿插的過程中,總體奏鳴曲式被中止,只有在穿插結束后才會恢復。與插部單元相反的是套曲外曲式單元:這是一個完全屬于總體奏鳴曲式的單元,在奏鳴套曲中不起作用。在這些單元的持續中,套曲的維度暫時處于失效狀態。”
因此,套曲外曲式單元的存在是二維奏鳴曲式的一個決定性特征,是這一曲式類型區別于其他類似曲式的關鍵。盡管如此,插部單元與總體奏鳴曲式并非毫無關聯,事實上,即使在兩個維度的曲式單元并不一致的情況下,兩者仍然可以通過插部單元與屬于總體奏鳴曲式單元之間的主題聯系來實現。
此外,莫特勒也提出二維奏鳴曲式的兩個維度在特定條件下可能發生重合,這種現象“只有在奏鳴曲式與奏鳴套曲之間是同一關系時”才會發生。這意味著,在二維奏鳴曲式中的某些部分,同一曲式單元展現出奏鳴套曲與奏鳴曲式的雙重特征,兩個維度的特征在這個單元中相互交織,可能會導致一個維度的某些典型特征在某種程度上使另一維度的一些特征暫時失效。因此,這并不同于馬克斯和里曼所認為的,奏鳴曲式的各部分和奏鳴套曲的各樂章在位置和功能上都具有一致性。事實上,盡管這些單元與另一維度中的對應單元有許多共同功能,但它們也具有一些與之不同甚至相反的功能,使其具備不同維度的特性。
莫特勒對二維奏鳴曲式的闡釋揭示了這種結構中各維度之間關系的動態性。實際上,這類作品在起始階段看似遵循一維奏鳴曲式的規范,此時曲式單元在兩個維度上發揮著相同的功能,因此,二維的存在并不明顯。然而,當一個曲式單元在兩個維度中開始展示出不同的功能與特征時,二維性開始顯現。莫特勒將此稱為“維度分離(dimensionaldisconnection)”,這不僅揭示了作品中存在曲式與套曲兩個維度,還促使人們對之前的曲式單元進行回溯性重新詮釋。這意味著,最初看似是一維奏鳴曲式的部分,隨著維度分離點的到來和二維的顯現,被重新理解為二維奏鳴曲式的開始。這種理解不僅改變了對作品開始部分的看法,也為理解后續的曲式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
由此可見,二維奏鳴曲式既區別于傳統的曲式分析中的曲式范型,又與馬克斯、里曼等理論家對大型單樂章作品的分析方法存在差異。那么,在實際的音樂作品中如何體現這一理論呢?以下將對勛伯格的《第一弦樂四重奏》進行結構闡釋,筆者通過逐步分析作品中的相同維度、插部單元和套曲外曲式單元,以闡釋奏鳴套曲的第一樂章與其他單元的關聯性,以及插部單元如何與總體奏鳴曲式相結合。希望通過此分析,可以深入理解作品的曲式結構和套曲邏輯,進而揭示二維奏鳴曲式在該作品中的具體應用。
二、勛伯格《第一弦樂四重奏》之結構闡釋
勛伯格《第一弦樂四重奏》(Op.7)創作于1904-1905年,是他創作生涯早期的代表作之一。這一時期的作品深受勃拉姆斯和瓦格納等作曲家的影響,充分體現了晚期浪漫主義的音樂語言。圖1展示了莫特勒用來呈現完整二維奏鳴曲式的曲式概述的格式:最上面一行在曲式的維度中描述了單樂章奏鳴曲式的各個部分;最下面一行在套曲的維度中描述了奏鳴套曲的各個樂章;中間一行提供了兩個維度的小節數;第二行描述了所屬曲式維度的具體曲式單元,第四行描述了所屬套曲維度的具體曲式單元;虛線表示某個維度在特定時刻暫時處于失效狀態。該圖還進一步闡明了在創作過程中,這兩個維度之間的動態關系:總體奏鳴曲式展開部的第一部分在兩個維度中具有相同的功能。與此相反,展開部(繼續)、兩個再現部以及尾聲僅在總體奏鳴曲式中起作用,而在套曲維度中暫時失效;諧謔曲、慢板樂章和終曲則僅屬于套曲維度,在總體奏鳴曲式中并未發揮任何作用。
1.共享單元
在分析勛伯格《第一弦樂四重奏》的呈示部時,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主要部分:主部主題(第1-96小節)、賦格部分(A段的第1-55小節)和副部主題(A段的第56-103小節)。其中,主部主題為帶再現的三段式,包括呈示段(第1-29小節)、中段(第30-64小節)和再現段(第65-96小節)。作品的開頭(第1-13小節)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句子結構,第1-3小節展現了基本樂思a,第3-6小節為基本樂思的變化重復a1。在這一變化重復中,旋律的第一個音符從強拍位置改變到弱拍位置,從而使整體的節拍位置發生了改變。此外,如瓦爾特·弗利什所指出的,基本樂思a的最后一個音與變化重復a1的第一個音之間存在重疊,這增強了音樂的連貫性。
在該作品中,主部主題呈現出勛伯格精心設計的調性結構。呈示段以d小調開始,隨后通過bb小調在中段轉入be小調和#e小調,最終在再現段回到d小調。中段的調性均為d小調的相鄰半音,它們與bb小調共同構成了作品的宏觀調性布局:be小調的平行大調bE大調為呈示部副部的調性;#c小調為局部奏鳴曲式中再現部主部的調性;bb小調為局部奏鳴曲式中再現部副部的調性;bB大調為總體奏鳴曲式中再現部副部的調性。
A段的第1小節標志著賦格部分的開始,該部分基于高度半音化的主題,調性極不穩定,被稱為“迄今為止勛伯格音樂中調性最弱的段落之一”。此外,其不完全的無調性與周圍部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主題首次在A段的第2-9小節完整呈現,由三個動機組成,分別標記為b、b1、b2。副部主題在A段的第56小節進入,該主題包含三個動機,分別標記為c、c1、c2。
副部主題的首次出現標志著一個新部分的開始,并在之后通過多種方式發展和變化。調性布局上,副部主題從bE大調進入,隨后轉入C大調、G大調和bA大調。在A段的第92-103小節中,動機c的原形在bE大調上再現,這標志著副部主題的結束,并預示著作品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部分。
我們可以觀察到B段的第1-34小節完全依賴于副部材料,這似乎暗示著副部主題尚未完全結束。然而,該部分不穩定的節奏和副部主題本身的再現單元(A段的第92-103小節)實際上表明一個新部分的開始。此外,B段的第1-8小節中第一小提琴的旋律與B段的第53-57小節展開部中心的材料密切相關。因此,該部分屬于展開部的引入階段。B段的第53-101小節,作品進入展開部中心部分,具有明顯的展開性特征:在B段的第53-59小節中,結合了呈示部的主部主題、賦格部分和副部主題材料,構成了一個7小節的原形。這一原形隨后進行模進和分裂,創造出新的動機,并且這些新動機也進行了進一步的模進和分裂。
在勛伯格的《第一弦樂四重奏》中,奏鳴套曲的第一樂章與總體奏鳴曲式的呈示部和第一展開部相一致,第1小節至D段的第33小節中的每個單元在曲式和套曲維度都發揮著作用。在第1小節至A段的第103小節中,曲式和套曲兩個維度完全重合,局部奏鳴曲式的呈示部和總體奏鳴曲式的呈示部完全相同。B段的第1-101小節,曲式單元在兩個維度上都發揮展開的功能。從C段的第1小節開始,兩個維度才真正清晰起來。這是因為在C段的第1小節至D段的第33小節中,同一曲式單元首次同時實現兩種完全不同的功能:在曲式維度上,它們是展開部的另一個單元,發揮展開功能;然而,在套曲維度上,它們則作為第一樂章的再現部,發揮再現的作用。這種不同功能之間的沖突為作品的之前部分提供了一種新的見解,揭示了作品始終存在兩個不同的維度。因此,我們不僅將其理解為奏鳴曲式的呈示部和第一展開部,還將其理解為奏鳴套曲的第一樂章。
C段的第1小節至D段的第33小節同時承擔了再現和展開的雙重功能,這造成了結構上的內在張力:一方面,再現功能需要保持穩定性,并與呈示部保持一定的平行,以及解決呈示部中建立的調性沖突;另一方面,作為展開部的一部分,需要對呈示部的材料作展開性處理,以及產生或延長作品的不穩定性。然而,勛伯格通過讓三個主題組按照呈示部中的原始順序在此回歸,并在每個主題組的再現中進行明顯地改變,巧妙地解決了這種對立功能。例如,再現部以#c小調而非d小調開始,避免調性沖突的解決;同時,呈示部的主題材料進行了展開性處理,如主部主題的分裂、賦格部分以密接和應開始以及副部主題結尾的分裂,使其既能具備再現部的穩定性,又能實現展開部的戲劇性。
2.插部單元
在勛伯格的《第一弦樂四重奏》中,每個插部單元的開始都與前后音樂形成鮮明對比,并逐步發展出自己獨立的曲式結構。諧謔曲主題源自呈示部中的賦格部分(A段的第3-7小節),但通過速度、節拍以及節奏上的變化,賦予了該主題新的性格。諧謔曲的曲式結構遵循傳統的三部曲式,由呈示部(E段的第1-133小節)、三聲中部(F段的第1-G段的第33小節)和再現部(G段的第34-111小節)構成。
K段的第1小節出現了一個新的主題,這標志著慢板樂章的開始。
理論家們對慢板樂章的曲式結構存不同的觀點。弗利什將其解釋為大規模的三段式,而達爾豪斯將其解讀為奏鳴曲式。反對其為三段式的原因是,從再現段開始(L段的第1小節),織體主要由中部的材料而非呈示部的材料構成,且在L段的第17小節之后,中段的材料甚至完全消失。若將其解釋為奏鳴曲式,那么只有副部主題在再現部中回歸,且其調性與呈示部相同(E大調),沒有解決調性沖突。筆者認為,將慢板樂章解釋為奏鳴曲式更為恰當。若將其解釋為三段式,則再現段的材料與呈示段基本無關,難以符合三段式的典型特征。在浪漫主義后期的作品中,非典型的奏鳴曲式結構并不罕見,其中包括省略呈示部主部主題再現的情況,以及在再現部中并不總是解決副部主題的調性沖突。
M段的第1小節中,慢板樂章的主題經過變形后重新出現,這是終曲的開始。終曲采用三段式的曲式結構,具體劃分如下:呈示段(M段的第1-59小節)、中段(N段的第1-67小節)和再現段(N段的第68-80小節)。
插部單元在建立一定程度獨立性的同時,也與總體奏鳴曲式緊密結合,如諧謔曲的結尾為恢復總體奏鳴曲式做了鋪墊。諧謔曲的再現部呈現出明顯的變化,不僅在織體上展現出展開性,而且在調性上保持開放。插部單元與總體奏鳴曲式的進一步融合通過主題材料的巧妙運用得以實現。在諧謔曲中,主題由賦格主題演變而來,并與主部主題開始的低音線條相結合,其中動機c2及其變形在中部發揮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慢板樂章中引入了動機e和c1,而這兩個動機在諧謔曲中并未出現。因此,慢板樂章中的呈示部材料與諧謔曲中使用的呈示部材料不同,即諧謔曲中再次出現的材料在慢板樂章中不再使用。終曲則將前三個樂章的材料進行了融合,它既包含曲式維度又包含套曲維度的材料。此外,終曲沒有引入任何新的材料,而是完全基于作品中已有的材料及其變形。這揭示了作曲家在創作過程中對材料的極致運用,以及如何在保持作品統一的同時,創造出豐富的內部結構。
3.套曲外曲式單元
在探討總體奏鳴曲式的套曲外曲式單元時,我們可以發現套曲外曲式單元與之前的插部單元存在聯系。在總體奏鳴曲式的第二展開部中(H段的第1小節開始),源自呈示部的主部主題和副部主題材料再次在這里出現,但其在諧謔曲再現中幾乎完全沒有出現。此外,這一部分的發展也受到了諧謔曲材料的影響,使得諧謔曲融入總體奏鳴曲式中。主部主題的再現中(Ⅰ段的第38-80小節),并未出現任何插部單元的材料。與此相反,副部主題的再現(L段的第52-91小節)包含了慢板樂章中的三個片段。
我們可以觀察到,總體奏鳴曲式的再現部位于慢板樂章的兩側。這意味著,在套曲維度的四個樂章中,慢板樂章和終曲是在曲式維度的再現開始時,也就是調性沖突解決之后出現的。為了在再現部開始后保持動力并防止曲式結構的瓦解,必須確保再現之后異常冗長的部分具有意義。勛伯格通過縮減再現部的規模、插入慢板樂章以打斷再現部,以及讓慢板樂章和終曲都參與總體奏鳴曲式大范圍的調性布局來實現這一目標。具體來說,再現部本身進行了縮減處理,其中主部主題縮減了將近一半,賦格部分沒有再現,副部主題略有縮減。慢板樂章與再現部的連接和副部主題組之間的相互調和,使得后兩個單元(L段的第38-91小節)往往都被納入慢板樂章的范疇中。作品每次以明確的再現性特征回歸主部主題材料直至總體奏鳴曲式的再現時,都明顯地避免d小調或D大調的屬音。
勛伯格在《第一弦樂四重奏》中巧妙地融合了奏鳴曲式和奏鳴套曲,體現了他對傳統曲式結構的創新。作曲家成功地解決了二維奏鳴曲式的三個基本問題:將奏鳴套曲的第一樂章與總體奏鳴曲式的一部分相聯系,將插部樂章融入總體奏鳴曲式中,以及將總體奏鳴曲式的再現部與奏鳴套曲終曲相聯系。這種結構上的創新不僅為當今作品的曲式結構提供了寶貴的啟示,而且為未來音樂創作的可能性提供了實踐性例證。同時,這也為音樂分析者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工具,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和解讀音樂作品。
——評《勛伯格與救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