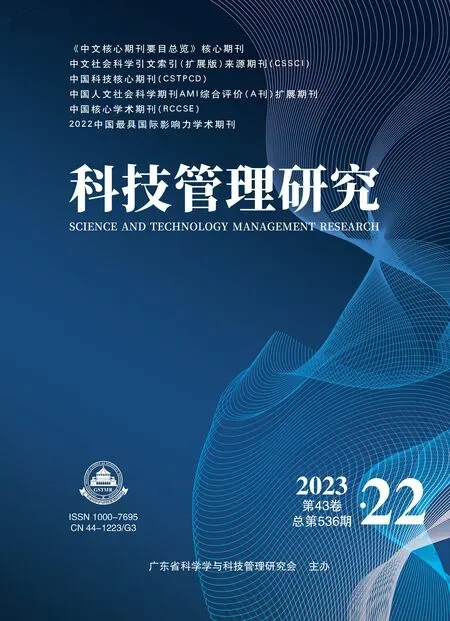欠發達城市工業碳排放的時空演變及脫鉤效應
——以廣西地市為例
曹金華,周小勇,章 玲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1106;2.桂林航天工業學院管理學院,廣西桂林 541004)
1 研究背景
工業是中國最大的CO2排放源,占中國碳排放總量的70%[1]。實現工業增長與碳排放的脫鉤發展,對中國實現“雙碳”目標具有重要意義[2]。城市是工業和碳排放集聚的主要地區,然而,中國不同地區的城市工業發展極不平衡,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存在明顯梯度差異。2020 年,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11 個省(區、市)能源消費總量達到13.96 億t(標準煤),約占全國(未含港澳臺地區。下同)能源消費總量1/3[3]。中國西部欠發達城市既是工業化程度的低洼地,也是碳排放的潛在增長區。因此,深入探究中國欠發達城市工業碳排放發展的特征規律,與發達城市形成對照,從而引導城市工業碳排放有序脫鉤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
作為國內典型的西部欠發達地區,廣西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工業振興發展。2021 年,廣西出臺《關于推進工業振興三年行動方案(2021—2023年)》,對工業經濟規模、結構和綠色發展都提出了更高目標要求。在工業振興行動方案的指導下,廣西各地市紛紛制定了工業發展戰略。南寧市以“強首”戰略為契機,堅持工業強市;桂林市提出重振桂林工業;柳州市實施“實業興市,開放強柳”戰略;防城港和欽州市以北部灣發展為契機,發展鋼鐵、石化等產業;百色市努力建成區域性鋁制造業中心。城市工業振興發展,有助于推動廣西經濟規模增長,但同時也將導致能源消費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碳排放。在“雙碳”目標下,廣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實現城市工業碳排放的脫鉤發展。
廣西的工業發展整體水平較低,而且各城市之間存在顯著的不平衡和差異。按照工業發展情況和特征,全區14 個地市可以大致分為3 類:第一類是基礎較好型,包括南寧、柳州和桂林三市;第二類是發展進步型,包括欽州、防城港、玉林等五市;第三類是基礎薄弱型,包括賀州、河池、崇左等六市。在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方面,柳州、欽州、防城港、百色等重工業城市實行以鋼鐵、化工等為主的高污染、高耗能發展模式,而南寧、桂林、北海等商貿服務型城市則探索電子、高科技裝備等高附加值工業發展道路。為了有效促進工業碳排放脫鉤發展,有必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有針對性的城市碳減排政策。
基于此,本研究以廣西14 個地市為例探討欠發達城市工業碳排放的時空演變及脫鉤效應,分析不同類型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發展的時空特征、脫鉤狀態及其驅動因素,為欠發達城市工業增長和碳減排的協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參考。
2 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脫鉤關系進行了廣泛研究。早期研究如楊曉華等[4],主要基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研究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是否存在倒“U”型關系,也有學者運用VAR 模型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研究[5],然而,這些方法是基于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同步變化,但現實中這兩者往往呈現出非同步變化的現象。2005 年,Tapio[6]提出了脫鉤理論模型,尋求突破經濟發展對污染排放的路徑依賴,以打破經濟增長與環境負荷之間的聯系[7]。脫鉤理論正是用來反映事物之間不同步變化的關系[8],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利用該理論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情況進行了大量研究。
具體到研究區域,李在軍等[9]對長三角、張華明等[10]對黃河流域的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關系進行研究,劉茂輝等[11]對天津市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情況及時空演化進行研究;王敏等[12]結合Tapio 脫鉤指數和對數平均迪氏指數(LMDI)方法,分析認為青海省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實現了脫鉤。也有學者從不同行業領域展開研究,如黃美忠等[13]對旅游業碳排放進行脫鉤效應分析;于卓卉等[14]對中國農業增長與碳排放的脫鉤情況進行分析。由于工業是中國碳排放主要部門,因此近年來成為熱點,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如何洋洋等[15]采用Tapio脫鉤指數對中國工業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脫鉤效應,認為不同工業行業的脫鉤指數有較大差異;劉偉等[16]從城市群角度對工業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脫鉤關系進行研究。
Tapio 脫鉤指數僅用作對脫鉤狀態的判別,無法對脫鉤變化的影響因素加以解釋,因此有學者采用LMDI 分解法進行驅動因素分析,如Zheng 等[17]將中國碳排放分解為7 個驅動因素,認為能源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能效提高是碳排放量增長放緩主要因素;徐國泉等[18]構建了二階段LMDI 分解模型分析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也有學者進一步深入對工業碳排放脫鉤驅動因素進行探討,如袁偉彥等[19]考慮了能源消費碳強度、工業行業結構、技術進步、資本存量和勞動投入等因素,研究認為能源強度、能源消費碳強度和勞動投入是中國工業碳排放脫鉤主要因素;馬曉君等[20]采用廣義迪氏指數分解法(GDIM)及“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模型(DPSIR)構建脫鉤模型,認為產出規模、技術進步、能源消費和人均碳排放量是導致中國工業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曲健瑩等[21]利用LMDI分解模型分析能源結構、能源強度及產業結構因素對中國工業碳排放脫鉤的影響。不同學者在構建驅動因素分解模型時考量因素有所不同,有的因素考慮不夠全面,有的又過于寬泛。驅動因素選取的準確性、合理性對正確識別工業碳排放關鍵驅動因素尤為重要。
綜上可知,從研究涉及區域來看,國內外學者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關系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以及經濟發達地區,針對欠發達城市層面的研究較少;從研究涉及行業來看,針對全行業的較多,針對具體行業部門的較少;在驅動因素選擇上,考慮科技創新這一重要因素對碳排放脫鉤影響存在不足。由于不同城市在經濟規模、產業結構、能源效率及科技創新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欠發達城市工業碳排放的時空特征及脫鉤效應,同時對其碳排放脫鉤的驅動因素進行分解,以揭示不同類型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發展的經濟社會動因,對欠發達城市工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3.1 研究方法
基于有關統計年鑒中城市工業能源消費、工業產品產量、能源碳排放因子(燃料熱值、單位熱值碳含量、氧化率)和工業總產值等相關統計數據,分別利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排放清單核算法、Tapio 脫鉤模型及LMDI 分解模型等方法,核算廣西14 個地市的工業碳排放,判定工業碳排放脫鉤狀態以及分析脫鉤狀態變化的驅動因素。分析框架如圖1 所示。

圖1 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效應綜合分析框架
3.1.1 城市工業碳排放核算
準確核算碳排放量是研究城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特征和識別其驅動因素的基礎。利用2001—2021 年《廣西統計年鑒》數據對城市工業碳排放情況進行核算,主要包括工業能源消耗產生的排放CEprocess及工業生產過程排放CEprocess。
式(1)中:CEij為工業行業j因燃燒能源i帶來的排放值;ADij為行業j的能源i燃燒量;EFi為能源i相關排放因子。
式(2)中:CEt為t種工業生產過程中排放的CO2量;ADt為工業產品t的產量;EFt為對應的碳排放因子。
3.1.2 城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關系測度
碳排放脫鉤表現為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降低碳排放量,由于Tapio 脫鉤模型在分析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時更加客觀和準確[22],故選用該模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兩者脫鉤關系通過脫鉤彈性系數加以判定,計算公式如下:
在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關系模型中,根據所得系數值將二者關系分為脫鉤、負脫鉤和連接3 種脫鉤狀態,按照0、0.8、1.2 臨界值進一步細分為強脫鉤、弱脫鉤等8 種脫鉤狀態。其中,強脫鉤是最理想狀態,即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碳排放量減少;弱脫鉤,即碳排放增長速度慢于經濟增速,是一種相對理想狀態。
3.1.3 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效應驅動因素分解
Kaya 恒等式用來研究經濟、人口等因素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其基本公式為:
式(4)中,C、E、G、P分別表示碳排放量、能源消費量、國內生產總值及人口。
宋旭等[23]在研究工業增長與碳排放脫鉤時便考慮了上述4 個方面的因素,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這些因素已不符合現實發展需要。《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指出科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路徑。結合張悅等[24]的研究經驗,考慮到科技創新碳減排效應的日益顯現,對Kaya 恒等式進行擴展,將科技創新水平和科技創新效率納入驅動因素分析,構建擴展的Kaya 恒等式。
LMDI 分解模型具有不產生殘差項且允許數據中包含零和負值滿足分解因素可逆等優勢,近年來在能源經濟與環境領域被廣泛使用[25],鑒于此,選用LMDI 分解模型進行驅動因素分解。基期t0到報告期t1的碳排放量變化可分解為:
對式(6)各碳排放增量采用LMDI 加和分解,得到:
由式(6)可證得:
結合式(3)脫鉤公式,得到擴展的工業碳排放脫鉤效應分解模型:
式(14)中,eES、eEI、eGN、eIN分別為能源結構效應、能源強度效應、科技創新效率效應及科技創新水平效應。
3.2 數據來源
研究需要廣西經濟統計數據、廣西能源平衡表、能源碳排放因子,以及廣西14 個地市工業能源消費量、工業總產值、科研經費投入等方面數據,相關數據來源于2001—2021 年《廣西統計年鑒》《廣西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碳排放數據庫》以及廣西各地市統計年鑒等。樣本研究期間為2000—2020 年,為真實反映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關系,剔除了物價上漲因素的影響,實際工業總產值以2000 年為基期進行換算。鑒于碳排放與經濟發展數據存在時間上的滯后性,選擇5 年為一個時間段進行時間序列的脫鉤分析,將2000—2020 年劃分為2000—2005 年、2005—2010 年、2010—2015 年、2015—2020 年4 個時間段。
4 結果與分析
4.1 城市工業碳排放的時空演變
2000—2020 年,廣西城市工業碳排放量隨工業總產值增長而增長,但增長速度逐漸趨緩,碳排放強度隨工業總產值增長而下降,下降趨勢放緩。如圖2 所示,廣西城市工業總產值獲得了快速增長,由2000 年的612 億元增長到2020 年的3 806 億元,年均增長9.57%;與此同時,工業碳排放量由2000年的1 361 萬t 增加到2020 年的5 620 萬t,年均增長率為7.35%,碳排放增速明顯低于工業經濟增速,特別是近些年響應國家低碳發展號召,實施一系列碳減排政策及低碳技術的推廣應用,有效地降低了碳排放。廣西工業碳排放強度由2000 年的2.22 t/萬元下降至2020 年1.48 t/萬元,呈下降趨勢。發展曲線顯示2000—2011 年間碳排放強度下降比較快,2011—2020 年間下降趨勢放緩。20 年間,隨著低碳政策落地及低碳技術的應用,廣西工業碳減排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在進一步的碳減排上遇到了瓶頸,需要分析其原因并探索新的碳減排路徑。

圖2 廣西工業總產值、碳排放量與碳排放強度的發展趨勢
廣西城市工業碳排放呈現明顯的時空差異,呈重點突出(柳州)、多點發散(欽州、百色等)態勢。如表1 所示,柳州市工業碳排放量由2000 年的中值型變為2005 年的較重型,2010 年進一步演變為重型并一直持續到2020 年;2000—2010 年,貴港、百色由輕型變為中型;2015 年防城港市由輕型變為較重型,南寧、欽州等市由輕型變為中型;2020 年,防城港、百色也加入了重型城市行列,欽州、貴港等市由中型變為較重型,北海、賀州等市由輕型變為中型。

表1 廣西各地市工業碳排放量時空演化特征
城市工業碳排放空間特征與其產業結構密切相關。柳州市自2005 年以來碳排放一直處于較重及重型,工業基礎強的柳州聚集了鋼鐵、化工等企業,承擔著較重的碳排放壓力。防城港、欽州、貴港的碳排放逐年惡化,這與廣西大力開發北部灣相關。以稀有金屬開采、冶煉等為支柱產業的百色情況也在惡化,2020 年已屬重型,碳排放增幅為2 919 萬t,增長率達508%。南寧、北海、玉林、賀州也由輕型變為中型。2000—2020 年,桂林、梧州、河池、來賓及崇左一直處于碳排放輕型城市,其中,桂林為旅游城市,梧州等市工業水平一直不高。如表2 所示。

表2 廣西各地市工業碳排放強度時空演化特征
從時空變化來看,廣西絕大部分城市碳排放強度呈逐年下降趨勢,但以柳州為代表的基礎較好型及以防城港、百色為代表的發展進步型城市碳排放強度依然較高。近年來廣西大力發展北部灣,防城港作為北部灣的主要城市,以鋼鐵、石化為代表的工業迅速發展,能源消費快速增長;百色的工業碳排放強度均處高值區,結合其碳排放量從輕型增加到重型,百色與防城港二市碳排放量與碳排放強度呈同頻變化的態勢;柳州的工業碳排放強度從高值區降到較高值區,得益于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及注重新能源汽車等新興低碳產業的培養;玉林、來賓從高值區降至中值區,南寧、桂林、北海、河池降為低值區,這6 個城市在產業調整、節能減排技術應用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特別是南寧的強首戰略、桂林的世界旅游名城戰略都有效促進了各自工業碳排放強度降低。
綜合以上分析表明,廣西各城市近年來在響應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號召、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全面增長、多點惡化態勢表明其碳減排形勢非常嚴峻,尤其是柳州、防城港、百色等城市仍需繼續降低碳排放強度。
4.2 城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的脫鉤關系
通過對廣西城市工業總產值和工業碳排放數據進行整理,得到其2000—2020 年四階段脫鉤關系以及變化趨勢,如表3 所示。14 個地市總體脫鉤狀態以擴張連接、負脫鉤為主向弱脫鉤、強脫鉤為主演化;從城市異質性來看,基礎較好型城市主要表現為弱脫鉤狀態,發展進步型城市主要表現為擴張負脫鉤狀態,基礎薄弱型城市主要表現為強脫鉤狀態。2000—2005 年,這一階段各城市以擴張負脫鉤為主,沒有強脫鉤的情況。2005—2010 年,脫鉤彈性最大的是防城港市(9.052),脫鉤狀態最差,這一階段為落實國家增加投資的宏觀調控政策,2008 年9 月武漢鋼鐵集團公司與廣西柳州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聯合成立廣西鋼鐵集團落戶防城港;脫鉤彈性比較理想的是北海、賀州等市,貴港、百色等城市脫鉤狀態不理想。2010—2015 年,桂林、梧州由弱脫鉤、擴張連接變為強脫鉤,桂林得益于國際旅游名城的定位,梧州得益于2012 年“工業轉型升級”及2014年“穩增長、調結構”的戰略;欽州、北海及賀州等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關系出現不同程度的惡化,欽州、北海積極響應《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大力發展工業增加了碳排放,賀州的“東融”戰略進一步拉升了碳排放彈性。2015—2020 年,脫鉤彈性下降的有柳州、賀州等六市,脫鉤狀態惡化的有南寧、北海、百色、來賓四市,維持強脫鉤不變的有桂林、河池,維持弱脫鉤不變的有貴港,防城港、欽州則保持擴張負脫鉤。

表3 2000—2020 年廣西各地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狀態演變
縱觀整個研究期間,脫鉤彈性持續下降的為柳州、桂林、玉林、河池等城市,其中桂林四階段的脫鉤彈性呈明顯下降態勢;持續惡化的有北海、欽州、來賓,北海近年來加快臨港產業聚集,熱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廣西石油分公司液化天然氣(LNG)等項目竣工投產等都讓北海碳排放面臨巨大壓力,來賓 “十三五”期間深化工業強市戰略、積極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有關;梧州、貴港、崇左等城市的變化為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南寧、欽州則呈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
4.3 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發展的驅動因素
為了對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彈性進一步分析,利用擴展的工業碳排放脫鉤效應分解模型得到eES、eEI、eGN、eIN這4 個驅動因素對廣西各地市工業碳排放脫鉤狀態的影響效應,如表4 所示。

表4 2000—2020 年廣西各地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狀態演變的驅動因素分析
4.3.1 能源結構
能源結構對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影響較弱,城市異質性不明顯。四階段來看,南寧、河池、崇左三市能源結構脫鉤效應均為促進作用,且促進作用在逐漸增強,如南寧的生態綠城建設極大地促進其能源結構調整;柳州、欽州等城市能源結構脫鉤彈性均為抑制作用,2009 年柳州提出“發展靠經濟、經濟靠工業”的發展思路,2019 年繼續提出牢固樹立“工業興市、工業強市”理念,這種發展理念反映在其能源結構脫鉤效應上。因此,還應加強能源結構調整,促進工業綠色低碳發展。
4.3.2 能源強度
能源強度效應對基礎較好型、基礎薄弱型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主要起促進作用,對發展進步型城市主要起抑制作用。2005—2010 年能源強度脫鉤彈性較理想的為南寧、桂林等10 個城市,能源強度效應起促進作用,其余城市能源強度脫鉤彈性為正,防城港的抑制作用明顯。2010—2015 年能源強度脫鉤彈性最理想的為河池,其次為桂林等10 市,防城港、欽州等發展進步型城市能源強度脫鉤彈性為正,起抑制作用,如防城港臨港產業集群建設帶來了較大的生態環境壓力,出現了生態赤字,產生了負效應。2015—2020 年,能源強度脫鉤效應較理想的為桂林,其次為玉林;在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導下,桂林、玉林等市積極去產能、調結構,對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大力扶持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能源強度明顯下降。
4.3.3 科技創新效率
科技創新效率對基礎較好型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起促進作用,對發展進步型、基礎薄弱型城市起抑制作用。2000—2005 年,科技創新效率脫鉤彈性幾乎全部為正,表現為抑制作用,尤其是河池的脫鉤彈性達到3.452、遠超1.200 的臨界值。2005—2010 年,科技創新效率對各市工業碳排放脫鉤呈現一定促進作用,但這種作用在2010—2015 年呈現減弱趨勢,2015—2020 年又表現為較強的抑制作用;近年來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廣西各市紛紛加大科研投入,但較低的科研創新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作為基礎較好型城市的代表,南寧、柳州兩市科技創新效率促進作用明顯,較好的工業基礎帶來了較高科技創新效率,特別是2015—2020 年,其脫鉤彈性值分別達到-1.251 和-1.908,對工業碳排放脫鉤起積極促進作用。
4.3.4 科技創新水平
科技創新水平對發展進步型、基礎薄弱型城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的影響由抑制作用轉變促進作用,對基礎較好型城市一直表現為抑制作用。防城港、欽州等發展進步型城市科技創新水平效應由最初的抑制作用轉變為促進作用,這些城市近年來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引進高新技術企業、避免低水平引進,對傳統企業積極采用新型節能技術與工藝,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研究期內,南寧、柳州等基礎較好型城市的科技創新水平表現為抑制作用,這些城市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往往忽略科技創新投入,特別是對傳統高能耗企業節能減排技術的創新投入。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基于欠發達城市視角探討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關系,在測算城市工業碳排放量基礎上,利用Tapio 脫鉤指數計算工業碳排放脫鉤狀態,并結合LMDI 分解模型對脫鉤效應驅動因素進行分析。得出主要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如下。
5.1 研究結論
一是城市工業碳排放呈現時空分異特征,并存在明顯產業結構差異,基礎較好型、發展進步型城市碳排放量明顯高于基礎薄弱型城市,發展進步型城市碳排放強度明顯高于基礎較好及基礎薄弱型城市,隨著時間變化碳排放量呈“重點突出、多點發散”態勢;同時,城市工業碳排放空間特征與其產業類型分布密切相關,聚集了鋼鐵、化工、金屬冶煉等以重工業為主的基礎較好型及發展進步型城市碳排放量及強度均較高,以輕工業為主的基礎薄弱型城市碳排放較低。
二是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從抑制脫鉤向促進脫鉤狀態演化,發展進步型城市主要表現為擴張負脫鉤,基礎較好型城市主要表現為弱脫鉤,基礎薄弱型城市主要表現為強脫鉤。
三是能源強度效應是促進基礎較好型、基礎薄弱型城市碳排放脫鉤關鍵因素,對基礎較好型城市碳排放脫鉤由抑作用演化為促進作用,柳州、桂林兩市轉變明顯;對發展進步型城市一直表現為抑制作用,防城港、欽州的能源強度碳排放脫鉤抑制作用較明顯;對基礎薄弱型城市碳排放脫鉤一直表現為促進作用,玉林、河池能源強度碳排放脫鉤促進作用較明顯。
四是科技創新效率是促進基礎較好型城市碳排放脫鉤關鍵因素,在第一階段對發展進步型、基礎薄弱型城市碳排放脫鉤表現為較強的抑制作用,第二階段則呈現一定促進作用,但該促進作用在第三階段呈減弱趨勢,第四階段又表現出較強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階段開始,南寧、柳州等基礎較好型城市科技創新效率脫鉤彈性均為負數,特別是在第四階段,脫鉤彈性值遠低于強脫鉤臨界值,對碳排放脫鉤起較為積極的促進作用。
五是科技創新水平是促進發展進步型城、基礎薄弱型城市碳排放脫鉤關鍵因素,對防城港、欽州等發展進步型城市以及賀州、來賓、崇左等基礎薄弱型城市碳排放脫鉤影響由抑制作用轉變為積極促進作用;對南寧、柳州等基礎較好型城市工業碳排放脫鉤一直表現為抑制作用,對高校眾多的桂林促進作用明顯。
5.2 政策建議
一是調整產業結構,打造低碳產業體系。欠發達城市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必須以綠色化、低碳化的產業結構作為支撐。基礎較好型城市應著力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打造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經濟增長新業態;發展進步型城市應摒棄高能耗、高污染發展模式,大力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走綠色發展道路;基礎薄弱型城市在大力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同時,要注重強約束的環境規制政策、綠色低碳的科學發展規劃,打造低碳產業結構體系。
二是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量較高的城市應逐步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從源頭上抑制碳排放過快增長;基礎較好型城市應加大生產工藝與技術革新力度,有效提高能源得利效率,降低能源強度;發展進步型城市在構建先進產業體系時應加快對綠色低碳技術的引進與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時加大對清潔能源的使用比例;基礎薄弱型城市可以利用豐富自然資源條件發展水電、風電及光伏發電,大力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
三是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提高科技創新水平。經濟發展應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科技創新是欠發達城市工業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基礎較好型城市應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創新水平,以新材料、新技術代替傳統生產工藝與落后技術,以科技創新推動傳統工業轉型升級,同時積極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創新服務方式;發展進步型城市通過科技創新投入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走科技創新型工業發展新道路;基礎薄弱型城市應當依托自身的生態資源,推動生態科技創新,承接發達地區的技術外溢,激發創新意識,通過科技創新探索一條適合自己工業發展的新路子。
四是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提升科技創新效率。欠發達城市科技創新效率不高,主要是科技資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科技成果產業化不高,應當利用發達地區科技創新的示范效應,調整科技資源配置結構,提升科技管理水平,提高科技資源的利用效率,同時通過科技產業扶持政策、搭建科技成果市場化平臺,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帶動欠發達城市科技創新效率提升;此外,針對不同城市工業發展水平的差異性,應降低科技創新資源自由流動壁壘,促進科技創新技術溢出,形成協調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