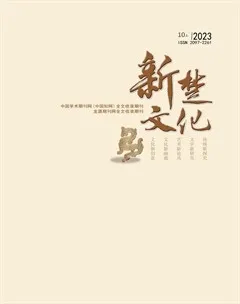從《詩經》看周代中和詩思想
【摘要】周代“中和”的思想觀念,影響著《詩經》的審美取向。“中和”精神以“重文尚用”為價值取向,采用“禮中樂和”的方式,追求“溫柔敦厚”的人格理想。其所體現的中和之美,是古代中國人所追求的理想,滲透著古代社會對人、道德倫理、社會政治的理想,不僅對當時的文學藝術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對后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詩經》;中和;禮樂
【中圖分類號】I206.2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28-0019-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3.28.005
周代中和詩歌作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的思想內容具有時代性、歷史性、永恒性的特點,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在繼承和發揚前人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又結合了時代背景、詩人所處環境等方面因素不斷地完善與發展,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個人生命價值的追求,還揭示出人們對于人生道路、生存環境以及理想抱負的思考。
一、“中和”來源
“中”一詞最初多用于表示“中央”的位置、“正中”的時間,但在宗教信仰、禮儀、音樂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中”一詞逐漸變化,衍生出了“中道、中正、中行”等,這些詞語在《易傳》中多處出現,可見當時人們對“中”的釋義范圍已經擴大,并得到了學者們的普遍認同。《尚書·盤庚》中盤庚在遷都前訓導民眾“各設中于乃心”[1]171,可以看到這時對“中”的理解已經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中”逐漸成為統治者“中正”身份的一種象征,而統治者之所以建立“中正”身份,也是出于“致中和”的考慮。《說文解字》中將“和”解釋為“相應也”[2]100,原意是指唱歌時的相互呼應。
“中”與“和”經常是相互補充、緊密相連的,因此經常被統稱為“中和”。《禮記·中庸》從個體修養的視角深入探討了中和這一概念:“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3]1625喜怒哀樂的情感沒有發生,可以稱之為“中”;喜怒哀樂的感情發生了,但都能適中且有節度,可以稱之為“和”。
禮強調的等級制度重在分,同時又將不同等級的人聚合在一起,以樂歌、樂舞等與禮儀相結合的方式,去影響人們的心性、欲望、意志、行為等,使人們的情緒在適當的范圍內,避免過于激烈與不及,使人們在潛移默化中遵從禮儀的規約,這就是禮的“制中”作用。禮“制中”的宗旨是為了使社會相互制約達到均衡,唯有以“中”為平衡點,方能達到“和”的目標,實現理想的“和”,“和”是“中”的目的與歸宿。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和”思想在周朝統治者的政治觀念中占據了無可替代的位置,這在中國美學觀念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中和思想的形成
禮之本為中,樂之本為和,禮樂合稱為中和。“中和”理念,源于音聲和諧,從一開始就被統治者所關注,并逐步成為禮樂制度的核心。只有堅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才能平衡所有事物,從而實現社會的和諧。中和理論在孔子的指導下得到了弘揚,這主要體現在“禮”與“和”兩個概念之間的更深層次的相互滲透。在《禮記·中庸》中,它被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層次:“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們普遍認為,“中和”這一概念主要強調的是位置的平衡與行為的適當性,以及不同事物間的和諧相處。對立的兩方要相互協調,在對立中求統一,不同要素間也要相互協調,在相互包容中發揮其創造性,使其和而不同。
周代中和詩學思想的形成與當時社會環境有著不可分割性的聯系。它是對先秦兩漢分文制度進行完善并吸收而來的產物之一——仁義禮教下道德規范及倫理綱常方面所做闡述的具體體現。在先秦兩漢分文制度中,對人的要求是以“禮”為基礎,而周代中和詩學思想則是從道德規范和倫理綱常方面進行論述。《禮記·曲公》有云:“德之至仁義也;法之至智厚矣也!若君子不與己、合家者不同其賢能否?故儒釋道以達倫。”這個觀點認為人是具有高尚品格修養的主體,是社會道德的主體,“禮君以德為本”“士與己之間不和也不能分其義理”等觀點認為人要具有高尚品格修養,就要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周代中和詩學思想正是對儒家文化傳統理解提出了符合當時社會的道德要求。《詩經·五大家》中說:“孝悌之謂禮之大者,故敬畏之旨也。”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社會道德上所占地位遠遠高于其他任何一種文學形式,這是通過文字與實用相結合,用文育和德智等方式來指導人如何行為。
三、《詩經》中的中和思想
“禮”“樂”和《詩》構成了周朝禮樂體系的有機統一,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禮”和“樂”從其產生之日起便密不可分,在上古時期,“禮”的傳播與教化,離不開“樂”的作用。《詩》最初應該是一首樂曲,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詩》與“樂”漸次分開,“樂”也隨之消失,《詩》的作用也隨之加強,通過口耳相傳和文字記錄等多種方式得以保存,并逐步演變為傳遞“禮”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禮”作為周代統治者統治人民的基礎,目的就是鞏固統治,穩定社會秩序。而《詩》作為記錄社會生活的作品,其中所蘊含的內容也大多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維護社會秩序穩定,具有重情、貴“中”的特點。《詩》在記錄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見事情的同時,還要通過對這些事的描寫來揭示一些社會問題,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詩》重情、貴“中”的特點及追求的目的與“禮”不謀而合,互為補充。《詩》作為禮的文字載體,抒發作者感情,更能為人所接受和遵循,正所謂《詩》教亦禮教,《詩》所贊賞的是“禮”肯定的,《詩》諷刺的也是“禮”否定的,二者相輔相成。況且《詩經》的編纂成集,本就是周代禮樂制度的結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反映了周王朝統治階層的意志,同時也必然蘊含著周代禮樂制度尚“中”貴“和”的思想。
(一)《國風》
在周代時期,《詩》被視為禮樂活動中的一種特定的樂歌形式,具有“祗敬雍和”的政治教化和示范作用。如《周南·關雎》,在鄉禮“典樂”中,《關雎》是最常出現的一首樂歌,它被認為是表達夫妻恩愛美德的典型。“君子”和“淑女”之間,他們的愛情與婚姻關系代表了一種非常理想化的婚姻形態。夫妻之間的關系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石,同時也是政治教育的起點。在這個時代,“琴瑟友之”和“鐘鼓樂之”不只是展現了君子之間的深厚情感,而且還表現出一種“以樂象禮”的禮儀意義。這是在“中和”觀念影響下的,與美德相聯系的“和樂融睦”的夫婦之道。
(二)《小雅》
用于燕饗儀式典樂的樂歌曲目主要是《小雅·鹿鳴》,其中呈現出一派君臣歡飲,圣君賢相們其樂融融的宴會場景。“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這說的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個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矯正偷薄的民風,可見宴會的目的是“安樂其心”,使赴宴的大臣們都對他心悅誠服,心甘情愿為他效力。正是在“中和”觀念的影響和約束下,詩歌自始至終洋溢著歡快的氣氛,所言皆是君臣有度、君臣盡誠的和諧場景。
(三)《大雅》
《大雅》樂歌主要是對祖考的政治功績與其精神道德品格進行夸飾贊美,目的是維護周王政治的獨尊地位。《大雅·文王》贊美了文王建周的偉業,在“歌詩發德”中表達了對宗周王朝永恒存在的期望,即在保持天子“中正”地位的基礎上,實現天下的和諧與大同。如《大雅·域樸》,歌頌周文王郊祭天神之后領兵征伐,文中描繪了人們在祭祀儀式上為周文王獻上玉璋的場景,旨在頌揚文王在人才選拔上的得當之處,以及他的綱紀如何震懾四方。《大雅·旱麓》則在歌頌文王的同時祭祀神靈,以求得神靈的福佑。
在祭祀神靈中,“玉”是經常被提到并用于祭祀的一種重要物品。玉的形狀方圓規整,質樸柔和,音色清澈,既有“中正”之意,又有君子高尚之德之意,也與古人以“和諧”“完美”之意相契合,因而被用作祭祀神靈的“禮物”。《詩經》里所描述的在禮樂儀式中出現的被稱為“禮玉”,這種“祭祀之玉”是用來祈求神靈賜福和保佑人間的,從這可以看出周人對“中和”的崇敬。而當“禮玉”作為佩飾之玉時,則強調君子須擁有“中正平和”的品格。由此可見,玉不只是用來裝飾人們的外觀,它還象征著社會地位和身份,更為關鍵的是,它代表著一種“中正平和”的君子品質。
(四)《頌》
在周代的五大禮儀中,祭祀儀式受到了極大的尊崇,創作《周頌》這首樂歌的目的是配合天子在祭祀活動中的典樂儀式。在典樂的過程中,通過《頌》這首歌來歌頌祖先的偉大貢獻,并向后代傳達治理國家的決心,鼓勵君臣之間的和諧,以實現政治的大業。
如《周頌·執競》:“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4]1307-1309金奏樂器與管吹樂器與鐘鼓相互映襯,演奏出的音樂回蕩在空中,產生了一種“鐘聲、鼓聲、磬聲和將聲”交織在一起的音樂效果。這種音樂充滿了崇敬與和諧的美感,這種和諧的音樂不僅讓我們的祖先和神靈得到享受,連諸侯和群臣也在其中獲得了美與善的精神啟迪,是“中和”之美在樂奏環節的體現。
四、中和思想的積極意義
《風》詩《關雎》中,“合敬同愛的精神內涵”反映了在“中和”思想的影響之下,與美德相關聯的“和樂融睦”的夫妻之道。《域樸》《旱麓》這兩首樂歌贊美了文王建周的偉業,在“詩歌”中表達了對宗周王朝永恒的期望,即在保持天子“中正”地位的基礎上,成就世界和平大同。深受“中和”審美觀念影響的《鹿鳴》歌詩,刻畫了君臣歡飲而又和諧的氣氛,使人們充分沉醉于受此“中和”思想強烈熏陶的儀式氛圍之中。《執競》和《清廟》這兩首樂歌通過“平德”的旋律展現了以“中和祗庸孝友”為核心思想的“樂德”精神,充分體現了“祗敬雍和”的“樂德”文化。這首歌詩的氛圍既優雅又莊重,仿佛參禮者就在其中,不自覺地接受著以禮、義、德為中心的精神陶冶。不可否認,儀式樂歌不只是周代道德和倫理觀點的藝術展現,也是一種展示周代宗法制度和社會秩序的方式。因此,具有儀式性的儀式樂歌已經變成了周代禮儀文化的標志,它起到了“中和”審美內涵的關鍵作用,為實現周代“歌詩發德”的詩教理念提供了橋梁。
從這一點來看,《詩》作為周代禮樂活動中的樂歌,它展現了“祗敬雍和”的政治教育和示范意義。在《風》《大雅》《小雅》《頌》這些詩歌中,都有對祖先在文學、武藝、戰略、品德等方面的高度贊美,同時也回顧了祖先在艱難困苦的歷史背景下,夫妻、君臣以及宗族之間的情感關系中,復雜且抽象的禮義含義,并通過儀式和樂歌的方式進行了表達,彰顯了其中蘊含的中和思想的文化內涵。
中和主張采用特定的方式傳達和釋放情感,但同時也要控制自己的情感,防止情感的過度擴散,確保內心的寧靜與平和,進而實現人的精神與人格的和諧統一。例如,在《論語·八佾》中有這樣的評價:《關雎》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一觀點后來演變為“溫柔敦厚”的“詩教”一說,提倡以適度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感情,同時不能過分地表達自己的感情。
“中和”實際上是一種“重文尚用”的審美觀念。“中和”精神的價值觀是“重文尚用”,“中和”詩學在此價值觀的指引下,追求“溫柔敦厚”的個性,“中和”思想則表現為“禮中樂和”的藝術表現形式。從這一點來看,“中和”的審美觀點無疑強調了“文的重要性”,同時,“中和”這一概念也被認為是“尚用”的,它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對政治、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的深遠影響上。
五、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也表現為“文質彬彬”。文,也就是指辭藻華麗,是指作品對外呈現出的效果;質,也就是質樸,是指作品內部蘊含的思想和價值。孔子主張,君子不光應當在外表上優雅,也應注重內在的道德修養,內外兼修以期達到內外統一的中和。儒家重視“文”和“質”,這一觀點受到了當時社會中“禮”的價值觀的深刻影響,即“君子在文學方面具有廣泛的學識,并以禮為準則約束自我,也就可以做到不畔矣夫”,當文質兩者都齊全時,就能實現美與善的完美結合。正如《論語·八佾》中所描述的“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強調了文藝作品應當追求“盡善盡美”。“文”與“質”原本就是一對哲學范疇,是一對辯證的關系,其特征在于其形式與內容上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在詩歌領域,文質論強調的是以質定形,以質勝華。“斯文而后君子”,“文”與“質”的關系是“禮”與“情”關系的外在表現,“文”與“質”的融合是達到“和”狀態的關鍵途徑,同時,“和”也代表了“文”與“質”之間和諧關系的一種理想追求。
普遍的和諧之美以“中和”的理念為其顯著特點,是中國古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古代社會,對人、道德倫理、社會政治中,都滲透著對這種和諧之美的追求。在政治上,追求的是一種“國泰民安,國泰民安”的和政之美;在道德和倫理學的角度上,君臣父子、長幼有序、尊卑分明,追求的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在人格上,追求的則是一個人的身心平和,氣定神閑,也就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不傲”的個人修養。這種“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主客體的和諧共處,才是人們所向往的理想社會。
參考文獻:
[1]孔安國,注.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M]//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
[2]許慎,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鄭玄,注.孔穎達,等,疏.禮記正義[M]//十三經注疏.李學勤,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毛亨,鄭玄,注.孔穎達,等,疏.毛詩正義[M]//十三經注疏.李學勤,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5]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M]//十三經注疏.李學勤,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6]張利群.中國詩性文論與批評[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7]丁進.周禮與文學[D].上海:復旦大學,2005.
[8]蘇保華.先秦諸子之前“中和”觀考釋[J].社會科學,2013(03):121-129.
[9]趙玉敏.“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與孔子“中和”美學精神[J].北方論叢,2012(01):20-23.
[10]李婷婷.論《詩經》樂章的娛悅性及審美[J].山東社會科學,2010(06):103-107.
[11]于雪棠.吉美貴善的綜合載體──《詩經》玉意象論析[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05).
[12]劉金波,劉肖溢.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和之美[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62(03):281-285.
[13]朱恩彬.談古代文藝理論中的“中和”思想[J].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03):45-52.
作者簡介:
張馨月(1999-),女,漢族,黑龍江哈爾濱人,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典文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