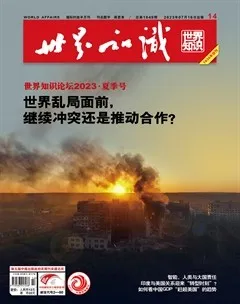印度與美國關系迎來“轉型時刻”?
林民旺

2023年6月22日,美國總統拜登歡迎到訪華盛頓的印度總理莫迪。
6月21~24日,印度總理莫迪自2014年上臺以來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一般而言,作為政府首腦,總理通常是應邀進行“正式訪問”,只有兼任政府首腦的君主、總統等國家元首才能得到“國事訪問”邀請。因此,外界普遍認為,此次莫迪的出訪得到了美國拜登政府的“超規格”接待并被美印雙方高層“寄予厚望”。例如,早在一個月前,美方就宣布將安排莫迪繼2016年后第二次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印度政府稱,這使莫迪成為首位兩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的印度總理。同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稱,這將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則稱此訪將使美印關系迎來“轉型時刻”。
莫迪的此次出訪及其成果毫無疑問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6月22日,莫迪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隨后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詳細落實并規劃了兩國的全面合作,其58款條文涵蓋的范圍與領域之廣,前所未有。不過,鑒于印度“戰略搖擺”的惰性與該國內外情勢發展的復雜性,美印在聯合聲明中宣布建立“世界上最親密的伙伴之一”的關系發展仍存相當大的變數,此訪究竟是否能成為美印關系的“轉型時刻”也有待歷史的檢驗。
美國在防務領域“下猛藥”
2016年6月,莫迪在美國國會第一次演講時稱,印度和美國已克服“歷史上的猶豫”,自此兩國關系發展走上快車道。莫迪本人,更是由美國眼中的國際“棄兒”轉變為“座上賓”。2005年,美國禁止彼時身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的莫迪入境,理由是他未能妥善處理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暴亂。直至莫迪及其所屬的印度人民黨(印人黨)贏得2014年的印度大選,美國才悄悄廢除了這一禁令。2021年,拜登上臺執政后,將中美戰略博弈的需要放在首位,而印度在其中的戰略價值日益凸顯,由此迎來了美國對印外交的“轉型”。
莫迪上臺執政后,防務合作成為印美關系的主軸,雙方達成了一系列“開拓性”協議。自2014年5月起,印美陸續簽署了《后勤交流備忘錄協定》(LEMOA)、《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COMCASA)、《工業安全附件》(ISA)及《基礎交換與合作協議》(BECA),為兩國的防務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礎。此次莫迪訪美,兩國最終敲定的國防工業合作路線圖及正式成立的“印美國防加速生態系統”(INDUS-X),進一步提升了美印未來的國防產業合作水平,推動兩國共同研發新技術,共同生產現有及新型裝備,并極大加速了兩國國防領域初創企業的合作。此外,美國還批準通用電氣公司向印度轉讓用于噴氣式戰斗機的F-414渦扇發動機技術,并同意印度采購31架先進的MQ-9B武裝無人機,它是由美國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的海上大型巡邏無人機,而印度也向美國回報以供軍艦維護與維修的前沿基地。此外,兩國在聯合聲明中還宣布,印度國防部和美國國防部決定展開談判,以達成供應安全安排,并討論互惠國防采購協議。
美國在防務和軍售上的“慷慨”,不僅是為武器出口,更多是從長遠目標出發,一方面削弱印度對俄羅斯武器的依賴,另一方面則是要采取措施分階段地鎖定印度的整個武器系統,一勞永逸地解決印度“戰略搖擺”的根源問題。
技術經濟合作正成為重要基石
全方位的技術經濟合作正成為印美關系的重要基石。此次訪問期間,莫迪會見了美國一系列包括谷歌、亞馬遜在內的高科技及電商巨頭高管,爭取美國商界對印度的投資。隨之,亞馬遜宣布將在2030年前新增150億美元的對印投資;谷歌則稱將在古吉拉特邦國際金融科技城設立全球金融科技中心。
更值得關注的是,印美要在技術上形成全面合作態勢。2023年1月,美印就啟動了“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2023年6月,雙方啟動跨部門戰略貿易對話,旨在解決出口管制問題,探索加強高科技貿易的途徑,促進兩國之間的技術轉讓。在此次訪問中,兩國還宣布了一系列在半導體、關鍵礦產、人工智能、太空、清潔能源、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例如,兩國簽署《半導體供應鏈與創新伙伴關系諒解備忘錄》;美國美光科技公司宣布在印度投資8.25億美元,建立一個新的半導體組裝和測試設施;泛林集團承諾培訓六萬名印度工程師,以幫助印度的半導體教育和勞動力發展;美國應用材料公司則宣布要投資四億美元,在印度建立合作工程中心。在電信網絡技術上,兩國宣布成立兩個先進電信聯合工作組,重點關注開放式無線網絡和5G、6G技術的研發。此外,兩國還宣布建立聯合量子協調機制,并將達成全面的量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協議。
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印美在國際及地區問題上承諾相互支持。2022年,美國正式加入印度在2015年倡議成立的“國際太陽能聯盟”(ISA)。此次訪問期間,美國也繼續承諾支持印度成為改革后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并承諾加入印度在2019年提出的“印太海洋倡議”。而印度在2022年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計劃”(IPMDA)后,此次也承諾支持美國在2022年6月與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日本建立的“藍色太平洋伙伴”倡議(PBP)。可以看出,兩國的合作范圍正不斷擴大,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兩國都達成了協調地區政策的承諾。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兩國將在2023年舉行首屆印度洋對話。
與此同時,加強印美人員往來,也是莫迪訪問的應有之義。在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中,美國承諾繼續為印度技術人員赴美工作提供簽證便利,印度也同意美國在印度的班加羅爾和艾哈邁達巴德增設領事館,此外,印度也要在西雅圖啟用其新領事館,并在其它兩個商定的地方開設新的駐美領事館。
伴隨著激烈爭論的關系前景
莫迪的此次訪問,可以說實現了印度右翼一直以來期待的在戰略上“倒向美西方”的夢想。而實現這一點的關鍵是,不斷打“中國牌”來獲得美國對印度的戰略“慷慨”。
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講中,莫迪仍沒忘記打“地緣政治牌”。他稱:“脅迫和對抗的烏云正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投下它們的陰影。該地區的穩定已成為我們合作伙伴關系的核心問題之一。”同時,他也告訴美國,印度未來將在戰略上對美國有多重要:“當我作為總理第一次訪問美國時,印度是世界第十大經濟體。如今,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且將很快成為第三大經濟體。”

2023年6月22日,印度總理莫迪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
雖然白宮否認將印度視為制衡中國的力量,但是拜登顯然對印度“寄予厚望”,他稱美印友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緊密、更有活力”。只是,不論是在兩國內部,還是國際社會,有關美印關系的快速發展及印度是否具有遏華作用,人們存在明顯意見分歧。
美國民主黨議員集體對拜登政府“犧牲價值觀”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接受美媒采訪時更是表示,希望拜登和莫迪談話時能夠關心“在印度教徒占多數的印度,如何保護少數的穆斯林群體”。奧巴馬甚至警告莫迪政府稱,若其不能很好地“保護穆斯林”,那么印度未來將會陷入分裂。印人黨政府高層立刻就批駁了奧巴馬的這一言論,印度防長拉吉納特和財政部長西塔拉曼反擊稱這是美國的“人權說教”。
而在印美兩國的智庫圈,人們同樣有激烈爭論。印度戰略界很多人懷疑美國“居心不良”——美國在2021年新冠疫情肆虐時面對印度的求助態度冷漠,又怎么可能在如今誠心幫助印度崛起?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界普遍質疑,拜登政府將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依托放在印度身上,是否是明智之舉。長期主張印美結盟的美籍印裔專家阿什利·泰利斯與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南亞問題專家丹尼爾·馬基都曾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發文,告誡美國政府不要對印度期望太高。阿什利·泰利斯稱,華盛頓在新德里下了一個“糟糕的賭注”,新德里會從華盛頓獲取各種各樣的好處,但它“永遠不會卷入華盛頓與北京的對抗”。在印度國內,印度知名戰略學者拉賈·莫漢和桑賈亞·巴魯也在爭論印度站隊美國是否明智,前者主張印度身心都要“融入西方”,甚至應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后者則主張印度還是要注重“套路”,應將印度和美國的防務軍工合作當作是簡單的商業合作,而不是戰略上的投靠。
莫迪對美國的戰略“投靠”同樣引起了俄羅斯的不滿。6月29日,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主動同俄羅斯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通電話介紹莫迪的美國之行。6月30日,莫迪更是主動要求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電話會談,向普京介紹他的美國之行。然而,俄羅斯國家安全理事會副主任梅德韋杰夫在7月3日接受俄媒采訪時就直言不諱地批評道,“新德里有權追求基于其國家利益的獨立外交政策,但其與華盛頓‘調情時,不要損害俄印關系”。
對中國來說,印度當然有權追求自身的外交政策,只是印度與美國發展關系時,同樣不應將其建立在損害中國利益的基礎上。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有關莫迪此次訪美的提問時已表明中國的態度:中方一貫認為國與國之間的軍事合作不應當破壞地區的和平穩定,不應當針對第三方,更不得損害第三方的利益。我們希望有關國家能為增進地區國家之間的安全互信,維護地區穩定多做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