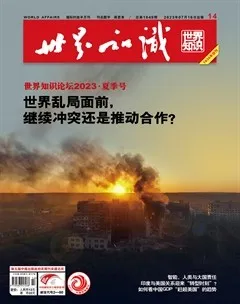“新華盛頓共識”能否取代“華盛頓共識”
鐘飛騰

2023年4月27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宣告“華盛頓共識”死了,提出了一套“新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主張。圖為沙利文。
2023年4月27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了一場題為《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演講,在演講中沙利文正式宣告“華盛頓共識”死了,提出了一套“新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主張。這是一項具有轉折性意義的重大宣言,其歷史地位可能堪比1947年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的馬歇爾計劃,或者1971年尼克松宣布的新經濟政策。這也是美國官方首次承認流行幾十年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是錯誤的。
“華盛頓共識”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1989年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工作時構造的術語,概括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主導推動的十項經濟政策——核心是放松管制、貿易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實行小政府,用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上世紀90年代以后,“華盛頓共識”風靡全世界,廣泛深刻地影響了全球的面貌,當然也波及美國自身的政治經濟體系以及中美關系的發展。
沙利文眼中美國面臨的幾大挑戰
在演講中,沙利文概括了美國面臨的四項根本性挑戰。
第一項是美國制造業的衰落。這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但沙利文在演講中卻將美國制造業遭遇的問題與流行數十年的經濟理念,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聯系在一起。沙利文強調,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這套政策主張有兩個錯誤的假設:一是錯誤認為市場總是能夠高效且多產地分配資源,但實際上在市場效率的引導下,美國戰略商品的行業和就業機會都被轉移到了海外;二是錯誤認為所有的增長都是好的增長,其結果是不區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增長,致使半導體和基礎設施等重要部門萎縮,金融部門享有特權。正是在其錯誤的引導下,美國的工業能力遭受重創。
第二項挑戰指向中國。沙利文認為,美國過去相信將中國納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通過更深層次的經濟一體化建設,會讓中國接受美國所謂的“自由”“民主”等價值理念,并變成像美國那樣的市場經濟體,遵循美國制定的規則。沒想到,中國的發展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美國對此失去了控制力。不僅如此,經過幾十年的貿易自由化,美國突然發現,在很多產品領域,美國事實上更依賴中國。在美國看來,這種依賴關系對美國的經濟地位和地緣政治不利,美國正進入一個越來越不受其主導的新環境,其突出特征是經濟和安全的互動前所未有地深入。
第三項挑戰是氣候危機日益加劇,公正高效的能源轉型迫在眉睫。美國民主黨政府重視氣候變化問題,不僅僅是出于“全球正義”的想法,也是將氣候變化視作一項新興產業,是美國抵御新興市場國家彎道超車的必爭領域。
第四項挑戰則是貧富差距以及由此引發的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破壞。在這里,沙利文再度批評了“華盛頓共識”的假設,認為貿易成果事實上并沒有惠及美國的大量勞動人口。“華盛頓共識”所賴以存在的“涓滴經濟學”(通過減稅和減少政府干預來激勵生產、創新和投資)政策,反而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同時,沙利文不忘再一次抹黑中國,認為對華貿易不利于美國,并承認對中國崛起的效應估計不足。
沙利文眼中美國面臨的四大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恰好證明了中國發展道路的正確性。如果中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聽信“華盛頓共識”,恐怕難以取得今天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兩大奇跡;如果沒有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作為對照,今天美國政府也不會反思自己,更不會否定美國30多年來走過的道路。
“新華盛頓共識”新在何處
沙利文主張的“新華盛頓共識”也包括四項主張。
第一,要求美國政府介入產業發展,實施新型產業政策。過去兩年,拜登政府已有多位高官呼吁,美國政府要大幅度介入經濟發展。拜登政府上臺以后,先后通過了《芯片及科學法案》《降低通脹法案》《兩黨基礎設施法案》等,標志著美國新型產業政策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果。
第二,與所謂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構建強大、有韌性和領先的技術工業基礎。沙利文提及的伙伴包括歐盟、加拿大、日本、韓國和印度。目前,美國已經和一些伙伴簽署了深化關鍵礦產供應鏈合作協議,并商定協調半導體激勵措施等。此外,沙利文還提及,美國要打破此前只將發達經濟體視作美國最重要伙伴關系的見解,視領域的需要拓展合作伙伴,可將安哥拉、印尼和巴西等國納入美國的合作伙伴。
第三,更新國際多邊經濟制度,核心是將中國排除在“印太經濟框架”之外。
第四,用“小院高墻”保護美國的基礎性技術,目的同樣是將中國排除在外。
沙利文提出的前兩項主張有一定的理論色彩:一是重新定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與“華盛頓共識”削減政府作用不同,“新華盛頓共識”的首要特征是擴大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二是重新定義經濟與安全的關系,即通過由美國財長耶倫提出的“友岸外包”等做法,減少與中國的經濟聯系,遲滯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后兩項主張實際上是美國“新華盛頓共識”戰略更為具體的操作手法。
支撐“新華盛頓共識”這一政治戰略的經濟學是耶倫建構的。在2022年1月舉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耶倫將拜登政府的經濟增長戰略命名為“現代供給側經濟學”,其特征是優先考慮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公共基礎設施、研發和投資。耶倫于今年3月在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所發表的一次講話中,強調“現代供給側經濟學”可突破勞動力供應增長的限制,最終有助于減輕美國種族和經濟的不平等。

2022年9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出席英特爾公司在俄亥俄州新半導體工廠的奠基儀式。
耶倫還強調,“現代供給側經濟學”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的“供給側經濟學”,后者通過積極的放松管制和減稅來促進私人資本投資。在耶倫看來,對資本大幅減稅并沒有實現承諾的收益,放松管制也不利于環境保護,因而舊的供給側經濟學在促進增長方面是一個失敗的策略。由此說明,耶倫否定了“華盛頓共識”的經濟理論基礎。
作為一名主要負責國家安全問題的官員,沙利文選擇在布魯金斯學會陳述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顯示出與前政府不同的策略。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時期,美國負責國家安全或者國際經濟事務的官員選擇闡述政策的場所,通常都是共和黨內對華不太友好的機構。而民主黨執政后選擇發表政策的場所,傳統上與中國的關系還不錯,拜登政府高官選擇這些與中國關系不錯的機構發表演講,仿佛是有意改善同中國的關系,但實際所釋放的信息仍是在新的政經框架內調整美國經濟政策以打壓中國,只不過更具欺騙性。
能否重塑中國的外部環境
也有一種論調稱,使用“新華盛頓共識”一詞表明,美國政府并不愿意完全放棄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式,加大政府介入并不改變自由市場這一基礎,因而美國政府仍存在低估市場破壞力的可能。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可·盧比奧最近撰文指出,雖然冷戰后的共識已經死了,但是誰能取代它還不確定;沙利文提出“新華盛頓共識”,并不意味著民主黨人吸取了教訓。而且,美國的盟友和伙伴,也并非全盤接受“新華盛頓共識”。例如,歐洲就擔心美國設計的新全球經濟架構更有利于美國企業和工人。
“新華盛頓共識”標志著美國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的系統性調整,中國將面臨與改革開放時期不同的外部環境。自美國提出和遵循“華盛頓共識”的30多年來,中國走出了一條新路,取得非凡的成功。“新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內容,反而增強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力。
中國的崛起是驚人的。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按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1990年前后,也即威廉姆森提出“華盛頓共識”時,中國經濟總量占美國的比重約7%,而目前已超過70%,膨脹了10倍。2021年,美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為24%,比1990年下降了約4個百分點。而同一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上升了15個百分點,2022年為18%。
再以貨物進口為例,在形成“華盛頓共識”的上世紀80年代,美國貨物進口占世界的比重平均為17%,2000年前后達到20%,但此后占比下降,2022年為13%,已低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中國貨物進口占世界比重曾長期低于2%,加入世貿組織后才開始起飛,2022年就幾乎和美國齊平。加入世貿組織被普遍認為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特別是貨物貿易飛速增長的重要原因。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數據顯示,2002~2008年,中國貨物出口額年均增速為27.3%。這在世界貿易史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爆炸式增長。
在被沙利文視作第一大挑戰的制造業上,中國的表現更驚人。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以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2021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為2.4萬億美元,是2001年的1.4倍。從橫向來看,美國的增速好于主要的發達國家,如日本、德國,低于新興經濟體,如韓國、印度和越南。2001年以來,越南制造業增加值增長4倍以上,印度約為3.5倍,韓國約為2.3倍。但所有這些新興經濟體的表現均不如中國,在制造業增加值方面,中國已是龐然大物。以現價美元衡量,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高達4.9萬億美元,是美國的2倍、德國的6倍、韓國的10倍、印度的11倍以及越南的50多倍。
提出“新華盛頓共識”的目的之一是重塑中國的外部環境。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的規模、發展勢頭和政策取向,這一進程并不容易。中國深嵌全球體系之中,與各方利益關聯緊密。中美經貿關系已不像30多年前更多由美方驅動,未來發展將受到整個全球秩序轉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