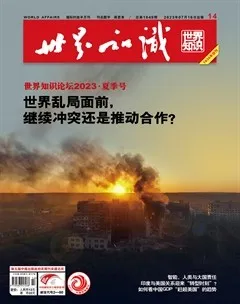漸入佳境的阿拉伯外交

牛新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在最近一波中東緩和潮中,阿拉伯國家表現特別搶眼,不僅彌合了內部的裂痕,而且改善了同周邊非阿拉伯國家的關系,還維護了同域外大國的平衡,增強了外交自主獨立性。阿拉伯國家的做法不僅使其在地區政治中左右逢源,也在全球政治中顯示出了四兩撥千斤的巧勁。
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在人口、資源、國家數量上享有絕對優勢,但是受國內政治動蕩和國家間矛盾影響,長期以來未能展示相應的整體政治影響力。特別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多個阿拉伯國家陷入內亂,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國家則快速介入該地區,阿拉伯國家與非阿拉伯國家間的關系急劇惡化,雙方的地區影響力出現顯著變化。在阿拉伯國家內部,沙特與卡塔爾因為在對待政治伊斯蘭和對待伊朗等問題上分歧嚴重,2017年沙特、埃及、阿聯酋、巴林四國與卡塔爾斷交,海合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內部分裂。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風險同步上升,阿拉伯國家困境愈益突出,內憂外患也讓地區國家開始反思。
最近三年,阿拉伯國家的外部環境大為改善。美國在中東持續進行戰略收縮,影響下降,中國、印度、俄羅斯的影響相應增大,大國關系在中東呈現多極化的態勢,阿拉伯國家合縱連橫的空間驟然增大。“阿拉伯之春”后相關國家長達十年之久的內戰、動蕩沖頂回落,政治伊斯蘭對阿拉伯國家的威脅大幅下降,主要阿拉伯國家對政權的控制力明顯提升,阿拉伯國家的自信心增強。同時,在全球層面,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對付中國、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美國的重點目標則是伊朗。阿拉伯國家成為美國拉攏的對象,議價能力攀升。
沙特等主要阿拉伯國家抓住機遇,積極調整外交政策,國際處境從四面楚歌變為左右逢源。首先,阿拉伯國家彌合了內部分歧。2021年1月海合會峰會上,沙特、阿聯酋、巴林和埃及四國宣布與卡塔爾恢復外交關系,長達四年的卡塔爾斷交危機結束。2023年5月阿盟外長級特別會議宣布,恢復敘利亞的阿盟成員國資格,阿盟22個成員再次大團圓。其次,阿拉伯國家改善了同周邊所有非阿拉伯國家的關系。2020年9月,阿聯酋、巴林與以色列簽署《亞伯拉罕協議》,拉開阿以關系緩和序幕。2021年5月,土耳其代表團分別出訪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國家與土耳其的關系解凍。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兩國同意恢復外交關系。第三,阿拉伯國家塑造了同美、中、俄等大國的平衡關系。阿拉伯國家不再僅僅圍繞著美國轉,而是發展多元外交關系,在美國、歐盟、俄羅斯、中國之間尋求新平衡。在油價問題上,阿拉伯國家同俄羅斯聯手制衡美國;在經濟問題上,阿拉伯國家不顧美國反對,深化同中國的合作;在安全問題,阿拉伯國家則持續依靠美國。
在大國間搞平衡對阿拉伯人來說并不陌生,數千年來中東一直是大國博弈的重要場所,阿拉伯人早已習慣周旋于大國之間,以獲取最大的利益。盡管美國仍然是在該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域外國家,但是一定程度上美國也不得不接受阿拉伯國家的自主性、多元化外交,收起其霸權國家的傲慢。拜登曾指責沙特是一個“賤民國家”,拒絕同沙特王儲接觸,但是2022年7月受油價困擾,又不得不親自去沙特拜訪王儲。今年3月中國斡旋沙特與伊朗復交后,美國接連派出中央情報局局長、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三位高官訪問沙特。據說在拜登政府內部有一個“中東例外”的做法,也即美國可以干涉全球“人權”問題,但是中東是個例外,因為美國在戰略上需要中東,“人權”問題可以擱置一邊。
不過,雖然風生水起的外部環境改善成為阿拉伯國家政治的一大亮點,但是,2010年席卷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卻是內生性的,其根源是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2019年,蘇丹、阿爾及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四個阿拉伯國家再度爆發大規模街頭示威,主要原因還是國家內部的治理問題。近年來,阿拉伯國家的政局趨穩,但國家治理模式并沒有出現實質性變化,福利國家、國家資本主義、依賴外國軍事援助仍然是多數阿拉伯國家的主要特征。未來,如果阿拉伯國家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國家治理模式,下一場阿拉伯危機只是時間、方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