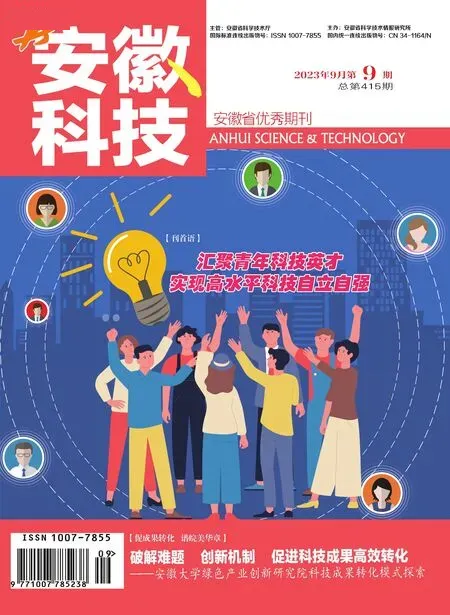合肥市科技服務業的發展現狀及對策建議
文/鄒振宇 屈 昊 孫民裕 吳 琦 楊 明 邱 爽
[1.合肥科創蜀山科學島運營管理有限公司;2.安徽省科技成果轉化促進中心(安徽省科學技術研究院);3.合肥市科學技術局;4.中共安徽省委黨校(安徽行政學院)]
合肥市堅持下好創新“先手棋”,扎實推進科技創新“栽樹工程”,大力實施“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戰略,不斷深化科技服務工作,將科技創新這一“最大變量”轉化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優增量”,綜合創新水平穩步提升。2022 年,合肥市躋身全球科技集群第55 位、全球科研城市第16 位,分別提升18 位和4 位。
一、合肥市科技服務業的發展現狀
合肥市科技服務業發展提速增效,已形成一定規模,成為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強省的重要支撐。
1.科技服務機構數量快速增長
2022 年,合肥市共有各類科技服務業企業約400家,服務市場主體約36 萬戶;建成21 家中試基地,依托大院大所自建或共建服務機構研發平臺35 個;培育市級及以上孵化器107 家(其中國家級24 家),眾創空間122 家(其中國家級28 家);創建30 余家省級及以上技術轉移示范機構。
2.科技金融活力不斷增強
合肥市結合科技企業“高技術、輕資產”的特點,推出覆蓋科創企業成長全周期的金融產品,打造了以“天使基金”“種子基金”為代表的基金叢林,創新開發“科大硅谷人才貸”等科技信貸產品,承接專利質押貸款,破解科技型企業融資難問題。
3.科技服務人才隊伍建設力度加大
依托“中科大系”“中科院系”等高校院所資源,引進和培育高層次科技服務人才,提升科技中介行業服務水平和質量。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通過開展自然科研系列職稱自主評審等舉措,累計匯聚創新人才超800 人,孵化企業超310 家,2018—2022年連續5 年入選安徽省發明專利百強榜。合肥市開展技術服務經紀人培訓,促進科技成果“三就地”,已累計培育初級技術經紀人近300 人。合肥市“科技成果轉化專班”實現了全員“持證上崗”,科技服務向更廣闊領域延伸。
二、合肥市科技服務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與北京、上海、廣東等國內先發地區相比,合肥市急需在延長和增強科技創新服務鏈上下功夫,集聚核心要素資源。
1.市場化運作不暢,服務機構規模小、水平低
合肥市大部分科技服務機構是從高校院所和政府單位剝離出來的,“官辦”和“半官辦”的色彩較為明顯,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科技服務經費主要來自于財政撥款,缺乏競爭意識和市場意識,主觀能動性不強。科技服務機構整體規模較小,注冊資金基本上在500 萬元以下,從業人員大多在20~50 人。科技服務機構同質化嚴重,缺乏對市場主體需求的深度挖掘,細分領域的專業服務能力較差,滿足于做“專利申請人”“信息咨詢人”,與培育科技初創企業、科技成果轉化落地等現實需求的差距較大。
2.人才隊伍建設不足,從業人員數量少、能力弱
合肥市科技服務業的從業人員數量、質量、結構等方面存在不足。2021 年,合肥市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約5.66 萬人,占當年就業人員的3.6%。由于科技服務業從業標準還未確立,入行門檻相對較低,缺乏有效的考查考核制度,導致相關人員服務水平參差不齊。人才選拔和激勵機制缺乏創新性,青年人在技術、法律領域上的領悟力表現較為突出,在管理和市場化運作中缺乏實踐經驗,在考評考核時仍然存在重資歷、輕能力的亂象。
3.服務體系建設不健全,協同合作能力弱、效果差
合肥市缺少類似泰坦科技、藥明康德、百普賽斯、華大基因等的知名龍頭服務機構,對中小型服務機構的示范性較弱。線上科技服務平臺建設滯后、涵蓋內容不全面,入駐機構數量偏少,科技資源共享率不高。線下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等科研平臺服務重點產業能力還不強。總之,合肥市科技服務業處于邊實踐、邊探索階段,產業集群化程度不成熟,沒能形成高效的運作體系。
4.資金支持力度不大,科技金融撬動性不強
合肥市雖然已采取政府貼息、建立風險補償基金、對科技擔保機構政策扶持等措施來降低金融機構投融資風險,但仍然存在風險補償形式單一、風險補償資金來源少、覆蓋面不足等問題。合肥市政府創業投資基金很多以直投基金形式進入競爭領域,由于資金量大、成本低、比市場創業投資基金更加具有競爭力,一直存在與社會資本爭利現象,不利于盤活社會資本、激發民間投資活力。
三、促進合肥市科技服務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1.完善“政府+市場”運作機制,把穩發展方向
(1)完善政府政策支持體系,做好頂層設計。建立健全市委科創委統籌推進機制,在財政稅收方面,制定出臺科技服務行業的稅收優惠、基金扶持政策,用真金白銀助推科技服務業發展。在人才引進政策方面,制定更加有效的“專、精、特”急需的科技服務業人才引進計劃,圍繞人才安居、企業穩崗、人才培養等方面細化落實,推動人才結構更加優化、人才資源總量穩步提升、能力顯著提升。在激勵政策方面,多部門聯合制定高效、便捷的長效激勵機制。要充分利用股權激勵、現金獎勵、成果表彰等措施激勵真抓實干、成效顯著的科技服務主體,調動相關主體的積極性、持續性和創造性。
(2)堅持企業是科技服務市場主體。健全“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科技型骨干企業—科技領軍企業”培育梯隊機制,充分依托眾創空間、科技企業孵化器、重點實驗室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平臺積極培育、扶持一批標準化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推廣合肥市“創業創新服務券”,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業開展研發創新、成果轉化等服務活動。積極探索科技招商新模式,既招引龍頭企業,又招引優質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平臺、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打造科技服務業廣袤森林。
(3)建立行業組織管理機制。成立科技服務業協會,建立健全科技服務業行業標準。明確科技服務機構資質認證、準入門檻,著力解決當前科技服務機構“亂、散、小”等問題。制定權責清晰的服務流程,規范科技服務機構操作,推動科技服務標準化。制定科技服務機構黑白名單,加大對“黑機構”的整治力度和對“白機構”的扶持力度。完善科技服務業從業人員職業資格考核制度,持證上崗。
(4)優化科技服務業發展環境。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專利審查等法規,加強多部門協同配合,以審查授權、行政執法、司法保護、仲裁調解、行業自律等關鍵環節為抓手,營造尊重創新、鼓勵創新的良好氛圍,為科技服務發展保駕護航。
2.組建復合型人才隊伍,占據發展制高點
(1)在人才引進工作上傾心。聚焦科技服務機構的用人需求,制定重點人才招引目錄,精準引才。組織專班高頻次“走出去”挖掘科技服務業高層次人才,推動校企合作,常態化開展“智匯合肥”線下高校行、線上云聘會等活動,開通人才來肥的快車道。依托“科大硅谷”“中國聲谷”等平臺載體,完善“揭榜掛帥”“定向委托”等重大科技項目組織管理方式。健全人才引進政策,優化完善薪酬待遇、項目經費、醫療保障、安家費用等配套政策,解決人才的后顧之憂。
(2)在人才培育工作上悉心。依托國家技術轉移人才基地,加強與國際知名機構合作,成立合肥技術轉移學院,培養一批知背景、懂科技、懂市場、善管理、具有創新思維的本土化專業人才。對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商學院資源,加大科技服務培訓基地建設力度,制定不同層級、不同內容的培訓方案,針對性地開展科技服務人才培訓工作,充實技術經紀人和技術經理人隊伍。持續完善技術經紀人信用積分評定機制,組建市場化的技術經理人事務所。
(3)在人才交流評價上盡心。建立人才柔性流動機制,實現人才資源共享。推行科技人員“雙聘制”,鼓勵高校院所科技人員到科技服務機構交叉任職。完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以能力、實績、貢獻為評價導向,打破原有不合理的制度藩籬,建立健全靈活的、公平的人才評價體系,暢通人才晉升渠道,激發科技人員干事創業的熱情。
3.完善科技服務業體系,構建協同服務大格局
(1)精心培育龍頭科技服務機構,打造一流科技服務業品牌。支持行業協會和政府引導服務機構通過并購或外包方式做大做強,鼓勵規模大、實力強的科技服務機構面向高新區、特色產業基地等產業集群,圍繞“芯屏汽合”“集終生智”等產業領域快速布局,開展專業化、多元化的科技服務,打造業務品牌。引入競爭機制,加強骨干科技服務機構科學化管理,定期對國家級技術轉移示范機構、孵化中心等科技服務機構開展績效評估,量化打分,獎罰并舉。對少數成效不明顯的機構要督促整改,提升相關機構服務水平和競爭力。
(2)構建一體化的創新要素集聚平臺,優化科技資源配置。借鑒上海、深圳等地科技服務平臺建設經驗,聚焦量子通信、智能汽車制造、生物醫藥等優勢產業,與高校院所共建科技成果轉化中心或產業技術研究院,推動人才、土地、資金等要素聚集,依托工業互聯網,打造匯聚各類創新要素的優勢平臺,促進科技成果“落地成金”。
(3)發揮科技服務業產業集群引導示范作用。充分發揮一帶(高新技術產業帶)、三區(蜀山區、高新區、經開區)、多園(中國聲谷·經開信創產業園、合肥醫藥健康產業園等)的產業集群作用,圍繞創新鏈的各個環節培育、引進科技服務機構,加快促進“政產學研用金”一體化大格局建設。一方面,摒棄原有的“單兵作戰”發展思路,加強產業主體的地理空間集聚,吸引國內外優秀科技服務企業入駐,加強機構與高校、科研院所、知識產權社會組織、金融機構等主體的常態化溝通和協作,促進科技服務機構的落地、生根、結果。另一方面,加強產業主體的虛擬空間集聚,通過互聯網網上交易平臺和常態化合作契約,培育、擴展合肥高端科技服務業“朋友圈”和功能群,打造跨越物理邊界的虛擬產業園和產業集群,實現創新型產業集群和科技服務業集群共同聯動、共同促進、共同發展。
4.切實加大資金扶持力度,用好科技金融活水源
(1)推動科技金融服務機構擴點增面。鼓勵有能力的商業銀行在科技園區、大型眾創空間等金融需求大的區域成立科技銀行,加大對中小型科創企業的早期投資。引導民間資本成立金融擔保機構、科技型小額貸款公司,豐富金融服務類型。
(2)做大做強科技金融產品體系。加強財政與金融聯動,豐富科技創新貸、科技小額貸等金融產品,確保資金能覆蓋企業成長發展全周期。打造科技基金叢林,面向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做到投早投小、投準投好。增加知識產權質押、股權質押、應收賬款質押及信用擔保、股票上市、企業債券等方式,為企業提供特色融資服務。
(3)差異化制定業務準入門檻。制定信用等級評定體系,搭建知識產權評估體系,將科技型企業的專利、知識產權等納入擔保質押范圍,采取多種質押物組合方式提供融資,暢通科技型企業“技術流”轉化為“資金流”的渠道。
(4)健全科技金融風險補償機制。加強政府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采用“政府背書”方式,設立“風險池”轉移部分金融機構風險,杜絕金融機構“懼貸”現象。通過稅收優惠降低投資風險,如實施種子基金投資稅收抵免政策來實現科技保險補償功能,鼓勵保險機構完善科技保險產品和服務,提高科技企業保險參與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