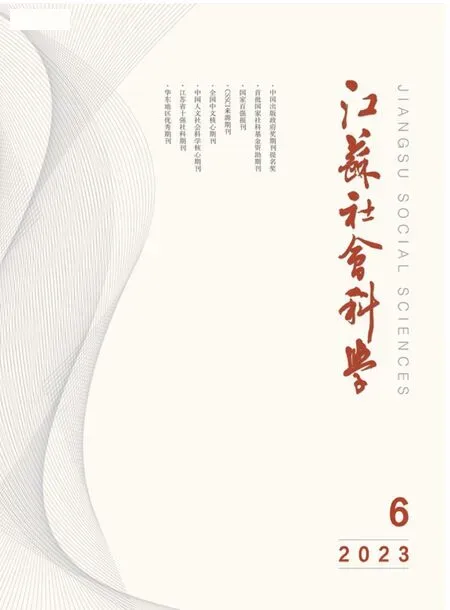柳如是“景觀”的塑造與晚明到晚清的文化嬗變
張娜娜
內(nèi)容提要 晚明人性解放思潮催生了才女品藻的名士化傾向和“女務(wù)外學(xué)”的女性觀,明清易代的政治失序更激發(fā)了時人對“女英雄”的想象。在此背景下,柳如是以名士的風(fēng)神氣度及書寫模式跨越性別界限,擴(kuò)大性別空間,成為男性世界中的文化“景觀”。男性士人在審視柳如是的過程中營造了“閑賞”的美感生活和情藝文化,并在“名妓-名士”的轉(zhuǎn)喻系統(tǒng)中,借女性聲音進(jìn)行自我人格設(shè)計,彰顯“深情”與“忠君”的文化理念。晚清民國,知識分子重新塑造柳如是“景觀”及其背后的國族記憶,并融入了革命話語、女權(quán)思想和“恢復(fù)中華”的民族精神。柳如是同易代士人的相互“觀看”,建構(gòu)涉及性別互動、士人出處、隱喻詮釋等問題,呈現(xiàn)了晚明到晚清的文化嬗變。
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對柳如是贊賞有加,認(rèn)為她作為“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能有“我民族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4頁,第75頁。,實(shí)屬難得。從明季詩詞、野史到晚清的報刊、小說,柳如是被不斷地塑造、建構(gòu),成為“俠女名姝”“文宗國士”的化身。學(xué)界關(guān)于她的研究涉及其詩詞創(chuàng)作、性別意識、社會交往等[2]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 年)以錢柳姻緣為線索,考察明清士人交往與生存境遇;孫康宜的《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圍繞“情與忠”的話題考察了詩體、詞體之變奏,以及柳如是的精神世界。其他相關(guān)代表性研究還有方秀潔,魏愛蓮的《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高彥頤的《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等。。值得關(guān)注的是,晚明時期,柳如是于“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3]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4頁,第75頁。,是男性士大夫經(jīng)營情藝生活和彰顯文人文化的盟友,也是他們進(jìn)行自我人格設(shè)計的媒介。時至晚清,柳如是畫像再度為知識分子觀摩和題寫,他們借此戲擬、模仿晚明歷史,詮釋社會、性別問題并展開對自我的檢視與反思,反映出晚清民初“恢復(fù)中華”的民族精神和女界革命的“維新”思想。在“名士-名妓”這一轉(zhuǎn)喻系統(tǒng)中,柳如是成為男性視域下的一道文化“景觀”,而面對景觀時,人們總會“攝取自己以為最主要、最具代表性、最符合自己需要的印象”[1]葛劍雄:《序》,安介生、周妮:《江南景觀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頁。。因此,作為文化“景觀”的柳如是,始終處在復(fù)雜、動態(tài)的變量聯(lián)系之中,這些變量包括種族、階層和性別等因素[2]伊恩·D.懷特:《16世紀(jì)以來的景觀與歷史》,王思思譯,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透過柳如是“景觀”被觀看、被建構(gòu)的過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晚明至晚清的文化嬗變。
一、雙性名士:柳如是“景觀”的生成
晚明時期,雙性審美特質(zhì)和“女務(wù)外學(xué)”之說備受關(guān)注,才女品藻更呈現(xiàn)出名士化傾向[3]比如,毛奇齡稱徐昭華“不是小鬟頻乞試,那知閨閣有陳思”;女詩人吳琪尤好大略,被譽(yù)為“嶺上白云朝入畫,樽前紅燭夜談兵”;錢謙益稱沈婉君詩“無脂粉氣”,“林下之風(fēng),閨房之秀,殆兼而有之”,都凸顯了女性的名士風(fēng)韻。。陳繼儒概括道:“名妓翻經(jīng),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4]秦望龍編著:《清言小品菁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也就是說,跨越性別、社會身份約束的言行,成為文人士子欣賞的“有致”生活面相。約翰·伯格在《觀看之道》中說,構(gòu)成女性身份的兩個因素是其內(nèi)在的“觀察者”與“被觀察者”[5]約翰·伯格:《觀看之道》,戴行鉞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63頁,第63頁。。對于柳如是來說,生活在男性主導(dǎo)的社會文化空間中,她“必須觀察自己的角色和行為,因為她給別人的印象,特別是給男人的印象,將會成為別人評判她一生成敗的關(guān)鍵”[6]約翰·伯格:《觀看之道》,戴行鉞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63頁,第63頁。。柳如是“性機(jī)警,饒膽略”,她時常著男裝,在江南一帶清游、雅集,擴(kuò)大自己的交際范圍;她談兵說劍、豪宕自負(fù),有巾幗須眉之論;她用男性書寫模式感喟國變窮途,以刀劍意象表達(dá)家國情懷,是“競雄”[7]與柳如是身處同一時代的徐燦、劉淑、顧貞立、李因等才女都有反映世末亂離、憂思國難之類超越閨閣的言語。柳如是的特殊之處在于,她以北里章臺之身而具復(fù)楚沉湘之志,集名士與名妓身份于一身。的典范。一方面,內(nèi)在的“觀察者”身份促使柳如是按照男性審美調(diào)整自己的言行,獲得男性的青睞和社會資源;另一方面,以柳如是為代表的女性文人也在思考己身與世變之關(guān)系,挑戰(zhàn)了性別界限、拓展了性別空間。
1.行旅文化中的漫游與造景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qū)旅游業(yè)繁盛。謝肇淛說:“夫世之游者,為名高也。”旅游活動不僅開拓心胸、陶鑄性靈,更是士大夫社交、娛樂的方式,故被譽(yù)為“名高”之事。士大夫甚至打造專屬的“游道”,以獨(dú)特的品味來彰顯自身的文人身份。柳如是離開歸家院之后,如同諸多名士一般,乘畫舫輾轉(zhuǎn)于吳越之間。她在船上讀書、寫字、賦詩、作畫,廣交才媛名士。船,是一個浮游的、無拘束的存在,無限性是其文化特征。畫舫,則是柳如是身份的寫照與隱喻,她同畫舫一起,成為江南山水中的一道“景觀”。
柳如是名聲大噪于崇禎五年(1632)。是年,她赴松江畬山,為陳繼儒賀壽。陳氏所居之處,亭榭數(shù)座、古梅百株。柳如是身量小巧、束腰緊身、亭亭玉立于“晚香堂”中,成為陳子龍、宋轅文、李存我等名流“凝視”的對象。陳繼儒作《贈楊姬》,詩歌“少婦顏如花,妒心無乃競。忽對鏡中人,撲碎妝鏡臺”[8]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五,明末湯大節(jié)簡綠居刻本,第4頁。,寫的是柳如是在周道登家的不幸遭遇。“顏如花”“對鏡梳妝”既是閨怨詩的傳統(tǒng)元素,也是柳如是“被觀察者”身份的表現(xiàn)。
崇禎十一年(1638),柳如是赴杭州汪然明之邀,登入畫舫“不系園”,這是眾多騷人韻士雅集的場所。她“扁舟一葉放浪湖山間,與高才名輩相游處”[9]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上),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頁。,尋覓“殷勤為其啟金屋者”。紅妝翠微間,柳如是與西湖煙水融為一體,成為眾人傾慕、游觀的對象。汪然明寫柳如是:“明妝憶昨艷湖濱,一片波光欲蕩人……老奴愧我非溫嶠,美女疑君是洛神。欲訪仙源違咫尺,幾灣柳色隔香塵。”[1]汪汝謙:《春星堂詩集》卷三,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當(dāng)時,需得身為“名流”“知己”或“美人”,才能夠進(jìn)入“不系園”,柳如是兼而有之,甚至還是神女和俠女。人們往往通過景觀想象構(gòu)建與事物的關(guān)系、重塑自身的社會角色。男性文人爭相“觀看”柳如是,或從其身上看到美色而希望貯之金屋,或于其身上投射自身理想并心生敬意。
柳如是游賞西湖的作品主要收錄在《湖上草》中。杭州濃縮了晚明流韻,聚集了各方游客,而女性既是西湖景觀的一部分,又是西湖景觀的制造者。柳如是寫道,“西泠月照紫蘭叢,楊柳絲多待好風(fēng)”[2]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頁,第67頁,第71頁。,其中,“紫蘭叢”“楊柳絲”指名媛才女;“邀人畫舫留鸚鵡,游女新綾織鳳凰”[3]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頁,第67頁,第71頁。,則寫佳人盛飾出游的場景;“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4]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頁,第67頁,第71頁。寫桃花得西湖美人氣韻而分外嬌媚,為世人激賞。可見,女性在杭州氣韻的塑造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琴詩為伴、漫游西湖是柳如是與一眾才女有意識的舉動,“她們顯然深刻地體察到自己身為女性,出現(xiàn)在杭州西湖,對這個城市的風(fēng)格與景觀有多大的影響”[5]胡曉真:《明清敘事文學(xué)中的城市與生活》,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頁。。可以說,她們既在賞玩,又在造景。
2.跨越性別的“文化展示”
馬克夢指出,“所謂的才子佳人是包含彼此的,其中一方具有另一方的相貌,或呈現(xiàn)另一方的氣質(zhì),男性可以把心目中更為完美的自己投射給女性”[6]馬克夢:《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jì)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guān)系》,王維東、楊彩霞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頁。。在這一互映性結(jié)構(gòu)中,柳如是從著裝到談吐皆呈現(xiàn)出“學(xué)士化”“名士化”的風(fēng)神氣度,這是一種跨越性別的“文化展示”。《河?xùn)|君小傳》這樣記載柳如是:“幅巾弓鞋,著男子裝,口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fēng)……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專國士名姝之目。”[7]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上),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著男服迎客在當(dāng)時并不少見,柳如是的特殊之處在于她獨(dú)特的氣宇風(fēng)神與懷抱胸襟,這促使她成為一道“文化景觀”,乃至男性士人心目中更為完美的性別形象。
柳如是歸錢謙益后,亦“常衣儒服,飄巾大袖,間出與四方賓客談?wù)摗盵8]黃承增輯:《廣虞初新志》卷二六,嘉慶癸亥寄鷗閑舫刊巾箱本,第14頁。,被稱作“柳儒士”。鈕琇在《觚剩》中稱其“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帔,出與酬應(yīng)。否則肩筠輿訪于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即英賢宿彥,莫能屈之”,錢謙益直呼其“高弟”“良記室”[9]鈕琇:《觚剩》卷三,康熙壬午臨野堂刊本,第6頁。。她流連文宴,接席雄談,儼然儒士、名士。王國維曾題寫柳如是《湖上草》:“幅巾道服自權(quán)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兒太唐突,薊門朝士幾須眉。”[10]谷輝之輯:《柳如是詩文集》,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xiàn)縮微復(fù)制中心1996年版,第256頁。柳如是帶給男性文人視覺與心理層面的沖擊,他們認(rèn)為“柳如是所擁有的,甚或多于自己,于是出于對己身‘匱乏’的焦慮,更渴望著柳如是”[11]嚴(yán)志雄:《牧齋初論集:詩文、生命、身后名》,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中國)2018年版,第45頁。。因此才說,柳如是是“景觀”,但又逸出“景觀”。
當(dāng)然,柳如是的男子氣度是由內(nèi)而外的,不僅表現(xiàn)在著裝打扮上,更滲透在其個人性情、文化藝術(shù)風(fēng)格之中。她具君子氣,以經(jīng)世自任、以天下為務(wù),喜縱橫之術(shù)、具文才武略。她的草書風(fēng)骨嶒峻、筆力雄健,見知于當(dāng)時,被程孟陽評為“書勢險勁”,亦被清人翁同龢譽(yù)為“鐵腕拓銀鉤”“奇氣滿紙”。幾社名士常常宴集于陸氏南園,這個文學(xué)兼政治團(tuán)體宴集具有時事座談會的性質(zhì)。柳如是多次參加南園雅集,經(jīng)名士政論熏習(xí),其本人亦被視為社員之一,其“天下興亡,匹‘婦’有責(zé)”的觀念逐漸成熟。
3.男性書寫模式和權(quán)力想象
世變之際,女子與國難的關(guān)系是男性文人一再吟詠的話題。反之,對于現(xiàn)實(shí)中的女性來說,男性亦是她們自我定義的一種方式。正如華瑋所言,“‘?dāng)M男’在為她們突破發(fā)聲困境的同時,還適可滿足她們的‘權(quán)力的想象’(illusion of power)”[1]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chuàng)作與批評》,“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147頁。。當(dāng)時女性文人的家國之論并不罕見,而柳如是除了以男性口吻營構(gòu)勇武的自我形象,還采用男性的書寫模式,甚至有《男洛神賦》這類直接“凝視”男性的作品。
柳如是《戊寅草》頗有云間派風(fēng)味,而云間派身為幾社旁系,本就擔(dān)負(fù)著匡時濟(jì)世的使命。柳詩超曠凌空、宏達(dá)微恣,被陳子龍贊為“絕不類閨房語”,認(rèn)為其“不謀而與我輩之詩竟深有合者”[2]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第24頁,第24頁,第30頁,第30頁,第73頁,第75頁。。此論體現(xiàn)出柳氏詩文對男性書寫空間的介入。“夏服左彎從白馬,鐃歌清徹比烏彈。千金元節(jié)藏何易,一紙參軍答亦難。我欲滎陽探龍蟄,心雄翻是有闌珊”[3]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第24頁,第24頁,第30頁,第30頁,第73頁,第75頁。展現(xiàn)了她心雄萬夫、探取龍蟄的豪情,并意欲成為一名身負(fù)弓箭、馳騁疆場的英武之士;“長空鶴羽風(fēng)煙直,碧水鯨文澹冶晴”[4]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第24頁,第24頁,第30頁,第30頁,第73頁,第75頁。中,她從直升的烽煙和遠(yuǎn)飛的仙鶴以及波濤與鯨鯊中,預(yù)見戰(zhàn)事兵禍的到來,這般慷慨正見其性別身份的游移以及對精神自由的追尋;在后金犯邊、國勢阽危之際,她贊頌、呼喚“杰如雄虺射嬰茀,矯如脅鵠離云倪。萃如列精俯大壑,翁如匹練從文貍”[5]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第24頁,第24頁,第30頁,第30頁,第73頁,第75頁。般抗敵救國的英杰;“丈夫虎步兼學(xué)道,一朝或與神靈隨”[6]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第24頁,第24頁,第30頁,第30頁,第73頁,第75頁。被《神釋堂詩話》評曰,“有雷電砰然、刀劍撞擊之勢,亦鬟笄之異致矣”[7]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補(bǔ)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0頁。,體現(xiàn)的正是她對自己人生的期許。
柳如是超越婉約秀雅的女子風(fēng)韻,表達(dá)世變當(dāng)頭,志同道合的共同悲感。比如,文人常借英豪廟碑書寫忠臣、英雄的悲劇命運(yùn)。柳如是承襲這一表達(dá)傳統(tǒng),寫道,“當(dāng)年宮館連胡騎,此夜蒼茫接戍樓。海內(nèi)如今傳戰(zhàn)斗,田橫墓下益堪愁”[8]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第24頁,第24頁,第30頁,第30頁,第73頁,第75頁。,以田橫五百士寧死不屈的壯舉激勵世人,呼喚孤忠勁節(jié)之士為國效力。時人評此詩:“脫盡紅閨脂粉氣,吟成先吊岳王祠。”[9]谷輝之輯:《柳如是詩文集》,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xiàn)縮微復(fù)制中心1996年版,第256頁。再如,她歌頌于謙“意氣吞龍荒,事業(yè)高云閣”,因其悲劇命運(yùn)而發(fā)出“灑淚空夕陽,英風(fēng)竟安托”的感喟,并于西湖之濱“慟哭霸王略”[10]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第24頁,第24頁,第30頁,第30頁,第73頁,第75頁。。此外,中國男性文人常以“女洛神”作為自己寤寐求之的理想女性形象,柳如是的《男洛神賦》則“顛倒傳統(tǒng)情詩的基樁”,寫自己訪求情郎的過程。她描摹“男神”風(fēng)姿,“泯滅男女詩人的傳統(tǒng)界限,打破陽剛陰柔的定見”[11]孫康宜:《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李奭學(xué)譯,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頁。。
總之,柳如是“牽動的欲望糾結(jié)、權(quán)力運(yùn)作,實(shí)則遠(yuǎn)遠(yuǎn)超過這種稍嫌‘簡略’的觀看之道”[12]嚴(yán)志雄:《牧齋初論集:詩文、生命、身后名》,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中國)2018年版,第44頁。。一方面,在男性文人眼中,柳如是游走于社會倫理規(guī)范的邊緣,其色、藝、才、情滿足了男性的文化需求,她士大夫般的氣節(jié)操守、胸襟境界、人文風(fēng)采亦是男性文人自我理想的投射。另一方面,在忠明的男性眼中,名妓的命運(yùn)是國家興衰的隱喻,正所謂“名姝失路,與名士落魄,赍志沒齒無異也”[13]李中馥撰,凌毅點(diǎn)校:《原李耳載》卷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6頁。。而對于男性的觀看,柳如是或許意識到,以男性裝扮和口吻抒情言志可適度緩解“己方以為才而炫之,人且以為色而憐之”[14]章學(xué)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頁。的焦慮。同時,柳如是對“名士”形象的塑造也使自己遠(yuǎn)遠(yuǎn)逸出“景觀”的范疇。
二、柳如是“景觀”與晚明文人文化
晚明時期,江南地區(qū)的文化精英階層在科考及第或踐行儒家德性之外,追求縱樂和炫耀性安逸,刻意營造美感生活。賞玩古董、珍藏書籍、游覽名勝、選妓征歌等都是士人經(jīng)營其美學(xué)生活的重要活動,圍繞著選妓征歌,出現(xiàn)了獨(dú)特的女色品賞文化。在此美學(xué)品味與文人文化的建構(gòu)中,柳如是等明季女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明中后期商人崛起的背景下,男性文人在觀看柳如是“景觀”的過程中,建構(gòu)了與富商巨賈附庸風(fēng)雅相區(qū)分的生活美學(xué);另一方面,男性士人借用柳如是之類的女性聲音進(jìn)行自我人格設(shè)計,呈現(xiàn)易代之際自我身份的復(fù)雜性。
1.“閑賞”之樂:美感生活的懸想與經(jīng)營
晚明時期,傳統(tǒng)社會的“四民分業(yè)”逐漸模糊,各階層的經(jīng)濟(jì)、文化行為趨同,尤其是商人的崛起,對文人精英群體的身份和地位造成一定的沖擊。因此,晚明文人致力于構(gòu)建一種不流俗的、超越官能的“看婦人的方法”。屠隆曾言:“登山臨水,曠望俯仰,必思佳麗。思佳麗必營樓臺,營樓臺必及聲色。嘲風(fēng)吟月必耽光景,耽光景必動才情,動才情必生歡戀。”[1]屠隆:《鴻苞集》卷三十八,茅元儀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刻本。由山水之美到佳麗之色,再到營建樓臺,兼收山水與聲色,他們懸想和經(jīng)營具有脫俗之美的生活,乃至構(gòu)造“色隱”的文化空間,從而安頓個人的情感和生命。
晚明士人將柳如是和建筑、山水等融為一體,塑造出一個被認(rèn)知、想象的“女性空間”[2]巫鴻認(rèn)為:“女性空間是一個空間整體——是以山水、花草、建筑、氛圍、氣候、色彩、氣味、光線、聲音和精心選擇的居住者及其活動所營造出來的世界。”參見巫鴻:《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版,第17頁。。錢謙益為柳如是建成絳云樓,金石文字、鼎彝環(huán)璧、法書名畫等充牣其中,柳如是于此“儉梳靚妝,湘簾棐幾,煮沉水,斗旗槍,寫青山,臨墨妙”[3]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上),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第142頁。,給觀者呈現(xiàn)的是一道頗具意味的文化景觀。類似的,徐錫胤寫柳如是“舞燕驚鴻見欲愁,書簽筆格晚妝樓”[4]谷輝之輯:《柳如是詩文集》,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xiàn)縮微復(fù)制中心1996年版,第192頁。,陳文述也曾描繪道:“金石千秋書萬卷,琳瑯都置妝臺畔。流水親調(diào)綠綺琴,墨香小試紅絲硯。”[5]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上),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第142頁。書簽筆格、金石書卷、琴棋墨硯與柳如是一并構(gòu)成博學(xué)文士、名士、居士的建筑空間和文雅世界。文房清玩與柳如是近乎成為一組相互轉(zhuǎn)喻的概念。衛(wèi)泳所作《悅?cè)菥帯穼U撊绾谓杳廊藸I造美感生活,稱“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jī)”,能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無學(xué)究氣,禪亦無香火氣”[6]蟲天子編,董乃斌等點(diǎn)校:《香艷叢書》第1冊,團(tuán)結(jié)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第32頁。。柳如是眾美兼?zhèn)洌瑸槲娜碎_啟了美學(xué)的、感性的、超脫的生活意境。
另外,晚明《燕都妓品》《蓮臺仙會品》之類的“花案”樹立了品賞美色的標(biāo)準(zhǔn),呈現(xiàn)“脫俗化”“傳奇化”的特征。文人“描摹想象,麻姑幻譜,神女浪傳……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閣中有之”[7]冒襄:《影梅庵憶語》,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這里的美人想象及“才子佳人”傳奇乃明清文人文化之特色,柳如是便被塑造為男性寤寐求之的“神話”女性。陳子龍《采蓮賦》視柳如是為宋玉的“神女”、曹植的“洛神”以及《游仙窟》中的“女仙”。程嘉燧的“翩然水上見驚鴻,把燭聽詩訝許同”[8]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6 頁,第126 頁,第147頁,第147頁。,偈庵的“杯近仙源花瀲瀲,云來神峽雨濛濛”[9]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6 頁,第126 頁,第147頁,第147頁。,亦將柳如是視作存在于洛水之上、桃源之境的傳奇女性。在《東山酬和集》中,朱云子稱“借問藍(lán)橋今共室,何如鄂渚昔同舟”[10]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6 頁,第126 頁,第147頁,第147頁。,林若撫也道“誰知宿世藍(lán)橋侶,即在今宵谷水舟”[11]柳如是撰,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6 頁,第126 頁,第147頁,第147頁。,柳如是又化身為《太平廣記》中的仙女云英。他們在觀看柳如是“景觀”的過程中,進(jìn)入神話世界的懸想。衛(wèi)泳在其書中道:“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真絕欲,以視買山而隱者何如?”[12]蟲天子編,董乃斌等點(diǎn)校:《香艷叢書》第1冊,團(tuán)結(jié)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第32頁。晚明文人通過柳如是建構(gòu)了一個淡化名利、安置自我的美感世界和桃源之境。
2.身份認(rèn)同:酬贈唱和中的相互建構(gòu)
“景觀”是觀者與被觀者相互作用而造就的結(jié)果,審美觀看不僅是對被觀者生命存在的探尋,也是觀者自身生命狀態(tài)的轉(zhuǎn)化。就柳如是而言,男性士人通過對其生命風(fēng)流的審美發(fā)現(xiàn),進(jìn)一步打開自身的存在境域。馬克夢認(rèn)為這種現(xiàn)象彰顯的是“才子佳人”式的“相似性與互映性”,并且在“對詩”,即唱和詩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xiàn)[1]馬克夢:《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jì)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guān)系》,王維東、楊彩霞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頁。。男性文人在同柳如是的詩文往來中建構(gòu)自我身份,并在文人群體中傳播、確證,而柳如是也在成就“他者”的同時彰顯自我人格與志向。
程嘉燧《耦耕堂存稿》中的《朝云詩》八首皆為柳如是而作。“香澤暗菲羅袂解,歌梁聲揭翠眉顰”[2]沈習(xí)康點(diǎn)校:《程嘉燧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頁,第8頁。中借用淳于髡“長夜之飲”中“男女同席,履舄交錯”的場景;“絕代傾城難獨(dú)立,中年行樂易離群”[3]沈習(xí)康點(diǎn)校:《程嘉燧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頁,第8頁。隱含著謝安攜妓和卓文君的典故。程嘉燧描摹的是同柳如是相處的情境,也在另一個層面將己身與謝安、淳于髡、司馬相如之類的風(fēng)流才子類比。陳子龍和柳如是的情詩對唱是一個共享事典、語典的象征隱喻系統(tǒng),是雙方相互觀看且不斷內(nèi)省的結(jié)果。柳詩“紫蘭蔭飛蓋,絳節(jié)煥華區(qū)”[4]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第25頁,第30頁,第125頁。期望陳子龍成為持紅色符節(jié)的使臣成就一番偉業(yè),自己則化身“紫蘭”,為其蔭護(hù)華蓋。“紛紛多遠(yuǎn)思,游俠幾時論”[5]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第25頁,第30頁,第125頁。以輕生重義、急人所難的游俠相期許,陳子龍則以“不然奮身擊胡羌,勒功金石何輝光”[6]施蟄存、馬祖熙標(biāo)校:《陳子龍詩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頁。酬答應(yīng)和。柳如是贈予友人朱茂暻的《朱子莊雨中相過》,是以塑造“他者”形象進(jìn)行自我表達(dá)的案例。詩中稱朱氏“才氣甚縱橫”“射策凌儀羽”“窈窕扶風(fēng)姿”,這是對友人安攘之才的景仰,也是她個人對英雄志業(yè)的向往。“天下英雄數(shù)公等,我輩杳冥非尋常。嵩陽劍氣亦難取,中條事業(yè)皆渺茫”[7]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第25頁,第30頁,第125頁。更是將朱茂暻引為同調(diào),她意欲成為男性群體中的一員,自覺或不期然地投合晚明士人欽羨的“俠女”情節(jié)。
柳如是初訪半野堂,贈錢謙益詩曰:“聲名真似漢扶風(fēng),妙理玄規(guī)更不同。一室茶香開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瓶拂因緣在,江左風(fēng)流物論雄。今日沾沾誠御李,東山蔥嶺莫辭從。”[8]周書田、范景中輯校:《柳如是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第25頁,第30頁,第125頁。她將錢謙益比作馬融、李膺和謝安。當(dāng)時,錢謙益在會推閣臣中獲罪罷歸,其遭遇與李膺相似,正如謝安一般等待時機(jī)東山再起。此外,錢氏一向自矜博探佛藏、洞達(dá)禪理,故柳如是將自己比作捧瓶持拂、供奉菩薩的侍女。柳如是贈詩可謂“識其天性,因而濟(jì)之”,句句道出對錢謙益的個人期許。錢謙益也在奉和詩中稱柳氏為卓文君,儼然自視為風(fēng)流多才的司馬相如了。
錢柳二人定情之后,《東山酬和集》中有諸多文人唱和之作,他們以詩語為媒,將晚明情觀中情欲的底蘊(yùn)與美學(xué)、文化元素交相滲透。男性士人在與柳如是的兩相唱和中相互建構(gòu),并彰顯了融合詩藝與愛情的情藝文化。這些酬唱交織著兩性之間的聲音、態(tài)勢、美學(xué)觀與權(quán)力意識。柳如是并非被動地接受男性士人的“凝視”,她在時而“男性化”的角色以及紅粉黛妝的女性魅力之間切換,從而獲得錢謙益等異性的認(rèn)可,男性士人也通過對柳如是的殷勤推崇以確認(rèn)自我。
3.移情作忠:女性聲音中的自我人格設(shè)計
晚明時期,海內(nèi)鼎沸,然江左士大夫益事宴游,“其于征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喧譽(yù),獨(dú)推章臺”[9]鈕琇:《觚剩》卷三,康熙壬午臨野堂刊本,第6頁。。一方面,他們從處于社會邊緣的女性身上看到自身才略的無處施展,以及國族命運(yùn)的風(fēng)雨飄搖。另一方面,以女性為基礎(chǔ)的情藝的經(jīng)營成為忠君愛國的表現(xiàn),即周銓所道:“情之所在,一往輒深:移以事君,事君忠;以交友,交友信;以處世,處世深……古未有不深于情,能大其英雄之氣者。”[1]朱劍心選注:《晚明小品選注》,商務(wù)印書館1991年版,第12—14頁。柳如是正是這一“情”與“忠”之社會思潮的參與者、建構(gòu)者之一。
王朝覆滅以后,錢謙益等易代文人頻繁追憶和一眾名妓于湖山間流連詩酒的生活。勝國滄桑之艷跡,承載著晚明的文人文化,激發(fā)著文人的故國懷想,是錢謙益等文人士大夫在晚明生活的象征。于錢謙益而言,柳如是的豪俠之風(fēng)、英雄之氣與忠君愛國不斷地促使他反觀自身,是其轉(zhuǎn)變?yōu)閻蹏斑z民”的關(guān)鍵助力,也是其一再洗刷污名、確立抗清志士身份的“符碼”。錢謙益追懷他同柳如是旅居杭州的生活,寫下“油壁輕車來北里,梨園小部奏《西廂》。而今縱會空王法,知是前塵也斷腸”[2]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有學(xué)集》卷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頁,第91頁,第9頁。。故地重游,“空王法”與“腸斷前塵”表示明王朝以及故明臣子身份的消逝。“楊柳”是柳如是的代稱,“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剺面柳攢眉”“楊柳桃花應(yīng)劫灰,殘鷗剩鴨觸舷回”[3]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有學(xué)集》卷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頁,第91頁,第9頁。等語抒發(fā)的是兵燹之后的“殘山剩水”之感,以及對柳如是所象征的晚明生活的緬懷。順治四年(1647),錢謙益因“黃毓祺案”下獄,柳如是孤身北上斡旋。錢氏記述道:“河?xùn)|夫人沉疴臥蓐,蹶然而起,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從死。慷慨首涂,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4]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有學(xué)集》卷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頁,第91頁,第9頁。正是在此番遭際的影響和柳如是的感發(fā)下,錢謙益試圖以新“遺民”身份開展復(fù)國運(yùn)動。
錢謙益曾于晚明時期與柳如是同訪韓世忠墓,二人追念梁紅玉“佩金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噴沸中”[5]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初學(xué)集》卷四十四(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6頁。,相與感慨良久。錢謙益《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懷八首》其七寫道:“月下旌旗看鐵甕,風(fēng)前桴鼓憶金山。余香墮粉英雄氣,剩水殘山俯仰間。”[6]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初學(xué)集》卷二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頁,第706頁,第666—667頁。他們以韓世忠、梁紅玉自期,希冀“中興”。沈璜與孫永祚在《東山酬和集》序中所道“桴鼓軍容,尚資纖手”“援桴賈壯于從軍”之語都用梁紅玉事。柳如是在晚明時期就已是文人筆下“情與忠”的符碼。入清后,錢謙益寫下“乍傳南國長馳日,正是西窗對局時……還期共覆金山譜,桴鼓親提慰我思”[7]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第10頁。,以梁紅玉擊鼓助戰(zhàn),暗示自己像韓世忠阻擊金兵一樣反清復(fù)明。柳如是赴海上犒勞抗清義師,資助神武軍等事跡確為忠烈之舉,錢謙益亦一度將其視作愛情與政治的聯(lián)結(jié)點(diǎn)。錢詩中“閑房病婦能憂國,卻對辛盤嘆羽書”[8]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初學(xué)集》卷二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頁,第706頁,第666—667頁。“閨閣心懸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歡悲”[9]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第10頁。之語都是對柳如是壯舉的感佩,而在“埋沒英雄芳草地,耗磨歲序夕陽天。洞房清夜秋燈里,共檢莊周說劍篇”[10]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初學(xué)集》卷二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頁,第706頁,第666—667頁。句中,錢謙益儼然模糊了二人之間的性別界限,他以英雄自期,更將柳如是視為同道中人[11]張娜娜:《明清易代士人“詩史”書寫中的自我建構(gòu)——以錢謙益為中心的探討》,《中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2年第6期。。
三、隱喻晚清:錢柳故事的再度演繹
兩三百年后的晚清民國,柳如是已化作荒莊拂水之畔的一座香墳,但作為文化“景觀”,她的符號價值仍在被持續(xù)地征用、重塑、建構(gòu)。知識分子目睹柳如是畫像[12]柳如是有多幅畫像存世,據(jù)陳去病記載:“柳夫人風(fēng)流放誕,嫵媚絕世。一時思慕者眾,爭圖形貌,頗有團(tuán)扇放翁之致。”參見陳去病:《五石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頁。,想到國士名姝東山酬唱的明末風(fēng)流,感受到一代國手裹挾于輿論紛爭的生存困境,以及九州塵煙、美人殉主的凄惶,他們因此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有關(guān)柳如是的題像詩。一方面,知識分子圍繞錢柳故事,以“隱微”寫作的方式,借“詩史”“隱語”戲擬歷史,映照當(dāng)下。另一方面,錢柳二人的生死抉擇是“男降女不降”[1]“男降女不降”史事及相關(guān)研究參看夏曉虹:《歷史記憶的重構(gòu)——晚清“男降女不降”釋義》,《讀書》2001年第4期。之說的范本。這一說法在明季關(guān)涉滿漢文化沖突和“華夷之辨”,在近代則與“民族主義”相融合,表面上看是“種族之見”,實(shí)際則是以“民族主義”抵制異族侵犯。他們重塑柳如是等明季女性和錢謙益等士人的形象,期望以女子的堅貞剛烈喚醒柔弱游移的男性,表達(dá)對國族復(fù)興的期望與對尚武時代的神往。
1.錢柳并稱與“隱微寫作”的可能
中國古典詩學(xué)向來有“隱微書寫”[2]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提出,“隱微寫作”產(chǎn)生于特定歷史語境中,失去言論自由的作者會以特殊的方式把情思隱藏于字里行間,這也促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學(xué)類型,即“隱微寫作”。參見列奧·施特勞斯:《迫害與寫作藝術(shù)》,劉鋒譯,華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頁。的傳統(tǒng),錢鐘書說文人常常“移花接木,繞了個彎,借古典來傳述”,以“詠史”影射時事,以“古意”訴說“新愁”[3]錢鐘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頁。。雖然在政治壓迫比較嚴(yán)重的情況下,這種“煙幕彈”未必能避害,但是在“主文譎諫”的基礎(chǔ)上,對于表達(dá)變局之下詩人思想之矛盾與張力等方面用處不少。錢謙益素有“詩史”詩人的稱號,其前朝遺老的身份與心態(tài)尤其復(fù)雜,且與柳如是暗中從事復(fù)明運(yùn)動,故其詩歌語言“燈謎交夾,市語雜出”。因此,時人在對女主角柳如是故事展開想象時,通過“古典”“今典”的映照,借用二人的姻緣以及錢謙益創(chuàng)作中的“隱微寫作”進(jìn)行時代言說,為“才子佳人”的“詩史”敘事,額外增添了末世的悲愴感以及“復(fù)國運(yùn)動”的革命色彩。
錢謙益在《錢注杜詩》中借晚唐史事書寫當(dāng)下,而晚清文人亦以錢柳所生活的晚明隱喻晚清,進(jìn)行古今交疊的“詩史”寫作。李貽德的《題河?xùn)|君小像后》是一首長篇敘事詩,從錢柳二人的東山酬唱寫到“忽傳噩耗破金甌,萬歲山頭苑樹秋”的國變。“供養(yǎng)珍同西竺書,飄零劫比《東京錄》”將柳如是故事視為對“興”的緬懷與對“亡”的警戒,稱之堪比遺民書寫典范的《東京夢華錄》。“只憐絕代佳人貌,誰識千秋國士心”[4]李貽德:《攬青閣詩抄》卷下,同治五年(1866)刊本,第32頁。詩句中,此“國士”之心指柳如是的忠貞孤烈,亦是詩人當(dāng)下心境的夫子自道。錢文選寫下“義師鼓舞非甘后,異族驅(qū)除誓必先……董狐史筆存真意,烈女忠臣一例編”[5]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二(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頁。。其中,“董狐史筆”將柳如是事跡納入歷史的范疇,此時“異族驅(qū)除”的對象不再是滿清,而是環(huán)伺中國的西方世界。丁傳靖有《柳如是妝鏡為曹君直題》一篇,“勝國滄桑艷跡多,殘脂剩粉照山河”中的“殘脂剩粉”是對國變后“殘山剩水”的隱喻,亦是對時局的隱憂。“珠冠星燦蛾眉笑,玉轡風(fēng)馳雉尾飄”是撮合野史筆記而成,而“一樣蒼涼可奈何”所道既是晚明,更是晚清[6]丁傳靖:《闇公詩存》卷二,民國乙亥白雪庵刊本,第11頁。。
在接受史中,錢柳二人往往“捆綁”出現(xiàn)、相互映襯,表現(xiàn)之一就是文人化用錢謙益詩語題寫柳如是小像。入清后,錢謙益的詩歌隱語頗多,借之進(jìn)行集句創(chuàng)作正好可以塑造迷離惝恍的詩境,影射當(dāng)下。光緒朝局在甲午戰(zhàn)爭、戊戌政變之后已然失控,光緒被軟禁、庚子事變等一系列事件昭示著封建王朝的式微。李葆恂在《題河?xùn)|君儒服小像集牧齋句》中摘取錢謙益“秋風(fēng)紈扇是前生,坐看人間滄桑更”“綠尊紅燭都如昨,都是昆明劫后人”“洞房銀燭辟輕寒,歷歷殘棋忍重看”[7]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4頁。等句,大概是世變的焦慮、分裂引起李葆恂心中山雨欲來的不安,而生出“昆明劫后人”[8]釋慧皎言:“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后泛指遭受巨大災(zāi)禍或變故之后的余燼。參見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一,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頁。之感。“攬鏡端詳應(yīng)自喜,為他還著漢衣冠”是錢謙益隱秘從事復(fù)明運(yùn)動后對自己“漢人”身份的審視,而諸如李葆恂之類的晚清文人又何嘗不面臨著滿漢文化沖突,以及自我身份界定的問題?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紅豆”意象。紅豆山莊曾是錢柳秘密反清的據(jù)點(diǎn),錢謙益以“紅豆”為詩集名,并有多篇歌詠之作。實(shí)際上,“紅豆”除了象征錢氏和柳如是之間的愛情,在明“遺民”詩中還表示對故國的思念,隱含恢復(fù)朱明王朝的心曲。“美人”“愛情”“紅豆”“南國”“中華”等意象融合在一起,成為時人表達(dá)末世感傷以及復(fù)國意念的媒介。晚清潘遵祁“棐幾湘簾轉(zhuǎn)眼空,飄零紅豆泣東風(fēng)”[1]潘遵祁:《西圃集》卷四,光緒刻本,第7頁。和錢謙益的“可是湖湘流落身,一聲紅豆也沾巾”[2]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有學(xué)集》卷四(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頁。屬于末世的異代同悲。費(fèi)念慈“枕熟黃粱春夢短,莊荒紅豆暮云涼。無窮家國傷心事,一事低回一曲腸”[3]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第155頁,第152頁,第143頁,第159頁,第199頁,第191頁。,張云驤“紅羊小劫須臾,虞山老卻尚書。莫數(shù)江南紅豆,年年恨滿蘼蕪”[4]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第155頁,第152頁,第143頁,第159頁,第199頁,第191頁。,亦是借“紅豆”的多重隱喻,抒發(fā)在個人關(guān)切與政治言說之夾縫中的無力感,以及新舊時代交接中短暫、虛無和不確定性的情感體驗。一直到現(xiàn)代,陳寅恪作《紅豆吟》,“灰劫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5]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1頁,第4頁。一句言其在抗戰(zhàn)期間旅居昆明,從舊書商手中購得一粒據(jù)說出自錢謙益故園的紅豆,二十年顛沛流離,而紅豆仍在。他借“紅豆情緣”窺探易代士人之孤懷遺恨,“表彰我民族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6]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1頁,第4頁。,儼然又是一重文化復(fù)興之思。
2.“男降女不降”與“民族獨(dú)立”
晚清民國論者對柳如是等明季奇女子青睞有加,原因在于她們的妓女身份與節(jié)烈行為之間的巨大張力,頗具示范性,《民立報》甚至稱“吾國女革命家,當(dāng)以河?xùn)|為第一人”[7]塞庵:《塞庵舊話》,《民立報》1911年4月3日。。1911年《申報》的《自由談·野史》欄目稱:“女杰,一娼婦也”,“而能獨(dú)其愛國思想深明大義”,“然諸多頂天立地之男子為求高官厚祿甘心賣國,絕無民族思想,與女子相去甚遠(yuǎn)”[8]參見1911 年12 月4—6 日《申報》。嘉定二我轉(zhuǎn)載柳亞子《為民族流血無名之女杰傳》,并易名為《松江女杰小傳》。。入清以來,一直流行的“男降女不降”的說法是屬于漢民族的易代記憶,錢柳二人在殉國之事上的抉擇堪稱此說的典范。晚清文人鋪陳演繹此類野史逸聞,凸顯明季女性之死的意義,目的之一就是激發(fā)男子的“民族思想”,爭取“民族獨(dú)立”。
晚清文人宣稱“明末清初之際,山川之秀不揚(yáng)為須眉之氣而吐作巾幗之光”[9]山淵:《余孝女》,《春聲》1916年第3期。。其實(shí),這種“男不如女”的說法在入清以來不曾間斷。袁枚“可惜尚書壽更長,丹青讓于柳枝娘”[10]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第155頁,第152頁,第143頁,第159頁,第199頁,第191頁。,陳文述“嬋娟都被須麋誤,不作忠臣傳里人”[11]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第155頁,第152頁,第143頁,第159頁,第199頁,第191頁。,應(yīng)時良“生得相隨原妾幸,死無他憾為公遲”[12]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第155頁,第152頁,第143頁,第159頁,第199頁,第191頁。等,表述的都是柳如是的義節(jié)俠氣為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晚清文人進(jìn)一步融合“殉節(jié)”與“殉國”的概念,即認(rèn)為柳如是的死體現(xiàn)出的不僅有“錢氏家難”所道的普通節(jié)烈綱常,更是“國家倫理”的價值取向。比如,吳清學(xué)“婦人能殉國,斯土亦生香”[13]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第155頁,第152頁,第143頁,第159頁,第199頁,第191頁。直接將“殉主”改為“殉國”,將柳氏之死拔高到家國層面。丁傳靖“海虞紅豆千秋艷,寂寂人間方芷生”[14]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第155頁,第152頁,第143頁,第159頁,第199頁,第191頁。將柳如是同民元前后文化視野中的方芷生并置。方芷生在國難之際逼夫自盡,自己亦引刀而去,《申報》稱其“為民族流血之英雄,增光種族之女杰”[15]嘉定二我:《方芷生傳》,《申報》1911年12月15日。。正如南社領(lǐng)袖柳亞子在《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所說,柳如是等所引起的“男降女不降”之說,已然被奉為“中國女界之魂而決民族思想”之起點(diǎn)[16]柳亞子:《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女子世界》1904年第7期。。
以推翻滿清統(tǒng)治并抵御外辱為目標(biāo)的革命思想,需要一種“女軍人傳統(tǒng)”作為支撐,而柳如是的事跡恰好印證了這一“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思想。當(dāng)時,《女子世界》傳記欄目先后為花木蘭、梁紅玉、秦良玉等“女軍人”立傳,表彰其衛(wèi)國殊勛。而當(dāng)時的知識分子將柳如是視為與花木蘭、梁紅玉比肩的人物,故借其小像重構(gòu)晚明歷史記憶。李黼平“到底不慚真女士,木蘭邨里斗新妝”[1]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頁,第204頁,第204頁,第203頁。,柳亞子“紅粉能談兵,何異梁紅玉。惜哉錢尚書,老去徒碌碌”[2]柳亞子:《題河?xùn)|君像》,《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頁。,等等。這些詩句中所道柳如是“京口祭拜韓世忠”“勸夫殉國”“北上救夫”“自縊殉主”的情節(jié),將其塑造為性豪俠、重然諾、尚信義的典范,順應(yīng)了時代的政治文化訴求。她的“海上犒師”之舉更是直接投入了民族戰(zhàn)斗的表現(xiàn)。張亞屏“千秋大義甘殉節(jié),一片孤忠獨(dú)犒師。志愿毀家能復(fù)國,才優(yōu)詠絮且工詩”[3]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頁,第204頁,第204頁,第203頁。,張卓人“工吟已見嫻風(fēng)雅,助餉尤能解橐囊”[4]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頁,第204頁,第204頁,第203頁。,錢文選“義師鼓舞非甘后,異族驅(qū)除誓必先”[5]范景中、周書田編撰:《柳如是事輯》卷一(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頁,第204頁,第204頁,第203頁。等詩句中所詮釋的柳如是,符合當(dāng)時鑄造“軍人之體格”和“軍人世界”[6]丁初我將“軍人之體格”、鑄造“軍人世界”作為“女子世界”誕生的首要任務(wù)。參見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1904年第1期。的時代要求,這也是知識分子對強(qiáng)權(quán)與帝國主義集矢中國而急切呼吁抵御之策的反應(yīng)。
文變?nèi)竞跏狼椋行晕娜藦哪姆N角度觀賞、重構(gòu)柳如是,取決于特定時代的政治文化訴求。借助對柳如是“景觀”的塑造,最終烘托及激勵的是男性人格,這是當(dāng)時社會的政治文化心理尤其是男性心理投射、作用的結(jié)果。當(dāng)然,晚清文人對柳如是等明季烈女的回顧與西學(xué)東漸及西方女權(quán)思想的傳播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精衛(wèi)石》錄有秋瑾的《改造漢宮春》:“可憐女界無光彩,只懨懨待斃,恨海愁城。湮沒木蘭壯膽,紅玉雄心。驀地馳來,歐風(fēng)美雨返精魂。脫范圍奮然自拔,都成女杰雌英。”[7]秋瑾著,郭長海、郭君兮輯注:《秋瑾全集箋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頁。便是最真實(shí)的寫照。時人謂“莫誕于柳如是,莫怪于吳弱男”[8]孫毓修:《綠天清話》“吳弱男”條,《小說月報》1912年第6期。,柳如是得以與“女權(quán)運(yùn)動之先驅(qū)”并稱。對這一理想女性的重新認(rèn)定和重構(gòu),也為當(dāng)時“新造中華資格之巾幗”以及“女界革命”提供了歷史依據(jù)。
四、結(jié)語
晚明時期,柳如是在男性世界中尋找自己的發(fā)聲方式,以漫游、造景和充滿雙性特質(zhì)的風(fēng)神氣度及書寫模式與男性對話,重塑了性別身份、擴(kuò)展了性別空間,成為一道矚目的文化“景觀”。男性在審視柳如是“景觀”的過程中,一方面通過帶有身份意識和性別權(quán)力的運(yùn)作,營造了與富商巨賈相區(qū)分的“閑賞”“閑雅”的美感生活,“此種結(jié)合美色、情藝與情感之情色文化,乃成為明代社會文化之重要特色”[9]王鴻泰:《美人相伴——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賞與情藝生活經(jīng)營》,《新史學(xué)》2013年第2期。。另一方面,在晚明“情觀”的時代背景下,男性士人還在“觀看”柳如是的過程中打開自身生命境遇的言說空間,移情作忠,借女性聲音進(jìn)行自我形塑和人格設(shè)計,彰顯了“深情”與“忠君”的情藝文化。推及后世,錢謙益和柳如是作為“明清痛史”的典型在晚清及民國的“新痛史”中重新煥發(fā)生機(jī)。知識分子對錢柳二人的書寫融合了“復(fù)國運(yùn)動”的革命話語與“恢復(fù)中華”的民族精神,為“女界革命”或婦女解放者所利用,呈現(xiàn)了晚清對晚明歷史的重構(gòu)、戲擬。因此,柳如是“景觀”和士人的相互觀看及建構(gòu),體現(xiàn)了政治失序狀態(tài)下性別聲音的混雜,其中涉及性別互動、朝代更迭、士人出處、歷史感傷、隱喻詮釋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了晚明到晚清的文化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