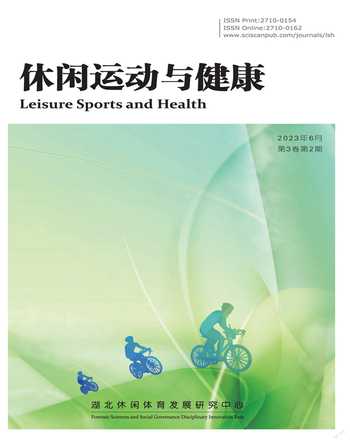我國武醫融合研究的發展歷程、主要特征與發展趨向
尹霞 劉軼
摘 要:“武醫融合”是實現“體醫融合”的重要方式,是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國民健康的有效手段。本文運用文獻資料法,邏輯分析法等方法梳理和述評我國武醫融合研究的發展歷程,總結武醫融合研究的主要特征,研究認為我國關于“武醫融合”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孕育萌芽期(1949年之前);初步探索期(1949—1978年);逐步發展期(1979—2015年);發展壯大期(2016年—至今)。縱觀武醫融合研究歷程,發現其呈現出“實踐—理論—實踐”的螺旋式上升、由現象描述到本質剖析的層層遞進、研究視角由窄到寬的特點。基于此,提出未來武醫融合研究的發展趨向:一是豐富研究主體、拓展研究范疇;二是加強武醫融合的應用研究;三是創新研究方法與手段;四是開展跨學科、系統性的研究。
關鍵詞:武醫融合;健康中國;武醫結合
The Development Cours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Medicine in China
YIN Xia,LIU Y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Wuhan430062,China)
Abstract: “Martial medicine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physical medicine integration”, it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carry forward our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 national health.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sort out and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 in China,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 in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 in China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embryonic stage (before 1949); Initial exploration period (1949-1978); Gradual development period (1979-2015);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period (2016 - present).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martial medicine integration, it is found that i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e-theory-practice” spiraling upward, from phenomenon description to essence analysi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narrow to wide.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 in the future: first, enrich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medicine; Third,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means; The fourth is to carry out interdisciplinary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 Healthy China; Combin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
2016年8月26日發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要促進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推進健康促進及慢性病防治,發揮體醫結合科學健身的特色作用[1]。“健康中國”戰略的提出,為武醫關系由“分化”向“融合”轉變的當代嬗變提供了契機。201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強調要突出中醫治病的特色,以“治未病”為核心,要做好骨傷、按摩等專科,并及時總結和制定相應的診療計劃,以鞏固和擴大中醫治病的優勢,促進特色發展。積極宣傳開展太極拳、健身氣功(八段錦、五禽戲)等健身活動,弘揚“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發揚中醫康復特色。推動中醫與傳統體育運動、現代康復技術的有機融合,形成中國特色的康復醫學[2]。傳統體育和傳統醫學融合發展正好符合國家相關文件要求,由此可見,推動武術和醫學的融合發展是國家提倡的發展方向。此外,雖外國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工作壓力也日漸增大,人們出現了亞健康狀況,同時也出現了多種慢性疾病。武術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一直以來,武術作為一項大眾喜聞樂見的傳統健身項目,對人體健康發揮著重要價值,所以,必須要加強武醫融合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運用文獻資料法、邏輯分析法等方法,梳理我國武醫融合研究的發展歷程,總結其特點,探索未來武醫融合研究的發展趨向,旨在豐富武醫融合研究體系。
1 我國武醫融合研究的發展歷程
1.1 孕育萌芽期(1949年之前)
武術和醫學相結合在我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治療手段,兩者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人類的健康服務[3]。早期關于武醫結合相關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醫中有武,如中醫中的武術最早可追溯到《黃帝內經》中記載的關于導引、按摩、吐納等運動養生方法。此外,華佗創編的“五禽戲”、《諸病源候論》中的導引和吐納方法、流傳數千年的太極拳、八段錦、易筋經和氣功等也都體現出傳統中醫與傳統武術的相互交融。另一方面,武中有醫,在《拳經》這本武學典籍之中,卷三名為“拳藝衛生篇”,卷四名為“拳藝錄”,講的都是傷科的理論與處方;在《按摩經》等典籍中,幾乎都記載了有關傳統武功對于改善推拿師身體素質和局部力量具有重要作用的論述,對推動中醫推拿學科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靈樞·官能篇》中也有這樣的記載:“手毒之人,可試按龜,置龜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國技大觀》《少林武功秘籍》等諸多武學經典,均有“人體學位并治法”“傷科秘要”的記載。這些秘傳的武學傷科典籍各有其流派,別具一格,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武、醫不分家”是早有淵源的[4]。
綜上所述,在新中國成立前,已有頗多涉及武醫融合研究的古籍文獻,為后續武醫融合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和重要的參考史料。但該階段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意識形態層面,未能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且由于時代的局限性,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不夠科學化和規范化。
1.2 初步探索期(1949—1978年)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在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變化和發展,對社會主義的發展之路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與武術相關的研究也是經歷了起起伏伏。從劉少奇同志1956年提出的“對武術進行科學研究,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宣傳和普及”到“文革”中被歸入“四舊”,發展受到阻礙,隨后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下逐漸復蘇,學術界的學術觀念逐漸增強,有關“武醫結合”的研究也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一個新的生長點[5]。在此期間,出現了一批武醫兼修的人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人物是被稱為“武醫宗師”的鄭懷賢,鄭懷賢是新中國建國以來鄭氏骨傷科綜合診療系統的開創者和實踐者,致力于將武術教育、武術理論與中醫骨傷科相結合的研究與實踐,創建了鄭氏傷科學術,在海內外產生了深刻的作用與影響[6]。鄭懷賢先生以“武與醫合”為指導思想,既將武醫相融的歷史進行傳承和推廣,又集百家之長,取其精華,自成一派,為鄭氏骨傷科的方藥體系、正骨手法、穴位推拿、練功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7]。與鄭懷賢同一時期的亦武亦醫型人才還有人稱“武神”的孫祿堂、“自然宗師”萬籟聲、“關東大俠”杜心武、“神力千斤王”王子平、“長江大俠”呂紫劍等人,他們不但是功夫高手,而且還是跌傷方面的專家。鄭懷賢教授曾主編、出版過《正骨學》《傷科診療》《運動創傷學》等傷科類專著10多部[8]。“神力千斤王”王子平,是我國第一屆武術協會副主席,其著有《拳術二十法》,自創“治百病二十式”。“自然宗師”萬籟聲也撰寫了《武術匯宗》《中國傷科》等多部專著[9]。他們對武醫的研究,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推動了“武醫結合”思想的興起,對后世的影響也很深遠,為后來武醫結合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3 逐步發展期(1979—2015年)
在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核心,大力發展生產力”這一發展方針,為促進社會主義政治和文化建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同時也為武術的理論研究和發展實踐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世紀之交,中國成功加入WTO之后,獲得了一個向其他國家學習先進成果的機會。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圓滿舉行,中國又一次被世人所熟知,國家飛速發展,也使得有關武術的研究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10]。在此期間,武術研究持續地將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科理論知識融入其中,并逐漸地與歷史學,傳播學,文化學,倫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生理學,生物力學,醫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建立了以人文社會科學類理論、運動人體科學類理論、教育訓練類理論為主要內容的武術理論體系[11]。武術與醫學結合的內容包括:運動干預,運動處方以及健康促進和疾病防治等。
也有學者開始對“武醫結合”一詞的概念進行界定,付強、周永紅(2006)首次提出了“武醫結合”一詞,他們對武醫結合開創自然療法提出了思考,認為中醫與武術本質相聯,息息相通,互為滲透,并闡明了武醫結合自然療法在臨床上的應用范圍和應用方法[12]。卿光明等提出“武醫結合”是鄭懷賢對清末民國武術家群體武醫兼善的集體人格的繼承,并在實踐中創立的鄭氏“武醫”流派和武學體系[13]。1978年,一代偉人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友人時揮毫寫下了“太極拳好”極具號召力的題詞,此后太極拳的開展卓有成效。這一時期關于太極拳促進人體健康的研究不勝枚舉,研究群體也更為廣泛。如陳玩輝等在運動處方干預對青少年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中,通過實驗數據驗證了太極拳運動處方干預可以提高青少年的生活質量[14]。劉鐵民等人的研究表明:長期堅持打太極拳可以有效改善中老年人高血壓病的血脂水平,降低靶器官損害的發病率,提高機體對應激的適應性和耐受性[15]。
70年代末的“氣功熱”興起之后,關于八段錦、易筋經、五禽戲等促進人體健康的研究層出不窮,這類研究不僅局限于健身氣功類運動項目對人體生理健康產生的影響,還結合心理學知識,對人體心理健康狀況的干預效果進行了研究。2001年末,經過有關部門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結合我國傳統氣功的特色,吸收各家之長,創作出了《五禽戲》《八段錦》《易筋經》《六字經》等四種健身功法。自2003年3月,這四種健身功法被國家體育總局公布為全國第97個體育項目后,開始對其大力宣傳,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在這四種健身功法的創編與傳承過程中,受到了醫學界、體育界的高度關注,他們運用生理學、生化學、生物力學、心理學等實驗方法和手段,對五禽戲、八段錦、易筋經等健身功法的健身效果進行了實證研究,并以研究中獲得的實驗數據來闡述健身氣功的科學健身價值[16]。例如,已有研究人員開展了健身氣功八段錦的降血脂作用試驗,發現八段錦運動能顯著降低受試者的 TC,TG,LDL-C,而HDL-C水平則明顯增高。這表明,健身氣功八段錦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從而降低冠心病、動脈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17]。潘華山在研究健身氣功八段錦后,還發現它對呼吸功能有很好的促進作用。作者認為,八段錦套路中的一些招式,可以極大地擴大胸廓容量,因而可以大幅度提高肺部的吸氣量。與此同時,膈肌收縮和舒張的幅度增大,使胸腔容積增大,肺部通氣能力增強[18]。除此之外,黃濤[19]、朱寒笑[20]等學者的研究發現:長期習練八段錦、五禽戲可以起到延緩機體衰老的作用。
由此可見,此階段,關于健身氣功類運動項目促進身體健康的研究成果豐碩,為后期武醫深度融合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和現實依據。
1.4 發展壯大期(2016年至今)
自2016年《“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發布之后,“武醫融合”相關研究以“井噴”之勢不斷涌現。此階段下,由于高新技術的發展,醫療設備更加先進,使得武醫融合的臨床應用研究越來越科學化、規范化和精確化,交叉研究的領域也越來越廣泛。如中醫學領域有研究者從默認模式網絡(DMN)探討太極拳緩解慢性疲勞綜合征(CFS)的機制,該項研究招募20例CFS患者和20名健康人進行每周7次,每次30 min,持續4周的太極拳訓練,訓練后的評估不僅用到了量表,還運用了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21],這種跨學科的研究彌補了單一學科在研究視角和研究手段上的局限性。
此外,武醫融合的基礎理論研究的方向更加明晰,學者們不僅對“武醫融合”的概念內涵進行了探討,還對其發展路徑進行了初步探索。丁省偉、范銅鋼首次對“武醫融合”的概念內涵進行了界定,認為:中醫與武學的結合,顧名思義,就是中華武學與中醫的結合。“武”指的是傳統的武術運動和保健體育,它既包括功法運動、格斗對抗和套路演練等武術運動,還包括太極拳、易筋經、五禽戲、氣功等養生功法;“醫”不僅僅是指中醫學,還包括以西醫為基礎的現代醫學,從廣義上說,“醫”是中醫和西醫結合的產物。從實踐的角度來看,武醫融合就是將武術運動作為一種方法和手段,以醫學為思想和引導,讓運動更具針對性、科學性和實用性,從而更好地促進人體健康,其中的武術運動可以在傳統中醫理論的指導下進行,也可以根據現代醫學的運動處方來實施[22]。“武醫融合”這一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對傳統武術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更是順應了“健康中國”戰略的需要。關于“武醫融合”的發展路徑研究,任定甲在觀念融合、制度融合、人才融合以及產業融合四個方面提出了武醫融合的路
徑[23]。林玉平在技術融合、資源融合、創新融合等方面提出了武醫融合的路徑[24],然而,兩位研究者都認為:武醫融合路徑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二者的融合理論尚不成熟,“武醫融合”的發展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社會和高校等多方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實現武術與中醫的深度融合。
綜上所述,自《“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印發后,關于武醫融合的研究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積極回應時代課題,表現出與時俱進的歷史姿態。相關研究既在理論層面有了升華,也在臨床應用層面有了突破,交叉學科融合不斷深入。
2 我國武醫融合研究的主要特征
基于武醫融合研究歷程,整體觀照研究發展脈絡,可以發現武醫融合的研究呈現出以下特點。
2.1 “實踐—理論—實踐”的螺旋式上升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一切認識都是由感性到理性能動發展的過程,所有的理論都來源于實踐,理論反過來指導實踐,武醫融合研究的過程亦是如此。縱觀武醫融合研究的發展歷程,學者們對武醫融合的認知過程具有明顯的螺旋式上升特點。
武術和醫學結合已有幾千年的歷史,相關研究源于人們對實踐的探索,武者善于接骨斗榫和治療跌打損傷,醫者運用武術進行布氣導引、點穴按摩、疏通經絡來醫治傷病[25]。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武術和傳統中醫相結合的治療方法,造就了武醫融合的萌芽。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古人利用穴位、刮痧、按摩等技術手段來治療跌打損傷,以此達到恢復健康的目的,經過長期的發展和完善,這種武醫結合的體系逐漸系統化。民國時期,“武醫宗師”鄭懷賢教授在長期的武術學習中繼承和發揚了武醫結合的傳統,并在前人的基礎上兼收并蓄,形成了系統的武學理論體系。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武醫融合研究逐漸出現跨學科研究的趨勢,學者們從不同視角進行了大量有關傳統養生功法促進人體健康的實證研究。經過長期的實踐和探索,再產生出新的理論。由此可見,武醫融合的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實踐—理論—實踐”的螺旋式上升發展軌跡。
2.2 由現象描述到本質剖析的層層遞進
武醫融合的研究歷程正是認識從感性上升到理性、從描述現象到把握本質的深化過程。初步探索階段的理論研究帶有較明顯的直觀性,大多止于現象描述。這既是由武術和醫學本身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也是人類認識發展內在邏輯的表現。
最開始的武醫融合,它僅僅是人們所把握的經驗對象,即人們在長期習練武術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治療傷病的一些特殊手段與方法,更多的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的自我體悟,當時并未得到科學的驗證。隨著實踐推進和技術發展,學者們開始深入探討武術和醫學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與內在淵源,理論研究也隨之形成熱潮并逐漸符合現代科學體系。學者們對武醫融合的理論基礎、應用邏輯與機理機制等根本問題的探討,充分說明理論研究已經開始由對現象的描述深入到對本質的剖析。此外,部分學者開始在研究熱潮中反思武術本身及其與醫學融合過程中逐漸顯現出的問題。這表明學者們對武醫融合的認識更加全面、客觀,理論研究也日趨成熟與理性,逐步實現認識從現象層面到本質層面的飛躍。
2.3 研究視角由窄到寬
縱觀武醫融合研究的歷程,從一開始體育學領域研究健身氣功類運動項目對人體健康的促進作用到醫學領域結合生理生化指標研究健身氣功類運動項目的臨床治療效果,武醫融合的研究逐漸得到生理學、免疫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領域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學科融入其中,各學科在開展研究工作中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出發,拓寬了武醫融合的研究視域和思路。其次,研究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從武術健身作用的挖掘到武醫融合的路徑、模式、機制等問題的探討,武醫融合研究往縱深化方向不斷發展。近年來,武醫融合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樣化,實驗法、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研究方法豐富了武醫融合的研究成果。這些新視角和新方法是推動武醫融合研究向深層次發展的有益嘗試。
3 未來武醫融合研究的發展趨向
3.1 豐富研究主體、拓展研究范疇
首先,必須充實“武醫融合”的研究課題,豐富研究主體。一方面,從“武醫融合”的需求方來看,“武醫融合”的衛生服務人群是“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從“健康中國”戰略的重大目標出發,要著眼于“兒童、老年人、慢性病、殘障”等人群,加強對常見的抑郁癥、焦慮癥等精神疾病及心理行為問題的干預研究。另一方面,從武醫融合的供給方來看,臨床醫師、武術社會體育指導員、康復專家和武術教練員是武醫融合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對象。
其次,進一步拓展“武醫融合”的研究內涵與范疇。關于“武醫融合”的模式和路徑,已有許多學者在理論上進行了探討,然而,對于“武醫融合”的實際推進,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目前已有部分學者對武術和醫學在理念上的融合進行了一些研究,但要使“武術”與“醫學”的真正的融合發展,還需要在“信息”“產業”“技術”“資源”四個層面上進行“武醫融合”發展探索與研究。
3.2 加強武醫融合的應用研究
武醫融合的應用研究可以從以下兩個部分進行:一是在運動傷害的預防與治療上,需要深入發掘前輩武術家積累的醫療經驗和傳統方藥,并將其與傳統中醫對各類創傷的治療相結合,尋找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為運動康復,延長運動壽命,保護受傷肢體提供最優的解決方案。第二,從全民健身的角度來看,中醫的某些養生療法,可以保證習武之人的日常訓練以及受傷后身體的康復,武術和醫學的融合,將會促使武術運動成為人們預防各種慢性病、科學健身養生、提高生活質量的有效方法與手段。
因此,未來研究者應立足傳統,發揚中醫藥的特色作用,同時拓寬視野,從多學科角度研究武醫融合對于人類慢性病預防和健康促進的作用。
3.3 創新研究方法和手段
當前“武醫融合”的研究,以文獻資料、邏輯分析、專家訪談等研究方法為主,多為理論思考,缺少實證與案例分析以及多案例交叉對比研究,單一、重復的研究方式制約了創新性成果的涌現。因此,未來研究者要在研究方法、手段上進行創新,并在實踐中加大實證調研與實驗研究力度,以增強研究結果的可行性與創新性。通過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結合的方法,如扎根理論、結構方程模型、定性比較分析法(QCA)等,對武醫融合的實際狀況開展調研,從而更加精準地識別出當前理論和實踐中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與此同時,充分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對國內外專家、學者的有關觀點進行追蹤、梳理和歸納,總結歸納武術和醫學發展和演進中的一般規律,進而推進“武醫融合”的研究。
3.4 開展跨學科、系統性的研究
當代科學的發展日益顯示出綜合化、一體化的特點,并逐漸呈現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與交叉的趨勢。當前學術界面臨著知識系統分化、知識條塊分割和學科藩籬林立等諸多現實問題,推動學科交叉融合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因此,今后研究人員應該拓寬自己的學術視野,進行多學科交叉、多視角的研究,從生理、免疫、預防、康復等多個方面對“武醫融合”進行多維度的研究。同時,重視武醫融合與產業經濟學的合作研究,如與醫藥企業的合作。很多傳統功法講究練養結合,例如,中國傳統拳術八卦掌的習練,不僅講究練,更重視“練”之后的“養”,即用特殊的藥水浸泡雙手,以免雙手在練習過程中產生的傷口發炎潰爛。民間的老拳師,掌握著諸多傳統醫藥古方,但缺乏傳承推廣路徑。而醫藥企業具備大批量生產的條件,卻缺乏這類民間處方。因此,未來研究者應加強老中醫、老藥工傳統技藝傳承研究,大力發掘與整理民間中醫藥驗方、秘方和技法,并探尋與醫藥企業的合作之路,讓醫藥企業用現代制藥方式批量生產此類醫藥制劑,促使中醫藥古方得到有效的傳承和推廣。此外,還應加強武醫融合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對其深層次的理論內涵、現實困境、實現路徑、評價反饋開展系統研究。
4 結語
武醫融合是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國民健康的有效手段。“武醫融合”的發展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社會和高等院校等多方的通力合作,以保障“健康中國2030”的實現。但是,當前“武醫融合”的研究尚處在初級階段,在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上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今后,研究人員應該圍繞“武醫融合”的理論和實際難題,積極主動,勇于擔當,深化“武醫融合”的研究,為我國體育和教育的改革提供科學依據。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國務院.“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EB/OL].[2019-10-20].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0/26/content_5445336.
[3]劉曉蘭.鄭懷賢武醫結合思想體系探討[J].文體用品與科技,2017(6):48-49.
[4]喻琳超,范辛堯.武醫健康養生學學科體系的研究與分析[J].中華武術(研究),2014,3(9):45-51.
[5]張山,溫佐惠,馬麗娜.中華武術發展的回顧與展望[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1(1):21-22,51.
[6]劉帥.雙重國家戰略下高校傳統武醫融合的傳承與創新研究[J].現代職業教育,2020(50):80-81.
[7]郝建峰,喻南錠.新課改理念下“武醫結合”式教學在高校武術課程中的應用分析[J].體育科技,2021,42(2):83-85.
[8]侯樂榮,解勇.鄭氏傷科理論與臨床[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9]吳誠德,樂秀珍.練功與養生[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82.
[10]郭玉成,李守培,劉韜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武術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體育科學,2021,41(7):13-23.
[11]邱丕相,郭玉成.論武術體系框架的構建[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1(3):64-67.
[12]付強,周永紅,黃廣勛,等.武醫結合開創自然療法之思考[J].光明中醫,2006(7):13-15.
[13]卿光明,馮媛媛,何穎.鄭懷賢“武醫”思想研究[J].中華文化論壇,2018(6):143-148.
[14]陳玩輝,楊遠平,林友彪,等.運動處方干預對青少年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15,35(2):105-109.
[15]劉鐵民,李書先.太極拳運動對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心血管系統應激性、適應性和耐受能力的干預效應[J].中國臨床康復,2004(33):7508-7509.
[16]曹云,楊慧馨.新編健身氣功與健康促進研究綜述[J].哈爾濱體育學院學報,2014,32(3):93-96.
[17]周小青,曾云貴,楊柏龍,等.健身氣功·八段錦對中老年人血脂的影響[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7(6):795-797.
[18]潘華山.八段錦運動負荷對老年人心肺功能影響的研究[J].新中醫,2008(1):55-57.
[19]黃濤,常建東.健身氣功·八段錦對不同性別中老年人一氧化氮、丙二醛和超氧化物歧化酶代謝的影響[J].中國臨床康復,2005(16):162-164.
[20]朱寒笑,郟孫勇,陳雪蓮.16周新編五禽戲鍛煉對老年女性身體機能相關指標的影響[J].中國運動醫學雜志,2008(4):499-500.
[21]吳康,李匡時,李媛媛,等.基于圖論與fMRI探究太極拳對慢性疲勞綜合征患者默認模式網絡的影響[J].中華中醫藥雜志,2023,38(5):2465-2469.
[22]丁省偉,范銅鋼.健康中國視域下“武醫融合”健康促進體系框架構想[J].湖北體育科技,2019,38(7):578-582,619.
[23]任定甲.健康中國視域下武術與中醫融合基礎與發展路徑[J].當代體育科技,2021,11(34):122-125.
[24]林玉平.健康中國視域下武醫深度融合發展研究[J].武夷學院學報,2021,40(10):79-83.
[25][漢]劉向.山海經[M]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