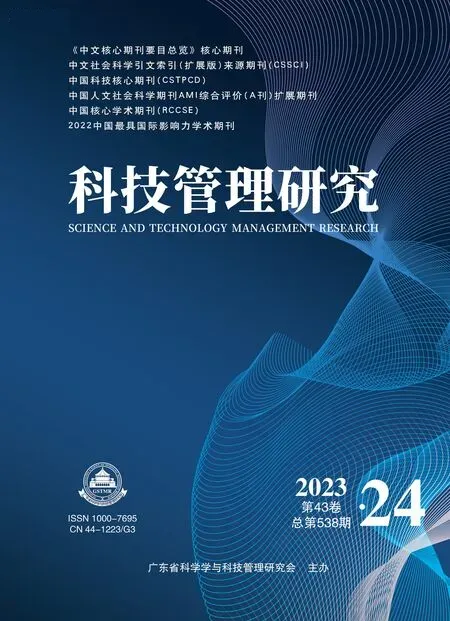中國古典音樂的精神內涵及當代傳播
——評《論樂之韻:中國古典音樂藝術精神研究》

書名:《論樂之韻:中國古典音樂藝術精神研究》作者:蔡曉璐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ISBN:978-7-5177-0332-7出版時間:2015 年5 月定價:36 元
中國古典音樂發源于先秦時期,歷經幾千年的藝術和文化積淀,綿延不絕,彰顯出所積累的深厚精神內蘊,及至當代亦散發著獨特的魅力。由蔡曉璐著、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的《論樂之韻:中國古典音樂藝術精神研究》將音樂之“韻”分為“形而下”的“器”和“形而上”的“道”兩個方面,以“器”和“道”為論點闡釋了中國古典音樂的精神內涵。筆者基于教育部“十四五”規劃重點課題《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科研成果《古典音樂的傳統傳播方式與新媒體傳播方式研究》(編號:JKY312027KT)的研究結合該書內容,探究中國古典音樂的精神內涵及傳播。
中國古典音樂是中國藝術中的一部分,以追求中國藝術中哲學和美學的統一為終極目標,即“天人合一”下的“道”。“道”為萬物之始,宇宙之元,道生萬物,萬物周而復始又最終回到“道”上。“道”還體現在萬物相生相克、一陰一陽的正反對立統一中。中國古典音樂的終極精神亦體現出“道”的典型特征。音樂的創作來源于人情感的自然表達,體現著物我的統一,最終旨向是欲達到物我相融的無間狀態。中國古典十大名曲(《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漁樵問答》等)無一不是自然與人的統一,回歸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狀態。中國古典音樂中的基本要素——律呂,便是以陰陽相對的形態出現,又歸于求同存異下的“和合”。十二律按次序分奇、偶數排列,奇數位為陽律,稱“六律”,偶數位為陰呂,稱“六呂”,合稱“十二律呂”。以陰陽相分的十二律呂組合成完整的音樂回歸于“一”。正如《呂氏春秋·仲夏紀·大樂篇》記載:“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音樂亦是由一陰一陽、一上一下組成樂章,在分合變化中歸于和合,體現“道”的精神。
中國古典音樂的精神內涵還體現為“盡善盡美”的儒家美學追求。儒家倡導以“仁”為核心的“仁義禮智信”的統一,中國古典音樂的精神內涵亦體現并闡發了儒家精神。孔子曾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做了人,卻不仁,會如何對待禮儀制度,如何對待音樂?可見,為人而仁方可得樂之義,證明樂的精神內涵包括“仁”。孔子的弟子子夏也曾說過禮樂是在仁義之后產生的,孔子對此十分贊同。孔子曾聞《韶》樂,而三月不知肉味,這正是音樂強大的內在精神的作用。孔子曾經評價《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對《武》樂的評價則是“盡美矣,未盡善也”。《韶》為舜時的樂曲,舜的天子之位由堯禪讓而來,合乎禮義;《武》為周武王時期的樂曲,周武王是通過伐紂建立的商朝,未盡善。二者都盡美,《武》卻未盡善,可見中國古典音樂不僅追求“形而下”的“器”之美,又追求“形而上”的“道”之善。中國古典音樂“盡善盡美”的精神內涵還體現在儒家一以貫之的教育體系中。古代中國有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樂”指音樂,這六者為六種技能,共同構成了古代教育體系中的主要內容,音樂作為其中之一,蘊含著教育精神中對盡善盡美的追求。
古代的音樂還蘊含雅正精神,發揮著教化的作用。《尚書·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舜帝任命夔掌管音樂,使夔發揮音樂的作用,教化學子們正直溫和、寬厚堅定、剛毅而不暴虐、簡約而不傲慢。由此可以看出音樂具備的雅正精神。《禮記·樂記》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樂的情狀直接和國家的政治狀態相關聯,太平社會的音樂是安詳而歡樂的,混亂狀態下的社會音樂便是怨恨而惱怒的,將亡之國的音樂哀愁而憂思。明君致力于國泰民安盛世之治,在其治理過程中輔之以音樂,正是源于音樂的雅正精神。包括《詩經》中的風、雅、頌無不與音樂相聯系,并有著嚴格的區分。與音樂相配合的《詩經》亦強調音樂所蘊含的雅正精神。
中國古典音樂蘊含著豐富的精神,不僅是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的代表,也是當代藝術和中國精神的重要淵源。中國古典音樂的藝術審美具有極高的造詣,所蘊含的精神更是國之瑰寶,理應得到傳承和發展。中國古典音樂在當代社會的傳播有其必要性,各方必須同心協力助推其在當代的傳播,并且充分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與時俱進,使中國古典音樂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共同守護并發揚中國古典音樂的精神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