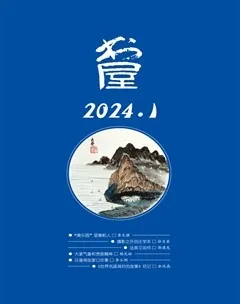照著葫蘆畫瓢
崔述偉
筆者退休經年,后應邀赴美游,客居舊金山“中國海灘”邊。邀請人鐘武雄,曾任抗戰勝利后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簽證官,1948年出任民國政府駐休斯敦領事館副領事,后代理館務,分管周邊十四個州的領事保護。他于抗美援朝戰爭后辭職下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移居舊金山,與其妻黃德榮(長沙人)開辦了“湖南小吃”,引起歐美主流媒體注目,登上了《紐約客》及1979年《時代》周刊。1981年,夫婦倆捐建“中國海灘”紀念碑,2008年7月1日《參考消息》載文《中國海灘立碑記》,稱他為“灘主”。
鐘武雄與“中國的辛德勒”何鳳山是連襟,他們共同創建了北加州湖南同鄉會。他有八個子女。我等二人抵達時,他(妻子已經去世幾年)和三女兒索菲一道迎接。索菲是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退休的科學家,曾任大連理工大學外籍教授,清華大學曾買下了她的計算機教材的版權。她1948年生于南京,后來生活在美國,會說中文,卻鮮識漢字。鐘老是醴陵人,向他女兒鄭重介紹道“密斯特崔、密斯特徐”,并讓她為我們各配一片鑰匙,以方便出入。第二天早上,索菲來時,老徐(黃德榮表內侄)問她:“索菲,喲茨勒?”講的是湖南“塑普”。索菲不懂,我只好臨時充當翻譯,用普通話復述一遍。索菲頓悟道:“你是說喲茨嗎?配好了,給你們一人一串。”老徐喜出望外地說:“你長沙話講得蠻不錯的嘛!”“那當然!我媽媽是長沙人。我從小就聽長沙話長大。”有天早晨,我見老徐輾轉于床,遲遲不起,便獨自作周邊游。中午回鐘宅,卻見老徐留條:“我隨鐘老外出了。”鐘家餐廳里有多種食品,僅罐頭就有幾十個。我隨便吃了些,寫下當天見聞,午睡醒來后,繼續坐在三樓客廳里寫文章,不覺太陽已西斜。忽見鐘家座駕開到車庫門前,一會兒,鐘老拎著個外賣盒進樓來,向我說:“索菲帶我們到斯坦福大學去了。你還沒吃吧?快趁熱!”我心中頓生失落。幾天后,索菲來了,見我即說:“老徐上次要去我家看看,我爸爸也很久沒去過了。我就帶他們去了斯坦福。今天我再帶你去看吧。”原來,她家在硅谷有一棟房子,夫妻倆常去斯坦福打球。我不想冒昧造訪她的家庭,便提議去胡佛研究所。
甫進研究所的圖書館,面對的是一位三十來歲、不茍言笑的亞裔面孔,但開口卻是讓我不知所云的英語。我只得在一旁待著,任憑索菲與之交涉,填寫卡片,辦理準入手續。索菲讓我拿出護照、簽證讓對方登記。我亦說聲“謝謝”,那人才回以“別客氣”,原來是中國人。進入后,索菲交給我兩張寫著她的英文名字的卡片,并告知,使用期限一直到八月份,可以多次使用。查閱資料時,不能照相和復印,卻可申請使用電腦。我心中一片茫然。閱覽室內,只有寥寥數人,但個個無言,人人低頭忙著,有如一堂菩薩!我想,我這是怎么啦?來這兒干嗎?我又能干什么?自己既非學者,又非專業人士,只是個退休的觀光客,一念之差,“誤”入胡佛,豈敢不懂裝懂?索菲告知:“每次只能看一冊,也就是一年的日記,看完后再換一本。你想看什么時候的?”我不敢說“隨便”,只好說,開始的那本吧。她又說了一句什么,我不懂。她指著室內的幾尊半身塑像讓我看。我搖頭說,我不認識這些洋人。“她是華人,很有名的,你也不認識?”我頓悟了那是誰,忽然不由自主地熱淚盈眶,索菲卻莫名其妙地搖搖頭。我一邊擦拭眼淚,一邊趨前觀看塑像底座上的文字:“張純如IR1S CHANG(1968.3.28—2004.11.9)。”她是美籍華人,《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一書的作者。
索菲此時已不辭而別,大概是回她家去了。我靜下心來,打開了“日記”的影印本。它是從1927年元旦開始的。某人首先以小楷,在當時那種普通的國民日記本右下方“社會紀事”中寫道:“又是一年了,列強如故也。”區區十個字,即描繪了當年中國的大背景,亦讓我的思緒回到了那個時代。我迅速瀏覽了日記正文,不過是一些行政、軍務瑣事。但日記的主人公,卻參與和改變了中國歷史。于是,我索取了紙筆開始抄筆記,而且按其格式,盡可能模仿原文的書寫特點,“照著葫蘆畫瓢”認真地抄了幾頁,一直到索菲來尋我。鐘先生問我有何收獲,我還真的談不上,只能將筆記呈上,以示交卷。沒想到他卻頗為贊賞:“不錯,真的不錯!沒想到你會以這種方式描繪史料,既到了這所名校,還進了胡佛研究所。很多學者史家都沒得你這樣的運氣,也沒得你這樣‘靈泛’。那天,我到了那里,都沒想要進去看看。”說著,他拿出一冊《世界周刊》遞給我說:“剛剛來的,我看了也想走進胡佛呢!送給你。”鐘老抗戰期間畢業于中央大學歷史系,當上外交官后,還在職讀研,在休斯敦大學攻讀過歐美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