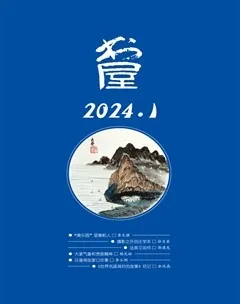“多余人”與“勞工神圣”
顧琛
1918—1920年,沈尹默在《新青年》雜志發表了十八篇白話詩,奠定了他新文學運動先驅的歷史地位,他與胡適一并成為中國白話詩的開拓者。《月夜》作為新詩史上第一首散文詩,成為白話詩的經典,受到了學界的關注。沈尹默其他白話詩亦精彩紛呈,富有時代氣息。不過,這些詩被關注的程度不高,有些詩的深意,需要被更好地挖掘。
人力車夫這個社會底層群體是五四勞工文學中最重要的形象之一。作為白話詩的代表性人物,胡適和沈尹默兩位文學大家在1918年第四卷第一號《新青年》雜志上各自發表了同名白話詩《人力車夫》。
人力車夫
沈尹默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風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門去,雇人力車。街上行人,往來狠〔很〕多;車馬紛紛,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車上人,個個穿棉衣,個個袖手坐,還覺風吹來,身上冷不過。
車夫單衣已破,他卻汗珠兒顆顆往下墮。
在1928年《民立學期刊》上有一篇文章《研究:詩概:人力車夫》評論道:“此詩寫車夫苦況。歷歷如繪。起四句以‘悠’‘流’為韻,是寫天時。第二段以‘多’‘么’為韻,是寫人事。第三段以‘坐’‘過’為韻,是寫坐車之逸。第四段用‘破’字‘墮’字承接前韻,是寫拉車之苦。一氣呵成,如畫如話。”
這首詩是以坐車人的視角去看人力車夫生活的艱辛和勞動的艱苦,但是如果僅僅局限在作者“同情”人力車夫,則低估了整首詩歌所傳達的思想。詩中“車馬紛紛,不知干些什么”這句,被許多人忽視。“不知干些什么”恰恰表達著“我”的迷失。“我”將做什么?“我”將去往何處?這種迷失,仿佛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精英階層對于自己使命的彷徨和迷失。面對著這車水馬龍,螻蟻一般辛勤勞作的車夫,精英階層或知識分子的“我”,該做什么?
“零余者”的形象,由這句“不知干些什么”表現出來。“零余者”又稱為“多余人”,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他們不愿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污,但因遠離人民,無法擺脫貴族立場,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為。“多余人”的形象也影響著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用郁達夫的話來說,(零余者)是一群生則于世無補、死亦于人無損的知識分子。他們被作者賦予感傷的心理,苦悶的情懷。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知識分子上無法改變局勢,下不能拯救黎民。他們受過“現代性”的啟蒙,現實卻讓他們無力改變。覺醒又害怕改變,這種矛盾心理表現出“多余人”的軟弱和一事無成。在對“多余人”精神頹廢和萎靡的描繪中,作者深刻地揭示出改變現實的重任要呼喚新人來擔當。
不得不說,我們從《人力車夫》這篇現代詩中感受到沈尹默對于“多余人”的思考。“人力車上人,個個穿棉衣”這句話,雖然讓我們聯想到古詩詞中“遍身羅綺者”“十指不沾泥”等對于社會不公的控訴,但是沈尹默的高妙之處,還表現在后面的“個個袖手坐,還覺風吹來,身上冷不過”。
俄國十月革命的現實震撼,激發出知識分子對于以往鄙薄做工做農的一種懺悔。于是,“勞工神圣”被提了出來。新文化運動倡導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學,旨在造就新的國民,在于通過文化內容的更新來改造國民性與實現新民。宣揚“勞工神圣”,其實是知識分子在尋找新的社會力量來實現新的社會發展途徑。
人力車夫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們顯然是作家描繪的最佳對象,從而被借以表達“勞工神圣”這個主題。
我們看到詩中車夫的單衣破、汗珠落恰好和車上的人形成對比。這里的嚴寒寓意時代的嚴寒,那么人力車夫的形象一下子就高大了。即便單衣已破,但是他們是沖破嚴寒的實踐者,是與車上“多余人”相反的一群人,是他們載著“多余人”沖破時代的嚴寒,走向彼岸。從這個角度切入,整首詩不經意地把五四“勞工神圣”這一核心理念表現出來。
沈尹默曾經謙虛地說:“說起五四運動,我自己覺得有點慚愧,因為我在當時不是隊伍中的一個戰士,不過是伙夫之流,說得好聽點,也不過是一名衛士,或者是一個伙夫頭兒罷了。”然而,讀罷《人力車夫》,這豈止是“伙夫頭”!周谷城先生曾經總結:“他(沈尹默)不認為自己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戰士,不過是一名衛士角色。這是謙虛之辭。他是早期白話詩倡導人之一,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名戰士。”作為《新青年》的編輯,白話詩運動的發起者和實踐者,沈尹默先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功績和貢獻影響著時代的進程,他的白話詩也需要有更立體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