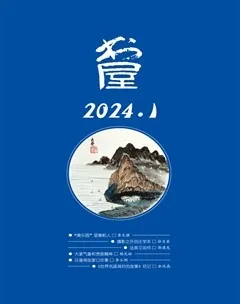《不開也不落》序
我自小不喜歡佛。
多年后,反省過自己,究其原因是生活環境與出生年代所致,亦有我個人的無知。也始終認為自己是個無根之人,受鄉間文化熏染不夠,沒有刻骨銘心的童年記憶。對母親說的供祖,叫飯點燈,大年三十接祖回家,祭灶王爺,正月十五前不生火,端午插艾、系紅絲結,以及挖野菜等諸多生活場景,陌生又羨慕。看似輕松的生活細節,實是一個人的根,這便是習俗的力量。
我生在1968年,名字叫迎春,堂弟的名字叫紅偉,皆前衛。打記事起,便抵觸“封建迷信”,認為那些東西土、灰暗,似陳舊年代的凍瘡,甚至有些令人恐懼。
直至四十歲,去到山東博物館,站在幽暗燈下,見到那些林立的佛造像,竟被深深吸引。那些眼瞼下垂、嘴角上揚,似笑非笑的佛,沉靜、自我、陶醉、內斂,旁若無人,仿佛能感受到它們內心深海般的平靜。沒憤懣,沒爭奪,沒一絲一毫廉價的情緒。情不自禁圍著佛像轉了好幾圈,飽滿的額頭,優雅的手勢,結構造型無一不美。并非幼時在破敗寺廟,或成年后在金碧大殿見到的涂脂抹粉的佛。它們來自邈遠的古代,是真正的佛造像,出自寺院遺址或地下。東晉青州的佛造像,無疑是全世界最美的佛造像。
這讓我明白,最動人的笑容是笑給自己的。
這幾年,我炒菜極少放佐料,油鹽即可,蔥、姜、蒜也省了,或者說壓根想不起。我開始越來越理解:尊重事物本身,盡量保持其原貌、其原始味道,以及獨立,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甚至認為那些佐料是噪聲,影響了事物本質的清寧。它們無法選擇自身,似《紅樓夢》里那盤二十多道工序的茄鲞,一定很好吃,但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構不成吸引力。
我甚至對友人說,有錢人吃的多半是垃圾。話雖偏激,擁有土地的勞動者能獲取第一手食材,這是不爭的事實。單純,淡而有味,淡而悠長,尤為珍貴。不屬珍味,卻裨益自身。
火力加時間,是永遠無法取代的法寶。火候到了,味自美。我相信火候,也盡量把這樣的理念帶進我的寫作。
《金瓶梅》《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皆一脈相承,風平浪靜,卻暗藏殺機。看似寡淡,并不影響其深遠。好文章是壓著寫的,不喜重口味,過分使力,必然做作,包括措辭與文風。相對于打打殺殺,我更喜歡平靜,哪怕廢墟上的平靜。
友人曾開玩笑說,你死后,墓志銘寫上“寫自己散文的人”。這個提法挺有意思,盡管我不知道自己有無墓碑,至今的想法是全然交還泥土。一個個墓碑連起來,人類前后相繼,該有多少墓碑,地球早晚會被占滿。泥土是個好東西,能消化分解諸多物質,平復修整自身細胞,循環孕育萬物。
人源自萬物,再歸還萬物,可以說是場奇妙之旅。地球的美好是靠生、死維護的,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
我甚至認為不需要來世,一把塵埃,何嘗不是生命最美的歸宿。
散文是我喜歡的一種文體,似石縫里的花,堅韌、蓬勃。同時,又是低調、不喧嘩的。它是一種調調、一種味道。人世間本無新鮮事,故散文是一種情感藝術,不僅滲透作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又是一種浸淫式表達。辭藻炫目,只是技術;大白話,能寫出高級感,才叫本事。就像吃飯,吃的是味道。
寫作,寫的是滄桑,文學亦藥,所以它是苦的。那些很甜膩的,本身就不是文學,故散文還有一個深度與見識的問題。
如安德魯·懷斯的畫,殘疾女孩匍匐在地,艱難扭曲地移向高岡。我們每個人到達高岡的姿態、心理,所付出的代價均不同,這便是藝術。
散文屬自畫像,即便繪群像亦屬自畫像。自畫像并非易事,一眼的孤單迷茫。甚至不需要名目,面對精神世界遙遠的太陽,它的升起、衰落,以及趨于黑暗,都是珍貴的。
不開就不落,是種靜止的生命狀態,也是永恒。似東晉佛像上手持蓮蕾的侍者,沉靜、自足,幾千年依舊保持同一姿勢,又如億年前被人遺忘的化石,忠實記錄下自身的渺小與孤單。本書遴選本人2021年至今發表的部分散文作品。分兩輯,第一輯,傾向人;第二輯,傾向物,兩者互融。一內,二外;一守,二行。有對往事的追憶,也有對當下發生的事的記錄,以及對未來、對死亡、對弱者的思考。
身體里住著月光、水分、土壤的人,是清涼的。春天,你得交出一切。夏天,看著它奔跑,歡笑,肆無忌憚地成長。而秋天是做減法的季節,冬日你得裹緊大衣,躑躅而行,護住最后一絲暖。生命從盛至衰,誰也躲不過。
過去讀書,常見“謀生”二字。生活是謀的,是要爭取、付出的。我的父輩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鐵路人,我們自小生活在外,故鄉對我們是遙不可及的夢,我甚至一度認為自己是沒有故鄉的人。當我們長大歸來時,故鄉已不太相認。那些鐵路,是工人一錘子一錘子,一撬棍一撬棍,手工建造出來的。它們蛛網般分布在全國各地,屬于工業時代的象征。
故鄉,也是一個人的精神父母,或陷阱。鐵路子女的故鄉,是由一個個站臺組成的,不僅父輩修山洞、架橋梁,子女也在不斷丟失著記憶和學習機會。在我們最需要故鄉的時候,正在漂泊著,但我們也會盡力去愛所在城鄉,且把每個經過之地都當成故鄉。
時間,真實的歷史,線性鏈條里曾經的一環。我一直癡迷這樣的瞬間與無休止的伸展,以及它所衍生的生命和生命本身附加的故事與意義,甚至灰塵與破敗之美。
寫自己的散文,是我堅守的坐標,而非目標。希望能深情演繹好這個自己深愛的世界,她的苦與痛、美與歡樂,以及結痂的傷疤都是筆下神經和紙上元素。保持自身純度,不陳詞濫調,有一目了然的敘述方式和辨識度,是必須的,也是極自然之事。同時,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對環境、對人與自然、人與自心的定位,有新的思考。洛陽作家淺藍曾說:“菡萏能寫極優雅的文字,也有難得的丈夫氣與清晰思辨力,讀她第一本書便看得出,所謂雌雄同體也。”謝謝如此中肯的評價。我寫思想隨筆也許更得心應手,這種細致柔軟的敘述,只是為了讓自己能更好地安靜下來,進入一種自我言說狀態。其中也會夾雜氣餒迷茫、審美疲勞、無法突破、言說毫無意義等心境,且一直糾結彷徨。但還是試著寫下去,分享給這個世界,或權作自身的一小片單薄的月光。
時間是不老的,是記憶森林里的“百草”,長在自己的年輪里,又似手中攥過的親切樸素的時光。不想拘泥于某些事物,尤其無意義的消耗,這是越來越迫切的想法。
感謝賜予我溫暖、理解我精神生活之人,也感謝親愛的讀者。
真正的快樂,非錢、物所能抵達。自然刮過的風,須有光與水的照耀與內心篩選。一個人若不能給他人送去溫暖與力量,減少傷害是最好的途徑與修養。
《不開也不落》是紙上定格,也是血肉回歸自身及泥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