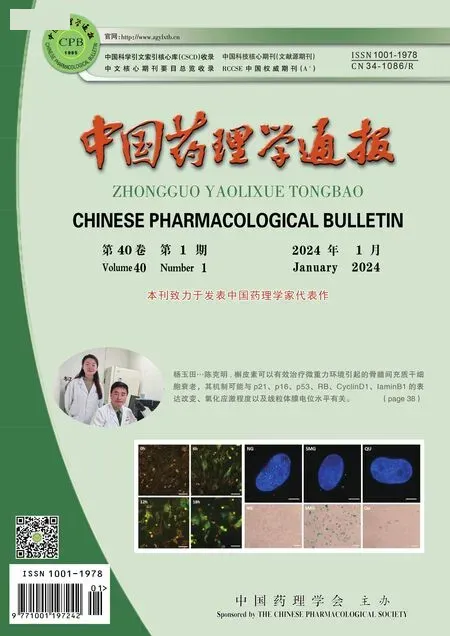細胞焦亡與肺動脈高壓的關系及治療肺動脈高壓藥物研究進展
顏 倩,孫 洋,龍俊鵬,劉莎莎,姚 嬌,林玉婷,陽松威,楊巖濤,裴 剛,艾啟迪,陳乃宏,4
(1. 湖南中醫藥大學藥學院,2. 湖南省中藥飲片標準化及功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208;3. 湘潭市中心醫院,湖南 湘潭 411199;4. 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北京協和醫學院藥物研究所,北京 100050)
細胞焦亡作為伴有炎癥反應的程序性細胞死亡方式,炎性體傳感器識別多種病原體和損傷相關分子模式,推動了caspase-1或4/5/11的激活,它們裂解gasdermin-D,分離N端成孔結構域(pore-forming domain,PFD)和C端抑制結構域(repressor domain,RD)。而后PFD在膜中形成大孔,驅動細胞膜膨脹和破裂。大量研究證據表明,細胞焦亡參與影響PAH的發生發展,抑制細胞焦亡可以緩解PAH疾病的嚴重程度。
1 細胞焦亡
1.1 細胞焦亡的發展歷史最早對細胞焦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6年。Friedlander指出用炭疽致死毒素(LT)處理原代小鼠巨噬細胞,可導致細胞死亡和內容物的快速釋放。1992年,Zychlinsky等通過觀察在革蘭陰性細菌病原體福氏志賀氏菌感染的巨噬細胞中發現的自殺現象,首次發現細胞焦亡。這種某些過程和特征與凋亡相似的細胞死亡形式,最初被認為是細胞凋亡。2001年,D′Souza等提出“細胞焦亡”一詞,用于描述促炎性程序性細胞死亡,使細胞焦亡和細胞凋亡(細胞非炎性死亡程序)區分開來。2002年,Martinon等首次提出炎癥小體可以加工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IL-1β)及激活炎癥性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caspase)。在2012年,Peter Broz等指出在不需要caspase-1的情況下,非經典caspase-11途徑也能增加沙門菌的感染率。2017年研究者發現細胞焦亡可由caspase-1或者caspase-4/5/11激活[1]。
1.2 細胞焦亡的機制先天免疫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炎癥小體,是識別致病原和無菌性損傷的宿主防御的第一道重要防線。炎癥小體檢測細胞質中的病原體和損傷,并響應觸發細胞焦亡,這是焦亡形成的關鍵環節。炎癥小體由五種特征明確的傳感器啟動,包括核苷酸寡聚結構域樣受體(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 like receptors,NLR)家族中NLRP1、NLRP3、NLRP4以及IPAF、AIM2炎癥小體,它們能夠識別病原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或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其傳感器與細胞質中的銜接分子凋亡相關斑點樣蛋白ASC(apoptosis associated speck- 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RD domain,ASC)相互作用,招募和激活caspase-1。caspase-1加工和激活IL-1β和IL-18,切割 GSDMD形成N端結構域,一旦通過切割分離,GSDMD-N通過與磷脂酰肌醇磷酸和磷脂酰絲氨酸結合而轉移到膜上,并通過形成多亞基孔寡聚化形成10~20 nm孔徑通道。孔道的形成造成滲透壓變化,進而破壞細胞膜,促進炎性因子IL-1β和IL-18的釋放和細胞焦亡,這就是經典細胞焦亡通路。在特意阻斷caspase-1通路后,并不能完全阻斷細胞焦亡的發生,這涉及到細胞焦亡非經典通路。非經典通路是不依賴caspase-1激活,直接由caspase-4/5/11炎性體結合細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從而激活GSDMD后形成孔徑通路,引起細胞焦亡。
1.3 細胞焦亡相關疾病細胞焦亡參與多種疾病的發生并發揮重要作用,如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代謝性疾病、肺纖維化、腫瘤、肝臟疾病及婦科疾病等。最初在巨噬細胞中發現細胞焦亡,其與感染性疾病密切相關。細胞焦亡的發生會釋放巨噬細胞內的細菌,比如沙門菌感染、志賀菌、李斯特菌及嗜肺軍團菌等。炎性體可以控制微生物細胞功能,如在革蘭陰性和革蘭陽性細菌感染期間,caspase- 1可以激活調節吞噬體,由此得知細胞自主免疫需要炎性caspase。細胞焦亡參與神經退行性疾病的調控,炎癥小體NLRP3和炎癥因子IL-1β的異常表達可促進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病變。細胞焦亡促進炎癥因子的釋放,這也是痛風、糖尿病等代謝類疾病的重要發病機制。細胞焦亡與癌癥之間的關系復雜,一方面,細胞焦亡可以抑制腫瘤的發生和發展;另一方面,作為一種促炎性死亡,細胞焦亡可以形成適合腫瘤細胞生長的微環境,從而促進腫瘤生長。女性常受婦科疾病的困擾,炎癥小體也可以誘導婦科疾病中細胞的焦亡,比如在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中,炎癥小體可以抑制宮頸癌的發生發展。細胞焦亡在肝臟疾病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已被證實,比如炎性因子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的過度表達,使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持續存在,反而增強了機體的先天免疫能力。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是當前我國高發病率疾病,也是世界范圍內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心血管疾病主要包括了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AS)、肺動脈高壓(pulmonary hypertension,PH)、冠心病、高血壓和糖尿病心肌病。當焦亡發生時,會造成心血管超微結構的變化和心血管組織損傷,誘導疾病快速發展和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不良預后。如現在研究較多的動脈粥樣硬化,其特征是主動脈中的異常脂質沉積、阻塞血流和隨后的斑塊破裂。細胞焦亡通過促進炎癥因子的釋放參與AS的形成和發展,與斑塊穩定性密切相關的caspase-1在AS斑塊中高度表達,研究發現,AS斑塊和破裂病灶中的caspase-1含量顯著增加。caspase-1炎性體通路可以感知升高的脂質,之后上調如NLRP3、IL-1β這類細胞焦亡相關炎癥小體,最終引發細胞焦亡。
2 肺動脈高壓與動脈性肺動脈高壓
2.1 肺動脈高壓PH是一種高發病率、高死亡率、預后差的以肺動脈異常高壓為特征的心血管疾病。PH最常見的原因是左心疾病,導致了左心房高壓和肺靜脈壓力長期升高。左心疾病導致肺靜脈壓力升高的常見原因有左室收縮或舒張期功能障礙以及二尖瓣或主動脈瓣疾病[2]。肺靜脈高壓長期存在可使肺血管阻力(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PVR)升高。全球大約有1%的成年人患有PH,在65歲人群中可能達到10%。PH的定義為靜息狀態下的平均肺動脈壓(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mPA)≥25 mmHg,而這不作為診斷,僅為血流動力學的異常狀態[3]。最近,第六屆世界肺動脈高壓研討會重新定義為靜息狀態下的mPAP>20 mmHg,同時PVR≥3 Wood[4]。不同形式的PH主要癥狀都伴有疲勞、疲憊感的進行性運動性呼吸困難,以多因素肺血管床結構和功能改變為特征,進而導致肺小動脈的強烈重構,嚴重時致右心衰竭和死亡[3]。肺動脈高壓的初期臨床癥狀較輕且不具有典型性,容易導致診斷不及時,從而錯過最佳治療時間段。
肺動脈高壓一詞涵蓋了除了肺循環中的血壓升高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共同點的各種疾病,所以對肺動脈高壓進行準確的診斷分類至關重要。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WHO)將PH根據病因、病理生理和治療分為五類:動脈性肺動脈高壓(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左心疾病所致肺動脈高壓(PH due to left heart disease)、肺部疾病或缺氧引起的肺動脈高壓(PH due to lung diseases and/or hypoxia)、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chronic thromboembolic PH)及不明或多因素引起的肺動脈高壓(PH with unclear multifactorial mechanisms)[4]。PH臨床五類及5類下亞組分類見Tab 1[4]。
2.2 動脈性肺動脈高壓PAH是PH的亞型,要滿足PAH有一個獨特的血流動力學定義,mPAP≥25 mmHg,肺毛細血管楔壓(pulmonary capillary wedge pressure,PCWP)≤15 mmHg,也有人提出新的定義mPAP的下限為20 mmHg。流行病調查PAH患病率為每100萬人口中約有25人患有PAH,其中大多數為婦女。目前,在PAH臨床試驗和登記處有新診斷的患者的平均年齡約為53歲,這不同于早期年輕育齡婦女主要為特發性PAH典型患者的描述[5]。PAH根據潛在的病因進一步分為亞組,包括特發性PAH、遺傳性PAH、藥物和毒素相關的PAH、肺靜脈閉塞性疾病、鈣通道阻滯劑長期反應者的PAH和新生兒持續的PH,以及與其他疾病相關的PAH,例如結締組織病、艾滋病和先天性心臟病[6]。
PAH可以理解為一種罕見的進行性疾病,其組織學典型表現為內皮功能障礙、肺動脈平滑肌細胞和成纖維細胞不受控制的增殖導致肺小動脈閉塞。肺小動脈閉塞后導致肺小動脈壓力增加,進而導致右心室衰竭和死亡。肺部毛細血管是由大約2 800億條迭代動脈分支構成,因此肺血管結構的細微致病性變化可使PVR升高。PAH病理學的基礎是肺動脈平滑肌細胞、內膜成纖維細胞以及肺動脈周圍細胞代謝、生存和生長模式的改變,其病理特征是叢生性動脈病變。隨著疾病的發展,毛細血管前和毛細血管后的主動重塑可能加重PAH[5]。
PAH的重要特征除了PVR升高,還包括肺血管重塑的重要結構改變,表現為內側肥大或增生、內膜和外膜纖維化、免疫細胞(B淋巴細胞、T淋巴細胞、肥大細胞、樹突狀細胞和巨噬細胞)在血管周圍浸潤、積累等[7]。PAH的發病機制與許多分子過程有關,主要包括細胞焦亡、種系突變、炎癥、肺動脈內皮細胞功能障礙、表觀遺傳修飾、DNA損傷、代謝功能障礙、性激素失衡和氧化應激等。
3 動脈性肺動脈高壓的焦亡發病機制
3.1 細胞焦亡與PAH關系細胞焦亡是伴有炎癥發生的細胞程序性死亡,即細胞焦亡和炎癥反應關系密切。炎癥是由身體損傷、感染或局部免疫反應引發的液體、血漿蛋白和白細胞的局部積聚的總稱。近十年來,隨著對PAH的炎癥發病機制研究深入,發現PAH肺阻力血管壁內以及叢狀病變周圍有各種炎癥因子的積累[8]。血管周圍的炎癥因子浸潤充分說明炎癥與PAH發病機制相關。
肺部循環細胞因子水平升高和血管周圍炎癥浸潤是PAH患者表現出的癥狀,PAH中炎癥驅動了血管重塑,其肺血管病變存在于極度發炎的微環境里。PAH患者肺部的組織病理學結果證明炎癥的確可以作為PAH的病理驅動因素,炎性細胞聚集在血管壁周圍,同時升高外周血炎性細胞數量。研究還發現PAH患者的細胞免疫[T淋巴細胞、自然殺傷細胞 (natural killer cell,NK cell) 和巨噬細胞)]受損。例如,NK細胞被確定為不同生理和病理條件下血管重塑的重要調節劑,從PAH患者中分離出的 NK 細胞表現出受損的表型,對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具有高反應性,并且伴隨著疾病相關殺傷性免疫球蛋白樣受體和基質金屬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MMP-9)的產生減少。對大量關于PAH的研究進行回顧和分析發現,PAH患者的細胞因子IL-1β、IL-6 和 IL-8水平升高,而且炎癥物質的循環濃度增加進而通過經典和非經典信號轉導途徑引起免疫反應。這些研究結果與先天免疫反應相關,而細胞焦亡和先天免疫反應密不可分。
炎癥caspase的激活是細胞焦亡發作時的一個重要初始事件,caspase-1/4/5/8/11介導的細胞焦亡在PAH的發病機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9]。NLRP3是參與誘導PAH內皮細胞焦亡中最有特征性的炎癥小體,NLRP3通過產生促炎細胞因子,介導肺動脈內皮細胞焦亡,導致肺動脈高壓[10]。
3.2 PAH中細胞焦亡發病機制
3.2.1caspase-1經典途徑的細胞焦亡途徑是PAMPs和DAMPs接受細胞內信號分子刺激,ASC招募Pro-caspase-1,在炎癥小體組裝后,將Pro-caspase-1切割并活化caspase-1,裂解Gasdermin-D形成孔結構域,而后促炎因子釋放。炎性環境促進PAH血管重塑,加速疾病的發展。實驗研究結果表明,抑制caspase-1介導的典型炎癥小體可以減輕PAH。將體質量180~200 g的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隨機分6組,通過免疫組化染色、免疫熒光、酶聯免疫吸附測定(ELISA)、蛋白質印跡的實驗方法檢測了caspase-1的蛋白表達水平。免疫熒光的結果和免疫組化結果表明抑制了PAH大鼠肺組織中capsase-1、NLRP3表達,蛋白質印跡結果顯示,抑制了PAH大鼠的HPAEC中NLRP3、caspase-1、ASC、IL‐18、IL-1β的蛋白表達水平,抑制效果與MCC950和MDL28170相似[11]。

Tab 1 The updated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of PH into five categories and subgroups under five categories
Circ-Calm4是特定環狀RNA(circRNA),其參加調節肺動脈平滑肌細胞(PASMC)焦亡相關的信號通路和靶點,進而導致PASMC焦亡和PAH發生。通過免疫印跡、實時定量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釋放測定、熒光染色和免疫染色等實驗結果,證明抑制Circ-Calm4,PASMC中細胞焦亡相關蛋白NLRP3、caspase-1、IL-1β和IL-18會顯著下調[12]。
3.2.2caspase-4/5/11 非經典途徑的細胞焦亡途徑是caspase-4/5/11直接與LPS結合,裂解Gasdermin-D形成孔結構域,而后促炎因子釋放。caspase-4/5/11可以介導PAH內皮功能障礙增強血管炎癥,進一步誘發血管重塑和右心室衰竭,從而促進PAH發病。內皮功能障礙可因炎癥介質如腫瘤壞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發生,其在PAH患者和動物模型中升高,研究使用TNF-α作為刺激因子。將200-250 g雄性SD大鼠分3組,通過免疫組化染色、免疫熒光、免疫共沉淀、蛋白質印跡的實驗方法首次證明了抑制caspase-4/5/11有助于減輕PAH的發展。研究結果也進一步揭示了caspase-4/5/11 誘導的細胞焦亡涉及caspase-3-GSDME軸,并且caspase-4/5/11可以直接與caspase-3結合,表明TNF-α誘導的細胞焦亡可由caspase-3介導的GSDME裂解而轉變為細胞焦亡。因此,通過抑制caspase-3的表達也可以達到抑制PAH發展的目的[13]。
caspase-8可以通過非經典和經典途徑參與了Pro-IL-1β的合成和加工,可以調節NLRP3炎癥體和裂解的caspase-1調節IL-1β的產生和釋放。實驗采用caspase-8基因敲除雄性SD大鼠和雄性小鼠隨機分組,通過組織學分析、免疫熒光染色、免疫蛋白印跡、流式細胞術等實驗,結果顯示caspase-8通過巨噬細胞中的NLRP3和caspase-1途徑影響IL-1β的分泌,從而促進肺動脈平滑肌細胞的增殖和炎癥細胞浸潤以驅動PAH的發展,抑制caspase-8的功能可對 PAH產生保護作用[10]。
非經典途徑細胞焦亡也可通過加劇骨形成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二型首體(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r2)信號傳導缺陷,進而加速PAH的發展。在這項研究中,使用了北京協和醫院于2006年11月至2016年3月 PAH患者和非PAH患者來源的樣本,并建立可靠的小鼠模型。研究結果顯示,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檢測PAH患者血清中針對BMP受體的LPS和自身抗體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質譜流式細胞技術(Mass cytometry)比較激素治療前后,PAH患者外周血中炎性細胞的存在變化。此外,還檢測到人肺動脈內皮細胞(human pulmonary artery endothelial cells,HPAECs)中檢測了響應 LPS刺激的Bmpr2信號傳導和焦亡相關因子[14]。
4 藥物治療
4.1 炎癥小體靶向抑制劑NLRP家族和Pro-caspase-1和ASC結合是細胞焦亡的關鍵事件,已確定K+流出、Ca2+信號傳導、Na+流入和氯化物流出,是NLRP3炎癥小體激活的關鍵因素。格列本脲(Glibenclamide,Gli)是一種磺脲類藥物,抑制LPS+ATP誘導的caspase-1激活、IL-1β分泌以及間接抑制NLRP3。Gil抑制細胞焦亡的機制是抑制ATP的K+通道,抑制ASC聚集,從而有效地阻斷caspase-1和IL-1β分泌的激活[15]。16673-34-0是Gli合成過程中產生的中間底物,Marchetti等[16]在小鼠巨噬細胞和原代成年大鼠心肌細胞中研究顯示,16673-34-0抑制 NLRP3炎癥小體的形成,炎癥小體的藥理抑制限制了小鼠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遺憾的是,16673-34-0抑制細胞焦亡機制并不完全清楚。用JC124治療后NLRP3、ASC、caspase-1、pro-IL-1β及TNF-α的蛋白表達水平顯著下降,表明JC124可作為新型的細胞焦亡抑制劑[17],但對于其機制研究少且不明確。FC11A-2通過靶向NLRP3炎癥小體,能顯著抑制促炎細胞因子(包括TNF-α、IL-1β、IL-18、IL-17A和IFN-γ)和mRNA水平,其機制主要為抑制pro-caspase-1,pro-IL-1β and pro-IL-18的裂解,從而抑制了NLRP3炎癥小體活性[18]。小白菊內酯(Parthenolide,Par)是一種運用廣泛的抗炎中草藥,其能顯著減少促炎細胞因子的釋放,包括IL-6、IL-1β、IL-1α、IL-18并且參與調節NLRP3 軸激活,雖具體機制不明朗但可能是通半胱氨酸修飾來抑制NLRP1、NLRC4 和 NLRP3的激活[19]。β-羥基丁酸酯(β-hydroxybutyrate,BHB)抑制NLRP3炎癥小體介導的炎性疾病是通過阻止K+流出和減少ASC寡聚化和斑點的形成,不抑制caspase-1/11激活響應的NLR家族[20]。MCC950是一種含有二芳基磺酰脲的化合物,被認為是NLRP3炎癥小體最有效的抑制劑之一,其能阻斷ATP 水解并抑制 NLRP3 活化,從而抑制NLRP3炎癥小體激活,但其分子靶點還沒有確定[21]。3,4-亞甲二氧基-β-硝基苯乙烯(MNS)特異性地阻止了NLRP3介導的ASC斑點的形成和齊聚,MNS的細胞內靶標是NLRP3的核苷酸結合寡聚結構域和富含亮氨酸的重復結構域,體外給藥也抑制了ATP酶活性[22]。CY-09直接與NLRP3中NACHT結構域的ATP結合并抑制NLRP3 ATPase活性,從而抑制NLRP3炎癥小體激活[23]。曲尼司特(Tranilast,Tra)直接與NLRP3的 NACHT結構域結合,并通過阻斷NLRP3寡聚化來抑制 NLRP3炎癥小體的活性[24]。冬凌草素(Oridonin,Ori)在NACHT結構域中,與NLRP3的279位半胱氨酸形成共價鍵,阻斷NLRP3與NEK7的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抑制NLRP3炎癥小體的激活[25]。OLT1177通過直接與NLRP3結合以阻斷其ATP酶活性,并阻斷NLRP3與ASC或NLRP3與caspase-1之間的相互作用來抑制NLRP3炎癥小體的激活[26]。
細胞因子反應調節劑A(CrmA)是第一個發現的caspase抑制劑,CrmA可以作為假底物結合caspase-1并阻斷caspase-1切割pro-IL-1β,從而減少IL-1β的分泌,其可有效抑制caspase-1/3/4/5/8表達[27]。Benzoxycarbonyl-Val-Ala-Asp (OME) -fluoromethylketone(z-VADfmk)是通過不可逆地烷基化半胱氨酸殘基來抑制casapase的活性,從而抑制細胞焦亡,這屬于caspase的廣譜抑制劑。VX740和VX765是caspase-1的選擇性擬肽抑制劑,均可通過共價修飾caspase-1活性位點處的半胱氨酸殘來抑制IL-1β和IL-18的裂解[28]。Ac-FLTD-CMK是GSDMD衍生的抑制劑,可通過體外抑制caspases-1/4/5/11活性,從而抑制對GSDMD的切割,減少炎癥因子的釋放[29]。
4.2 肺血管擴張劑目前針對PAH的肺血管擴張劑治療有3種途徑:刺激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環磷酸鳥苷(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cGMP)生物途徑、增加前列環素(prostaglandin I2,PGI2)對受體的作用和拮抗內皮素(Endothelin,ET)途徑,而采用多種治療途徑的肺血管擴張劑聯合藥物治療在生存結局和臨床惡化時間方面優于單一治療方案[6,30]。NO通過激活可溶性鳥苷酸環化酶(guanylate cyclase,cGMPase)發揮肺血管擴張劑的作用,刺激cGMP的產生,進而激活肌球蛋白輕鏈磷酸酶,降低肌球蛋白的磷酸化,而后降低肺血管張力。增加細胞內的cGMP也可抑制鈣的進入,減少細胞內鈣從而減少肥大和增生,以及可能逆轉肺動脈重塑。PGI2來源于血管內皮細胞和平滑肌中,它會引起血管舒張,并抑制平滑肌細胞增殖和血小板聚集,是一種有效的肺動脈血管擴張劑。合成的前列環素包括依前列醇(prostaglandin I2,PGI2)、曲前列素(treprostinil,Tre)、伊洛前列素(iloprost,Ilo)和選擇性前列環素受體(IP受體)激動劑如司來帕格(selexipag,Sel)。ET-1主要由血管內皮細胞分泌,是一種有效的內源性血管收縮劑。ET受體拮抗劑,如波生坦(bosentan,Bos)、安立生坦(ambrisentan,Amb)和馬西替坦(macitentan,Mac),可阻斷ET-1的活性,促進PAH 患者的肺血管擴張。

Fig 1 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 injury mediated by pyroptosis and related therapeutic drugs
5 結語與展望
總之,細胞焦亡中炎性體傳感器識別多種病原體和損傷相關分子模式的能力表明,焦亡對機體防御病原體至關重要。焦亡使細胞釋放細胞質內容物,從而提供啟動炎癥級聯反應的有效信號,局部炎癥導致免疫細胞的募集和啟動,最終有助于從機體清除病原體。研究細胞焦亡與PAH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新的信號成分和通路機制,這或許可以進一步預防或治療PAH。遺憾的是,動物實驗雖證明了多個靶點藥物對PAH的抑制作用但很多作用機制不明或其分子靶點不確定。許多問題仍待解決,例如16673-34-0、小白菊內酯抑制NLRP3的具體機制,確認MCC950分子靶點。相信隨著研究靶點抑制劑機制的不斷深入,探索藥物靶點的開發,可以為PAH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案,提高臨床療效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