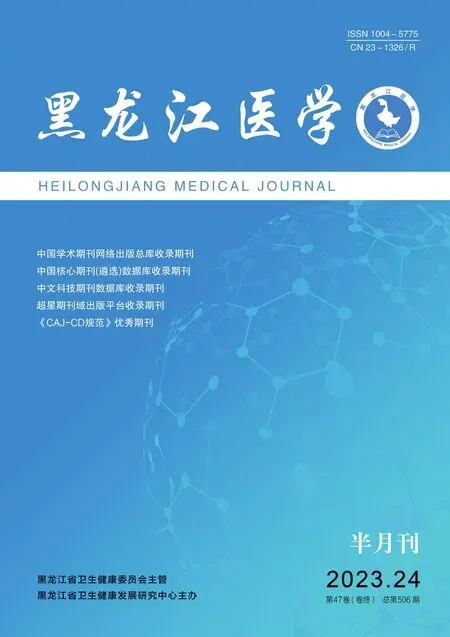職業性噪聲聾發病機制及防治的研究進展
寧 津,蘇彥祥
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分院職業病科,天津 300250
職業性噪聲聾是指人們在工作中長期接觸噪聲而出現的漸進性感音神經性聾,可出現聽力下降、耳鳴等癥狀[1],并可引起頭暈、失眠等情況,嚴重影響工人的生活,并導致溝通困難、社會孤立和生活質量下降等危害,影響工人的身心健康。目前,估計全世界有超過1 億人由于噪聲過度暴露引起聽力下降,引起了嚴重的健康問題。我國職業性噪聲聾的發病率非常高,目前已成為繼塵肺病后第二常見的職業病,并且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2],因此職業性噪聲聾的防治研究十分重要。本研究就職業性噪聲聾的發病機制及防治進行綜述。隨著對職業性噪聲聾不斷深入的研究,發現其發生是由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現報告如下。
1 遺傳因素
1.1 噪聲性耳聾
噪聲性耳聾(NIHL)的遺傳易感性已經在動物實驗上得到證實,年齡相關性聽力損失的小鼠(C57BL/6J)更容易受到噪聲的影響[3]。目前已經證實與Ahl有關。Ahl是一種CDH23基因,此基因缺失有導致NIHL可能。
1.2 對NIHL易感基因的人群研究
由于受試者幾乎不可能都暴露在相同的噪聲條件下,同時由于存在大量混雜因素(個人生活史、耳毒性化學藥物史等),故人類NIHL的遺傳研究非常困難。目前,鑒定易感基因常用方法是篩選已知在內耳中起到不同功能及形態作用的不同基因的單核酸多態性(SNPs)。單核苷酸多態性是基因組中的常見點突變,它們的基因分型被認為是分析復雜疾病遺傳背景的重要工具。目前內耳鉀離子(K+)再循環基因、熱休克蛋白(HSP)基因和原鈣黏蛋白15(PCDHl5)基因,肌球蛋白14(MYH14)基因研究效力較高。
內淋巴液中特有的高濃度K+在毛細胞的功能中有著重要的作用 對于聽力過程是必不可少的。K+循環相關基因(KCNE1、KCNQ1、KCNQ4、GJB2 和GJB6)的突變可導致聽力損失。Van Laer等[4]在瑞典暴露于噪音的男性工人群體的NIHL 病例對照關聯研究中發現,KCNE1 基因的三個位點SNPs 在等位基因、基因型及單倍型以及KCNQ1 的一個位點及KCNQ4 的一個位點的等位基因頻率在易感個體和耐藥個體之間有顯著的差異。有研究[5]在波蘭噪聲作業工人中對99個SNP進行基因分型后亦得到相似結論。同時,研究認為GJB2 基因的突變位點基因型與NIHL存在相關性。Grillo 等[6]的研究認為GJB2 和GJB6 基因中的SNPs可能對人類的常染色體非綜合性聽力損失(ARNSHL)產生影響。
HSP 是一種保護性蛋白質在暴露于嚴重噪聲后被誘導,可以使耳朵避免受到過度的噪音損害。HSP 的合成主要有三個基因:HSP70-1,HSP70-2 和HSP70-hom。Yang等[7]首先對中國漢族人群暴露于噪聲環境的工人樣本描述了HSP70 基因與NIHL 的關聯。Konings 等[8]分別在206 個瑞典人和238 個波蘭噪聲暴露受試者中發現HSP70-hom 中一個位點(rs2227956) 與NIHL 顯著關聯,另外兩種HSP70 基因的兩個位點(rs1043618 和rs1061581)在瑞典樣本中存在相關性。
內耳毛細胞的穩態主要依靠頂連接來維持,而頂連接主要成分為兩類蛋白:CDH23 編碼的鈣黏蛋白23 和PCDHl5編碼的原鈣黏蛋白15。Konings等[9]于瑞典和波蘭人群中都發現PCDHl5 基因的一個位點(rs7095441)與NIHL 存在顯著相關性。Zhang 等[10]在中國漢族人群中亦發現PCDHl5基因與NIHL存在相關性。
MYH14 是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耳聾的致病基因,其編碼肌球蛋白在內耳中廣泛表達,包括Corti 的器官[11]。Konings 等[9]發現在瑞典和波蘭人群中,MYHl4 基因2 個位點(rs667907和rs588035)與NIHL的存在相關性。
2 環境因素
暴露于噪聲會導致兩種類型的內耳損傷,具體取決于暴露的強度和持續時間:較長時間的噪聲暴露或噪聲強度較大時,聽覺敏銳度的短暫衰減,稱為臨時閾值偏移(TTS);長期反復的噪聲暴露,會發展為永久性閾值偏移(PTS)。動物模型的研究表明,盡管聽力閾值在TTS 后不久完全恢復,但TTS 會加速與年齡相關的聽力損失。低強度的噪聲暴露后TTS 的恢復,可能是由于外毛細胞立體纖毛與構造膜可逆地分離和/或可逆性中樞增益增加[12]。但這并不意味著聽覺系統的完全恢復,這樣仍然會遺留突觸的損傷,這稱為隱性聽力損失(HHL)[13]。
PTS 的特征性病理特征是毛細胞的喪失。在顯著的噪聲暴露后,毛細胞和其支撐結構會破壞,從而成為融合、分裂或缺失的立體纖毛束排列,最終,支配毛細胞的神經纖維也會破壞[14],中樞神經系統內同時存在變性[15]。由于哺乳動物的毛細胞不會再生,一旦毛細胞被破壞,NIHL就會永久存在[14]。
在具有足夠強度和持續時間的噪聲的情況下,不僅毛細胞,而且Corti的整個器官都可能被破壞。短時間暴露于高于130 dB 聲壓級(SPL)的噪聲中會對聽覺系統造成直接的機械損傷,導致Corti器與基底膜分離,細胞連接被破壞以及內外淋巴混合。長時間暴露于噪聲后會引起代謝失代償,引起包括立體纖毛破壞、細胞核以及線粒體腫脹、細胞質囊泡和空泡化的后果,隨后激活信號通路導致毛細胞死亡[16]。目前的代謝損傷理論集中在自由基或活性氧(ROS)的形成、過度噪聲刺激引起的谷氨酸興奮性毒性以及鈣(Ca2+)超載上。
ROS 是細胞呼吸的正常副產物,對于各種細胞過程,一定程度的細胞內ROS是必需的。但是,過量的ROS會對細胞造成損傷,甚至導致細胞死亡。研究表明,噪聲暴露會增加耳蝸中ROS 的水平,并激活信號通路導致細胞死亡[17]。噪聲產生自由基的機制未知,目前大多數認為ROS的產生是由于線粒體的代謝,而ROS升高的最可能觸發因素是鈣,可能機制包括鈣誘導的脂質過氧化、蛋白激酶活化或線粒體膜通透性的變化[18]。
谷氨酸是興奮性的神經遞質,作用于第八顱神經內毛細胞的突觸。過度的噪聲暴露會導致谷氨酸大量釋放產生興奮毒性,導致過度的刺激突出后細胞,導致毛細胞水腫、空泡樣變[19]。但這種毒性為短暫性的,在脫離噪聲暴露后會逐漸恢復。依據相關研究推測TTS可能與此相關。
噪音暴露會導致毛細胞內游離鈣含量異常增多,目前認為胞內鈣濃度增加主要是通過離子通道進入和從細胞內儲存釋放來促成。在暴露于噪聲的耳蝸中,鈣超負荷會導致細胞結構損傷及細胞功能代謝障礙,可能同時參與毛細胞和神經元的損傷[20],會觸發獨立于ROS 形成的凋亡和壞死細胞死亡途徑[21]。上述理論在動物試驗中得到了驗證:通過阻斷L 型或T 型電壓門控鈣通道成功地改善了噪聲引起的聽力損傷[22]。
3 職業性噪聲聾的預防措施
職業性噪聲聾為感音神經性耳聾,這種受損是不可逆的。因此,對于職業噪聲,通過法律法規控制和減少噪聲是根本措施。預防措施的主要目的包括監測職業噪聲暴露、減少工作場所的噪聲暴露及通過定期職業健康檢查在聽力永久性損傷之前及早發現。研究表明,將職業噪聲降至80 dBA 以下,職業性噪聲聾的風險可以降至最低[23]。為了防止職工的聽力損失,我國已經實施了有關職業噪聲暴露的法律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詳細規定了不同噪聲等級情況下,采取不同的健康監護措施以最大程度降低噪聲對工人健康的影響。
雖然控制噪音是預防職業性噪聲聾的最有效的措施,但受到噪聲控制技術水平等的制約,這些措施通常難以完全實現。個人防護用品護耳器(HPD)成為重要的保護手段,HPD包括耳塞和耳罩。研究表明,耳塞等個人防護用品可以有效地預防工人發生聽力損失[24]。但護耳器使用頻率低和護耳器使用過程中聲音感知不足是影響個人護耳器使用預防職業性噪聲聾效果的最重要因素[25]。耳塞的使用頻率隨著耳塞舒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26]。調查顯示,新的材料、新的設計以及個人定制等能夠提高護耳器的舒適程度,從而增加護耳器的使用頻率。同時,工人對聽力防護知識和用品的認知有利于工人佩戴護耳器,接受職業衛生知識培訓的工人在護耳器使用方面有明顯提高[27]。
4 職業病噪聲聾的藥物治療
目前預防職業性噪聲聾最有效的辦法仍是護耳器,這并不能完全避免噪聲性耳聾。類固醇通過其抗炎作用,可以減少噪音引起的創傷,口服類固醇是臨床上常用的治療方式。但由于類固醇的副作用明顯,顯然不是職業性噪聲聾治療的長期選擇。臨床中其他手段包括活血化瘀類藥物及高壓氧治療,但這些治療的效果不是特別理想,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案非常重要。
4.1 抗氧化劑類
自由基、ROS 和氧化應激在NIHL 的發病機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抗氧化劑理論上是有效的治療方法。谷胱甘肽是人類最豐富的內源性自由基清除劑,參與許多代謝過程,包括清除自由基和ROS。動物實驗證實,應用谷胱甘肽能對暴露于脈沖噪聲的小鼠起到保護作用[28]。但在人類中口服谷胱甘肽是有爭議的,因為谷胱甘肽在被吸收前會被快速降解,生物利用度非常差。而N-乙酰半胱氨酸(NAC)可以避免這個問題。NAC 在體內用于合成谷胱甘肽。NAC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抗氧化劑,還可以增加谷胱甘肽的產生。NAC可以減少感覺動物毛細胞中細胞凋亡的進展,并顯著降低聽覺閾值偏移。在研究中發現,武裝部隊噪聲暴露后口服NAC 可顯著降低TTS 變化[29]。在比較NAC 和人參對紡織工人NIHL 的保護作用的研究中發現,NAC 和人參可以減少暴露于職業噪音的工人引起的TTS,NAC中的保護作用比人參更突出[30]。
HK-2 可以治療NIHL。HK-2 是一種新型合成的多功能氧化劑,具有金屬螯合劑和自由基清除劑特性。在噪音暴露前10 d 給Sprague-Dawley 大鼠口服HK-2 對耳蝸具有顯著的保護作用,不僅提高了毛細胞存活率,而且與未治療的大鼠相比,還降低了聽覺閾值的變化。同時,研究[31]表明,HK-2可以口服給藥,并且在大鼠中沒有副作用。但是,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HK-2 是一種對人類有效且無明顯不良反應的藥物。
其他可能對噪音引起的耳蝸創傷起保護作用的抗氧化劑包括人參以及幾種維生素。目前這些研究尚未在大規模人類研究中進行。
4.2 神經營養因子
神經營養因子可以恢復帶狀突觸,可以對噪音創傷起到保護作用。鼠神經生長因子是其中之一。研究[32]表明,鼓室內注射鼠神經生長因子治療職業性噪聲聾,可以改善患者的聽力,減輕耳鳴等癥狀,且無明顯不良反應。動物研究提示,噪聲暴露后馬上在圓窗上應用一次神經營養因子-3(NT3)和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可能減少突觸病變,有助于恢復聽力[33]。另一研究[34]中發現,將分泌神經營養因子的嗅覺干細胞移植到大鼠的耳蝸中,有助于恢復噪聲暴露后的聽力損失。這類研究需要進一步觀察長期的效果,且需要在人類中進行研究證實效果。
5 總結與展望
預防職業性噪聲聾的根本措施是控制噪聲源。盡管目前的法律法規已經采取各種噪聲控制措施,但由于噪聲控制技術水平的制約及各種其他原因,目前全世界范圍內職業性噪聲聾的發病率仍持續上升,并且因其具體機制仍舊不十分明確,使得職業性噪聲聾的防治研究進展緩慢。目前依據NIHL 機制研究的最新成果,多種不同的藥物在小規模人類或動物研究中已取得初步進展。相信隨著對NIHL 發生機制研究的不斷深入,更多與NIHL 相關細胞因子及通路的揭示,NIHL的治療藥物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