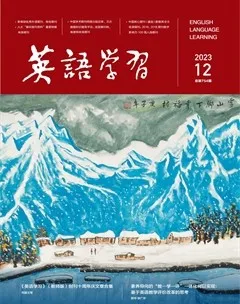四十載相伴同行:我的《英語學習》之路
武和平 西北師范大學
《英語學習》(教師版)不覺已經十歲了!此刻,我更愿意把時間線拉長一些,從我如何與《英語學習》結緣談起,為這本既有歷史積淀又散發朝氣和活力的刊物送上真誠的祝福與祝賀!
我的英語學習生涯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高中畢業后,我被當地的師范學校錄取,入學后做的第一道“選擇題”是在“英語班”或“普通班”中作出抉擇。也許是自己在潛意識里不甘“普通”,我懵懵懂懂地選擇了“英語班”,雖然當時自己的英語幾乎是零基礎。沒想到正是年少時期的這一選擇,不經意間決定了我今后的職業生涯和人生道路。
我在“英語班”的第二年就訂閱了剛剛復刊的《英語學習》。當時我的英語水平還很低,大多數文章都看不太懂,但有些欄目令我至今難忘。記憶最深刻的是北外劉承沛教授主持的刊物問答欄目。這一欄目雖然在每一期雜志的最后兩頁,卻是我每次拿到雜志后最先閱讀的。看得久了,慢慢就看出了一些“門道”——劉教授在解答來自全國各地英語愛好者五花八門的問題時,經常會告訴讀者這個問題可以參考牛津學習者詞典哪一頁的哪一個例句。他的回答給了我一個“啟發”——詞典就是英語學習的“魔法書”,詞典中的例句更像是解開英語學習之謎的“魔咒”,會查詞典就能解決英語學習中的大多數問題。工作后,我就用自己的第一筆工資買了屬于自己的牛津學習者詞典。
師范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一個鄉鎮中學當英語老師。這是一個基本上與英語絕緣的地方,當地幾乎找不到任何與英語相關的資源。而《英語學習》這本雜志成為我眺望“英語學習”世界的唯一窗口,慢慢地《英語學習》就更像一位默默陪伴在我身邊的師長,我會將一本薄薄的刊物反復翻看,將每一期都珍藏起來,到年末還會把當年的全部期刊裝訂起來,閑暇時間經常翻閱,大概直到我在90 年代又一次去外地負笈求學才停下來。如果說我目前在英語學習的道路上還有一點成就,那《英語學習》這位啟蒙老師功不可沒——她教會了我什么是“好”的英語,以及怎樣才能“學好”英語。
2014 年,《英語學習》(教師版)誕生了!看上去似乎刊物的受眾由英語學習者變為教育者,但我認為刊物的宗旨并沒有變,因為國民外語能力的提升最終要靠外語教師整體能力的提升。新版期刊在網絡時代應運而生,順勢而為,充分發揮網絡媒體和紙質媒體各自的優勢,通過微信群、公眾號和視頻號來傳播文章觀點,以“網”為媒,建立編者、作者和讀者的聯絡通道。雖然是一本面向基礎英語教育的“新刊”,但很快風靡全國,備受英語教師的青睞。
大概是在2015 年,編輯部約我牽頭組織一些教師,就課標中有關“核心素養”的“文化意識”在《英語學習》微信群展開討論。我當時邀請了自己英語教學生涯中結識的一些“故交”,如浙江師范大學的付安權老師和甘肅省民勤一中的王國己老師,也邀請了在《英語學習》微信群里“認識”但至今尚未謀面的“新朋”——人教社的陳力老師、時任浙江省教育評估院副院長的龔姚東老師、廣州大學附中的陳曉云老師,還有一些“不期而至”的老師共同參與討論。幾位老師都對語言教學中文化教學有獨到而深刻的理解,“聊天室”氣氛熱烈,吸引了很多英語教師前來“圍觀”。我們的討論隨后在當年《英語學習》發表,也引起了我對這一話題的持續思考。
在我接觸的中小學英語教師中,很多教師對自己所從事的英語教育工作內涵的理解越來越狹隘,把“英語教育”等同于“英語教學”,又很容易把“英語教學”等同于“英語測試”,在教學過程中過分看中與“考點”直接相關的內容,對于英語課程的人文教化的功能越來越漠視,正如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所批評的那樣:“只看見了工具,‘人們’沒有了。”
我一直堅信,文化的核心是人。從文化的本義上來講,文化就是一個“以文化人”的動態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外語課程中的文化教學,“文化”就不再是課標中的教學理念,也不只是教材中的文化知識點,更不是測試卷中的考點,而是以“人”為圓心和原點,通過“化人”來實現“育人”和“樹人”的課程目標,將語言教學中的文化知識“內化”為個人的文化品德、文化自覺和內在氣質,“外化”為對多元文化差異的尊重和理解以及對跨文化交流能力的獲得。從這一意義上理解,文化教學的過程是一個提升國際理解精神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過程,是一個人的內在人格和外在行為的塑造過程,是一個在“自文化”和“他文化”交流與碰撞中提升跨文化意識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過程。
我個人雖然在20 世紀90 年代初就離開了中學教師崗位,忝列高校教師行列,但由于自己早年英語學習和在中學教學的經歷,仍然心系基礎英語教育教學,也非常關注其中的“文化缺位”現象。在與中小學英語教師有限的交往交流中,我發現了一個讓人非常憂心的現實,那就是英語教育不斷被“空心化”,不斷被抽走“教育”的內涵——把語言教育簡化為語言教學,再把語言教學簡化為語言測試:凡是考試不涉及的內容,老師們大多選擇“少教”或者“不教”;而與“樹人”“育人”直接相關的文化教學,在很多英語教師眼中,恰恰屬于可以“少教”或者“不教”的內容。如果說語言和文化如一對孿生子女,共同構成了語言教育中的“鳥之雙翼”和“車之雙輪”,那么脫離了文化內涵的語言教學就像“單翼鳥”和“獨輪車”,學生最終學到的英語也是缺乏豐富文化營養的“畸形”英語。也正是基于這種擔憂,每次編輯部就這一話題約稿,我都欣然應約,在《英語學習》上陸續發表的幾篇相關文章也都是對這一話題的持續深入思考和探索。如果這種探索有助于外語教師能用“文化之眼”來發現語言教學中文化盲區,我將非常欣喜。
回望自己與《英語學習》四十年的緣分,深感《英語學習》不僅是我的知識伙伴,更是我思想的激蕩者。感謝她陪伴了我整個教育生涯的每一步,也期待未來能夠在英語教育這條道路上,與《英語學習》繼續相伴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