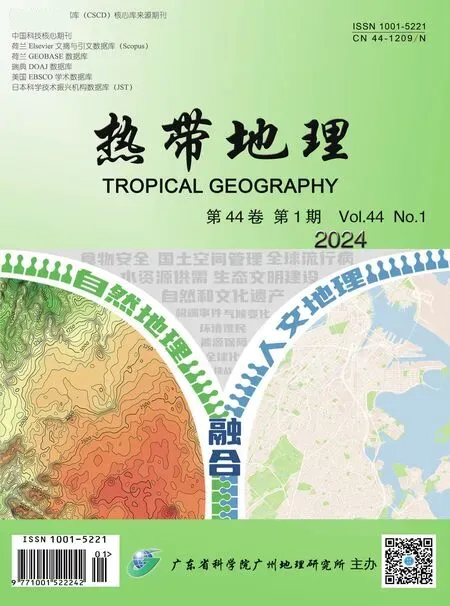面向城鄉融合的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研究進展及其關鍵科學問題
楊 忍,林元城
(1.中山大學 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州 510006;2.中山大學 鄉村振興聯合研究院,廣州 510275;3.中山大學 土地研究中心,廣州 510275)
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全球范圍內陸續開始反思傳統農業發展方式,并積極探索適應城鄉協調和融合發展的新型農業生產組織和發展方式(Russo and Cirella, 2019),農業功能轉型及多功能農業備受關注,相關的實證分析和理論探索應運而生。國際上有關農業功能轉型的研究由來已久,大致可劃分為20 世紀90 年代以前注重農業適宜性和生產功能提升、20 世紀90 年代到21 世紀初關注農業的生態功能及其對鄉村發展的作用、21世紀以來探索農業可持續轉型及農業多功能性等3 大階段,研究重點從農業機械化、規模化和經濟效應逐漸轉向農業多功能性、可持續性及社會效應(Pr?ndl-Zika, 2008; Klein et al., 2014; Sabatier et al., 2014; Rijswijk et al., 2021)。研究方法也趨于豐富和多元,相關研究綜合運用因子分析、模型回歸、GIS空間分析、聚類等定量方法以及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等定性方法,以探索農業功能轉型的程度評價、空間分布、多重效應及綜合影響等(Kiminami et al., 2020;Grassauer et al., 2021; Anwar et al., 2022)。反觀國內,改革開放以來農業農村發展先后經歷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鄉鎮企業崛起、農業結構調整、城鄉統籌發展、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等多個政策階段(Liu and Li, 2017)。作為農村地區主導性產業的農業被賦予更多的功能和作用,延伸并發揮農業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等功能,成為促進城鄉融合及鄉村振興的重要著力點(Lu and Yao, 2018)。國內關于農業功能轉型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產業化、農業功能演變、農業發展模式、現代農業發展、農業功能區劃等方面(姜長云,2013;匡遠配 等,2016;劉玉 等,2020;高帆 等,2023)。相較而言,國內對于農業功能轉型研究起步較晚,20 世紀90 年代末,涉及農業功能轉型的研究才開始出現,主要服務于農業區劃和城鄉發展,目前相關的理論分析和深入的案例探索仍在不斷豐富和完善。近年來,在全球城鎮化不斷推進和農業轉型的大背景下,國內外研究逐漸關注都市范圍內的農業在聯系城鄉地域系統中發揮的作用,都市農業以其多功能性及城鄉連接效應成為關注的焦點(Rivera et al., 2018;楊其長,2022)。
城鄉融合需要將農業發展與城市空間有機相嵌,而都市農業生產空間的有序整合是城鄉網絡化發展轉型的重要途徑,都市農業的持續發展是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和方式(劉彥隨,2018)。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以農業為基礎通過產業聯動、技術滲透和體制創新等方式,將城鄉資源進行跨界整合和重新配置,促使農業產業鏈延伸和產業協同發展(劉彥隨 等,2022)。都市農業地域系統是由社會、經濟、環境和空間等4個子系統相互關聯和作用的復雜系統,系統要素變遷和結構重組使其呈現多樣且動態的地域系統功能。伴隨城市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持續發展,都市農業發展對城市社會經濟和城鄉融合的影響逐漸顯現,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逐漸從傳統農業的農產品生產轉向多樣化和復合化,兼具經濟、社會和生態等多種功能,生產組織和空間布局等也隨之重構(楊忍 等,2023)。都市農業以鄉村水資源、土地資源、農業氣候、生物資源等為基礎,聯動設計、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和領域,是典型的“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都市農業價值鏈是農業生態系統、家庭農戶和市場的連接紐帶,是都市農業地域系統核心要素組成部分,全面分析不同類型都市農業價值鏈的構成要素、關鍵銜接環節和運行機制,將有助于創新都市農業產業價值鏈和農村產業融合理論。都市農業的發展直接受到都市本身的輻射和影響,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和通訊網絡等都是都市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城鄉地域系統間各種要素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增強了現代技術、企業資本和物質裝備對都市農業投入的動力,推促都市農業發展轉向集約化和現代化(林元城等,2023)。
在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下,高科技農業、生態高效農業、“互聯網+”農業和智慧農業等多種都市農業形式不斷涌現,都市農業逐漸向專業化、規模化和基地化轉變(楊忍 等,2023)。在經濟發達的城市群地區,城鄉地域系統間的要素流動和交互作用較強,都市農業發展直接影響城鄉融合和混雜區域的農業經濟形態和結構(喬家君 等,2016)。土地資源、水資源和氣候等自然資源稟賦是農業生產和發展的基礎和先置條件,都市農業系統作為一個社會和自然交互作用的綜合系統,在要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特定的地域系統結構和生態服務功能(如涵養水源、凈化空氣、保持水土、綠化景觀、休憩娛樂、農耕文化傳承等)。在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進程中,都市農業逐漸由生產主義向后生產主義、消費化和多功能等轉型(楊忍 等,2022),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的研究進展、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所帶來的空間重構、及其產生的生態環境效應仍有待深入探究。鑒于此,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以及CNKI收錄的中文核心期刊中關于“都市農業轉型”“都市農業功能”“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等主題的文獻展開分析,文獻檢索時間截止至2023年9月,按照研究領域及主題相關性進行篩選,共計得到約500篇相關文獻。在全面梳理和總結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相關研究進展的基礎上,提出未來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研究的關鍵科學問題,以期為都市農業高質量綠色化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分析框架和科學理論支撐。
1 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研究進展
在城鄉融合的視角下,都市農業是指布局在城市內部及其周邊地區,集城鄉農業生產供給、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和生態保育等功能于一體,服務于城市需求的農業及其延伸產業。都市農業概念涵蓋了空間范圍、生產結構、功能目標及其與城市間的關系等不同維度,在空間范圍方面,都市農業強調位于城市內部或周邊地區,并將空間區位作為劃分的重要依據;在生產結構方面,都市農業的產業結構根植于農業,以農業為核心特色,是一種從生產(或養殖)、加工、運輸、消費到為城市提供農產品和服務的完整經濟過程;在功能目標方面,都市農業是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等功能結合于一體的農業業態,具有多功能性的特點;從與城市的關系看,都市農業強調農業和城市共生的發展理念,是城市經濟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全球范圍內,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推動了區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重塑了城鄉關系和空間格局,但同時也對城鄉地域系統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等造成巨大挑戰,可持續發展理念逐漸融入城鄉發展和規劃管理中(Gr?dinaru et al., 2018; Langemeyer et al., 2021)。糧食供應與分配、低耗能的食品供應鏈構建、有機食品發展潛力和農業生產空間消費化等議題引發高度關注(Seto and Ramankutty,2016; Schmutz et al., 2018; McDougall et al., 2020),都市農業作為提高農業生產品質、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徑逐漸受到社會重視(Ashkenazy et al.,2018)。國內外學者從多個維度對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的過程、模式、空間組織、農業用地競租與利益主體協同機制,以及都市農業功能轉型帶來的綜合效應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5個方面:
1.1 都市農業發展轉型評價及類型劃分
都市農業發展的綜合評價是優化其地域系統功能的基礎,有必要準確辨識和評定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的過程和結果。評價指標體系因發展階段不同而呈現一定差異,但主要圍繞農產品產出、現代化技術投入、社會生態及經濟效益等維度(周燦芳 等,2020),評價方法主要涉及層次分析、灰色關聯度、因子分析法和生命周期評估等(Robineau and Dugué, 2018; Van der Werf et al., 2020),評價內容包括都市農業綜合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農業系統生態安全程度、都市農業發展潛力和都市農業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等(Clinton et al., 2018;安曉寧 等,2020;Amiri et al., 2021;羅珂 等,2023)。都市農業發展具有依托城市產業發展并服務于城市需求的特性,都市農業的發展及布局受城市人口規模、地域范圍、資源稟賦、地理條件和城市形態等基礎性因素的影響(Hara et al., 2018)。水資源條件、土地資源質量、距居住地距離、耕地資源使用權穩定性、市場需求和農業政策等不僅影響農戶的農業生產選擇,同時也深刻影響都市農業的產業結構和發展布局,進而影響都市農業功能的演變方向和發展類型(Poulsen et al., 2015; Tiraieyari et al.,2019)。從農業和城市發展的依存關系看,都市農業并不特指某種農業形態,而是涉及一二三產業各個領域的生產活動(蔡建明 等,2008),各產業間的協同關系是劃分都市農業發展類型的重要依據(王曉君 等,2017)。生產要素、需求條件和支撐產業等因素是劃分都市農業發展類型的重要基礎,決定都市農業的具體功能及轉型模式。都市農業是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市消費需求將直接驅動都市農業的發展與功能轉型,生產組織形式和產品銷售方式等與都市農業發展類型聯系密切(Nadal et al., 2018)。
1.2 都市農業多功能轉型及可持續發展
城市對鄉村商品和服務的多樣化需求是多種農業活動共存的驅動因素,都市農業多功能的發展范式旨在解決其發展的薄弱環節(Zasada, 2011; Peng et al., 2015)。總體上,都市農業多功能主要分為經濟、生態和社會3個維度,各類功能間的強弱關系處于動態變化,衍生出偏重經濟功能、偏重生態和社會功能以及經濟、生態和社會功能兼顧的3種發展模式(Kanosvamhira and Tevera, 2020)。針對都市農業多功能發展的研究集中在4方面:1)辨識都市農業多功能轉型發展過程中土地利用和空間布局等的演變過程(龔蔚霞 等,2021);2)探究都市農業多功能轉型過程中各行動者的行為決策和社會網絡重構等問題(Schulp et al., 2022);3)探析都市多功能農業發展過程中涉及的金融服務、技術創新等市場運作機制(Bannor et al., 2022);4)探討政策和監管等對都市多功能農業發展的影響(Barthel et al., 2015; Ayoni et al., 2022)。
都市農業可持續性發展對土地利用管理、社會關系和福祉、生態效益及主體作用機制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相關組織機構和學者開展了相應的研究工作。例如,聯合國糧農組織制定的可持續土地管理評價框架(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FESLM)通常作為都市農業可持續發展評估的基礎(Orimoloye and Egbinola,2019)。McClintock(2018)認為都市農業可持續發展是一種生態紳士化的體現,主要依據都市農業發展過程中涉及的各類物質和群體間的作用關系,分析其可持續性問題。Russo 和Cirella(2019)認為,都市農業能與綠色基礎設施(Edible Green Infrastructure, EGI)相結合,創造環境福祉、倡導社會健康和提高經濟利潤率,在可持續發展中發揮獨特作用。Mupeta等(2020)認為利用成本效益和生產估值等經濟分析方法,能更好地衡量都市農業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各種影響因素的作用。具體地,社會環境和政策制度是影響都市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低效的資源利用將導致都市農業發展的不可持續(McDougall et al., 2019);科學知識和農業科技創新則使得都市農業發展煥發生機(Armanda,2019);科學家、農民、政府部門、企業和社會組織多主體的交互協作機制,對實現都市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Eyhorn et al., 2019)。
1.3 都市農業空間組織與生產組織方式
都市農業的空間組織是人類為實現都市農業差異化的功能轉型目標而實施的一系列空間建構行為及其產生的空間連結關系。都市農業發展顯現產業化、信息化和外向化等特征,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對其空間結構產生一定影響(Pulighe and Lupia,2016)。杜能的農業區位論、辛格萊爾的“逆杜能圈”理論、區域分工理論及布林克曼的農業區位選擇行為理論等,構成都市農業空間結構分析的理論基礎,其研究內容包括都市農業總體空間范圍及內部空間結構2 方面(王曉靜 等,2019)。人口、文化和經濟收入等因素直接對都市農業土地利用結構和空間形態產生影響(Alves and De Oliveira,2022),大部分西方國家的都市農業布局從城市內部至周邊的地塊均有涉及(Ernwein, 2014),充分利用屋頂、陽臺、地面停車場、社區花園和庭院等用地空間(W?stfelt and Zhang, 2016; Sayigh and Trombadore, 2021)。城鄉混合的地區因布局都市農業進而維護了城市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Follmann et al., 2021)。都市農業布局的空間組織與各城市的空間結構存在一定相宜性,同時也受到經濟、自然、科技和交通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王曉靜 等,2019)。在空間組織上,都市農業空間布局和組織結構呈現網狀和帶狀的空間結構。在城市規劃與城市設計中,都市農業將基層群眾納入與其他主體進行博弈、談判與合作的范疇,以此推動社會結構和城市空間結構的變革(Mancebo, 2016)。都市農業空間布局的點、線、面的空間網絡結構是城鄉地域系統生態網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Hammelman et al., 2022)。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GIS空間分析方法,揭示各都市農業的區位布局及功能的空間分異特征(Kazemi and Hosseinpour, 2022)。
都市農業生產組織方式是指都市農業生產過程中各社會主體整合及利用各種生產要素的方式(張永強 等,2019)。依據制度經濟學的觀點,組織創新和產業鏈升級必然引起都市農業生產組織的演變(朱蕾 等,2019)。都市農業的生產要素不限于傳統的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等,但技術、知識和信息等要素顯得更為重要,新的生產要素重組將直接影響都市農業的生產組織方式。隨著都市農業產業鏈的轉型升級,各個環節參與者間的分工與協作趨于優化,生產組織形式也更加多元。農業企業、管理機構及社會團體積極參與都市農業發展(鄭娟娟,2017),形成了“公司+農戶”“經紀人+農戶”“中介組織+農戶”“農業技術協會+農戶”及“合作經濟組織+農戶”等多種都市農業生產組織形式。農民之間的合作以及不同背景的外部合作伙伴(如消費者、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等)參與異質集體的創建,被視為增強社會整體資本的保證(Bizikova et al., 2020)。各種生產組織下的都市農業運作也被視為一種與公眾互動的有效方式(Hermans et al.,2023),如德國的市民農園、美國的家庭農場、法國的中型家庭農場、新加坡的現代集約型農業科技園,以及廣泛的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等。都市農業生產組織通常具有集約性、可持續性、廣泛性和內部依賴性的特點,能有效協調各方利益,在時代變遷中不斷演變和創新,反映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的新模式(Hawes et al., 2022)。
1.4 都市農業發展中土地利用及競租機制
競租理論源于對農業用地的觀察和總結,反映的是隨著離城市中心距離增加土地價格和需求間的變化關系。20 世紀60 年代以來,隨著后工業化國家城市不斷擴張,新古典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土地經濟學等學派均形成競租理論的主要觀點,阿隆索在新古典經濟學思想的基礎上建立了經典的城市競租模型。Sinclair(1967)強調決定農業用地利用模式的因素并非交通成本而是土地價值,新的農業發展和布局模式越來越難以用傳統的農業區位理論加以解釋(W?stfelt and Zhang, 2016)。快速城市化致使城市地區的農業要素和非農要素進行重組,在競租理論的分析框架下,學界主要對都市農業發展過程中的土地競租、土地利用、土地權屬、土地保護等問題進行研究(Ayambire et al., 2019),研究方法以質性為主,包括收集報紙、文件等二手資料,進行歷史文獻追蹤,在實地考察中進行半結構化訪談、問卷調查、攝影和文本記錄(Chandra and Diehl, 2019)。定量方法則包括土地權屬數據庫建立、地理制圖、聚類分析等(Pirro and Anguelovski,2017; Westlund and Nilsson, 2022)。
城市蔓延致使都市農業發展空間急劇收縮(Azunre et al., 2019),都市農業土地與土地非農化間沖突激烈,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村土地受到非正式農民、職業農民、市政規劃者、大都市機構和投資者等多重利益主體的爭控(Pirro and Anguelovski,2017)。土地需求增加、土地投機和激烈競租等因素助推土地價格的不斷攀升(Cobbinah and Aboagye, 2017; Horst and Gwin, 2018),導致大量都市農業用地轉變為住宅用地,牧場轉變為大型娛樂場所用地等(Pham et al., 2015; Westlund and Nilsson,2022)。不受控制的農用地非農化,致使都市農業用地脫離城市土地使用管理系統(Amponsah et al.,2016)。阿隆索的競租理論將其歸因于農地使用者的低競租,導致農用地使用者無法與非農地使用者爭奪城市空間(Azunre et al., 2019)。由于西方土地私有制的根源,農民的土地所有權(Land title)和使用權(Land tenure)存在不穩定性,農民與土地所有者之間僅存于短期契約,難以維系都市農業穩定持續發展(Pribadi et al., 2017)。Chandra和Diehl(2019)認為農業耕作主體是當地人和具有非正規的土地權屬移民的混合體,非正式土地權屬狀態(Informal tenure status)導致土地所有權(Land title)的不穩定。
都市農業土地的持續非農化,阻礙了都市農業在經濟、社會和生態上對城市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支撐(Opitz et al., 2016; Walker, 2016; Ma et al.,2018)。政府通過土地征用、土地出租、土地轉讓和土地儲備等方式(Eagle et al., 2015; Rose et al.,2017; Ayambire et al., 2019),維護都市農業生產空間的穩定性。同時,政府還通過構建由公共地方當局、農民代表機構和私人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社會自治模式,維護都市農業的有序發展(Perrin et al.,2018)。城市閑置用地、邊際土地和廢棄復墾土地是都市農業發展空間載體的重要組成部分(Carlet et al., 2017)。都市農業的從業者通過建立社會凝聚力,重新利用空置和被遺棄的土地,為邊緣化群體提供獲取農業土地使用權的機會(White and Bunn,2017)。農民為維持生計,主動參與爭奪土地資源的使用權,推遲土地的代際流轉,享受地價上漲帶來的收益(Nguyen and Kim, 2019)。城市地區失地農民通過集裝箱耕作、園藝耕作、薄膜耕作(Film farming)、氣培和水培耕作等,以滿足自身部分生活需求。為了提高都市農業土地的可獲得性,城市農業聯盟等社會組織重新政治化土地問題(Manganelli and Moulaert, 2019),建立土地所有權(Land ownership)的法律體系,促成農民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合法契約,保障都市農業持續發展(Pribadi et al., 2017)。在此背景下,都市農業衍生出“購買發展權”(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的概念,以確保城市和城市周邊地區都市農業發展的土地資源穩定性(Ayambire et al., 2019)。政府將都市農業作為開放綠地統一納入城市規劃和管理,對都市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Nguyen and Kim, 2019)。
1.5 都市農業發展問題及其多維效應
面對城市內部農用地不斷縮減的現狀,都市農業的發展空間被迫轉移到城市內部空地或被污染的廢棄地(Kazemi and Hosseinpour, 2022)。高密集的粉塵污染和汽車尾氣排放等致使城市土壤中含有過量的鎘、汞、鉛等有毒元素(Huang et al., 2018),土壤中的污染物向農作物轉移會帶來潛在的食品安全風險(Dala-Paula et al., 2018)。水資源緊缺則進一步增加了灌溉型都市農業的生產成本,限制其規模擴張(Pratt et al., 2019)。在高產出和高收益的經濟利益驅動下,農民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造成土壤中氮、磷、鉀等元素含量超標(Huang et al.,2018),導致水體富營養化和農業生態環境失衡。農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固體、液體和氣體廢物因缺乏有效的處理,給城市生態環境帶來污染和較大壓力,影響城市居民生活質量(Ulm et al., 2019)。都市農業發展同樣面臨復雜的社會文化聯系,迫切需要解決農戶與消費者間的信任危機、農戶社會邊緣化、社區組織機構運作和權益歸屬等問題(Padgham et al., 2015; Ding et al., 2018)。都市農業發展帶來了生產、經濟、生態以及社會等綜合效應,也存有對自然環境和當地社區產生潛在危害的風險,具有正反雙面性的特征(Tan and Jim, 2017;Azunre et al., 2019)。
都市農業融入城市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其帶來的效應是多維的(黃姣 等,2019)。在經濟效應方面,都市農業是具有產生外部性經濟利益的公共財產,對優化產業結構、促進農業增產增值和創匯等方面有積極作用,同時也為勞動技能較低的群體提供潛在的就業機會,為城市中的“弱者”提供保障(Diehl and Kaur, 2022)。都市農業的發展有助于保障城市的食物供應,緩解城市的“食物沙漠”(Food deserts)危機(Chagomoka et al., 2017;Palmer, 2018)。在社會效應方面,作為“城市花園”的都市農業跨越了年齡、種族和經濟障礙,將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整合到城市公共空間的使用和管理中,增強了城市公共空間的凝聚力。在都市農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與民間社會團體的參與及合作越來越頻繁,城市居民與農民之間的溝通交流日益增多,增進城鄉聯系與對話(Halvey et al., 2020)。都市農業改善了跨文化和跨世代的聯系,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通過建立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提升社會的凝聚力和融合度(Palmer, 2018),對自我意識、公民權利和民主水平產生深遠影響(Ferreira et al., 2018)。但在部分國家和地區,都市農業助長了童工和逃學現象,產生弱勢群體權利剝奪和社會負面影響(Edet and Etim, 2013)。在生態環境效應方面,都市農業的發展有利于增加城市綠色空間和生物多樣性,減少城市熱島效應和噪聲污染,調節局部小氣候(Mancebo, 2018)。隨著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的縱深演化,都市農業為協調城市復合生態系統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生態支撐(金玉實 等,2022),但也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包括農業結構變化直接影響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產能力、恢復能力和穩定性。農用化學物質的過量使用、未經處理的廢水灌溉等對人體健康和環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Sellare et al., 2020; Kumar et al.,2022)。都市農業作為城市擴張的伴生產物,農用地持續非農化導致景觀破碎化,影響都市農業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價值(Azunre et al., 2019;彭銳 等,2021)。
2 面向城鄉融合的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研究的關鍵科學問題
在城鄉要素快速流動和產業聯動的背景下,都市農業具有連接城鄉要素、強化城鄉聯系和推動產業融合的重要作用,但同時其空間布局和功能等也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崔紅志 等,2022)。根據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的要素變遷與結構關系重組、功能演變與空間網絡整合、都市農業用地配置和農業生態系統等優化調控的基本需求,未來亟待重點解決的關鍵科學問題包括: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的內外部驅動機制是怎樣的?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的空間重組核心機理是什么?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轉變對生態環境帶來怎樣的影響,并產生怎樣的生態環境效應?圍繞上述科學問題,需開展3 方面的研究:
1)厘清都市農業系統地域功能演化的內源性和外部性驅動力間的交互聯動和耦合作用機制。都市農業地域系統作為一個由社會、經濟、環境和空間等子系統構成的復合系統,各子系統中的要素變遷和結構重組等都將影響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的功能演化和空間重組。在城鄉融合的背景下,城鄉發展形態、空間結構、需求變化、技術變革、景觀和功能等對都市農業地域系統演化產生內源性(都市本身)以及外部性(鄉村地域)的多重驅動和影響(堯玨 等,2020;Yuan et al., 2022),應從都市農業發展的資源環境支撐系統和生產生活主體系統來認知和理解。未來,應基于國際農業多功能理論和農業去中心化理論,結合國內理論和實踐發展的實際情況,以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為指導,全面分析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的要素變遷、結構關系重建、城鄉聯系互饋、利益主體與生態環境演變過程(楊忍等,2020),科學辨識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的本質內涵和表征形式、地域多功能的權衡與協同等。基于城鄉連續體的視角,深度解構都市農業生產空間資源配置過程、農業價值鏈的城鄉關聯結構、城鄉地域系統空間連接和融合過程、農業用地生態網絡動態、農業發展主體變遷、農業產品的市場網絡、都市農業消費群體結構和農業用地利用隱性轉型過程等(Ge et al., 2020)。面向未來,需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深化都市農業系統功能演化階段和過程的分析,關注城鄉聯系的經濟融合、區域生態環境效應、社會穩定與可持續性以及都市農業系統空間重組,重視城鄉需求變化、技術創新以及城鄉聯系遠近程耦合帶來的影響,歸納和凝練出基礎性和主導性影響因素及其交互關聯機制,揭示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的內源性和外部性驅動力交互聯動和耦合作用機制(圖1)。

圖1 人地關系地域系統視角下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的分析框架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region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system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2)揭示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的空間重組核心機理,以及利益主體的作用關系與土地競租的內在邏輯。在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過程和驅動機制分析基礎上,需對都市農業空間組織體系和空間布局形態的演變過程和規律進行歸納,探明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轉變和農業生產空間重組之間交互作用的內在邏輯。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空間重組的認知體現在區域層面的都市農業生產空間布局和組織重構,以及微觀層面的農業用地利用方式、農業用地形態和景觀結構、農產品類型格局、土地資源權屬、生產主體社會網絡等方面結構性和關聯性的重構過程(鄭書劍,2014;Fanfani et al., 2022),實際上涵蓋了中宏觀和微觀在多個維度的空間要素和結構重組的本質內涵。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系統論和博弈論等為基礎,從成本和地租均衡視角出發,結合中國土地公有制及國土空間總體規劃等實際情況,分析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轉變過程中的利益主體(包括涉農企業、農戶、合作社、政府、科研機構、代耕農等)對都市農業生產空間用地的競租博弈過程和結果,揭示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和空間組織體系重構的地理關聯規律(圖2)。均衡博弈視角下,都市農業發展利益主體對農業發展空間的爭奪,以及農用地利用形態和空間布局轉變的競租機制是什么?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空間重組的行動者網絡結構和轉譯機制是什么?農戶、企業、科研機構、中介組織、市場主體等在都市農業生產空間集約化、現代化、網絡化、生態化、消費化和智慧化等轉向過程中的聯動機制是什么?主體、產業、技術、制度和空間之間的關聯邏輯是什么?以上都是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空間重組研究急需破解的關鍵性科學問題。

圖2 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的主體與要素關聯邏輯Fig.2 The subject correlation logic of urban agriculture regional system
3)探索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機制。針對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和空間重組帶來的生態環境影響和效應,需建立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的生態環境效益診斷與評價理論方法,構建聯動效應和溢出效應的理論模型,揭示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對資源利用效率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機理,以及開展都市農業風險的識別、形成機制及其防控研究(圖3)。具體包括:①基于城鄉空間梯度典型樣帶調查,診斷分析不同區位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的要素重組變遷誘發功能演化過程中資源利用效率(水、土、氣、生等)及農業生態環境問題(農業面源污染、畜禽養殖污染、景觀破碎化、水源涵養弱化、文娛休憩空間變差等),并甄別都市農業地域系統演化的生態環境異化核心指標。②建立都市農業系統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和理論框架,揭示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過程中的資源利用效率、生態環境效應協同機理及其傳導機制,深化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聯動效應和溢出效應。③針對都市農業發展的地域系統功能演化及其空間重組帶來的生態環境外部性效應,構建都市農業系統生態環境要素多源數據庫和效應評價模型,開展典型城鄉空間梯度樣帶上不同區位都市農業系統演化的生態環境綜合效應評估與分類,并進行都市農業系統功能演化的生態環境效應多情景模擬。④針對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變帶來的生態環境影響,揭示由都市農業生產和經營方式變革產生的農業碳源/匯效應,以及都市農業應對自然災害、經濟風險沖擊的韌性功能等,反之也需要關注都市農業風險的形成機制與應對路徑,探尋破解都市農業發展潛在的生態、經濟和社會風險的科學路徑。

圖3 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的生態環境效應機制研究的內容體系Fig.3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ffect of urban agriculture regional system function evolution
3 結論
1)都市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與城市密切關聯,是城鄉融合的重要環節和表現形式。關于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都市農業發展轉型評價及類型劃分、都市農業多功能轉型及可持續發展、都市農業空間組織與生產組織方式、都市農業發展中土地利用及競租機制和都市農業發展問題及其多維效應等5 方面。目前學界主要以農業發展理論、農業多功能理論和農產品需求理論為指導,開展都市農業功能轉型相關問題研究,但針對城鄉地域系統間的內外部要素交互作用對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的影響機制的研究相對欠缺,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和空間重組的動力機制有待深入研究。在城鄉地域系統由分離到一體認知轉變的基礎上,從系統視角看待都市農業發展和探討其地域功能演化,需要遵循系統論的要素、結構、功能和效應的分析邏輯,以認知和詮釋都市農業發展的地域多功能權衡和協同理論。
2)都市農業發展呈現多主體、多環節和多目標的復雜特征,存在基于不同利益主體訴求下混雜社會關系協調問題,都市農業空間競租和主體利益協同博弈過程和結果,對都市農業生產體系和空間組織重組產生重要影響。針對都市農業土地利用和競租機制的研究,重點關注農用地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異化、權屬安全、農業生產主體多元化等內容,亟待強化基于地域系統視角的都市農業發展中的土地競租、土地權屬和相關利益主體等研究。都市農業系統地域功能演化伴生空間競租重組,并產生一系列的生態環境效應,需要基于不同尺度、不同主體、不同類型的視角,厘清和揭示都市農業系統演化的基礎性和主導性影響因素,揭示其空間重組的競租機制以及產生的生態環境效應。未來可以傳統的競租理論為基礎,但應不局限于理論分析,需突破傳統理論框架,拓展和創新都市農業用地競租機制和空間重組的理論。
3)前期研究多關注都市農業的資源利用、社會公平和經濟職能等,都市農業多功能轉變的多維聯動和溢出效應有待進一步揭示,尤其是都市農業的生態環境效應及風險評估和防控。都市農業的多功能性產生多維的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效應,由于區域經濟發展階段和程度的差異,導致發達國家和經濟發達地區重視都市農業的環境效應,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側重于經濟和社會效應。鑒于都市農業功能轉型具有正負外部性特點,未來亟待解決的科學問題包括都市農業地域系統功能演化的內外部驅動力間的作用機制、都市農業地域系統的空間重組核心機理、都市農業空間重組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聯動效應和溢出效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