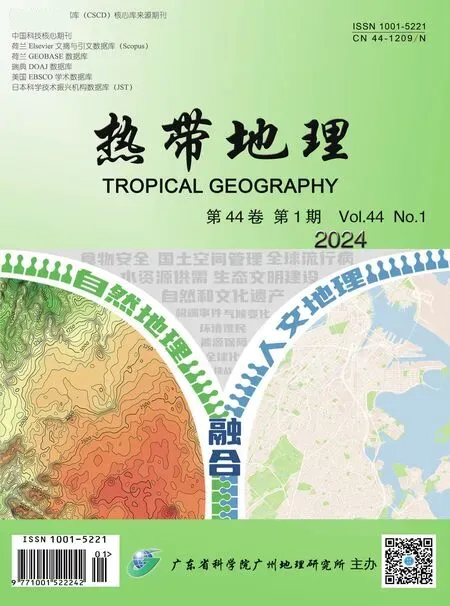淺談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融合的基礎
——與凱斯特洛特與巴尼奧利文章的對話
周尚意
(北京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部,北京 100875)
在學術史脈絡中理解一個科學的發展非常重要。Human and Physical Geography:Can We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 History of Their Relations?(Kesteloot and Bagnoli, 2021)就是這樣一篇文章。感謝丁雁南和安寧兩位譯校者,為讀者提供了該文的漢譯稿(下稱該文)。該文以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之關系為抓手,扼要介紹近代以來的地理學史,以及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難以合流的原因。由于我在2023年5月的《熱帶地理》編委會換屆會議上提出,區域地理或許是將地理學多個學科綜合在一起的研究路徑,因此《熱帶地理》編輯部邀請我為該譯文寫一篇評述。
本文不再從共同的研究對象“區域”來討論二者的融合,而是從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彼此融合的基礎闡述自己的看法。該文作者的主要觀點是,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都關注人類生存環境的問題,在人與自然矛盾日益凸顯的當下,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勢必結合。這一問題被地理學界歸入“人地關系”主題。誠如該文第一部分所說,該主題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自近代地理學出現它就已經存在了。但是為何它一直未能有效推動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深度融合?我結合北京中心城區色彩管控案例,談自己的三個心得,它們指向本文的題目——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融合的基礎。
1 兩個學術群體面對的本體論需要接近
所謂本體論是指探究世界本原或本性的哲學。廣義的本體論是指一切實在(being,也譯為存在)的最終本性。狹義的本體論則是指宇宙的起源、結構和宇宙本性。黑格爾定義本體論是“論述各種關于‘有’(on)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學范疇,這是抽象的形而上學的”(黑格爾,1996)。在地理學界,有些學者認為可感知的世界是真實的,他們只用可感知的素材推導結論;另外一些則認為可感知世界是變幻的,超感知的世界中有永恒性的存在,它左右可感知的世界;還有地理學者的觀點處于這兩端之間。多數中國地理學者不去觸碰本體論,因為怕違背馬克思主義哲學。其實馬克思并非要否定、終結一切形而上學,而是批判特定類型的形而上學(毛艷,2021)。
城市色彩管控是城市規劃中的一項內容,北京城市規劃已包含北京中心城區色彩管控。如果說色彩是客觀的,那么色彩美學就是抽象的。自然地理學者或許說,城市色彩不是他們的研究對象,但是如果他們意識到城市中有自然元素,那么城市色彩就包括了自然元素的色彩,城市色彩管控問題就轉化為對城市中大氣、水體、植物的管控。如果自然地理學者不單是檢測環境質量,還參與城市色彩美感的討論,那么他們就已經開始邁進抽象世界了,這就是該文提到的自然地理學者的“文化轉向”。
試想人類觀察到,且在意的環境質量內涵,與其他生物感受且在意的環境質量內涵是否一樣?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那么人類“發現”的自然地理知識也就不是絕對“客觀”的。該文提及的超越人類的地理學(more-than-human geography)就是統合可感世界和超感世界、統合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新概念。這個視角在2000后的英美地理學界十分流行(Braun, 2005)。
2 兩個學術群體彼此包容對方的方法論
方法論是研究一切實在最終本性(本體論)的路徑(approach),其中既包括上位的哲學方法,也包括下位的技術方法(如制圖、統計分析、數據獲取方法等),該文側重介紹前者,大概率是因為作者認為前者決定了技術方法的使用取向。
絕大多數自然地理學者使用的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他/她們的基本思路是通過觀察到的信息,找出普適性的規律。許多中國人文地理學者,也偏愛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按照這樣的方法論,可以通過處理海量的城市影像數據,找到北京中心城區不同地方的色彩基調。但是現存的城市色彩基調未必是人們認為最好的狀態。因此,還可以用經驗主義方法,調查多數人在若干可選擇的方案中,選擇認同的色彩基調。然而在許多情況之下,多數人選擇的方案,也未必代表正確的色彩管控方向。到此,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就顯得無能為力了。有學者反省:地理學長于事實而短于理論,大多數地理學思考和活動只能歸屬于經驗資料的搜集、整理和歸納(蔡運龍,2015)。
人文科學研究的對象(歷史、詩歌、藝術等)包含著人類的主觀價值。研究它們需要的是理解,而非分析(維柯,1989)。結構主義方法論是一種理解途徑,即透過多樣化的表層結構(如色彩基調),看到使表層結構得以形成的深層結構(動因)。而了解動因比了解表層結構更為關鍵。后結構主義是不斷發掘動因鏈的終極動機。按照拉康的觀點,這樣一環套一環的動機,可以稱為能指鏈(Lacan, 1993;杜超 等,2017)。就城市色彩基調而言,它只是表象,人們對城市色彩基調的評價來自審美心理;審美心理的本質(essence)是視覺與其他感官感覺的協調,以及與社會建構的美學經驗的協調;色彩與身體、與精神的協調是指向生活或生命的意義(存在)。“審美心理”是深層結構,但是“審美心理-協調本質-存在”則是一個鏈條,它幫助我們深挖本原。馬克思主義把美界定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馬克思,2009)。自然地理學者雖然也采用結構主義,例如探索地表形態形成的機制,但是在他們探究的深層機制中較少涉及到人的機制。
人文主義方法論是直接從結構鏈條中的“存在”出發,不斷審視本質、心理基礎和外在表現。因為存在是無需證明的、所有人都懂的(阿維森納等,2016),所以它可以作為思考的起點。在城市色彩基調管控的問題上,此方法論的研究要點之一是基于研究者日常生活經驗,審視人們對色彩美的心理需求層次——人們既希望享受現代化城市生活(物質層面),也希望保留古都的風韻(精神層面)。因此,城市色彩管控要兼有古今風貌。古都風貌色彩區與當代風貌色彩區的空間關系,就是地理學要研究的;要點之二是審視美學本質,“協調”或許是一種美學本質,而協調與不協調的對立且辯證關系,或許才是更高層次的協調;要點之三是審視存在與城市色彩管控之間的關系。我與研究生的研究結果表明,北京故宮建筑群紅墻碧瓦的色彩,必須在藍天白云映襯下才能顯現其美,在霧霾籠罩下就毫無生機;故宮建筑群中星星點點的古木綠色雖不顯眼,但正是它們令這個建筑群富有真實歷史的美感,而橫店影視城里的那座明清宮苑,盡管是按照故宮的形式,以1∶1的比例建造的,也不能充分展現出歷史真實感(周尚意 等,2019)。這個結論是我們在做調查時發現的,這種關于美的結論,無需找到統計上的論據。這些對色彩美的判斷是盡人皆可理解的,它是自在的存在,無需證明。而自然地理學者會認為這種不言自明的結論“太低級”,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發現這種美的“本質”,及其對應的“存在”也很不易。在我們調查的眾多被試中,只有一兩個人有這種美學感悟。
3 科研運行組織方式有利融合
該文認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融合是有歷史背景或歷史基礎的。作者指出:地理學的發展受到“時代精神”(Zeitgeist)的影響,所謂“時代精神”是指在某個時期內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觀,以及表述它的語言。在我看來,這種時代精神還會傳遞到科研運行和組織方式上,進而引導和規范地理學者的科研實踐,雖然該文較少涉及科研運行組織方式的作用,但是為了呼應本文的題目,我在此將不利于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融合的科研運行組織方式歸納為兩點。
首先,科研隊伍是專業化還是以區域化。地理學要么被劃歸人文和社會科學,如英美許多大學;要么被劃歸自然科學,如中國;要么徹底分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如德國和北歐的一些大學分設兩個系。這樣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科研隊伍建設都不利于融合。而以區域研究的隊伍,有利于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學融合。例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地理系有一個以“人地關系”為核心的區域研究團隊。這里列舉三位:一位是已經退休的William M.Denevan 教授,他在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地理系獲得,是Carl O.Sauer團隊的成員。他的研究領域是歷史生態學、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亞馬遜地區)。另一位是還在任的William J.Cronon 教授,他本科就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地理系就讀,后在牛津大學和耶魯大學分別獲得博士學位,他的研究領域是美國西部和邊疆地區環境及其演變。第三位是中年的Ian Baird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地區發展研究、邊界地區研究。他們的信息可以在該單位的網站查到。
其次,科研評估機制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融合的影響。由于人文與自然相融合的研究難度大,研究周期長,因此這類研究成果的發表數量相對少。在以成果數量作為評估重要依據的科研運行背景下,研究者更傾向做非融合的研究。而重視中長期成果的評價體系,才有利于二者融合成果的出現。英國在2006—2010 年期間,逐步形成了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評估框架。該框架有三大評估維度:科研質量、社會影響、對科研獲獎的影響(如研究條件、研究隊伍)(劉婭,2013)。
在北京城市色彩管控規劃研究的運行中,地方規劃管理部門約請了來自建筑、美術、歷史、景觀設計等領域的專家。2020年《北京城市色彩城市設計導則》印發。遺憾的是,地理學者未能參與這項工作,或許是因為在中國的學科管理框架中,地理學者更被認為是自然科學學者,與城市色彩管控無關。如果下一期北京城市色彩管控規劃可以吸收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者共同參與,一定會有更為新穎的視角,并讓兩方面的學者感受到學科融合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