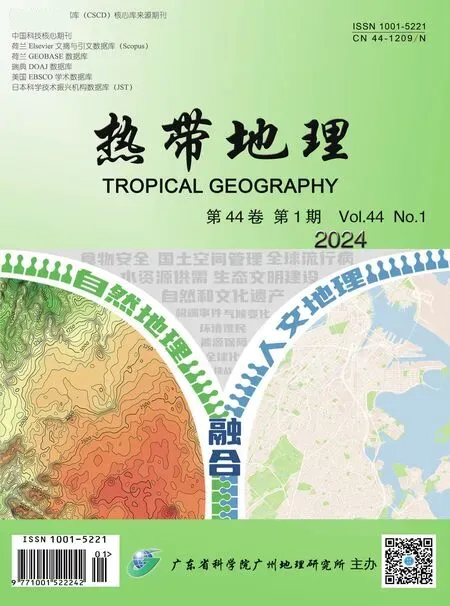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構建與應用
吳朝瑋,稅 偉,黃志剛,汪春輝,喬 璐,吳葉玲
(1.福州大學 環境與安全工程學院,福州 350108;2.復旦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上海 200032;3.福建省氣象局,福州 350001;4.福建省氣象服務中心 福州,350001;5.湖南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長沙 410006;6.福建醫科大學 附屬第一醫院,福州 350005)
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極端高溫給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幾乎可以肯定熱天和熱夜的數量以及熱浪的持續日數、頻率和強度將繼續增加(Meehl and Tebaldi, 2004;Sun et al., 2014;葛全勝 等,2014;Li et al., 2018;Seneviratne et al., 2021)。2021年北半球經歷了罕見高溫,加拿大、美國、歐洲多地因高溫死亡數百人(央視網,2021)。2022年中國報告了氣象觀測史上最熱的夏天,上海、福州、長沙等多個城市高溫日數超過60 d(中國氣象愛好者,2022)。極端高溫一方面加劇了城市熱島效應(Oleson et al., 2018;Zhao et al., 2018),破壞陸地交通基礎設施(Chinowsky and Arndt, 2012; Chinowsky et al., 2019),影響航空(Zhou et al., 2018)和能源運輸(Craig et al., 2018; Gao et al., 2018a),造成農作物減產甚至歉收(Tesfaye et al., 2017; Vogel et al., 2019),還影響人們開展戶外運動(Heaney et al., 2019)、舉辦體育賽事(Smith et al., 2018),威脅著戶外高溫作業人員的安全和效率(Orlov et al., 2019)。在高溫天氣期間,人們中暑(俞龑韜 等,2018)、高溫敏感相關疾病發生率(Yin and Wang, 2017)、住院率(Goldie et al., 2017)甚至死亡率(Han et al., 2017;Mora et al., 2017)均顯著上升。在中國(He et al.,2021)和西班牙(Diaz et al., 2019)開展的研究模擬預測了極端高溫對死亡風險和死亡率的影響還將不斷增長。極端高溫已成為當前和未來人類生產、生活和健康面臨的重大挑戰。
國內外學者在極端高溫和高溫災害影響領域開展了大量研究。國外學者側重于醫學視角(Haines et al., 2006; Hu et al., 2008;薛倩 等,2020),關注高溫熱浪對人體健康的影響(Curriero et al., 2002;Basu and Ostro, 2008; Luber and Mcgeehin, 2008)。國內側重于氣象學視角(扈海波 等,2015;趙顏創 等,2016;王芳 等,2021),關注氣象數據時間序列反映的高溫變化趨勢(林榮惠 等,2020)和高溫災害風險的空間格局(彭建 等,2014;王芳 等,2021),注重揭示高溫天氣的成因、機制等(彭保發 等,2013;薛倩 等,2020;王太然 等,2020),也對高溫引發的健康風險進行了研究和評估(謝盼等,2015a;羅曉玲 等,2016;趙顏創 等,2016;陳倩 等,2017;李歡歡 等,2020)。然而,目前仍不確定區域內哪些人類活動在遭受高溫威脅時更容易受損或表現敏感脆弱,也不清楚個體狀況或經濟社會條件哪些變化會擴大或減少區域高溫的負面影響。僅僅通過歷史氣象數據已無法準確評估極端高溫事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綜合影響,因而無法采取針對性的預防和應急措施來減少高溫災害造成的損失。
Turner等(2003)將人類與其繁衍生息的自然系統視為一個整體——人與環境耦合系統,認為其是一個統一的地理單元。在過去幾十年中,相關領域學者已由傳統的“災害-風險”視角轉向人與環境耦合系統視角開展高溫災害影響研究(Eakin and Luers, 2006)。Cutter(1996)提出建立地方災害脆弱性模型(Hazards-of-Place of Vulnerability)的工作具有前瞻性,是人與環境耦合系統研究框架指導下的經典成果,該模型綜合了地方尺度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狀況,對地方開展防災減災決策具有實踐指導作用。目前,基于人與環境耦合系統視角構建的脆弱性模型能對遭受高溫脅迫的承災體(人口、道路交通、農業等)在多重經濟社會擾動下的暴露性和敏感性進行刻畫(Wolf and Mcgregor,2013;鄭雪梅 等,2016),揭示地區在應對外部壓力時表現出的適應力差異(稅偉 等,2017;Wu et al., 2022),進而識別高溫敏感群體(Reid et al.,2009;黃曉軍 等,2021)或繪制高溫脆弱地圖(陳愷 等,2019;Johnson et al., 2012)。同時,結合研究區實際,在地方層面開展的高溫脆弱性評估對當地政府和利益相關者更有實際意義,如優化當地的醫療設施布局和政府的降溫政策等,將有助于提高福州市的高溫適應能力(稅偉 等,2017)。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研究理事會的專題報告也強調了在地方尺度開展脆弱性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地方尺度耦合系統的跨尺度脆弱性機制將是今后研究的重點,但由于區域地理特征存在差異、缺乏地方數據獲取途徑和海量數據處理能力低下等問題(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0),國內基于脆弱性研究框架在地方層面開展的高溫災害影響研究仍然不足,而且,現有城市高溫脆弱性的研究框架、指標體系參差不齊,導致地方層面的評估技術方法無法有效推廣。
習近平總書記在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建設集體學習會議(新華網,2019)曾做出“實施自然災害監測預警信息化工程,提高多災種和災害鏈綜合監測和預報預警能力”的重要指示,為信息時代和“數字中國”建設背景下城市應對極端高溫災害影響提供了數字化解決路徑,即在現有災害應急管理體系上,探索建立多部門協同聯動的災害監測預警與決策支持平臺(滕五曉,2019),實現預報預警、信息發布、決策輔助等全流程統籌安排,使上級決策者和應急管理下屬各部門及時地協同組織調度各類減災資源,可以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目前,國內外學者已對高溫災害監測預警系統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工程建設(Ebi and Schmier, 2005; Chau et al., 2009; 孫 慶 華 等,2015)。國外在自然災害監測預警系統的建設方面開展工作較早,20 世紀80 年代美國地質局和氣象服務中心聯合在舊金山灣建立了泥石流災害預警系統,結合降雨強度、巖土體的滲透能力、含水量以及氣候變化等條件綜合分析泥石流可能發生的位置和強度,并及時發布預警信息(Garcia et al.,2003)。隨后氣象領域災害預警體系與業務逐漸興起,美國、日本、英國、中國等相繼建立了各有特色的氣象災害防御體系(呂明輝 等,2021)。隨著研究不斷深入,發現針對高溫災害發生強度和位置等的監測預報對減災儲備、決策制定、應急處置等而言缺乏進一步的實踐指導意義。于是,90年代末美國在多個城市建立了高溫災害監測與健康風險預警系統,主要通過監測高溫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影響來預警可能導致的人員死亡情況(Toloo et al.,2013; Nitschke et al., 2016)。如美國的酷熱天氣健康預警系統(HHWS)(杜鈞 等,2018)將天氣類型劃分成“干熱”(Dry Tropical)、“濕熱”(Moist Tropical)、“極端濕熱”(Moist Tropical)等類型,建立不同類型狀況下因高溫死亡的人數與溫度條件之間的定量評估關系,實現高溫災害健康風險的識別與預警。國內學者和相關技術人員也在高溫健康風險預警系統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如談建國等(2002)通過對比分析天氣類型與高溫相關死亡率,發現上海地區高溫熱浪侵襲時出現的“侵入型”氣團天氣類型可能導致超正常的高溫死亡率,研究結果為上海市2001年建成中國首個高溫健康風險預警系統——熱浪與健康預警系統提供了科學支持。隨后,南京(汪慶慶 等,2014)、哈爾濱(蘭莉 等,2016)、深圳(方道奎 等,2019)等地也相繼開展了高溫災害與健康風險預警系統研發、業務運行與效果評估等工作。2015年,中國建立了多災種信息統籌監測、預警發布等業務集合的國家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系統(孫健 等,2016),打開了信息技術支持下氣象災害業務服務的新局面。
總體上,國內的高溫熱浪預警系統多面向政府、氣象部門等提供輔助決策服務,缺乏考慮不同用戶的個性化需求或群體的特征差異,如在高溫天氣下出行的普通大眾、外賣快遞配送員、施工工人等群體僅能知曉氣溫高低,無法獲得預防和應對高溫的進一步信息。隨著城市高溫事件頻繁發生,現有高溫災害預警技術的局限性逐漸暴露,包括傳統高溫預報產品局限于高溫災害自身特質、以行政區為基本單元開展業務運作(袁成松 等,2012;孫慶華 等,2015),可能存在預報位置精度低、預報信息參考性弱、預報期限短等問題。目前也缺少能為普通大眾,尤其是脆弱人群提供高溫下健康生活服務的產品。鑒于此,本研究將基于人與環境耦合系統視角構建城市高溫脆弱性研究框架和預警指標體系,以業務運行為目標開發系列預警關鍵技術,依托福建省公共氣象服務平臺——“知天氣”設計預警系統架構和功能模塊。以福建省廈門市為案例區,開展試點部署和業務運營。以期通過發布預警信號和提供輔助決策信息的方式提高政府和利益相關者政策制定和應急行動的有效性,鞏固減緩高溫災害損失的公共投資和成效,最終減少極端高溫事件對城市系統,尤其是城市中的老年人、兒童、高溫敏感疾病患者等高溫脆弱群體的健康風險。
1 城市高溫脆弱性研究框架與預警指標體系
1.1 脆弱性與高溫脆弱性的概念界定
20 世紀60 年代末期,脆弱性概念雛形開始出現于自然災害領域,研究關注災害發生的可能性、識別災害影響的范圍等(Adger, 2006; Janssen et al.,2006)。在地學領域,Timmerman(1981)較早關注脆弱性并認為“脆弱性是由一個系統所受到的災難性事件對其的影響程度、對風險災害的適應性以及從災害中恢復的能力所構成”。根據李鶴等(2008)對國內外脆弱性內涵定義的系統梳理,一方面,災害風險和全球變化領域的學者將脆弱性定義為遭受不利影響或損害的可能性或程度(Timmerman, 1981; Turner et al., 2003),強調外界干擾造成的影響或結果;另一方面,社科領域在發展經濟學、生計和貧困方面的研究認為,脆弱性是個體或群體在遭受外界不利影響時表現出的應對、適應或恢復的能力(Dow, 1992),側重揭示脆弱性內部,尤其是人文社會層面的驅動力及其影響作用(Adger and Kelly, 1999)。進入21 世紀以來,脆弱性研究對其內涵的界定不僅關注災害脆弱性中的暴露、風險等概念,更將社會、制度、經濟等人文因素也整合進內涵體系(Turner et al., 2003; Young et al., 2006;史培軍 等,2006),開始嘗試運用多尺度研究框架沿著耦合系統路徑探討脆弱性,把脆弱性看成是一個多要素、多維度和跨學科的概念體系(李鶴 等,2011)。在過去十幾年間,相關領域學者已由單純考慮災害的風險視角轉向綜合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狀況、資源可得性的人與環境耦合系統脆弱性視角,定量表征區域災害對經濟、社會和人類健康的綜合影響(Mccarthy et al., 2001; Turner et al., 2003;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0;稅偉 等,2017;Huang et al., 2020)。在全球變化領域,IPCC等國際性研究組織強調科學界和社會應該關注人類活動給全球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以及人類社會對全球變化的響應和適應問題(王黎明 等,2003),該觀點受到較為廣泛的認同(陳萍 等,2010)。
綜合現有文獻,本研究認為脆弱性是災害暴露性、敏感性、易損性、適應能力等多要素的耦合體,既考慮外界多重擾動對系統脆弱性的綜合影響,也強調脆弱系統的要素、結構與功能及與外界環境的相互作用及產生的交互效果。因此,人與環境耦合系統視角下的高溫脆弱性可定義為:耦合系統遭受高溫災害多重不利影響的可能性及其損失程度,以及人或系統應對其影響的多尺度適應和恢復能力。
1.2 研究框架
作為典型的人與環境耦合系統——城市,其生態穩定性較差,脆弱性較高,表現為容易受自然災害的影響,遭受外界干擾時(如極端高溫)的損失亦較大(Turner et al., 2003; 彭建 等,2014;孫洋等,2017)。城市系統在極端高溫脅迫下的脆弱性可以通過暴露性、敏感性、易損性和適應能力等要素進行表征和評估(Cutter and Finch, 2008; Reid et al., 200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0; Bradford et al., 2015;薛倩 等,2020;黃曉軍 等,2021;郭禹慧 等,2021),其中,暴露性是城市系統(承災體)遭受極端高溫不利影響的可能性,包括人類健康、生態系統、基礎設施、社會和文化資產可能受到不利影響的地點和影響的最大范圍(謝盼 等,2015b;稅偉 等,2017;薛倩 等,2020;Huang et al., 2020);易損性指人與環境耦合系統受到極端高溫不利影響的損失程度,是系統具備的內在屬性,包括自然環境和可用于抵御外界干擾的各種資源(Cutter, 1996; Cutter and Finch, 2008; 稅偉 等,2017);適應能力是城市系統主動、被動地減緩或抵御高溫影響的能力(謝盼 等,2015b;稅偉 等,2017;薛倩 等,2020;黃曉軍 等,2021),在本研究包括個體和區域2個層面多尺度的適應能力,其中居民個體的適應力會因其自身生理狀況、家庭特征等(職業、健康狀況、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擁有降溫設備等)的不同呈現差異(Reid et al.,2009;謝盼 等,2015b;Huang et al., 2020;郭禹慧 等,2021);在區域層面,社區組織或城市的經濟狀況、福利、基礎設施等發展水平往往能減輕人與環境耦合系統遭受高溫的損失,成為城市系統高溫適應力的重要構成部分(Bradford et al., 2015;Araya-Mu?oz et al., 2016;稅偉 等,2017)。
綜上所述,城市高溫脆弱性研究框架應當體現城市系統在多重擾動下遭受到的高溫災害影響,突出系統自然和社會經濟屬性,并能反映個體、家庭和區域多層級主體應對和適應高溫災害的能力差異。因此,本研究提出由“暴露性-易損性-適應力”三要素構成的城市高溫脆弱性研究框架(圖1)。

圖1 研究框架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1.3 預警指標體系
1.3.1 暴露性 暴露性與承災體和災害體本身均有關聯,且暴露性應當包含時間、空間和數量的概念,可用密度、頻度等對其進行衡量(程芳芳 等,2016),因此本研究從暴露源、暴露數量和暴露時長3方面衡量城市系統的高溫暴露性(表1)。首先,采用溫度和濕度共同表征城市系統面臨的高溫脅迫(災害體)。盡管目前可通過獲取高溫持續天數等氣象站點監測數據(謝盼 等,2015a;李歡歡 等,2020;Huang et al., 2020;郭禹慧 等,2021),或者基于熱紅外遙感反演的近地表氣溫反映城市系統遭受的高溫脅迫(趙顏創 等,2016;陳倩 等,2017;稅偉 等,2017),但采用環境氣溫和相對濕度的綜合協同效應對高溫脅迫進行表征已是氣候變化背景下高溫災害和健康風險評估的前沿熱點(Gao et al.,2018b; Sylla et al., 2018;陳曦 等,2020;王芳 等,2021),而且綜合溫度和濕度的指標更能反映城市系統中個體面對的高溫挑戰,這是因為高溫環境伴隨著較高的空氣濕度,不僅人體流汗散熱的能力將會下降,還可能引發中暑等不適癥狀(范永芬 等,2013)。對于生理狀況較差的高齡人群、或患有呼吸、循環系統等相關疾病的個體,長時間暴露于高溫可能會促使其疾病發作甚至發生死亡(牛彥麟等,2022)。其次,人口分布密集區域的高溫暴露的可能性較高(Weber et al., 2015;稅偉 等,2017),城市系統是本研究中高溫災害的承災體,因此采用人口密度衡量城市系統的高溫暴露數量。最后,城市系統在高溫影響范圍內的暴露時間越長,暴露風險和損失危害將隨之增長(程芳芳 等,2016),加之預警預報業務對結果的時效性要求較高,因此采用實時氣象監測數據中的暴露持續日數和當日高溫持續時長2個指標表征暴露性中的暴露時長。

表1 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指標體系Table 1 Index system of early warning for urban heat vulnerability
1.3.2 易損性 人類活動深刻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類型、結構和數量變化(董光 等,2020),而不同土地覆被類型對城市熱環境的貢獻度存在顯著差異(喬治 等,2022),表現為城市系統遭受高溫脅迫的潛在受損程度不同(稅偉 等,2017)。人類活動的范圍還受海拔高度的限制(Chen et al., 2007),海拔越高,人口分布越少,城市系統高溫暴露數量也越小。城市的“藍綠空間”——湖泊、河流、海岸、海灣等區域具有顯著的降溫效應,這些區域遭受高溫損失的可能性較小(Zhou et al., 2019;連欣欣等,2021)。目前,土地利用/覆被、水體、高程等指標已被廣泛用于表征人地耦合系統易受損或高溫敏感的程度(Reid et al., 2009; Johnson et al., 2012;Bradford et al., 2015;稅偉 等,2017;陳愷 等,2019;黃曉軍 等,2021)。因此,為區分城市系統內在脆弱屬性的具體特征(程芳芳 等,2016),將不同土地覆被類型、高程、與河流湖泊和海岸線的距離作為易損性要素的評價指標(見表1),有助于綜合識別高溫脅迫下受損程度高的區域和采取針對性措施降低損失。需要說明的是,當指標體系推廣至遠離沿海的內陸城市時,可將與海岸線的距離指標移除,或根據地方特征采用與其他大型水體的距離作為評估指標。
1.3.3 適應力 在個體層面,老年人、兒童和高溫敏感疾病患者等脆弱人群面臨著健康威脅,大量研究已證實老年人、兒童和高溫敏感疾病患者等群體由于身體調節機能較弱或生理狀況較差等原因,在熱環境中暴露后將比同等條件下的普通人承受更大的健康壓力,如中暑、多種高溫癥狀的發生率上升,甚至死亡(許明佳 等,2015;謝盼 等,2015a;羅曉玲 等,2016;奚用勇 等,2019;李歡歡 等,2020;牛 彥麟 等,2022;Huang et al.,2022)。長時間處于戶外的游客、戶外作業群體(如外賣送餐員、環衛工人、快遞員、建筑工人等)也容易受到高溫天氣的影響。因此,由于自身健康狀況和個體所處外部環境等不同,個體、群體的適應能力存在明顯差異。在區域層面,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醫療救助空間配置水平、高溫信息宣傳和城市街道灑水等服務的供給水平體現城市系統減緩和適應高溫的能力(Reid et al., 2009;謝盼 等,2015a;稅偉 等,2017;黃曉軍 等,2021;Wu et al., 2022)。
因此,為了面向個體提供脆弱風險預警預報,本研究將“個人生活、旅游出行、戶外作業”作為個體層面預警的應用場景,劃分“老年人、兒童、高溫敏感患者、游客、外賣送餐員、高溫戶外作業人員”6類群體(見表1)。通過結合由個體健康特征不同造成的高溫適應能力差異,使用矩陣判定方法劃分耦合個體層面適應力的高溫脆弱性等級。同時,這6類群體也是預警系統面向群體服務的主要對象,可由系統依據群體特征提供個性化的健康生活服務。本研究區域層面的高溫適應力通過納涼設施和醫療衛生設施的空間位置、數量表征(見表1),使用觀察和經驗方法評價耦合區域適應力的城市高溫脆弱性水平。具體而言,政府等城市治理者可通過觀察降溫、醫療資源的空間供給狀況,判斷區域預防高溫災害和降低經濟損失的能力,或對高脆弱水平、適應力不足區域的公共基礎設施進行及時補充。設施的空間位置信息還可以為城市居民、游客等在高溫天氣下尋找納涼避暑場所提供路徑規劃等輔助決策支持。
2 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關鍵技術
以格網為基本統計單元對預警要素的組成指標進行逐格網的運算得到最終的預警結果,并以圖層的形式在終端進行可視化展示。考慮數據處理效率和業務需求,規定格網的地理分辨率為500 m×500 m。
2.1 城市高溫指數
2.1.1 城市高溫指數模型 為突出夏季高溫的影響,提出基于“暴露性-易損性”構建城市高溫指數模型與城市高溫指數(Heat Index, HI),即HI由暴露性指數(Exposure Index, EI)和易損性指數(Susceptibility Index, SI)構成。采用乘除法(式1)對評估模型進行多維數據融合。目前乘除法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應用較為廣泛,能有效反映指標要素之間的協同關系(謝盼 等,2015a;黃曉軍 等,2021)以及外部高溫脅迫和內在易損屬性協同作用對城市系統的綜合影響程度。模型構建前均需使用線性函數歸一化方法(式2)對各代理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模型建構方法為:
式中:X*代表各指標的歸一化值;X、Xmin和Xmax分別代表各指標的原值、最小值和最大值。
EI 和SI 均采用加權求和法進行綜合。具體如下:
式中:Zi為第i個要素的綜合加權值;aij為第i個要素第j個指標的權重系數;X*ij為第i個要素第j個指標的歸一化值;m為構成第i個要素的指標數量。
2.1.2 模型中要素與數據的處理方法
1)暴露性指數。暴露源由溫度和相對濕度2個代理指標組合表征。中國氣象局和各級氣象部門實際業務運用的溫濕指數(Temperature Humidity Index, THI)可有效反映氣溫和相對濕度的協同效應。國家標準(中國氣象局,2011)、地方標準(海南氣候中心,2018)和相關研究(孔鋒,2020;蔚丹丹 等,2021)也已將THI廣泛用于反映城市熱環境可能造成的風險威脅。THI計算公式為:
THI =Ti- 0.55(1 - Rhi)(Ti- 14.4) (4)式中:Ti為第i個格網的最高氣溫(℃);Rhi為第i個格網的相對濕度(%)。
THI的計算規則為:根據中國氣象局定義日最高氣溫≥35℃的天氣現象為高溫天氣(中國氣象局,2008),規定格網最高氣溫≥35℃時才開始計算該格網的THI,否則將該格網的EI直接置為0。
暴露源所需的氣象要素數據通過設計應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至福建省氣象服務中心服務器獲取FZ-MOS系統生產的細格網氣象要素預報數據產品。MOS是采用統計方法通過將歷史中相同或相似的資料數據建立模型開展氣象要素數值預報的系統。目前福建省氣象局研發的FZ-MOS 系統是全國領先的MOS 預報系統(劉會軍 等,2018)。FZ-MOS 系統每日北京時間T 08:00 和20:00 發布2 次預報,預報時效為0~240 h,其中0~72 h預報時段內時間分辨率為3 h,72~240 h預報時段內時間分辨率為6 h。FZ-MOS系統生產的氣溫和相對濕度等數據產品的空間分辨率為0.025°×0.025°(地理距離約為2.5 km)。本研究擬開展小時級別與未來6 天的城市高溫指數預警預報,選用的產品為:1)對于小時級別的短時預警預報:采用每日北京時間T 08:00 發布的時間分辨率為1 h 的溫度和相對濕度動態細格網氣象要素產品對當日T 09:00—20:00 的HI 進行逐時預警預報;2)對于未來6 天的長時預警預報:采用每日北京時間T 20:00 發布的時間分辨率為24 h 的溫度和相對濕度動態細格網氣象要素產品對次日平均HI進行預警預報;采用每日北京時間T 08:00 發布的24 h 產品對未來第3至第7天的平均HI進行預警預報,并使用每日T 20:00發布的24 h產品對其進行一次更新。
衡量暴露數量的人口分布指標采用Stevens 等(2015)的研究產品,通過南安普敦大學WorldPOP研究計劃團隊的官方途徑①https://www.worldpop.org/獲取未經行政邊界調整的人口空間分布數據產品,地理分辨率為100 m×100 m。本研究使用的人口空間分布模擬產品結合了遙感技術和大數據技術優勢,不僅能突破行政邊界的限制,還通過耦合夜間燈光、道路網數據、居民點數據、高程等自然和社會經濟驅動因子將產品的模擬精度提高到90%。
暴露時長由高溫持續日數和當日高溫持續時長2個指標衡量。考慮到上述2項指標在系統中均需動態更新,因此通過設計程序接口逐格網獲取和匹配高溫持續日數和當日高溫持續時長的數值。兩者的計算原理和規則為:
①高溫持續日數。夏季高溫天氣持續不僅造成人體感不適,還會增加心理壓力(俞國良 等,2020)。在城市層面,持續高溫天氣下城市生產、能源等各部門運轉負荷都將增大。但隨著高溫持續日數的增加,城市系統能通過自身的調節機制逐漸過渡到新的狀態(Alwang et al., 2001; IPCC, 2007),而高溫的持續影響也將上升到趨于穩定。因此,通過式5 反映系統隨高溫持續日數增加的暴露狀態變化:
式中:wi是反映格網i高溫持續日數;ni為格網i系數;di是格網i累計≥35℃的高溫日數。本研究規定若當日格網i預報溫度首次≥35℃,則di置為1,開始計算wi,否則wi置為0;若格網i次日更新的預報溫度再次≥35℃,則di置為2;只要格網i再次的預報溫度≥35℃,則di一直累加,直到格網i下一日更新的預報溫度<35℃,則下一日的wi自動歸0,待系統再次監測到預報溫度≥35℃時才重新計算。
②當日高溫持續時長。獲取北京時間T 08:00發布的1 h 分辨率溫度要素產品數值至各格網,累加各格網≥35℃的時數,把累加時數作為各格網當日的高溫持續時長。
2)易損性指數。對不同土地覆被類型與人口分布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王珂靖 等,2016),反映不同土地覆被類型的人與環境耦合系統遭受高溫影響的受損程度。土地覆被數據采用劉良云團隊研發的1985—2020 年全球30 m 精細地表覆蓋動態監測產品(GLC_FCS30-1985_2020)(Zhang et al.,2021)。首先,將研究區內各街道/鄉鎮的常住人口作為預測變量,并統計各街道/鄉鎮范圍內所有土地覆被類型的面積作為解釋變量;其次,采用IBM SPSS 21.0 進行線性回歸建模,篩選影響人口分布的主要土地覆被類型,并將主要類型作為解釋變量與人口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取線性趨勢擬合值R2最大的模型為最優模型。最后,將最優模型中各類型土地覆被預測人口分布的重要性值作為權重,表征各土地覆被類型的潛在受損程度。
結合數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研究海拔與人口分布的關系,反映不同海拔的人與環境耦合系統高溫易損屬性的差異。使用ArcGIS 柵格統計模塊Quantize 方法將研究區域的DEM 數據根據實際情況等間距分割,并進行重分類;隨后利用Spatial Analyst 工具統計各高程等級中的平均人口密度,再采用線性函數、冪函數、指數函數、二次項函數等對各高程區間對應的平均人口密度進行擬合,取擬合優度高的函數模型衡量不同海拔人與環境耦合系統的潛在受損程度。
運用緩沖區分析工具建立河流湖泊和海岸線緩沖區(緩沖區距離需根據地方實際情況設置),反映在河流湖泊和海岸線緩沖距離內人與環境耦合系統潛在的高溫受損程度差異。當在內陸等無海岸的地區進行預警應用,同樣需要對湖泊、河流以及其他大型水體進行緩沖區處理。
3)模型構成指標的權重
考慮模型的推廣需求和相關研究(稅偉 等,2017),各指標的權重系數采用層次分析法和德爾菲法相結合的專家群決策方法確定。在選定的試點應用區域,通過向來自相關領域、氣候研究機構、規劃咨詢單位和政府研究室的20位專家發放問卷咨詢,最終得到各指標權重:THI 0.345 2、人口分布0.123 2、高溫持續日數0.253 4、當日高溫持續時長0.278 2;土地覆被0.508 2、高程0.111 6、與海岸線的距離0.169 2、與河流湖泊的距離0.211 1。經過調整不滿足一致性的判斷矩陣和補全殘缺矩陣,所有專家的決策結果最終均滿足一致性<0.1,即判斷矩陣確定的權重適合用于城市高溫指數模型的構建。為滿足系統的迭代更新需求,在系統核心算法設計階段已將各指數內部指標的權重置為彈性變量,當在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特征不同的城市開展推廣應用時,可組織專家對上述指標權重進行重新評價。
2.1.3 指數等級劃分方法 參考《全國氣象災害風險評估技術規范(高溫)》(中國氣象局,2021),采用標準差法對反映城市高溫災害綜合影響程度的城市高溫指數進行分級(表2)。城市高溫指數分級的基準參數為過去5 a 同期的城市高溫指數平均值和標準差。

表2 城市高溫指數等級Table 2 Urban heat index warning scales
2.2 多元主體適應力耦合技術
通過設計與用戶進行交互的終端界面,將城市系統中個體和區域層面的高溫適應力與城市高溫指數進行動態耦合,實現對城市高溫脆弱性的預警。同時,個體和區域層面的不同主體(6 類群體和城市治理者)也是預警系統的服務對象,根據應用場景(個人生活、旅游出行、戶外作業、城市治理)提供差異化的高溫輔助決策支持服務。
具體方法為:1)對于屬于6 類人群的終端用戶,在其選擇不同的角色后,程序結合用戶設定的地理位置的城市高溫指數等級檢索“多元群體脆弱風險評價標準庫”中對應的矩陣評判標準,對該用戶在設定地理位置的高溫脆弱風險進行評級,并提供對應的健康生活建議,實現耦合個體層面適應力的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2)對于政府等城市治理主體,工作人員通過搜索定位或觸摸點擊定位2種方式查看定位處的城市高溫指數信息,再結合區域中已有的景區、納涼設施和醫療設施的空間分布(設施空間位置在終端進行標識),經驗地定性判斷定位處耦合區域層面適應力的城市高溫脆弱水平,以對現有設施布局的合理性進行評價,或為減災規劃、高溫補貼福利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如某一區域的城市高溫指數經常性偏高,而其避暑納涼的場所數量又較少,則可考慮在該區域增加設施數量。
納涼設施和醫療設施數據來源于高德地圖的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 POI)數據集,其中,納涼設施的POI主要包括地鐵站、普通商業中心、公園廣場、公共建筑、大型商場和納涼中心;醫療設施的POI包括藥房、鄉鎮診所、社區衛生院和綜合醫院。通過編制Python爬蟲程序對POI進行采集、清洗、篩選和地理坐標轉換。
2.3 多元群體脆弱風險評價標準庫
由于身體素質、健康狀況和戶外暴露時長等個體生理和物理差異,不同人群在相同HI等級下可能承受不同的脆弱風險。本研究結合游客、老年人、兒童、高溫敏感疾病患者、外賣送餐員和高溫作業者等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群體較為普遍的自身素質和工作性質等特征,提出建立在HI基礎上的脆弱風險預警分級標準。根據與福建省氣象局的“健康氣象”團隊和福建醫科大學的醫師、護士進行訪談和討論的結果,定制各群體的健康生活提示和建議,形成一套多元群體脆弱風險評價標準庫。
1)游客群體 夏季是旅游旺季,也是個人、家庭出游的時節。必要的防曬防暑的措施和預備降暑藥品,使得旅游出行的群體能夠抵御一定程度的高溫影響。根據《避暑旅游氣候適宜度評價方法(QX/T 500-2019)》(中國氣象局,2019)、《區域性高溫天氣過程等級劃分》(QX/T 228-2014)(中國氣象局,2014)對旅游氣候舒適度和高溫強度的定義,通過將高溫強度等級與HI預警等級建立判斷矩陣的方式規范游客群體的脆弱風險等級表(附表1)和旅游出行建議(附表2)。
2)老年和兒童群體 在夏季高溫時期,老年群體和兒童群體較普通人的身體調節機能等表現弱勢,但青少年的生理恢復調節能力較老年人更強,因此老年人可能承擔著更大的脆弱風險(談建國等,2002;許遐禎 等,2011)。已有研究證實夏季氣溫與中暑、死亡發生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俞龑韜 等,2018;Kim and Kim, 2017),當外界溫度超過人體表溫度(33~34℃)時,中暑的癥狀開始在人群中出現;日最高氣溫達到35℃時更加容易發生中暑癥狀,且當日最高氣溫達到36~37℃時,中暑癥狀將可能更為嚴重,個體死亡現象開始頻繁出現(陳正洪 等,2002;陳輝 等,2009;俞龑韜 等,2018)。根據上述資料,提出老年群體和兒童群體的脆弱風險分級方法及其相應的健康生活提示(附表3至6)。
3)高溫敏感疾病患者群體 已有研究指出,當日最高氣溫每升高1℃,對高溫敏感疾病患者帶來的健康負面影響隨之增加,如疾病復發甚至死亡(Hu et al., 2008;王佳佳 等,2009);當日最高氣溫上升4.7℃時,心腦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率顯著上升(Basu and Ostro, 2008);且目前高溫熱浪對呼吸和循環系統疾病患者的附加效應高度顯著(Chen et al., 2015; Dong et al., 2016),在國內272個城市的研究(Yin et al., 2018)顯示,對上述疾病的影響達到14%和13%。結合老年人和兒童群體的高溫脆弱性等級,劃分該群體的脆弱風險分級表和生活提示(附表7和8)。
4)戶外高溫作業群體 外賣送餐員、建筑工人、高壓電網維修員等夏季高溫依舊堅守崗位的群體應該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已有研究指出,中暑癥狀在從事體力活動、勞動強度較大的男性群體更易出現(許明佳 等,2015;陳振龍 等,2015;付文娟 等,2020),且發現中暑甚至死亡的病例大多與經歷了持續的高溫影響有關(Chen et al., 2015;Lee et al., 2016)。因此,采用高溫持續的天數與HI預警等級建立判斷矩陣設定該群體的脆弱風險等級(附表9)。外賣送餐員和高溫作業群體共同使用一套脆弱風險等級表,但需要據行業性質分別制定兩者的作業建議(附表10和11)。
3 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設計與應用
3.1 技術架構和功能模塊
基于高德地圖JavaScript API 和高德地圖組件API等,依托福建省氣象局公共氣象服務平臺——“知天氣”設計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的技術架構(圖2)。

圖2 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架構Fig.2 System framework of early warning for urban heat vulnerability
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以“城市高溫指數”為名作為“知天氣”平臺的重要模塊,系統主要包括為用戶提供交互式操作界面的移動應用程序模塊和處理應用功能數據的專用管理后臺,其中移動應用程序模塊包括4大功能模塊:城市高溫指數預報模塊、人群高溫脆弱風險預警服務模塊、戶外工作指導服務模塊、公共設施輔助適應與決策支持菜單模塊;專用管理后臺包括2大功能模塊:圖層數據管理模塊和提示語數據管理模塊(圖3)。

圖3 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功能模塊Fig.3 System function modules of early warning for urban heat vulnerability
3.2 試點應用
3.2.1 試點概況 廈門市(24°26′46″ N、118°04′04″E)隸屬于福建省,是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特區,也是海峽西岸經濟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旅游目的地,目前全市擁有近516萬常住人口,轄區總面積為1 700.61 km2,其中廈門島的陸地面積為157.98 km2(包括鼓浪嶼),海域面積為390 km2(廈門市人民政府,2021)。資料顯示,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廈門市的近地表監測氣溫不斷上升,且城市極端高溫事件的發生頻率越來越頻繁(李文勇,2008)。《2020 年廈門市氣候年報》(廈門市氣象局,2021)顯示,廈門島內外年平均氣溫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一直處于偏高狀態,近幾年氣候變暖趨勢愈加明顯。2020年廈門島內外平均氣溫分別為22.2 ℃和22.7 ℃,分別比常年高1.5 ℃和1.3 ℃,均為異常偏高,其中島內創1953年有氣象觀測來歷史最高紀錄。
3.2.2 應用情況 通過與福建省氣象局、福建省氣象服務中心合作,2021年9月,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城市高溫指數”模塊在廈門市正式上線運營(圖4)。以廈門市同安區西柯鎮的古龍醬文化公園和廈門市思明區的中山路步行街為例示范“城市高溫指數”模塊的應用情況。

圖4 “城市高溫指數”用戶界面Fig.4 User interface of the "Urban Heat Index"
1)城市高溫指數預警預報 用戶通過搜索框查詢“古龍醬文化園”,結果以標記打點在地圖上顯示(圖5)。“智慧高溫卡片”立即更新該點位的詳細地址、指數等級、高溫發生時段和溫馨提示。通過播放條可查看該位置未來6天的指數空間格局。

圖5 廈門市西柯鎮古龍文化公園的高溫指數預報Fig.5 Forecast of HI in Gurung Cultural Park, Xike Town, Xiamen
2)人群脆弱風險預警與信息提示、戶外工作指導 在古龍醬文化園高溫指數預報等級為3 級時,游客的脆弱風險為2 級,兒童為2 級,老年人為2級,高溫敏感患者風險為1級。當日在古龍醬文化園周邊配送外賣和戶外高溫作業的人員的脆弱風險均為3級。同時,卡片分別對屬于不同人群和兩大行業群體的用戶提供次日脆弱風險預警信息和防暑降溫建議(圖6)。

圖6 古龍醬文化園的游客群體和外賣送餐群體的脆弱風險等級和提示Fig.6 Vulnerability scale and tips for tourist groups and delivery workers in Gurung Cultural Park, Xike Town, Xiamen
3)公共設施輔助適應與決策支持 以古龍醬文化公園和中山路附近的納涼設施(地鐵站、公園、商場超市、公共建筑)、醫療設施(衛生服務、綜合醫院)和景區為例,對比2個區域的城市高溫脆弱性水平。相比中山路步行街(圖7),古龍醬文化公園附近的景區、納涼和醫療設施數量都較為有限,且當日中山路步行街并未出現指數等級預警。由此,決策者可初步判定當日古龍醬文化公園及附近的城市高溫脆弱性較中山路步行街更高。結合相關部門的應急預案處理流程,古龍醬文化公園附近的社區組織可加強防暑降溫宣傳,開放更多的納涼場所和臨時醫療點,市政部門可開展街道灑水作業等。若該區域長期出現高溫指數等級較高的情況,還可通過增加植被覆蓋率,或增加人造水體等提高區域適應和減緩高溫的能力。同時,普通大眾可在前往古龍醬文化園附近區域前,查看各類降溫和醫療設施的分布情況,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提前規劃出行路線,降低高溫可能帶來的健康和財產損失。

圖7 古龍醬文化園和中山路步行街周邊的納涼和醫療設施空間分布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ling and medical facilities around the Gurungjam Cultural Park and Amoy YatSen Road
4 結論與展望
本文基于人與環境耦合系統視角綜合運用地理學、大數據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等理論和方法,對城市高溫脆弱性及其預警方法進行了研究,建構了“暴露性-易損性-適應力”的城市高溫脆弱性研究框架與預警指標體系,提出了城市高溫指數、多元主體適應力耦合技術和多元群體脆弱風險評價標準庫等系列預警關鍵技術,設計開發了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城市高溫指數”,并在廈門市試點部署,應用期間得到了廈門市民的良好反饋。2021 年9 月,系統依托福建省公共氣象服務平臺——“知天氣”正式上線業務化運營。綜合示范成果于2021 年12 月通過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驗收,驗收評價為優秀。城市高溫脆弱性預警系統為居民和有關部門提供了高溫天氣下生產生活的輔助決策支持服務,為今后省內(如福州市)和省外其他高溫城市的推廣奠定了良好基礎。
盡管多元群體脆弱風險等級的劃定建立在廣泛的團隊討論和氣象局業務經驗基礎上,但其設計仍存在不足,尤其是不同群體受高溫環境影響的健康閾值,還需進一步開展針對性的實證研究來科學劃定。目前,研發團隊已考慮設計由城市高溫指數和個體基本生理健康要素構成(性別、年齡、慢性疾病史等)的綜合模型,定量表征個體在空間上特定位置的脆弱風險,為用戶提供更加準確的風險信息和針對性的健康建議。此外,當前研究中區域層面的高溫脆弱性水平僅能通過結合使用者當前位置的指數等級和周邊資源位置與數量的方式進行主觀判定,因此,區域層面適應力的耦合技術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如引入資源的自動可達性分析功能對區域的高溫適應力進行分區分級,探索將區域高溫適應力動態地與高溫指數進行耦合,計算耦合區域層面高溫適應力的城市高溫脆弱性指數,從而政府可根據指數等級高低和已有的應急處置預案對特定區域定制針對性的防災減災方案,也有助于規劃部門識別降溫和醫療資源短缺的地區,在市政規劃中完善優化應對極端高溫資源的空間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