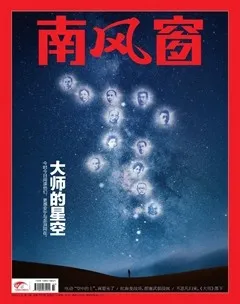趙元任,好玩的大師
王晴

1919年,在康奈爾大學當物理講師的趙元任,把電池的正負極放在舌頭上,給自己拍下了一張照片。
這不是刻意去模擬某種震顫,這個27歲的年輕人,只是想“親口嘗嘗電伏特的滋味”。
“嘗嘗滋味”,大概是趙元任掠過人生的一景一幕時,頂愿意做的事情。生在一個世界格局紛繁復雜的時代,又曾作為庚子賠款留學生,肩負著“開眼看世界”的種種期許,趙元任身上一度被戴上許多頂沉重的高帽。
在后來者的追憶中,他是“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之父”,是蜚聲國際的結構主義大師,是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中最年輕的一位。他曾任哈佛、耶魯、伯克利等名校教授,涉獵范圍從物理、天文至哲學、音樂,無一不及。在整理檔案時,他的外孫黃家林曾說:“我想象不出來,他到底花了多少時間,能做這么多事。”
趙元任不是諸多緊擰眉頭的大師中的一員。身在變動不居的外部世界,他更多被純粹的知識吸引。他深知日子的“滋味兒”是嘗的,很難說的。趙元任一生所做之事,無過于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將種種難以言說之物,或以相片,或以文字,或以曲調,一一記錄下來。
他的一生,被詳細而瑣碎地留在了20多萬件影像與文字材料中,除學術成果外,還有成年后便不間斷的照片、記載了70余年的日記。在這些浩瀚的材料下,趙元任似乎在輕松地微笑。
“好玩兒。”他說。
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寫過一本小傳,記錄趙元任一家的后半生,名為《趙記雜家》。趙元任將其翻譯為“Family of Chao’s”,取“Chao’s”既可以看作“趙”的音譯,又可看作“chaos”(混亂)。趙元任素喜歡用雙關逗人一樂,而這“趙氏”的另一重含義,也隱隱裝點了他的人生底色。
1892年,趙元任出生于天津。由于祖父為官,頻換差事,在他人生的頭十年,趙元任隨著家人幾乎每兩年換一處居所,輾轉在磁州、祁州、保定、冀州和常州之間。直到祖父過世,趙元任一家回到家鄉(xiāng)常州,才相對長久地定居在一處。
盡管當時的趙元任尚未懂事,但有語言天資的他,很小便喜歡琢磨各地的方言,也在其中琢磨“平常日子”的滋味。單是祖父這一大家子人中,便有說京話、常州話、保定話、山東話等各地方言的。在復雜的語言環(huán)境中,趙元任很早便感知到語言與身份的聯(lián)系。
彼時,趙家?guī)讉€孩子尚未完全掌握發(fā)音方法,像“天、全、面”等字,只能發(fā)成“貼、瘸、滅”音。小時候的趙元任看見有貓兒偷吃面,也只能大叫“貓雌我的滅”(貓吃我的面)。
但有一日,趙元任比家里哥哥姐姐先開竅,忽然學會了前鼻音的發(fā)音方法。他將這發(fā)音方式告訴哥哥,卻沒得到想象中的贊許。因這種說話方式,和照顧孩子的保定人周媽的口音相似,趙元任哥哥回他:“別學那些老媽子說的那種話!”
這種方言和身份的關聯(lián)并不是固定的。日后回憶起來,趙元任反想起友人傅斯年的口音。因其一家是搬到北京的山東聊城人,家中傭人說話多為北京話。當傅斯年在讀書時學會說北京話時,家里人也笑說:“你怎么說起老媽子的話來了?”趙元任推測,許是這一笑,讓傅斯年即使在已推行以北京話為標準國音的時期,仍愛用“閃董料秤”(山東聊城)的方言說話。
與更寬廣的世界產(chǎn)生聯(lián)結的新語言,迅捷切入趙元任的生活中。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趙元任這類世家子弟,開始走入新式學堂。這個階段前后,因私塾老師、祖父、父母的接連過世,趙元任于1906年到常州本地的溪山小學讀書,隨后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高等學堂,正式翻開新的一頁。彼時,晚清一批知識分子已開始望向世界,不少國人開始反思自身文化傳統(tǒng),試圖在對比中搭建橋梁。1898年,中國第一部系統(tǒng)的語法書《馬氏文通》比照著拉丁語的語法寫就,借拉丁語的語法結構,講述中國古代漢語語法體系。
在南京讀書的趙元任接觸了這本書,同時師從美國老師學習英語、物理,并選修了德語。種種知識交雜在腦中,如他筆下的日記般,開始使用多種語言和記音符號。趙元任談及:“(我們)開始以現(xiàn)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開始劃分人類為文明人及野蠻人。”變革,成為這群青年學生心照不宣的呼號。
1910年,趙元任以總分第二名的成績取得了第二批用“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的名額,其日后的好友胡適也在其中。趙元任被分至康奈爾大學學習物理,隨后也沉迷于哲學和音韻學。一個自由的知識世界在他面前打開,這一去便是十年。
在美留學期間,趙元任與同仁一同創(chuàng)辦了《科學》雜志,希望譯介國外新知到中國。彼時正值“世界語運動”初期,在這翻譯與介紹浪潮中,趙元任加入“世界語俱樂部”,成為其中的活躍分子。
由俄國猶太裔的柴門霍夫醫(yī)生所創(chuàng)立的世界語,其誕生背景與趙元任等留學生所處的環(huán)境暗暗相合。柴門霍夫生長在俄國人、波蘭人、日耳曼人和猶太人四個族群中,深感不同民族的人們由于語言不通等障礙而產(chǎn)生了種種隔閡,在19世紀末出版了第一本世界語教科書《Unua Libro》(世界語譯作“第一本書”),希望通過一門更好掌握的語言,讓人們消除溝通的障礙。
受世界語這類撫平溝通障礙的語言目標所影響,選修音韻學后的趙元任,對語言學產(chǎn)生了真正的興趣。1916年,他與胡適合寫一篇英文論文《中國語言的問題》,其中主動比較了中國當下使用的白話文與印歐語言的發(fā)音規(guī)律,認為二者其實同源。此外,他們還在其中談及使用一種中文之外的輔助語言,國語羅馬字,即一種以筆畫式為載體的拼音文字,希望借此打破國人溝通讀寫的障礙。
這篇文章在日后由胡適進一步發(fā)揚討論,成為后期白話文運動的起源之一。
提倡將書面語由文言改為白話文,既是書寫載體的轉換,也是自命為啟蒙者的知識分子希望降低讀寫的門檻,向大眾普及思想的努力。但在推廣時,難免涉及與文言傳統(tǒng)相關的“文白之爭”。趙元任曾作三篇以口語的單一音節(jié)寫作的文言故事,借以說明文言與口語的距離。其中流傳甚廣的,是一個全文78字均用“ji”音寫作的《季姬擊雞記》,全文如下:
季姬寂,集雞,雞即棘雞。棘雞饑嘰,季姬及箕稷濟雞。雞既濟,躋姬笈,季姬忌,急咭雞,雞急,繼圾幾,季姬急,即籍箕擊雞,箕疾擊幾伎,伎即齏,雞嘰集幾基,季姬急極屐擊雞,雞既殛,季姬激,即記《季姬擊雞記》。

這一文章,朗讀和翻譯都不易。趙元任作此故事,并非意圖完全否定文言,但他也實在地指出:“文字這個東西既然成立了一個制度,它就有自己的獨立的趨向。特別是經(jīng)過若干時代,要是不拿這個文字來寫活的語言,它就可能會離開了活的語言走得很遠。”當寫作成為脫離日常說話的口語,就容易忽視文字的語音,滑入佶屈聱牙的困境中。白話文寫作與拼音文字的推廣,是教育普及道路上相輔相成的兩樣。
1920年,趙元任留學歸國,加入“國語統(tǒng)一委員會”(后改名為國語統(tǒng)一籌備委員會),并在此前思想的基礎上,參考“世界語”及其他民族國家的標準語,撰寫了一套結合國內多種方言發(fā)音的標準國音。盡管后來有錄制的唱片輔助推廣,這套標準國音由于不是任何一個人所使用的語言,最終推廣失敗。
1925年,趙元任應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人共事,并擔任下設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主任。他退到了學術論戰(zhàn)之外,走到田野間,開始了這一生中最富心血的活動:漢語方言調查。
與從前看到的《馬氏文通》不同,趙元任希望用實驗的方法,記錄和分析正在被言說的漢語。由于南北方言均有不同,而在此前,并沒有一套針對當代漢語的完善系統(tǒng),這無異于是一個開山工程。
但趙元任一家均有就此安家的準備。在海外奔波半生,趙元任希望的正是能踏實做一份學術。為此,他和妻子楊步偉回到南京,一點一點將史語所和一家人的住所修建起來。
此時,他和好友劉半農均引進西方技術,幾乎同時用實驗觀測到聲調的高低是聲帶震動頻率變化的現(xiàn)象。
趙元任拜托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丁西林所長研制出一套“自動音調記錄儀”,并向史語所內部添置了許多最新的實驗機器。他帶人先從周圍吳地出發(fā),隨后進一步到兩廣、湖南等地做中國方言的調查研究,拿著錄音機,四處錄下當?shù)厝说陌l(fā)音。
在這個階段,趙元任才真正從書齋中走出來,并認知到現(xiàn)象的多樣。不同于以往照搬理論,他選擇遵照現(xiàn)實。后來回顧方言調查時,趙元任曾表示,在一個地方做調查,當?shù)厝说陌l(fā)音,就是最有效力的事實。“知識求博”的趙元任,在不同的學科和環(huán)境中交叉往來,有意無意間,將結構主義、田野調查等時興的研究方式嫁接到國內,發(fā)展了面向當下的共時研究。
但在史語所初見雛形、方言調查工作開始依照計劃進行時,七七事變來臨,南京也不再是一片安穩(wěn)地了。原本趙元任準備進行的福建方言調查只得中止,他隨大部隊南下云南。即使在這個過程中,趙元任仍轉變計劃,在途經(jīng)湖北時完成了《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可惜書稿在交付商務印書館后,印刷工廠被炸毀,時隔10年才正式出版。
1938年,為尋找一片可以安靜做學問的地方,趙元任接受了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邀請,再度赴美任教。在駛離祖國的船上,他唱起了周若無作詞、自己作曲的《過印度洋》。
“照天蓋著大海,黑水托著孤舟。
也看不見山,那天邊只有云頭。
也看不見樹,那水上只有海鷗。
那雖是亞洲?那雖是歐洲?
我美麗親愛的故鄉(xiāng)丟在腦后。
怕回頭,怕回頭,一陣大風,雪浪上船頭。
颼颼,颼颼,吹散一天云霧一天愁。”
此次一別,在趙元任一家看來,都以為只是暫時避亂。哪里想到此后竟隔了34年,才重新踏上故國。1946年,趙元任本欲隨次女趙新那和其女婿黃培云歸國教書,但為避免落入行政事務的窠臼,他想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暫任一年教職,等國內行政事務的邀請冷卻后再起身回國,但此次耽擱,卻讓其隨后在伯克利一待便是17年。
在其學生、朋友陳原看來,這番離別之于趙元任,是在他與祖國之間蒙上了一層互難看清的迷霧。“他一心追求學術上的真理,他很不情愿參與政治,這就加大了他對社會變革理解的難度。”
外部世界在這躊躇與等待的30年間,發(fā)生了另一番變化。當初自詡為啟蒙者的知識分子們,逐漸發(fā)現(xiàn)“開蒙”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庚款留洋這批學生所興辦的《科學》雜志,在1950年悄然停刊,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已經(jīng)迫切地投入建設中。作為一生都在研究活的語言、當下的語言的趙元任,此時卻離自己的研究對象如此遙遠了。許多新的語詞加入這片土地上,而他卻無法直接接觸。在這個階段,趙元任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東方語言學教授,轉向了對中國語言系統(tǒng)的完善和教學研究。

但趙元任也并非常是憂愁的,相反,他的家仍然是友人們在當?shù)氐臅蛷d。這段時間,心中對純粹知識的喜好浸潤著他,讓他在語言和邏輯的游戲中流連。與趙元任打過交道的人,總會為他冷不丁兒的玩笑所折服。
一個廣為流傳的例子便是,楊步偉再度回到美國時,因見當?shù)卦S多食材可以做菜卻被浪費,可惜之余,她干脆寫一本中國菜食譜,趙元任參與編輯。
楊步偉在書中讓趙元任出場,教大家做炒雞蛋,趙元任便一本正經(jīng)說,炒6個雞蛋,需要準備7個蛋。“由于將兩個雞子兒碰撞時,只會有一個碎,因此需要取第7個蛋用來打碎第6個蛋。如果第7個先碎而不是第6個,也是常有的事情。一個辦法就是用第7個蛋,把第6個蛋放回去。另一種做法就是,把數(shù)數(shù)字的過程推后,等第5個雞子兒被打碎之后,再碎的那個雞子兒就叫作第6個。”這種冷之又冷的機靈,總在他們的生活中抖落一通,而升級版本,便是將語言玩到極致。在外孫黃家林的記憶里,趙元任會根據(jù)發(fā)音方式,將字母歌“a、b、c、d、e、f、g”對著錄音機倒過來唱一遍,并在唱完后將錄音帶倒放,竟真和按正向順序唱出來的一模一樣。“倒著唱”并不是簡單地從“z、y、x”唱起,而是將每個字母反著讀,如“x”發(fā)“e-k-s”三個音,倒著讀便是“s-k-e”。如此加上歌曲音調,難怪當趙元任成功唱出時,臉上難掩得意。
更進一步的游戲,則是一種真正的以學術為生活。1951年,因在家中照看外孫女,趙元任聽得孩子的發(fā)音有趣,便日日錄下外孫女的聲音,并寫出一篇研究嬰孩語言的論文“Cantian Idiolect”。后來埋頭于研究的日子中,他只講與研究的語言有關的話,甚少公開談論其他。
1973年,在中美關系緩和后,趙元任終于回到中國大陸探親,見到了闊別多年的二女兒趙新那一家,以及許多舊日朋友。1982年1月26日,趙元任寫下最后一篇日記:“Up late, took a nap after breakfast. PM took another nap.”(起晚了,早飯后小睡一覺,晚飯后又小睡。)
20多天后,1982年2月24日,在一個“沒什么事情要著急的,也沒什么專門要指望的事情,覺得也不是怎么高興,也并不不高興,大半兒覺得自己人還挺舒服的,可是又覺著像有一點沒落兒似的”日子中,趙元任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