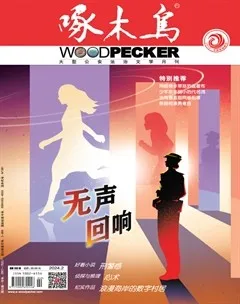陽臺上的女孩兒
子方

周日上午,我還在睡覺。陳慧已起床,床頭柜上的手機響起,她拿起來砸到被子上,下手有點兒重。我知道她情緒不好。剛過去的清明節(jié),我和她都回靈山縣老家祭祖,我沒去祭她的祖,她也沒來祭我的祖。我們的關系還沒到那個分兒上。我們是同居男女朋友,還不是未婚夫妻,雖免不了談婚論嫁。我們彼此相愛,只是若在新州城里安家,物質基礎還遠不具備。
是金主任的電話。
我立即從床上坐起來,挺直腰桿子。他言簡意賅。明天省公司分管黨建的副總要來市公司調研,重點聽取去年巡察發(fā)現(xiàn)的黨建工作中存在問題的整改進展情況。劉總認為黨建科提供的匯報稿不行。抓住機會,小龍。他掛了電話。
我匆匆與陳慧打聲招呼,拎起公文包出門去,在蘆浦大廈前攔下出租車。很順,無需我掏手機叫網約車。或許今天是個好日子。
節(jié)骨眼上,我不能在乎這百來塊錢。
金主任在辦公室候我,說劉總認為黨建科的匯報材料眉毛胡子一把抓,說倒是啥都說到了,但重點不突出,結構紊亂,層次混淆,條理不清晰,諸多句子不通順,標點符號亂用,云云。
我表態(tài)說,保證完成任務。
剛要掩上他辦公室的門,聽得他說,劉總中午過來。
劉總的家在南州。我不知金主任說的是他從南州回來,還是從新州的宿舍過來。其宿舍就是繆總留下的宿舍,車也是繆總留下的,辦公室自然也是繆總留下的,辦公室里的擺設都沒怎么動,可見他隨遇而安。誠如金主任所言,他很低調,什么都很將就,不想標新立異。就是不知他為什么在擇用跟班秘書一事上遲疑不決,金主任是向他保薦過我的。
電子稿金主任已用內網郵件發(fā)給我。我修改得很投入、很仔細,恍如回到了去年修改黨建科撰寫的繆總迎接巡察見面會匯報稿的情境。兩個稿都一樣,菜料、調料齊全,但就像是剛從農貿市場買回來的,胡亂堆放在廚房角落。什么菜配什么料,如何烹飪制作,如何掌握火候等,黨建科搞得一團糟,需要我大刀闊斧地調整修正完善,說推倒重來亦不為過。
時間過得快。金主任推門進來說,劉總到了,問稿子修改好沒有。我告訴他,只剩最后一段了,表態(tài)、表決心。他說好,現(xiàn)在出去吃飯。
我知道去哪兒吃。公司大樓附近有一家叫“黃府飯攤”的中式快餐店,步行即可,金主任平時簽單,一個月結算一次。
我第一次和劉總一起吃飯,不大敢說話。不知為啥不見司機老瞿,卻也不好問。劉總戴著金邊鏡框眼鏡,看上去斯文而溫和,像南州大學那些儒雅的老教授。
金主任挑起話題說,劉總,小龍和您是南大校友,還是中文系的系友。
劉總卻波瀾不驚地說,我知道,我才本科,文化程度比小龍低,小龍素質也比我高,不抽煙。
說到這個分兒上,如果我還不說話,那就是榆木腦瓜了。我懷疑劉總看過我的人事檔案,這還不能說明什么問題嗎?我說,劉總過謙了,我的碩士專業(yè)是外國文學,導師是李利劍教授,不知李老師是否給劉總也上過課?
上過,我在校時他還是講師,后來也不知抓住了哪里來的靈感,據說連續(xù)出了好幾本關于人類學、美學、詩學如何與文學批評相結合的著作,職稱就噌噌上去,都博導了。
劉總說得風輕云淡,我看不出他對我導師的情感傾向。本來我還希望同一個老師教過我們,也算同門,能拉近彼此距離。
金主任顯然看出了我的少許尷尬,解圍道,這么說劉總和小龍是師兄弟,小龍敬師兄一杯。
我舉杯,盡量顯得不卑不亢。我還有許多需要向師兄學習的地方,我敬師兄一杯。
劉總舉杯和我碰了一下,一點兒也不顯得勉強,我心里竊喜。和他碰杯(雖不是喝酒),于我來說是史上頭一遭。
金主任說,劉總,明天的匯報材料我交代給小龍,基本修改好了。他顯然看出來劉總不是很樂意和我聊大學時代。
劉總說,不急,再斟酌斟酌,我得在辦公室午休一陣子。
回公司的路上,劉總噴云吐霧,把我看傻了眼,金主任卻見怪不怪的樣子。劉總到任快三個月了,我第一次看見他抽煙,足見我和他的疏離。
我繼續(xù)回辦公室修改稿子,很快結了尾。想到劉總在午休,就安心地花了一個來小時做了潤色和校對,起碼不能出現(xiàn)病句和標點符號使用錯誤,否則師兄一眼就看出來了。今天我特別高效,因為辦公室另外兩個秘書小胡、小吳不在。
金主任早就向我透露過劉總是我?guī)熜郑谌徲嬏幹敖o省公司領導做機要秘書,職務是辦公室副主任,分管文秘。
我把稿子交給金主任。他翻了翻,說,很好。
沒任何修改意見?
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表現(xiàn)出急躁,劉總已經過來兩個月,應該快有眉目了。
我唯唯諾諾地點頭稱是。
我有一大攤子事,不方便老是給劉總拎包、端茶杯、下基層,總得有人接手,但據說小胡、小吳也找人給劉總打招呼了。
我小心翼翼地說,今天這稿子是你擅自決定交給我的?
是我職權范圍內的事,其他科室起草的領導講話稿或匯報稿,都得辦公室核過。
他如此信賴我,我也不能藏著掖著。我說,繆總說他和劉總打過招呼,為我的事。
這個我不知道,他跟你說有,那就是有。但他交代過我,照顧好你。
如果去南州,我一定去看望繆總。
人事無小事,不是安排辦公室、宿舍、車輛那么簡單。何況選跟班秘書,只差睡在一起,誰不得謹慎點兒?
N公司是國有大企業(yè),總部在北京,在多數省份有省公司,省公司下有市公司,市公司下有若干縣級分公司。
春節(jié)過后不久,新州市公司總經理繆直達榮遷省公司任綜合業(yè)務四處處長,新來的總經理劉盛文此前是省公司審計處處長,均是平調。沒啥好說的,每個人都要自覺服從組織安排。
年前就有風聲傳到我耳朵里,說繆總會被拿下,原因是去年下半年省公司對市公司常規(guī)巡察時發(fā)現(xiàn)諸多問題,有些還是上綱上線的。繆總本就是省公司下派的業(yè)務型干部,巡察發(fā)現(xiàn)市公司對黨建工作不重視、監(jiān)督執(zhí)紀問責偏松軟等,可見繆總還是沒擺脫重業(yè)務、輕黨建的固有思維,那么讓他回省公司繼續(xù)搞業(yè)務也可謂人盡其才。估計這就是省公司領導的邏輯。
不得不說明的是,劉盛文就是省公司去年巡察市公司的第五巡察組組長。這就難免令人浮想聯(lián)翩。今年下半年省公司還要對市公司巡察回頭看,第五巡察組屆時也只能臨陣換將,回頭看的對象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劉總自己。雖不能說違反了啥規(guī)定,但總歸是比較好玩。
對我來說卻沒啥好玩,跟了繆總三年,如影隨形,節(jié)骨眼上他卻拍拍屁股走人,讓我情何以堪。他臨走時雖對我說過已向劉總推薦我,我千恩萬謝心里卻沒底。他到底有沒有說,說到什么分兒上?
如果公司參照地方政府五年一屆任期,繆總在市公司待滿五年一般需調回省公司,榮升省公司副總或總師最理想,如不能升,則只能平調回去做個處長。這個年紀,省公司不會讓他換個市公司繼續(xù)擔任老總。我一直相信他在任期內肯定會解決我的事。按照慣例,市公司老總的跟班秘書都能提拔到中層副職,個別提早謀劃的,能弄到中層正職。對我來說,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滿打滿算的事變成了爛攤子工程。
我可是在陳慧面前打過包票的,鑒于老總一般不會在任期最后一年提拔調整干部,那么最遲在繆總任期的倒數第二年就會解決我的問題。
聽聞繼任者恰恰是省公司審計處處長、第五巡察組組長劉盛文,離任之際的繆總在金主任面前跺腳大罵,明擺著這就是公權私用,把老子搞下去,把自己搞過來!巡察重在整改,現(xiàn)在倒好,根本不給人家整改機會,直接撂下去了。金主任可謂把形勢清晰擺在我面前,他一向認我這個小兄弟。既如此,繆總和劉總相當于你死我活的敵對關系,繆總會委曲求全地為一個小秘書向劉總打招呼?即便他在劉總面前提及我了,劉總又怎么可能把斗爭失敗、灰溜溜滾蛋的前任的招呼放在心上?除非寄希望于劉總出于某種隱秘的愧疚心理,給被“驅逐出境”的繆總找補找補。何況,心胸寬大的新領導為了穩(wěn)固統(tǒng)治,應該秉持舊人為我所用的理念,對不對?但劉總不是李世民,我也不是魏征。
劉總查看市公司內設科室沒讓我隨行,走訪縣級分公司沒通知我,微服檢查市區(qū)各大經營部也沒帶著我,甚至召開退休員工代表座談會我都沒列席的份兒……這就是劉總新官上任后我面臨著的窘迫處境。
我回到了四年前碩士畢業(yè)剛分配入市公司時的狀況,單純的辦公室文字秘書。我因為是省城南州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yè)生,剛進公司就被金主任截留下來,放在辦公室用,起草文件、撰寫領導講話稿、公文核稿、寫作新聞信息宣傳稿等。三年前,繆總空降新州市公司,金主任把我推薦給他擔任跟班秘書,那時我剛滿見習期,角色就此發(fā)生重大變化。跟班秘書材料寫得不多,更重要的角色是生活秘書,領導出行要隨從拎包,領導上臺講話要早點兒擺好講話稿、放好茶杯,要隨時向領導匯報近期行程安排,甚至于領導拿不定主意時要提供參考意見等。我自從做了繆總的跟班秘書,老瞿每天早上要先接上我,再一起去接繆總。市公司大樓在新州市郊外,這也是公司性質決定的,我們不能混跡于鬧市區(qū)人們熙來攘往的地方。三年來,只要繆總還在公司,我就不可能先下班。來回路上,繆總除了和我探討公司的經營發(fā)展思路,還會就具體經營網點的設置和調整、某些員工(大多有職務)的脾性特點和性格缺陷、新州的人文習俗甚至陋習等征求我的意見或向我了解情況。我老家在新州市下轄的靈山縣,好歹也算新州人。我盡我所能地向繆總匯報我所知道的、理解的、設想的、認為是努力方向的。
在這三年里,我覺得自己是受重用的,在市公司的前途也是美好的,同事們看我的眼神也是羨慕的。如今,所有努力都打了水漂。不僅被打回原形做文字秘書,也不能再蹭老總小車,不得不坐公司班車上下班。坐班車沒啥,只是同事們的目光讓我不好受。
我坐劉總的車回市區(qū),老瞿就像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金主任上午自己開車去公司的,不坐這個車。
繆總喜歡坐后排,還叫我也坐后排,簡直不存在尊卑有序。劉總喜歡坐副駕駛位,每個領導都不一樣。他和我說話時也基本不回頭,像在和前擋風玻璃說話,這使得我的耳朵神經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狀態(tài)。但想到他看過匯報稿后沒叫我改一個字,我的心底又踏實了些。
老瞿自然先把劉總送到宿舍,在東浦錦園小區(qū)。車子從南大門進去,開到7幢樓下劉總下車,他住803。我作勢要下車給他開車門,被他制止了。
老瞿熟門熟路,車子從北門出了小區(qū)。
小龍,劉總今天對你的態(tài)度很好。
老瞿你啥意思?
估計你時來運轉了。
啥意思?
劉總要重新起用你。
我沒吱聲。一路上過來,劉總和我說了些啥我自然有數,有那么點兒意思,旁敲側擊、隔靴搔癢,但話題所指方向大致明確。老瞿在領導身邊待久了,鬼精靈。劉總沒想過換司機。老瞿是臨聘人員,領導不可能讓他知曉啥核心秘密。我進入公司時,老瞿已在為繆總的前任開車。作為老總司機,小甜頭是有的。比如有些上下游客戶有求于老總,需要了解老總行蹤;或老總下基層調研,某些分公司負責人為表達心意,均會送點兒土特產。免不了請老瞿幫忙,于是見者有份。我估計各任市公司老總均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臨聘人員工資收入低,老瞿也不例外,但他做的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必要予以適當安撫。我和老瞿共同為繆總服務三年,他有時求教我,一些名義上是土特產卻分明超越了土特產含義的禮品是否該收,人家要放他車上。我總是能當機立斷,給他明確答復(多半情況下是不要拂了人家情面)。為此他格外感謝我。即便繆總事后認為不妥,也該是我的責任,而禮品他已妥妥收下,不可能還回去。毋庸諱言,人家送繆總土特產,我和老瞿一起沾光。某種意義上我和老瞿是利益共同體,看到新老總把我掛起來,他表現(xiàn)得比我還要著急,卻不好開口。
車子在蘆浦大廈前停下,老瞿知道我住這里。他的家還在前面,一個叫華僑新村的地方。老瞿是新州市區(qū)的原住民,不必像我這個新新州人還要租房子。
陳慧在家,在廚房里準備晚餐。聽到門口有響動,面無表情地瞥我一眼,繼續(xù)低頭干活兒。我很想告訴她喜事來了,卻無憑無據的,不大好開口。我就問她中午一個人吃的什么,像家長問小朋友中午在幼兒園里吃什么。
方便面。她說。
我一陣心酸,低頭往房間里走。我出生在靈山縣城,家境一般。她不僅出生在鄉(xiāng)下,家境只能用勉強填飽肚皮來形容。她就讀的是新州學院,就是個大專生,目前在一家叫新州玲瓏科技公司的私企做文員。我和她在市人力資源和社保局某個下屬單位舉辦的企業(yè)辦公室人才培訓班上認識。在企業(yè)里我們角色相當,在大學里念的都是中文系,加之同是靈山縣人,最關鍵的一點是我被她的美貌吸引,我們走到了一起,是謂“非法同居”。如果我身在國企也算是公家人,她在私企,身份上我比她高,收入也是她的兩倍,好像處處在她之上。我想這就是她為什么能夠認可我、接受我,盡管我們只能租房子住。但歲月不饒人,今年我三十,她二十五,雙方家長都著急,但他們均不知自己的孩子戀愛了、同居了,好像我們在為隨時散伙做準備。
我在陳慧面前打包票,是去年的事。去年我信誓旦旦地說今年繆總會提拔我,哪知今年初風云突變,連拎包端茶杯的權力都失去了。我本不想她為我擔心,但我愁眉苦臉傻瓜都能察覺到異常,何況冰雪聰明的陳慧。這不怪我,我在單位里尚可強顏歡笑,回家還讓我表現(xiàn)得無憂無慮,這也太強人所難了。我只得如實招來。陳慧安慰我,又不是失業(yè),換老總而已。過一些時日,她攛掇我,不能一味畏縮,要勇往直前,要大膽地向新老總展示你的才華,最差的結果無非他還是不用你。她強調說,男人嘛,就要對自己狠一點兒。然而我沒聽她的,繼續(xù)韜光養(yǎng)晦、大智若愚,任憑劉總暗中考察。她漸漸失去耐性,顯然怨憤我爛泥扶不上墻,偶有冷臉冷眼。我得承認,我們之間稍微出了點兒罅隙,之前掛在嘴上的談婚論嫁也漸漸淡了下去,但絕不至于提分手。事實將馬上證明我做對了,就像金主任一再提醒我的,少安毋躁,保持低調,是金子總會發(fā)光。
不過還是得耐心等一等,我想要不了幾天,事情就會明了。那時報喜不遲。我暫且放下心思,去廚房幫陳慧擇菜。她難得地買了一條黃魚,估計是因為周日有時間對付。我便提出我來殺魚,剛拿起剪刀,房間里的手機響了起來。是老瞿來的電話。我心頭怦怦跳,雖然他只是一介司機。
小龍,明天開始你官復原職,我老瞿沒說錯吧。
盡管有思想準備,我還是整個人蒙了。
我剛開到家樓下,劉總給我打電話,說沒有存你的聯(lián)系方式,他問你的住址,問我去接你再去接他方便還是……還是反過來更方便啥的,我說先去接你順路,他說那就好,明天開始就這么辦。你說,你說……
謝謝、謝謝老瞿……告訴我這個好消息……
他掛了電話。我卻手擎手機,好半天沒放下。我腦子里突然有了點兒別的想法,驚天動地的想法。
我去廚房,盡量心平氣和地告訴陳慧這個事,不是那個想法。
她已剪開魚肚子,正往外掏魚肚子里的雜七雜八。看不清她臉上有啥明顯變化,但總算點頭了,勉為其難似的。我不免有些愕然。
這在我的職場生涯中是個重要轉折點。我提醒說。
她似乎感覺過意不去,說,我明白,對你很重要。然后把掏光了內臟的魚放到水龍頭下沖洗。
不值得咱小兩口慶祝慶祝?
咋慶祝?
比如說喝點兒酒,比如說夜里……
把魚切了。
切成一塊一塊?
蠢,你以為黃魚是帶魚啊。
那怎么切?
在魚身上劃一刀、劃一刀,她比畫著說,我要用黃酒清燉,容易入味。
還要撒上蔥花、姜絲啥的對不對?我終于明白劃一刀是怎么回事了。
我們房子的租期是不是要到了?她問。
租期還沒到,但快要付下一年度租金了,一年一付嘛……不急,夜里我要跟你商量個事情。
什么事情?她茫然地看著我。
我喜氣洋洋地做了繆總的三年跟屁蟲,到頭來得到了什么?不能再坐以待斃了。
也是啊,又來一個碌碌無為的三年可咋辦。
如果劉總認為自己鐵定將在新州干滿五年任期,他就沒必要急著安排我。他四十三,比繆總年輕許多,扎根基層埋頭苦干,力創(chuàng)一番事業(yè),積累上升資本,對他是不二選擇……可萬一哪天他也因某種意外因素倉促離職呢?
你到底要跟我商量啥?
我要跟你商量的是,不能一味死等,要把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她虛心請教,怎么樣才算把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呢?
我說,那就是夜里我要和你商量的。
我們租下了東浦錦園8幢1004。
東浦錦園建于二十一世紀初。靠近小區(qū)南大門的是一排十層的小高層,后面幾排均為二十五層的高層,前后排距離三十幾米,錯落有致,后排的視線不至于被前排全擋住。但每幢樓的內部格局實在無法恭維,電梯井設置在最當中,相當于四合院的天井位置。每層樓有01、02、03、04四個套型,朝向分別是東北、東南、西南、西北,面積均為一百平米出頭。對我們來說,承租房面積比蘆浦大廈那個大了,租金也高了若干,但朝向差了,衣服晾曬在北面陽臺上,只有下午短暫時間可曬到太陽。我把陽臺頂燈換了,把晚上的陽臺照得亮閃閃、明晃晃。陳慧詢問何意。她大事明了,細節(jié)還含糊。我說烘衣服。她知道我在胡說八道,但沒深究。房東因前個承租客要求,把陽臺和主臥之間的矮墻拆掉了,做成了一個超大主臥,在原矮墻位置添置落地窗簾。把陽臺外沿護欄也拆掉了,做成全透明落地窗,下半部分是固定的鋼化玻璃,上半部分是推窗,外沿落地窗自然也配了落地窗簾。
我非常滿意,感慨運氣真好。
8幢1004,可俯瞰7幢803。時隔不久,我發(fā)現(xiàn)后者亦可仰望前者。我沒料到這一點,不過無妨,船到橋頭自然直嘛。
劉總雙休日不一定回南州的家,滿打滿算一個月回去一趟。這是老瞿提供的信息,準確可靠,因為他要來回動車站接送。按老瞿的說法,劉總可能并不是很想念老婆。我做了跟班秘書后,不用時時問老瞿,亦不難掌握劉總行蹤。我就趁他難得回南州的一個雙休日,把家從蘆浦大廈搬到了東浦錦園。沒啥大件東西,叫了一個貨拉拉小四輪,兩趟便解決問題。
我對老瞿說我租在了東浦錦園北邊的瑞興園,希望更好地為劉總服務,但不希望劉總知曉此事。他頗為善解人意地表示理解。我相信他求之不得,從華僑新村過來到東浦錦園,要經過蘆浦大廈多少繞了一點兒路。每天早上我在東浦錦園北門(也就是瑞興園的南大門)候他的車,我上車后,車子開進東浦錦園小區(qū)停在7幢樓下等候劉總,接上劉總后,車子從南門出去。每天傍晚車子從南門進入,在7幢樓下稍做停留,從北門出來,我下車,目送車子離去。我和劉總一樣,一般情況下,工作日一日三餐都在公司食堂對付。
一個傍晚,劉總叫我一起下車,說是議一下明天上午去橋東縣分公司調研的事。下午我已把調研提綱給他過目了,甚至把他在實地調研過后擬召開的座談會上的講話稿都寫好了。分公司那邊我也已銜接好,陪同調研的幾個科室負責人都通知到位,應該沒啥遺漏。
我就是在這一天發(fā)現(xiàn)803可仰望1004的。其實用腳趾頭早點兒想想,也該明白這一點。
劉總就講話稿提了幾點意見,交代我在他的電腦上修改。他去洗澡了。他知道我有隨身攜帶U盤的習慣,平時一些重要資料,尤其是經營數據可隨時隨地查看。我把講話稿拷貝到電腦上修改。調研結束后,他的講話稿將以市公司內部信息簡報增刊的形式印發(fā),發(fā)送給內設各科室和各分公司,用以指導今后一段時間的相關工作。
改動不是很大,我坐在電腦前等劉總過來驗收。其間我給陳慧發(fā)了一條信息:我在你的眼皮底下,沒事別聯(lián)系。
劉總把換下來的衣服拿去陽臺上放洗衣機里洗了,我聽著滾筒轉動的聲音,心想自己是不是能幫得上什么忙。但想到自己的衣物平時都是陳慧在洗,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劉總坐電腦前看稿子,我立在他身后聽指示。他卻指示我去燒開水,等會兒在陽臺上喝茶。他哪來的閑情雅致與我喝茶?雖不免奇怪,我還是照做不誤。
陽臺上有兩把藤椅和一張小圓桌。我泡好茶,等著劉總過來。不僅人站著,耳朵也豎著,怕聽不到他喚我去書房改稿子。
他來到陽臺上,說,稿子就這樣了,明天結合實地調研和聽取匯報情況,我再脫稿補充就行。
我說回來后我會及時整理錄音。我的公文包里除了U盤,錄音筆也是不可或缺之物。
我們坐下喝茶。
橋東有什么好玩的?他突然沒頭沒腦地問。
明天下午不是回來嗎?我反應不過來。根據行程,明天上午到了橋東縣分公司后,即在分公司領導陪同下視察幾個縣城的經營部,走訪幾家合作營銷公司,去分公司食堂用餐,午休后召開座談會,會后即回新州市區(qū)。
你有事?
沒有,只是如果行程改了,我得與幾個科室負責人和橋東的王經理做好銜接。
行程不改,會后他們幾個先回新州,不是有兩輛車嗎?
我請分公司安排明晚住宿?
不必驚動他們,明天不是周五嘛,回到新州也沒事干,我回不回來他們幾個也未必知道。他臉上露出一絲狡黠的笑意,就像小孩兒耍了一回惡作劇,成功瞞過了大人明察秋毫的眼睛。
我說,我沒事,周六一天我們可以逛……游山的話就靈峰,玩水的話就南溪江,劉總您是?
他大手一揮,不必事事未雨綢繆,走著瞧。他愜意地抿了一口茶,說,聞著清淡,喝起來倒真的有回味。
我對茶不講究,但也裝模作樣地細品起來。這個雙休日他顯然又不回南州了,莫非真如老瞿猜測的那樣,他并不想念老婆?我還設想,他去年帶領巡察組如此賣力干活兒,目的就是堂而皇之地趕走繆總,自己取而代之,從而名正言順地離開南州,離開老婆?
小龍,你一直不抽煙?
在南大抽過。我老實承認。他手里握著一包煙,新州人喜歡的小利群,幾口就能抽完的。
要不,今天來一支?
我稍為遲疑,便接了過來。他把自己的煙點上,遞了打火機過來。我一伸手,他又把手縮了回去。他向我攤開手掌,我把煙還給他。
我到新州這么久才起用你……對不起啊,師弟。他朝陽臺外吐出一口煙,沒看我。
我也沒看他,只垂著腦袋。讓我吃驚的當然不是他遲遲才起用我,而是竟然向我道歉。
他抬頭看著三十幾米開外8幢的某一處說,繆總和我提起過你,金主任也認為你是最佳人選。
謝謝劉總,也謝謝繆總和金主任。我說著,順勢抬頭,眼角的余光偷偷順著他目光的方向略微向上。他的目光定格在了某處。五一過后,天黑得遲了,這個時候即便不開燈,也不影響陳慧在陽臺上活動,但她早早地把陽臺上那盞亮閃閃、明晃晃的頂燈點亮了,亮如白晝。而周邊陽臺均尚處在一片昏暗中,活動著的陳慧此刻看上去特別顯眼。她穿著天藍色的無袖短裙,裙子上點綴著幾朵白云。她彎腰俯身拖地,長發(fā)松垮垮地扎縛在頭頂上,隨著身子運動,不時有幾縷頭發(fā)飄散在眼前,她動輒停下拖地的動作,用右手在額頭上捋一把。她頭上飄揚著幾件晾曬著的衣服,主要是她的,也有我的。我無端地擔心劉總認出那就是我昨天穿過的衣服。顯然她把三扇推窗都推開了。拖地就拖地,她干嗎不停地轉動身子?多半時間還挨著鋼化玻璃活動,不怕沿著鋼化玻璃擺放的一盆盆花草扎到她?
小龍,你看到對面那個女孩子了嗎?
我裝作大夢初醒,抬頭用目光尋覓一番后,說,看到了。
這個女孩子真美……不,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說,我看到的是一幅絕美的風景畫。
一幅辛勤勞動的畫面?
你總結得對,你看,她在拖地,我有時看她在晾曬衣服,有時給盆栽植物澆水,有時也不算是勞動,只是自由健身,扭腰提臀擺腿,無論哪幅畫面都很美。
她看上去是挺漂亮。
不,小龍,漂亮和美在美學范疇里是兩個概念,我看不清她的五官,只看得見一個輪廓,有時甚至只是模糊的身影……我好久沒這么熱血沸騰了。
我的肚子無端地抽搐起來。在陽臺上大張旗鼓地賣弄身姿,我不記得如此攛掇過陳慧。或許我忘了?
我不知道你在南大時,教美學的王堃教授是不是已經退休。他跟我們說,美不是漂亮,美必須要有內在的力量支撐。小龍你看,這個女孩兒不是特別瘦,顯然也稱不上豐滿,普通身高,但你有沒有注意到她臀部和肩部的弧度?如果弧度里面也有個黃金比,那她就是。你看她拖地前推后拉的動作,有一股充沛的力量蘊含其內。不僅弧度優(yōu)美,而且充滿自信,她每次用力手臂肌肉就會縮緊,皮膚會有輕微跳躍。當然你不必看得那么仔細,事實上你也看不了那么細,但你完全可以想象……小龍,你在看嗎?
我努力擠出一絲笑意,借以掩飾窘態(tài)。我說,我在聽您說話呢,劉總,盡管您從南大畢業(yè)比我早,但記得的知識比我多。
這不是該死記硬背的知識,這只是生活中時時該有的美學,而今天,我請師弟一起欣賞美的存在。
是,是,我木訥地應答著,美……美的存在。
對面的女孩子剛入住不久,估計一個月不到,這真是我的幸運。原來陽臺上老是有一個大腹便便的老娘客咋咋呼呼,所幸她搬走了。
我盡量用平和的語氣附和說,舊貌換新顏。
她一定不會注意到對面有個熱心觀眾。
是,她肯定不會。話雖如此,我卻有一絲懷疑,陳慧在“釣魚”。
其實我也不希望7幢還有人注意到她,我愿默默地享受這幅美好的流動畫面。
可是劉總,您已經請我分享過了。
是啊,師弟除外,可今天你也只是順便而已,你看,你看……
此時陳慧把地拖當支撐物,一只手扶著拖柄,另一只手在地上摸索著什么。她剛好背對著我們,撅著豐滿圓潤的臀部。天藍色的背景下,兩腿之間一片淺黑色。當然,那只是她穿著的內褲顏色,對此我相當確信。我相信劉總也是這么想的。
小龍,你看到了沒有?
我不明白他具體所指,只含糊地應答,看到了,很美。
你像如坐針氈,是不是急著回家?
我搖頭說,不急,女朋友還沒回家呢。
我聽老瞿說你和女友住在一個叫什么大廈的地方?
是,蘆浦大廈。
有公交車嗎?
有直達公交車。
那行,你早點兒回去,明天上午大伙兒在食堂用過早餐就出發(fā)。
從橋東分公司回來后的一段時間,劉總看上去有點兒蔫,憔悴,甚至可以說萎靡不振。
我不明所以,但也不好主動發(fā)問。按理說,那兩天他在橋東縣分公司負責人王建勇的陪同下玩得挺開心,一點兒也沒架子,甚至可以用沒心沒肺來形容。靈峰和南溪江都去了,山珍江味都吃了,直至周日下午才心滿意足地回新州。王經理一再聲明是個人請客,八項規(guī)定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上。
聯(lián)想到劉總近段時間的身心狀態(tài),我懷疑他在橋東的尋歡作樂只是強顏歡笑,除非他從橋東回來后,生活中發(fā)生了某種重大變故。
工作上我沒發(fā)現(xiàn)有值得劉總煩憂的。很可能還是老瞿提及的老問題,即劉總后院起火。他的家庭情況究竟如何,市公司沒人知道,他的人事檔案放在省公司。按他的年齡,孩子應該在讀初中或高中。妻子應該在南州上班,關鍵就是“她”。清官難斷家務事,何況我只是他的跟班秘書,他不開口,我能怎么辦。
我和陳慧原本只是把家當作瞭望哨,陰差陽錯她把自己當成了某種誘餌。我聲明沒讓她在陽臺上做撩撥人的動作,她卻一口咬定就是我指使的,看來此事成了無頭懸案。我們偶然能看見劉總在陽臺上看書,身子后仰,腳擱在小圓桌上,那是在晚上。我總懷疑他是在裝模作樣,陽臺燈供人活動沒問題,看書的話明顯亮度不夠。但夜里,我們經常能看見他坐在陽臺上抽煙、喝茶或喝酒,那時他沒開陽臺燈,只有煙頭一閃一閃。
某個下午劉總提前下班回市區(qū),讓我跟他一起走。我估計晚上有人請他的客,之前他也偶有早退,多半是為晚上的應酬。
老瞿把車子停在7幢樓下。劉總回頭說,小龍你也下來。
他之前出去應酬從不帶著我。我只知道他有幾個南大的同學也是新州人,在什么單位、做什么的,甚至是男是女均不清楚。
在電梯里,我問,劉總,是不是有什么任務?
能有什么任務,莫非你想回家給女友做飯?
沒有,工作日我們幾乎從不在家里開伙。
果不其然,他說,晚上我?guī)愠鋈コ裕c省公司有合作的一個上游客戶今天在新州活動。
我有點兒受寵若驚,這就像男女談戀愛,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帶出去見彼此的朋友。說明劉總把我視為了自己人。我內心又有點兒不安,他對我如此信任,我和陳慧卻躲在陽臺落地窗簾后對他干著見不得人的偷窺勾當。我在搬到東浦錦園之前就把高倍望遠鏡買下了,還帶紅外線,夜里管用,可惜不能穿墻過壁。當然啦,如果能穿墻過壁那還得了,簡直就是犯罪。陳慧沒問我為啥如此煞費苦心,她已被我說服,一心一意幫助我成就好事。
是,是我讓陳慧暫時躲起來的。她不該如此撩撥人,弄得人家欲火中燒有啥意思呢?她竟然說這叫引蛇出洞,人家只能看不能摸,還不得另想辦法解決問題?如此一來,招蜂引蝶便亦屬可預料的后果。至于人家是招引什么樣的蜂蝶上門,那就看他個人愛好了。找小姐吃快餐利索,不怕麻煩就去勾引少婦,更不怕花心思可以去勾引少女。什么樣的女人和我們有關系嗎?我們只管把他的風流韻事拍錄下來即可。她就是如此振振有詞。好歹,她答應我收斂一段時間。陽臺頂燈能不開就不開,裙子要穿有袖的,不能把胳膊窩露出來,裙子領口不能太低,下邊的裙擺也要過膝,最起碼不能露底褲……
一進門,劉總就把公文包丟在茶幾上,去陽臺轉了轉。像是遭受了什么打擊,回來時垂頭喪氣,頹然跌坐在沙發(fā)上。
小龍,櫥柜里有瓶XO,你去拿一下。
我提醒說,劉總,晚上出去還得喝酒。
沒事,先喝點兒開胃酒。
我的提醒只能點到為止。XO是開過瓶的,瓶口標簽封條已撕成兩半,一斤裝的洋酒還剩大半。我試著把木塞子拔出來,再塞回去。
他看我拿著XO和一個玻璃杯過來,擺手說,不行,師弟也來點兒。
酒還沒開始喝,他看上去就有點兒醉了。我想到了借酒澆愁,只是不知他愁在何處。到任三個多月,他算是原形畢露,比繆總還平易近人,那么初來乍到的前兩個月他端著架子偽裝,也確實是難為他了。但一想到可能是他一手趕走了繆總、破碎了我的美夢,我又無法對眼前這個人完全放下心來。古人說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么我?guī)е惢鄣闹赝胁檎抑虢z馬跡亦屬情理之中。不過廚房里是聞不到女人氣息的,我也沒在瓷磚地面上看見一兩根女人的長絲。803有廚房,但對劉總而言只是擺設。
我和劉總便像去橋東分公司之前的那個傍晚一樣對飲。只不過把陣地從陽臺搬到了客廳,把小圓桌變成了正方形的茶幾,把茶變成了酒。小半杯洋酒入口,肚子里便覺火燒火燎。但劉總似乎習慣這口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
酒壯人膽。我說,劉總,您來新州工作三個多月了,怎么只見你回南州,不見我嫂子來新州探望您呢?
劉總斜我一眼,面無表情,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說,師弟酒量如何?
碰了個軟釘子。我說,還行,白酒三兩,紅酒一瓶,啤酒沒測過。
你在南大和同學喝的不都是啤酒?
也喝加飯酒,紹興花雕,最多的一次喝過一瓶半,躺著實在難受,又吐不出來,就在校園里瞎逛,最后躺在大樹底下睡了一夜。
他忍俊不禁地豎起一根手指抖了抖,說,你啊你,叫我怎么說你好。
還有一次喝五加皮,半夜里全吐在自己床上,渾身沒一點兒力氣,就躺在嘔吐物里睡到天亮。
有時我也想一醉方休,不管不顧,就像回到大學時代。
劉總年紀輕輕便是市公司老總,哪里還有什么煩惱。我用的是陳述語氣,盡管很想用疑問語氣。
本來下午也不必這么早回來,但我想看看對面的女孩子回來了沒有。
回來了嗎?
沒有,劉總不加掩飾地唉聲嘆氣,她顯然是個女白領,不是新州人,一個人在城里打拼。
我在心底干笑一聲,說,她的工作強度肯定很大,不到點下不了班。
我很少看見她了,她似乎在和我捉迷藏,房間里明明燈亮著,但就是不出現(xiàn)在陽臺上。趁我稍不留神,衣服已經晾曬在桿子上,估計那些盆栽花草也澆過水了。偶爾我能看見有人影在陽臺上晃動,房間里的亮光隔著窗簾投射到她身上,影影綽綽,那畫面同樣很美,充滿無限魅惑。但她為什么不開燈,她是在黑暗中健身嗎?
我干巴巴地說,也許,可能。
她好像單身,只有一兩次,我看見陽臺上像有男人的身影掠過,也或許是我看花了眼。
肯定是您看花了眼。
你肯定?
我回答不出一個字。
晚上我在陽臺上看書,但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心不在焉地翻著書,無論目光還是注意力都在對面的陽臺。即便在公司,我腦子里也在不停地想著她,但不是通常男人對女人的相思,我只希望回到有她活動于其中的畫面里。無論她在做什么,無論她姓啥名啥。
起碼您掛念著她?
是。
您是不是懷疑她發(fā)現(xiàn)了您對她的關注,所以躲起來了?
不可能。
為什么不可能?
我又沒對她存在任何非分之想,對我來說,那只是遠方的一道風景,只可遠觀,不可褻玩焉。
她不會這么認為。
師弟,你何以如此肯定?
師兄,您亦何以如此肯定?
我倆同時哈哈大笑。
笑過后,我說,要不我去找物業(yè)打聽打聽,這個年代打聽一個人易如反掌。話一出口,我便惴惴不安,龍永順你是犯傻還是怎么的。
他模棱兩可地說,我還考慮過讓金主任把這個套房退了,看看7幢上面還有沒有套房出租呢。
我說,那就一目了然了。我按捺住咚咚心跳,順勢拿起XO給他倒酒,不料手卻抖個不停,把酒灑了一些出去。我說,我去拿抹布。
我竄進衛(wèi)生間,剛好有塊布躺在地上,估計是劉總把不用了的毛巾拿來當地巾。但我沒有馬上出去,而是順勢查看衛(wèi)生間各處,看看有沒有女性活動留下的痕跡。啥也沒發(fā)現(xiàn)。按照陳慧提醒的,不僅要關注劉總有沒有帶女性回家睡覺,還要看一看他家里有沒有貴重禮物,最好去一趟儲藏室,要隨時拍照、拍視頻固定證據。生活作風問題、廉潔問題,均是扳倒領導干部的好手段。一旦把柄在手,某人還不得乖乖就范。
我不能在衛(wèi)生間待太久,出來發(fā)現(xiàn)劉總已用紙巾把茶幾擦拭干凈。我尷尬地站在一旁,此時才意識到拿地巾擦拭茶幾似有不妥。
就算我關注某個女孩子,師弟你緊張什么?劉總笑瞇瞇地看著我。
我和陳慧商量從東浦錦園搬走。為此,我也不得不告訴她實情,即劉總喜歡上她了。商量的結果是,她可以繼續(xù)光明正大地出現(xiàn)在陽臺上,略以慰藉劉總孤苦的心靈。
劉總的問題得以暫時解決,但我自己的問題解決無望。即劉總在家的情況下,我依然不能在光天化日或陽臺燈的照耀下出現(xiàn)在陽臺上。好在習慣成自然了,對我來說不算太難的事。
不出所料,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劉總的狀態(tài)恢復如初,工作上風風火火,雷厲風行。他沒想著再邀請我去他家,工作上暫無需要,其他方面亦無需要。他完全無視我在這個事情上所做的偉大犧牲,相當于我行賄,他心安理得地受賄,卻不知行賄者為何人。
漸漸地,我多少有些心理失衡,但我沒有破題契機,只能寄希望于他再次邀請我上他家,目前看來遙遙無期。對他來說,有了陽臺上的陳慧就夠了,盡管他不知道她叫陳慧。
我甚至起過犧牲陳慧從而把他牢牢掌控在手心里的齷齪念頭。別看他關于美和漂亮的理論一套一套,真把他朝思暮想的女人擺他床上,沒哪個男人做得了柳下惠。我堅信這一點。當然我只是想想而已,且不論陳慧贊同與否,我首先過不了自己這一關。
陳慧聽了我的情況通報,深信她已牢牢釣住了這個男人,竟然顯得很開心。她在陽臺上愈加放開了,或者說更開放了,因為她知道對面有個男人在仰望她,帶著無比崇拜和愛慕的目光在仰望她。她只有賣力表演,才對得起他的虔誠。她表演時,陽臺邊沿的落地窗簾自然是敞開著的,我卻只能躲在里頭的這一幕窗簾后偷窺她的表演,心頭滿不是滋味。
我和陳慧罕見地發(fā)生了爭吵,因為觀點不一致。我的觀點是,她愈是輕易滿足劉總對美的欣賞,他愈是沉湎其中,從而對別的女人不屑一顧,包括他在南州的妻子。不過說實話,我不能排除他是個離異人士的微小可能性。我甚至為此起過問一問繆總的念頭,終究還是不敢。她的觀點是,他是一個獨居異地的領導,從他很少回南州來看,夫妻關系一般,他急需異性撫慰,她能最大程度挑逗起他對異性的美好向往,而不僅僅是非“她”不可。弗洛伊德有一個替代性滿足理論,可見他完全有可能把對她的憧憬轉移到別的女性身上,他甚至可以在和別的女性親熱時腦子里想著她。她就是我,陳慧,哈哈……
她沒再哈哈下去,因為我給了她一巴掌。我痛苦地意識到,這是我們成為戀人以來我第一次動粗,準確地說,是我們認識以來。
我向她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她兩天沒理我,夜里與我背對背睡覺。這兩天她也喪失了在陽臺上表演的興致,洗衣服、澆花、拖地啥的都是潦草應付。兩天后迎來了雙休日,我建議出去走走,比如去神仙居景區(qū)。她同意了,她老早就想去神仙居。神仙居在天成市的神仙縣,兩個小時車程。周六晚上我們住在縣城的萬豪大酒店,總算重歸于好,標志事件就是進行了某方面的深度交流。這使得第二天我們以幾乎從未有過的愉悅心情游覽了神仙居的美好風景。
從神仙居回來,她主動向我提議,再度把自己隱匿起來。我想都沒想就同意了。
我擔心的事情發(fā)生了,幾天之后劉總就變得失魂落魄。我列席總經理辦公會議,只負責記錄,沒發(fā)言權。劉總表現(xiàn)異常,某個議題上他搶先發(fā)言,搞得其他副總無所適從。按規(guī)矩他不能先發(fā)言定調子,以免先入為主。另外一個議題上他一言不發(fā)。副總們發(fā)表意見后,需要他總結,他一言不發(fā)是啥意思呢,莫非下次再議?常務副總不得不提醒他,劉總你總結一下。他這才把思緒從天上拽回來。還有一個議題,他中途插話,打斷了某個副總的正常發(fā)言,搞得后者茫然不知所措,以為自己哪里說錯了……
回家后我和陳慧商量怎么辦。
你說呢?她把皮球踢回來。
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見嗎?我把皮球踢回去。
她笑嘻嘻地說,從你實地調研反饋過來的信息看,劉總一不嫖宿,二不受賄,這樣潔身自好的領導干部少見,如果他單身,我嫁給他算了,你龍永順反正也不愁娶不到老婆。
我實話實說,我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單身,要不,我明天請繆總到省公司人事處問問,領導干部每年都要向組織申報個人重大事項。
如果我嫁給他,就給他吹枕邊風,讓他在任期內提拔你兩次,把你弄成市公司最年輕的中層正職。
行,那你打算跟他明說,是我把你奉獻出去的?
你傻啊,我就說你是我親戚,要等到水到渠成才能說。
這個好辦,既然你是我親戚,我明天就帶你去見他,他住7幢803。
你傻啊,只要我想認識他,還不是易如反掌。
說來聽聽。
他晚上回來后是一直窩在家里,還是偶爾會下樓在小區(qū)散步?
按照常理推斷和我們的觀察得知,他應該偶爾會下去散步。
那行,我特意穿上高跟鞋,裝作不小心崴了腳,倒在他面前……不出幾天,我就能幫你了解他的底細。
什么底細?
他是單身呢,還是夫妻關系不好。
我粗了聲音,不許你操勞,想了解這個我自有辦法。
你不是不好意思麻煩繆總嗎?
那也無需你使苦肉計。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怎么,你不想趁年輕盡快提拔?
我想,但是……
你舍不得犧牲一個不是你老婆的女孩子?天涯何處無……
我舍不得!
我緊緊把她摟在懷里,好像她明天真的會一頭栽倒在劉總面前一樣。她蜷縮在我懷里渾身顫抖,顯然,她與我一樣也動了真情。孩子啊狼啊什么的,逞口舌之快而已,否則不是明顯違背我們搬到東浦錦園、從而把劉總置于眼皮底下的初衷了嗎?只可惜節(jié)外生枝,劉總愛上了這個陽臺上的女孩兒。
有些話是真不能說,說了就無可挽回。盡管我們都裝作無事人一樣,但彼此心里都明白,愛情的溫柔稻田里已埋下了硬疙瘩。
七月上旬,省公司召開半年度工作例會,允許各市公司總經理帶一名助理與會。我陪劉總去了南州。本來這差事輪不到我,繆總在任時帶的都是金主任。足見劉總對我的器重。
我們坐動車,兩個小時。如果老瞿開車起碼四個小時。
前天報到,會期兩天,今天下午是務虛會,只有省公司領導和各市公司主要領導與會。我得以脫身,劉總前腳剛進會議室,我就直奔綜合業(yè)務四處。十八大后,各級公司會議均放在單位內部會議室,除早餐外吃飯也都安排在單位食堂,倒也便利。當然沒辦法在單位內部住宿,我們這次就住在省公司附近的梅地亞大酒店。
我來南州之前就和繆總打過招呼,但在劉總眼皮底下不敢動彈。這個下午是最后機會。
寒暄過后,繆總問我怎么樣。我實話實說,并感謝他在劉總面前替我美言。我后悔近半年來都沒向繆總通報情況。
這個也屬正常,繆總說,劉總需要考察人選,而你最終勝出。
我感慨地說,劉總一心撲在工作上,很少顧家。
他顧什么家,去新州赴任前就妻離子散了。
我吃驚得半天合不攏嘴,盡管這種可能性我早已料到,可事實擺在眼前,還是猶如走夜路遇見鬼。在我的觀念里,領導輕易不離婚,哪個仕途上混得風生水起的領導沒有一個穩(wěn)固的后院?可見劉總是個異類。
小龍啊,我也是回到省公司后才知道這事,他是去年上半年離的婚,女兒跟了前妻,無牽無掛。于是去年下半年省公司黨建工作領導小組在正處級干部中物色各巡察組組長時,他主動報名出征。對他來說,去哪里巡察不要緊,只是恰好分配去了新州。
他并不是沖著您去的。
前后聯(lián)想,我想只可能是這樣,一開始他只是想暫時離開南州這個傷心之地,巡察不是整整一個月嗎?可后來他的想法變了。
什么想法變了?我有點兒聽明白了,裝懵懂,虛心請教。
他想長久離開南州,巡察是個好機會,完全可以借題發(fā)揮,而我正好撞在他槍口上。
我提醒說,他偶爾也回南州。
他是土生土長的南州人,父母在,也要看望女兒,她女兒應該還在念高中。
我用不帶感情色彩的語氣說,劉總還年輕,可以考慮再娶。
怎么,他在那邊有對象了?繆總果然來了興趣。
沒有。我矢口否認,見繆總有些失落,便補充說,其實我不知道具體情況,雖是跟班秘書,但也不是總在一起。
繆總察言觀色,斷定我不想多說,便不勉強。只說,晚上不回去的話,我請你吃個飯,你就和他說南大的老同學請吃飯。
下午務虛會一結束,我和劉總就馬上打車去東站,車票我已經買好了。
我向繆總告辭出來,先行回酒店打點行裝。劉總進會場前已把房卡交給我,我得把他的行裝一起收拾好。他會在會議即將結束時給我發(fā)信息,我再下樓退房,拖著兩個小拉桿箱去省公司一樓大廳候著他。這些都是跟班秘書的分內之事。我很高興看到劉總神奇地從困境中走了出來,一個多月來狀態(tài)正常,無論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中。他顯然已從一場海市蜃樓般的夢境里幡然醒悟。不是他的菜就不是他的菜,他畢竟是個事業(yè)型男人,職場上還有上升空間,犯不著為一場無望的單相思葬送大好前程。之前的異常狀態(tài)只不過是偶感風寒,打一個噴嚏便見煙消云散,康復如初。
我和陳慧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玩笑后,她繼續(xù)保持隱匿狀態(tài)。劉總即便再怎么仰望,也輕易不會看到在陽臺上活動的她,偶爾運氣好看見一回,也不是先前那樣顯山露水的她。她在昏暗的陽臺上腳步匆匆,做著一些必須要做的活兒,全然沒有了表演興致。我自然持續(xù)向她通報劉總的信息,她一臉淡然,完全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嘴臉。我們心照不宣地放棄了搜集劉總可能存在不軌素材的行動,提都懶得提了,好似那根本不曾發(fā)生過。我認為我們依然親密無間,就像從沒發(fā)生過啥齟齬。只不過那是我一廂情愿的錯覺。我倒是再次提議過搬出東浦錦園,在它北面的瑞興園另租一個套房,但她也不為所動,說搬家麻煩,過一天算一天唄。聯(lián)想到她滿懷熱情地從蘆浦大廈搬家到東浦錦園,我只覺得好笑。我搬家的意愿也不是很強烈,此事便不了了之。但她凡事均漠然處之的態(tài)度也令我莫名驚詫,就像活潑可愛的小女孩兒眨眼間變成了安靜恬淡的大姑娘,我找不到緣由所在。我忘了那句話,驚濤駭浪往往潛伏在平靜水面下。
總而言之,無需再為劉總的單相思操心,陳慧也看似安分守己,說實話我對現(xiàn)狀很滿意。我甚至不愿回首給劉總上手段的初衷。
我和劉總在動車上吃盒飯。一個盒飯六十元,我們都沒浪費,飯菜吃了個精光。我把兩個空飯盒送去兩節(jié)車廂之間的內置垃圾桶扔掉,又把他的茶杯拿去倒?jié)M開水。
小龍,你今年三十,我今年四十三。你是不是因為我見不到陽臺上的女孩兒心里難受而吃驚?我一度很難受,這讓你很吃驚,是不是?
他突然起這個話頭,讓我無所適從。我想說您作為單身男人,看見順眼的女孩子心生愛慕,屬人之常情。但我只是翕動嘴巴,啥都沒說出口。
人過了四十,不僅身體感覺不一樣,心態(tài)也會不一樣。比起你,我是老了,大你一輪都不止,但我還是會被某一類女孩子吸引,我說不清是什么類型的女孩子,但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又怎么會否認呢……與其否認,不如坦然應對,勇敢接受。你說對嗎?
我想表示贊同,卻總覺得如鯁在喉,最終只費勁兒地舔了舔嘴角。
陽臺上的女孩兒總有一天會來到結實的地面上。
我還是不明所以,只木然點頭。
省公司主要領導在大會上的講話稿估計還要結合脫稿內容修訂,過幾天才能印發(fā)下去,明天你抓緊整理一下,我要第一時間在全市系統(tǒng)傳達貫徹。他如是總結,結束了短暫談話。
老瞿去新州動車站接我們,到東浦錦園時已過九點。我提議送他到樓上,幫他拖拉桿箱,他卻說你以為我殘廢啊,連這點兒小事都做不了嗎?
我在小區(qū)北門下車,看著老瞿的車子一溜煙消失在夜幕中,腦子里掠過“小別勝新婚”,這使得我回家的步伐鏗鏘有力。
打開1004的門,里面卻是漆黑一團。陳慧知道我今晚到家,應該是有啥急事臨時出去了,也或許在單位加班尚未回家。
接下來的幾分鐘里,我確認了一個事實。她把屬于她自己的、能帶走的全帶走了。屬于我們共同的生活用品,她慷慨地一樣都沒拿走。她還把家里打掃得干干凈凈,足以抹去曾經有個女孩兒在這里生活過的一切痕跡,可見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責任編輯/吳賀佳
插圖/子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