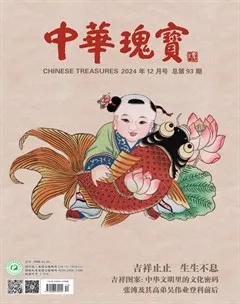《琴操》、琴操與\"琴操\"




琴操的本義是琴曲,在《琴操》著作及其衍生的文學(xué)作品之外,歷史中也有琴操其人的傳說。
琴曲匯總著作
“琴操”之名,最早出現(xiàn)在漢代。《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有東漢桓譚《琴操》二卷,但因《后漢書·桓譚傳》《隋書·經(jīng)籍志》都未載錄,東漢桓譚著《琴操》的真實性引起了學(xué)術(shù)界的質(zhì)疑。其后蔡邕著《琴操》,曾被唐代李善所著《文選注》、徐堅等所編《初學(xué)記》和宋代的《太平御覽》等征引,流傳至今,存有對“五曲”“十二操”“九引”的解題。《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等唐宋書目又著錄有晉人孔衍所著《琴操》,《初學(xué)記》曾有征引,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用《中興館閣書目》對此書的解題:“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diào)《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可見《琴操》一書到南宋還有流傳。《后漢書·曹褒傳》李賢注稱:“操,猶曲也。”并引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zāi)害不失其操也。”“操”即曲之意。《文心雕龍·知音》稱“操千曲而后曉聲”,其中“操”取動詞義,“琴”則是曲的物質(zhì)載體。“琴操”之為書名,取其本義,即為琴曲之意,《琴操》即匯總琴曲并對其進行解釋的著作。
蔡邕所著《琴操》包含曲、操、引等多種文體,其中的“十二操”篇名,分別是《將歸操》《猗蘭操》《龜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雉朝飛操》《別鶴操》《殘形操》《水仙操》《列女操》。因《琴操》同時是一部匯總琴曲的書籍,故在后世還有模擬這些古曲名而進行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復(fù)取“琴操”之名,故相關(guān)創(chuàng)作也聚焦在操名。唐代韓愈作有《琴操》十首,相較蔡邕所述,保留前十篇而刪去《水仙操》《列女操》。其后如宋代曹勛作有《琴操》十首,元代楊維楨作有《琴操》十一首,王逢作有《孔子琴操》七首、《顏子琴操》一首、《吳季子琴操》一首、《衛(wèi)女琴操》一首,明代朱右作有《廣琴操》十首,王祎作有《古琴操》二首,清代邊連寶作有《琴操》十首,等等。其他單篇操名的擬作更多,展現(xiàn)出“琴操”主題強盛的文學(xué)生命力。
琴操其人
在著作與衍生的文學(xué)作品之外,在歷史中也有琴操其人的傳說。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記錄了杭州歌妓琴操將秦少游《滿庭芳》改韻的故事,重新?lián)Q字用韻,意境竟不輸秦觀原作。蘇軾聽聞琴操改韻之事后,十分欣賞其才華。等到蘇軾在杭州,有一日與琴操游賞西湖,便與她打禪機,以己作和尚,讓琴操發(fā)問參悟。琴操與蘇軾的問答,既有情景之應(yīng),也因最后的“究竟如何”而頗具佛禪的味道。蘇、琴的一番問答十分精妙,聰慧的琴操由此頓悟而出家。后世如《事類備要》引稱“妓學(xué)禪語”、《事文類聚》引稱“妓學(xué)問禪”,又宋人只稱琴操“善應(yīng)答”,明人則干脆稱琴操“頗通佛書”,都是從二人參問而作的引申。
琴操拋卻塵俗,雖出家為尼,還是躲不開世俗,免不了被人拿來繼續(xù)與蘇軾及其“朋友圈”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清代褚人獲《堅瓠集》乙集卷四“僧妓相譏”條稱:“蘇東坡與僧佛印、妓琴操每相往來,飲酒賡和。”明代陳汝元所作傳奇《金蓮記》記述,琴操與蘇軾之妾王朝云原為青樓姐妹,她在西湖上遇到蘇軾和佛印,琴操先前已有厭棄繁華之感,被蘇軾的三言兩語擾得心灰意冷,又被佛印言語影響,便生出家之意。“和尚對佳人”之類有污視聽的言語為小說家言,不可信也。
類似的故事在明代已有流傳,但主人公是佛印與蘇小妹而非琴操。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二四記載佛印和蘇小妹的舊傳對話,與《金蓮記》中佛印與琴操的對答內(nèi)容完全一致。馮夢龍與陳汝元為同時代人,可見當(dāng)時傳聞已有不同版本。褚人獲改“佳人”為“娘子”,襲用陳汝元的痕跡更為明顯。馮夢龍還對此條“舊傳”進行評價:“此乃后人好事者之為,公雖曠遠,印不應(yīng)直入臥闥也。”其也是對其取質(zhì)疑的態(tài)度。
據(jù)說,琴操死后還有墳塋存在。明人談遷《棗林雜俎》中集“琴操冢”條稱:“臨安縣玲瓏山琴操冢殘碣,東坡居士書,萬歷十七年被發(fā)。”其稱琴操墓碣為蘇軾所書。黃汝亨《寓林集》卷九《天目游記》記載,其登玲瓏山時曾見到琴操墓,稱琴操墓碑為許太胤書,也對琴操因附驥蘇軾而得以埋骨靈山表達了感慨。《玲瓏志》記載琴操墓按宋制規(guī)造,錢塘許太胤立碑于上,稱琴操“以其脫鉛華而皈禪悅?cè)耍嘤袘{而吊之者”。童守德《玲瓏山記》亦稱:“舊從蔓草中埋一墓,甕石鱗砌,大非今制,舊傳琴操墓,許玄稚信而題額。”可見從明代開始,杭州玲瓏山已有琴操墓,其墓碣先由蘇軾書寫,后由許太胤補題,但以“舊傳”而言,則亦疑而未定。
吳之鯨《武林梵志》卷六記載稱,玲瓏山大雄殿內(nèi)造有蘇軾、黃庭堅、佛印之像,寺旁則有琴操之墓,加以南宋已有的蘇軾、琴操故事,也給好事者留下了無盡的想象空間。其他如明代李應(yīng)征、清代楊琳、近代徐映璞等均作游記來記載琴操墓,明代鄭日近、馮夢禎、張元芳、邵穆生、俞景寅,清代魏述祖、俞瑗及近代陳三立、葉淺予等有哀吊詩作,形成了以“琴操墓”為主題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
1934年3月29日,郁達夫與潘光旦、林語堂三人同游玲瓏山琴操墓,郁達夫作《玲瓏山寺琴操墓前翻閱新舊〈臨安縣志〉,都不見琴操事跡,但云墓在寺東》詩:“山既玲瓏水亦清,東坡曾此訪云英。如何八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郁達夫認(rèn)為琴操、蘇軾之事屬實,還為《臨安縣志》未載琴操情事而憤憤不平,翻為古人抒其憤懣。
琴操其人真實性存疑
然而,琴操真的曾存在過嗎?至少,蘇軾的筆下并沒有出現(xiàn)過琴操其人。有關(guān)琴操及其與蘇軾的互動,最早是南宋高宗紹興年間吳曾《能改齋漫錄》的記載,雖距離蘇軾不遠,但其真實性仍存疑。《事類備要》《事文類聚》引述琴操、蘇軾對問事則稱出自《泊宅編》,其作者方勺與蘇軾處同一時期,今存《泊宅編》中多記蘇軾之事,但此書的各種版本中并未見到與琴操有關(guān)的文字。至于明代而有的琴操墓,以及琴操與佛印的關(guān)聯(lián)故事,則更多是建立在吳曾所著內(nèi)容基礎(chǔ)上而進行的敷衍。至少可以認(rèn)為,琴操其人的存在是可質(zhì)疑的,尤其是琴操之名與《琴操》著作及其衍生的文學(xué)作品的名稱相同,琴操改韻也與音樂相關(guān),因此琴操其人更有可能是衍生出的人物。故孔凡禮作《蘇軾年譜》《三蘇年譜》,雖于元祐六年(1091年)有“守杭,嘗與琴操諧謔”一條,但在征引《能改齋漫錄》后仍稱“頗有傳聞因素”,可見其審慎態(tài)度。
如果琴操其人并不存在,其又是如何與蘇軾、佛印這些名人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的呢?據(jù)考證,蘇軾作有《琴操·醉翁引》,又寫有《琴操》書法,曾經(jīng)刻石,并存拓本。南宋王象之《輿地紀(jì)勝》卷二五“崔閑”條載:“字誠老,星子人,結(jié)廬于玉澗兩山之間,自謂玉澗道人,東坡過之,為書《琴操》云。”根據(jù)蘇軾自跋,可知其《琴操》創(chuàng)作的因由。歐陽修謫守滁州時曾建醉翁亭并作《醉翁亭記》,后太常博士沈遵為其作《醉翁引》曲。歐陽修與沈遵卒后,沈遵門客崔閑請?zhí)K軾作詞,以補其缺,蘇軾即作《醉翁引》詞,然后聲、詞皆備。蘇軾好友黃庭堅亦作《跋子瞻〈醉翁操〉》稱:“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
除為蘇軾《醉翁操》作跋外,黃庭堅也曾書寫過《琴操》。《輿地紀(jì)勝》卷一五三“偶住亭”條載:“在江安縣之對。建中初,山谷自僰道還,過邑宰石諒,同游此亭,書《琴操》。”清人郭嵩燾曾見到黃庭堅書《琴操》之跋。
郭嵩燾所稱黃庭堅跋,其全文為:“予舊得東坡所作《醉翁操》善本,嘗對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嘗從成都通判陳君頎得其譜。’遂促琴彈之,詞與聲相得也,蜀人由是有《醉翁操》。然詞中之微旨,弦外之余韻,俗指塵耳豈易得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書。”據(jù)此,可知蘇軾、黃庭堅均曾書寫過《琴操》。蘇軾所書寫即其《醉翁操》一首,黃庭堅所見當(dāng)即蘇軾手書或其拓本,后來又有仿書。這里的《琴操》,具體指向蘇軾所作《醉翁操》。
至于佛印與琴操的關(guān)聯(lián),則當(dāng)是因蘇軾故事連帶所及,因蘇軾與佛印交游,逸聞頗多,又將馮夢龍記載“舊傳”中的佛印與蘇小妹故事置換為琴操,形成故事模塊的拼接,又如明代劉榮嗣《簡齋先生文選》卷二《與范質(zhì)公》書稱:“賴有佛印在,琴操不俗耳。”而佛印與琴操也成為公案中某類特定人群的代稱,明代律法如《鐫大明龍頭便讀新例律法全書》卷七“居喪及僧道犯奸”條判語稱:“豈德裕之患病,侍擁女奴;抑佛印之風(fēng)流,點悟琴操。”《新刻御頒新例三臺明律招判正宗》卷三“僧道取妻”條判語稱:“駕言佛印,曾高琴操風(fēng)流;假口純陽,亦為牡丹樂事。”即徑以佛印、琴操代指僧、妓。又稱佛印點悟琴操,仍是受到明代傳奇《金蓮記》之類的影響。
可以說,作為人名的琴操最早見于南宋吳曾所著的《能改齋漫錄》,并與蘇軾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相關(guān)故事在后世不斷被敷衍,但其真實性仍值得懷疑。最大的可能性是,因為蘇軾曾創(chuàng)作《琴操》,又在杭州做官,并與歌舞妓王朝云產(chǎn)生過愛情故事,吳曾遂據(jù)《琴操》而偽造名妓“琴操”之名,為蘇軾的情感生活再添內(nèi)容。這一故事又被好事者不斷以訛傳訛,至于明代借助筆記、傳奇而達到鼎盛。又因杭州玲瓏山上舊有蘇軾、佛印等名人游覽遺跡,進而更相附會,乃至于出現(xiàn)琴操墓碑,并遺留至今。但此純?yōu)橥茰y,無從證真,也無從證偽。無論如何,因為吳曾所著《能改齋漫錄》的內(nèi)容,琴操最終與蘇軾產(chǎn)生了不可分割的關(guān)聯(lián)。而在陳汝元所著的《金蓮記》中,琴操又被佛印影響,從宋人筆下身具才情的女性,一變而為明代世俗享樂的象征,并在律法中成為特定人群的代稱。又因《金蓮記》中對琴操、蘇軾、佛印等人物交往的細節(jié)書寫,后世對于琴操身世經(jīng)歷的各種想象與考據(jù),也就大多源于陳汝元之傳奇。
盡管宋代杭州歌伎琴操的“進入歷史”是一個由《琴操》而引起的美麗的“誤會”,但還是為中國雅俗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母題和素材。
從《琴操》到琴操再到“琴操”,從著述、文學(xué)到人物,再到人物和文學(xué)的再造,內(nèi)容不斷被重塑,琴操的形象也從純粹的雅文學(xué)一路向下兼容,直到純粹的俗文化。明代以降一直到當(dāng)下,“琴操”早已不是宋代的琴操,甚至宋代的琴操是否真實存在過也都無法確認(rèn)。但是,借助《能改齋漫錄》之類的著作、《金蓮記》之類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一些影像改編,“琴操”終究還是以文學(xué)和影像的形式存留了下來,進而產(chǎn)生了新的影響。這對于琴操而言,未嘗不是一種幸運。
翟新明,湖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