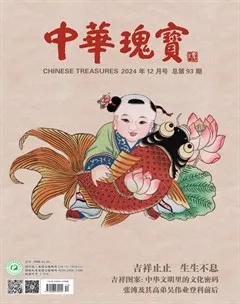張溥及其高弟吳偉業(yè)登科前后




張溥有『江南士林領袖』『東南壇坫主盟』之譽,在晚明黨社、學術及文學方面兼領一時風氣,頗具影響。在吳偉業(yè)的成才之路上,張溥的熱情賞識與悉心教導起到了重要作用。
張溥(1602—1641年),字天如,號西銘,明南直隸蘇州太倉(今江蘇省蘇州市太倉市)人,復社主盟、著名學者、文學家,有“江南士林領袖”“東南壇坫主盟”之譽,在晚明黨社、學術及文學方面兼領一時風氣,頗具影響。其高弟吳偉業(yè)(1609—1672年),字駿公,號梅村,為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詩歌成就尤為突出,開創(chuàng)婁東詩派,其詩有“梅村體”之稱,與錢謙益、龔鼎孳并稱“江左三大家”,在明清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吳偉業(yè)生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在明代生活三十五年。其青少年時期,尤其是登科前后,與乃師張溥交游密切,受到張溥的諸多影響。
張溥早年行跡
張溥年長吳偉業(yè)七歲,收吳偉業(yè)為弟子約在天啟五年(1625年)。在此之前,二人雖然同處太倉西城,人生軌跡卻各不相同。張溥因為是庶出(其父與婢女所生),在大家庭內(nèi)受官至工部尚書的大伯張輔之家奴多次凌辱。少年張溥忍無可忍,憤而在墻壁上血書“不報仇奴,非人子也”。欺辱他的家奴知道后,輕蔑大笑:“塌蒲屨兒,何能為!”(陸世儀《復社紀略》)意思是,一個賤人生的庶子能有什么作為呢!受此刺激,張溥夜以繼日發(fā)奮苦讀,凡所讀書皆認真抄寫一遍,再高聲朗讀一遍,然后燒掉,再抄、再讀,如此重復七遍。其書齋名為“七錄齋”,正是其勤學苦學的見證。張溥后來以學問淵博和富有氣節(jié)著稱,與這一段遭受欺辱、發(fā)奮苦讀的經(jīng)歷有很大關系。
張溥十六歲時,父親病逝。少年喪父,本是人生的至痛,又因身處復雜的大家庭,其間的家庭糾葛更是令人傷感寒心。于是,張溥奉母金氏搬出大家庭,居住在太倉城西郊一處陋室,潛心向?qū)W。這一時期,張溥結(jié)識了住在太倉南郊的張采,成為生死之交。后來,二人影響日巨,并稱“婁東二張”。
“二張”均少年喪父,以勤學著稱,志在大儒。張溥邀請張采到“七錄齋”共讀五年。在這期間,“二張”一方面準備時文,以應對科舉;另一方面著意研讀經(jīng)史,廣覓同道。天啟三年(1623年)冬,“二張”前往金沙(今江蘇省南通市中部)拜訪著名時文選家周鐘。三人相談甚歡,最終達成以經(jīng)史厚殖學問的共識。次年冬,“二張”又去常熟拜訪楊彝、顧夢麟。因?qū)W術旨趣相近,他們聯(lián)合楊彝、顧夢麟、周鐘、楊廷樞、朱隗、王啟榮、周銓、吳昌時、錢栴創(chuàng)立應社,每人分治一經(jīng),眾人合治五經(jīng)。張溥此時名聲漸起,影響日大。
吳偉業(yè)投師張溥
吳偉業(yè)祖上原居昆山,為昆山名族。然而至其祖父吳議時,家道中落,遷居太倉,入贅于太倉瑯琊王氏。其父吳琨,字禹玉,號約齋,能文章,但多次科考不中,便以教學課徒為生。吳偉業(yè)少富才華,隨父在外坐館讀書,不斷提升學養(yǎng)。
約天啟五年(1625年),吳偉業(yè)投師張溥。當時,張溥創(chuàng)立應社,與江西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艾南英等組織的豫章大社和山東宋玫兄弟組織的萊陽社鼎足而立,頗具影響。年輕學子也樂以文章投師其下,請其指導。其時,嘉定有一富家子弟,竊取吳偉業(yè)多篇文章冒充己作獻于張溥。張溥讀后頗為欣賞,后來得知為吳偉業(yè)所作,于是主動邀請其在門下學習(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恰逢此時,與吳琨同在王家坐館的李明睿因宴會瑣事與東家發(fā)生口角,于是負氣離開。吳琨前來相送,并慷慨解囊,資助路費。李明睿頗為感激,臨別時對吳琨說:“令郎是奇才,貴鄉(xiāng)后勁張溥正以古學振興東南,前景無量,何不讓令郎拜入其門下以得早售?”吳琨對張溥也頗有好感,于是讓吳偉業(yè)拜入其門下(程穆衡《婁東耆舊傳·吳偉業(yè)傳》)。張溥對吳偉業(yè)頗為激賞,認為其是“大賢之器,非徒顯文之流”(張溥《吳駿公稿序》),對其文章予以高度評價:“文章正印,其在子矣!”(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可以說,在吳偉業(yè)的成才之路上,其父作為啟蒙老師、李明睿的慧眼識人、張溥的熱情賞識與悉心教導均起到了關鍵作用。
張溥鄙薄一心只知時文的淺俗時風,主張加強經(jīng)史的學習,以通經(jīng)致用,通過改變學風來凈化社會風氣,以期將來務為有用。吳偉業(yè)在投師張溥之前也是厭棄俗儒之所為。師徒二人,治學宗旨一致,教學相長,俱有所獲。張溥以身示范,吳偉業(yè)心摹手追。張溥的勤學與治學精神,對吳偉業(yè)尤其富有激勵作用。
師徒雙雙高中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張溥和張采前往南京參加鄉(xiāng)試。張采中試,張溥落榜。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駕崩。八月二十四日,遺詔以信王朱由檢即皇位,以第二年為崇禎元年。崇禎以登極恩典,令每學選拔一人入京學習。張溥被選為恩貢,得以進入國子監(jiān)學習。
崇禎元年(1628年),吳偉業(yè)也考中生員。四月,張溥入京師國子監(jiān)學習,這時張采已考中進士。張溥廷對時得高等,更為崇禎新政所激勵,頗以振興學術為己任,大聲倡議:“尊遺經(jīng)、砭俗學,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黨乎!”(吳偉業(yè)《復社紀事》)于是“二張”召集參試士人舉行成均大會,并結(jié)燕臺社,一時名徹都下。
張溥回鄉(xiāng)送別張采赴任臨川后,又集合吳越間優(yōu)秀的年輕人,在吳江縣令熊開元、吳江大戶吳?的支持下又建立復社,明確以“興復古學,務為有用”相標榜,在其學術精神上實也寓“復東林”(唐文治《張?zhí)烊缦壬z像記》)之意。其高弟吳偉業(yè)成為復社骨干成員,以至后來有好事者一度將張溥比擬為孔夫子,將吳偉業(yè)比為“十哲”之一。
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詔定逆案,消除魏黨殘余,朝政一新,正氣與革新的氣息彌漫于朝野之中。胸懷大志的年輕士子更加熱衷于研讀經(jīng)典和討論時文,準備大顯身手。在此熱烈氛圍下,張溥因勢利導,通過其卓越的組織統(tǒng)籌,將十五個地區(qū)的十七家社團統(tǒng)合到復社,此乃文壇曠古未有之事。這既為眾多年輕士子切磋交流提供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平臺,也通過文章的選集、評點、標榜而擴大了其影響和聲譽,為其接下來考中科舉奠定了學養(yǎng)和人氣的雙重基礎。
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鄉(xiāng)試,張溥和吳偉業(yè)師徒二人雙雙高中。鄉(xiāng)試后,張溥又組織前來參加鄉(xiāng)試的復社舉子近兩千人召開了金陵大會,匯聚其文為《國門廣業(yè)》。張溥和吳偉業(yè)儼然成為這次大會的焦點人物,也成為眾人眼中明年會試高中的熱門人選。
次年二月,張溥和吳偉業(yè)至京師參加會試。在會試前半個月,張溥與吳偉業(yè)、陳子龍、楊廷樞等九人又成立日社,切磋制藝,每人作文十至二十余篇,并擬刻《九子社義》,以記一時鳴和之樂(張溥《楊伯祥稿序》)。
此年會試主考由首輔周延儒、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何如寵擔任。按照慣例,以往由次輔擔任主考。但首輔周延儒這次親自下場,既為國家選拔人才,又為自己招攬門生,擴大其勢力與影響。這當然引起了次輔溫體仁的不滿和攻訐(陸世儀《復社紀略》)。張溥、吳偉業(yè)及復社后來與溫體仁的矛盾,也與此有關。
在會試中,張溥和吳偉業(yè)所選本經(jīng)都為《易經(jīng)》。張溥出于《易》一房楊世芳門下,吳偉業(yè)出于《易》三房李明睿門下。吳偉業(yè)高中會元,張溥為會魁,名列第八名。據(jù)陸世儀《復社紀略》所載,吳偉業(yè)能高中會元,除了自身高才外,自然也有人情因素。原來,其座師首輔周延儒為諸生時,路過婁東,與吳偉業(yè)之父吳琨相善,房師李明睿則與吳偉業(yè)之父吳琨有共同坐館、詩酒唱和、慷慨相助的雅誼。周延儒意在收羅名宿,于是授意各位房師在交卷前,悄悄打開中式封號以確認姓名。李明睿因此確定吳偉業(yè)為本房頭卷,周延儒也很高興其為故人之子,擬定其為會元。溫體仁授意黨羽薛國觀將此事泄露于朝廷,御史袁鯨準備上疏參論。情急之下,周延儒將會元卷進呈御覽。崇禎皇帝閱后,在卷首書寫“正大博雅,足式詭靡”八字,一時輿論才得以平息。
其后殿試,吳偉業(yè)高中榜眼,張溥為三甲第一名,一時傳為佳話,天下爭傳二人文章,推敲模仿(張采《治婁文事序》)。殿試后,吳偉業(yè)授翰林院編修,張溥選翰林院庶吉士。此時又發(fā)生了一個插曲。按照慣例,新進士的刻稿一般請房師作序,吳偉業(yè)的會元刻稿竟以“天如先生鑒定”的名義出版,這實際也是張溥影響力的一個側(cè)證。李明睿知道后大為光火。于是同館兼張溥妻弟王啟榮連襟的徐汧帶領吳偉業(yè)前來請罪,并將此事推諉給書肆。盡管此事以此了結(jié),但李明睿心中對張溥大為不滿。另外,瓊林宴排座次一事,也可看出張溥的影響。瓊林宴上,新進士的座位一般按考試名次排序,吳偉業(yè)雖為會元、榜眼,但不敢坐在老師張溥之上,于是皇帝下旨“張溥坐會元之上”,這可謂科舉史上的“盛事亦奇事”(陸世儀《復社紀略》附錄)。此時,周延儒作為座師,對門生張溥大為欣賞,恩禮倍至,既推薦張溥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又令其撰寫《進士題名記》。
中進士后
吳偉業(yè)中進士前一心學文,不曾作詩。此期中進士后,因為交游酬贈,于是先向張溥學習作詩,并受其激發(fā),開始講求詩歌創(chuàng)作。清乾隆《鎮(zhèn)洋縣志》卷十四《雜綴類》記載:“王中翰昊述吳梅村語:“余初第時不知詩,而多求贈者,因轉(zhuǎn)乞吾師西銘。西銘一日漫題云:‘半夜挑燈夢伏羲。’異而問之,西銘曰:‘爾不知詩,何用索解。’因退而講聲韻之學。”
九月,吳偉業(yè)得皇帝賜假回鄉(xiāng)完婚,張溥作詩《送吳駿公歸娶》,為其贈行:“孝弟相成靜亦娛,遭逢偶爾未懸殊。人間好事皆歸子,日下清名不愧儒。富貴無忘家室始,圣賢可學友朋須。行時襆被猶衣錦,偏避金銀似我愚。”字里行間,既有調(diào)侃,也有羨慕,讀來頗有趣味。
此時的張溥春風得意,年輕氣盛,說話做事難免有孤傲和不盡老練之處。于是,本就心懷不滿的次輔溫體仁借機敲打:“庶吉士成材就留下,不成材就離開。”張溥對此毫不畏懼,反而針鋒相對,搜集溫體仁結(jié)黨營私諸事,寫成奏疏,授意吳偉業(yè)參劾。吳偉業(yè)考慮到立朝未久,不敢直接參劾溫體仁,于是將奏疏稍加調(diào)整,轉(zhuǎn)而參劾溫體仁的得力干將蔡奕琛。溫體仁勃然大怒,準備嚴厲處罰,幸得首輔周延儒從中調(diào)解。從此,溫體仁與蔡奕琛對張溥更是側(cè)目而視,房師李明睿又因會試刻稿事而不時督察責備于他。在這種充滿敵意與挑剔的政治氛圍下,張溥頗不自安,次年便以請假葬親之名回太倉,從此不再復出。
陸巖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