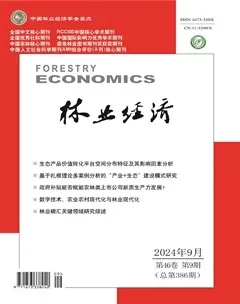數字技術、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林業現代化
















摘要: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數字技術是提升農業發展水平、增加農民收入和改善農村生活方式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13—2022 年我國省級層面數據,采用相關模型測度數字技術、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林業現代化,運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和空間效應模型相結合的方法實證檢驗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和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發現:(1)數字技術會顯著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且該結論通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2)數字技術會通過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來提升林業現代化發展水平;(3)數字技術會通過增強勞動生產率、提高產業結構發展水平,進而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4)在中部地區及經濟規模較大和電商規模較大的省份,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程度更大;(5)數字技術會通過技術溢出來促進周邊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且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趨勢相同。文章將研究視角聚焦于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豐富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相關理論,完善了數字技術的經濟效應研究。文章提出要加快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的應用,推動農業數字化轉型,加強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提供思路。
關鍵詞:數字技術;農業農村現代化;林業現代化;空間溢出效應
中圖分類號:TP399; F323; F3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338X(2024)9-055-23
1 引言
2023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加快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當前我國農業基礎差、底子薄、發展滯后,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仍是農業農村(李文,2023)。農業現代化是以現代科學技術、工業裝備、管理方法來武裝農業的過程(張小允等,2022)。黨的十八大提出農業現代化同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協同發展的“四化”之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林業現代化作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生態保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林業與自然生態系統本就血脈相連,作為大地的“綠肺”,調節氣候、凈化空氣,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動寫照。在農業發展的宏大版圖里,林業與農業更是相依相存,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鄉村發展的生態與經濟命脈。一方面,林業不僅為農業提供了生態屏障,阻擋風沙侵襲、涵養水源、調節氣候,保障了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與人力物力,也為林業的種植技術革新、經營管理輸送養分,二者攜手開啟聯合生產的新模式。總體而言,林業不僅為農業提供了生態屏障,保障了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還通過森林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創造了可觀的經濟價值,成為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從產業鏈角度看,林業產出的木材、林果等原料,能融入農業衍生的加工業,深化農產品附加值;反之,農業豐收后的秸稈等剩余物,也能為林業土壤改良、林下養殖提供助力,強化了二者的經濟紐帶,彰顯出林業和農業和諧共生的深層邏輯。
林業在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是國家重要公共事業和國民經濟的基礎,而且也是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鄉村振興發展視角下,林業生態修復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林業作為我國重要的自然資源,在生態保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林業經濟涵蓋了森林資源培育、木材生產、林產品加工、森林旅游等多個領域,是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林業經濟與農業經濟深度嵌套,做農村產業規劃時統籌二者布局,才能進一步催生新業態,促使農村經濟從“單一驅動”邁向“雙輪聯動”,進而全方位助力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多元化增長。
農村現代化要求農村經濟、文化、生態、環境、生活等各方面需統一協調發展,農村現代化是實現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二者相互融合,農業現代化是農村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農村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導向,二者相互促進、協同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21 年11 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導向、主要目標、重點任務和政策措施等作出全面安排,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數字技術推動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同時,也為優化生態環境、創建農村低碳生活、實現農業農村的林業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工業反哺農業一直是我國大力倡導的戰略方針,近年來,隨著我國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及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數字技術在各個領域的應用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劉鵬飛等,2022)。新時代應用數字技術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現、推動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的應用,成為加快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路徑。數字技術不僅能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推動農業資源整合利用、改進農業管理和服務、增強農業高質量發展(Klerkx et al., 2019;Ralandi et al., 2021;羅千峰等,2022),也有利于農民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質量、緩解農村相對貧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加快鄉村振興進程(溫濤等,2020;張衛東等,2022;陳飛等,2022;張旺等,2022)。
在國家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背景下,探討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二者的互動關系,不僅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助力農業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主題,也有助于了解數字技術帶來的農村經濟績效,可以為新發展階段下扎實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提供理論與實踐參考。據此,本文將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放入同一個分析框架,以期解決如下問題:數字技術是否會影響農業農村現代化?其作用機理是怎樣的?二者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數字技術在帶來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同時,是否會帶來其他的社會效應,如推動林業現代化發展等。
本文選取中國31 個省份為研究對象,首先,對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數字技術的相關文獻進行了回顧與評述,通過理論分析闡述其作用關系及影響機制;其次,構建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數字技術的指標評價體系,基于2013—2022 年各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相關模型測度數字技術、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林業現代化,運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和空間效應模型相結合的方法,實證檢驗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和空間溢出效應,并根據研究結果進行深入討論,提出相應的政策啟示。
本文可能的學術貢獻有三點:在研究方法上,創新性地將林業相關指標納入農業農村現代化體系,使用熵權-TOPSIS 模型對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進行測度;在研究內容上,構建了“數字技術—勞動生產率、產業結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理論分析框架,完善了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作用機制;在研究視角上,聚焦于數字技術、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林業現代化,彌補了現有領域關于三者之間關系研究的不足。
2 文獻回顧與評述
針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研究,學術界主要聚焦于內涵測度、現實路徑與水平測度等視角進行分析。盡管這些文獻廣泛深入地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展開了研究,但少有從數字技術視角切入,將農業現代化、農村現代化和農民現代化整合為農業農村現代化,對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關系展開深度分析。同時,本文梳理了數字技術與林業發展的相關研究。
2.1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及測度
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兩個基本方面,兩者之間相互聯系,農業現代化與生產力相連接,農村現代化與生產關系相連接,兩者相互促進,共同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魏后凱,2019;王兆華,2019)。陸益龍(2018)、孫賀等(2021)從綜合視角分析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認為必須把鄉村建設、城鄉一體化、促進農民增收與鄉村振興等納入農業農村現代化框架,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整體綜合性系統工程;葉興慶等(2021)從動態視角認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變化過程,內涵可以概括為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農民精神和生活質量、農村治理體系等的現代化。《“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在主要目標中明確提出,到2025 年,農業基礎更加穩固,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2035 年,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瞄準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建設、農業科技創新、鄉村建設、城鄉融合發展與國內國際市場統籌等戰略重點,應分別從“十四五”時期的“五位一體”和“國情農情”里的中國特色角度來確定農業農村現代化(高強等,2020;姜長云等,2021)。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實現產業現代化、地域現代化和人口現代化的融合發展,要采用新型舉國體制來推進“物”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治理現代化,一二三產業融合生產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社會學發展角度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王春光,2021;杜志熊,2021;孫德超等,2022)。
由于農業農村現代化提出概念時間不長,關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測度問題是基于對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指標體系的測度。覃誠等(2022)從農業現代化的6 個方面和農村現代化的5 個方面構建了一套評定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標體系,分析全國及各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基于某個特定區域或省份,構建適合該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特點的指標體系有:梁俊芬等(2022)從農業現代化、農村現代化、城鄉融合3 個維度構建了包括24 個指標的珠三角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分析珠三角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階段,探尋制約其發展的因素;何正燕等(2022)運用熵權-TOPSIS 模型和障礙度診斷模型,對2005—2019 年甘肅省14 個市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及其障礙因子的時間變化和空間差異進行測度;肖冰等(2021)從農業、經濟、環境、醫療、文教、治理、交通、生活等8 個方面,從影響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因素出發,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驅動力。
2.2 數字技術的經濟效應研究
數字技術是指利用現代計算機技術,把各種信息資源的傳統形式轉換成計算機能夠識別的語言數字的技術,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和5G技術等為表現形式。數字技術的相關研究主要表現數字技術帶來的經濟效應。從宏觀層面上看,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的基礎,數字技術與生產部門的整合助推了實體經濟轉型發展;數字技術通過提升傳統要素資源配置,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貿易交易質量,促進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分工(Acemoglu et al., 2018;王彬等,2021;任轉轉等,2022)。從中觀層面上看,數字技術的發展改變了眾多產業的發展模式,提升了產業融合水平,如傳統的文化、教育、旅游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等,提高了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Lee, 2009;Kleis et al., 2012;趙星等,2022)。從微觀層面上看,數字技術催生互聯網平臺商業模式的興起,微觀主體可以利用互聯網平臺建立自己的商業模式(Srinivasan et al., 2018);數字技術的可供性提升了企業創新價值強度,企業數字化水平的提升助推了企業新產品開發績效(溫湖煒等,2022;程聰等,2022)。
2.3 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研究
數字技術是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方式、推動鄉村振興的可行保證(唐慧敏,2022)。關于二者關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數字技術對農業生產經營的影響。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必要工具,數字技術可重構農業經營體系,數字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推動農業綠色發展,數字要素整體提升了農業產品價值(羅浚文等,2020;樊勝岳等,2021;陳衛洪等,2022)。二是數字技術對農民、農村的影響。數字技術的應用整體上提升了農民收入,緩解了農村的相對貧困,縮小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驅動了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提升了鄉村治理水平(Dunleavy et al., 2006;Asongu, 2015;唐文浩,2022;華中昱等,2022;樊軼俠等,2022);關于數字領域的某個方面帶來農業農村的變化,以數字普惠金融為例,其快速發展有效提高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力推動了農村產業融合,顯著促進了農戶增收,穩步推進了鄉村振興進程(張岳等,2021;唐建軍等,2022;陳亞軍,2022;張兵等,2022)。
2.4 數字技術對林業發展的影響研究
林業作為我國最大的綠色產業,是構成鄉村經濟的重要產業部門,農業農村現代化離不開林業高質量發展(王笑涵等,2020),數字經濟發展為林業產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持和要素保障。國外學者更多是分析數字技術在林業領域的應用,如智能林業在森林管理中的應用,借助森林圖(Forest Plot)技術對熱帶森林地塊數據進行匯總與可視化呈現(Gabriela et al., 2011;Florian et al., 2024);而國內更多研究數字相關領域對林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如數字普惠金融帶來的林戶收入及林業碳匯總量的影響(陳燦等,2022;王火根等,2023),以及數字經濟與林業經濟相互關系的研究(張瀚丹等,2023;翟郡等,2024)。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學者們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及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都展開較為豐富的研究,但側重在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某一個方面的研究,對整體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研究相對欠缺。為此,本文將研究視角聚焦于整體農業農村現代化,將林業相關指標納入農業農村現代化,從理論上分析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采用2013—2022 年全國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現實意義。同時,本文探究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影響的內在機理,分析數字技術通過技術溢出來推動周邊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此外,進一步分析發現,數字技術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后,區域的林業現代化有較為穩定的提升。
3 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為深入探究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影響機理,本文分別從數字技術對農業現代化、農村現代化和農民現代化三個視角展開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研究假設。
3.1 理論分析框架
數字技術主要通過提高生產效率、提升銷售規模和促進產業升級融合來作用農業現代化。首先,數字技術通過對農業生產需要的土地、水、肥料、資本等要素進行精準把控,降低了農業生產投入成本,同時由于對天氣和效益的準確預測,使農業生產效率得以提升(梁琳,2022)。其次,數字技術把以小農戶為經營主體的農產品,通過電子商務平臺的搭建,形成規模化效益,降低農產品銷售成本,提升銷售規模;數字技術使得農業公司得以進入,農業經營得到保障(Kansanga et al., 2019;李靜等,2022)。再次,數字技術促進生態產業的發展壯大,如發展智慧農業、構建數字化生態資源管理平臺,整合森林、土地、水資源等,推進林業治理現代化。最后,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互聯網及云計算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通過對農業種子的優選、農業資源數據要素的合理配置、農業生產過程的智能化管理,使農產品質量得以提升(管輝等,2022);數字技術把傳統農業與制造業、旅游業等產業相結合,實現農業在一二三產業中的融合,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升級,提升農業發展水平(王定祥等,2022)。
數字技術進步在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現代化進程。首先,數字技術通過挖掘農民需求,提升政府部門鄉村治理水平,提高農村公共服務質量,有力保障了農村現代化(陳弘等,2022)。其次,數字技術帶來的醫療、教育、衛生、金融及公共交通的變革,使得農村的生活居住環境得以現代化,農村居民可以通過數字化實現生活現代化。再次,數字技術改變了農村生態環境,數字技術通過產業融合和創新催生出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完善產業的網絡體系,減少傳統產業的能源消耗,降低污染,農村生態環境變得更好(韓晶等,2022)。最后,數字技術通過提高城鄉融合發展效率,加快農村的城鎮化進程,帶動農村現代化發展(Huttunen, 2019;王海艷等,2022)。
數字技術除了能改善農業生產經營、農村生活生態環境外,對農民實現現代化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首先,數字化經營提高了農民收入,且低收入群體顯著大于高收入群體,有助于緩解相對貧困(劉蕾等,2022)。其次,在社會階層的認同領域,數字技術使得農民社會階層認同感得以提升,農民整體素質得以提升,農民精神文明生活得到增強(彭艷玲等,2022)。最后,數字技術進步通過與金融、醫療衛生等領域相關企業的合作提升了農民整體生活質量,農民生活幸福感得到提高(封思賢等,2021)。總體來看,數字技術改變了農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農民現代化水平得到提升。
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已滲透到各個領域,林業現代化建設也迎來了全新的機遇與變革。數字技術通過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緊密結合,在林業資源管理、生產經營、產業升級以及生態保護等諸多方面全方位賦能林業現代化建設。一方面,數字技術通過技術共享與融合來助推林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中廣泛的衛星遙感、無人機監測可以應用到林業中,為林業資源精準管理提供支持,同時農業機械自動化技術啟發了林業機械智能化,提升林業生產效率;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建立的大數據平臺應用于林業時,能顯著提升森林資源監測能力,同時借助數據挖掘技術可以合理安排森林撫育和采伐時間,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此外,農村電商銷售渠道的完善也能提升林產品市場競爭力,促進林業現代化發展。
依據理論分析,本文構建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影響的作用機理,如圖1 所示,并提出假設H1。
H1:數字技術能正向影響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數字技術在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同時,也能提高林業現代化發展水平。
3.2 中介效應
長期以來,影響農業農村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水平不合理和勞動生產率低下。
數字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為鄉村產業帶來了新的技術范式和發展模式,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的應用,推動了農業產業的升級與創新,鄉村產業結構得以升級(錢明輝等,2021)。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和數據的核心功能,既能推動傳統產業的升級融合,也能重構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等全產業體系,提高農業經營效率(王定祥等,2023)。而產業升級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的農業生產現代化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產業基礎和物質保障,農業產業結構的現代化要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蔣永穆等,2024)。數字技術會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來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
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緩解了農業生產的內轉化(程名望等,2015),農業勞動力的“大齡化”問題正逐步顯現。手機、計算機及互聯網的使用顯著提高了土地和勞動生產率,改善了農業生產技術(Issahaku et al., 2018)。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的技術范式,有著強滲透性、廣覆蓋性和高協調性,能夠改善農業技術效率、促進農業技術的進步和推廣、創新農業發展模式(史常亮,2024),使得農業要素配置得以進一步優化,農民素質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而農業勞動生產率是衡量一個國家農業強與不強的重要指標,囊括了具體的農業現代化指標。數字技術的發展為農村勞動生產率注入了新活力,提升了整體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設H2。
H2:數字技術會通過提升產業結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來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
3.3 研究方法
根據理論分析框架,數字技術會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為此,本文首先參照已有研究及數據的可得性,選擇熵權-TOPSIS 模型對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進行測度,同時利用熵權法測度各區域數字技術水平;其次,根據理論分析構建面板固定效應模型,探究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產業結構和勞動生產率在二者之間的作用機理;最后,采用空間杜賓模型(Spatial DurbinModel, SDM)分析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空間溢出效應。
為分析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模型設定如式(1)所示。
4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基于理論分析,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本文以中國31 個省份為樣本數據,結合學界關于農業農村現代化構建指標體系,加入林業相關指標,再對相應指標進行處理,測度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同時借鑒已有研究測度林業現代化,對相關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
4.1 數據來源
為保證數據的可取性、客觀性和科學性,本文選取中國31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地區)2013—2022 年共10 年的面板數據。所有數字技術相關數據均來源于《各省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大為專利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農業農村現代化相關數據部分來源于農業農村部、商務部、《農村統計年鑒》、《中國金融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及各省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字技術水平部分指標數字技術專利申請量來源于大為數據庫,數字金融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各城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報告。
需要說明的是:金融科技指數的數據根據《“十四五”國家科學技術普及發展規劃》《“十四五”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21)》以及相關重要新聞、會議,從中提取出與金融科技相關的關鍵詞,然后將這些關鍵詞與中國的省級行政單位進行匹配;接著,在百度新聞的高級檢索中,按年份搜索每個省份與其匹配的關鍵詞,例如搜索“北京+5G”,利用爬蟲技術爬取百度新聞網頁的源代碼,并提取出該搜索結果的數量,然后將同一省份中所有關鍵詞的數量加總,得到總搜索量,作為金融科技發展指數的衡量標準。
4.2 變量選取
本文主要研究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作用機制,分別介紹各變量的度量指標構建及測度。
(1)被解釋變量:農業農村現代化(MARA)。本文在收集大量文獻資料,參考國務院印發的《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 年)》《“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借鑒錢佰慧等(2021)、何正燕等(2022)、覃誠等(2022)對農業現代化研究的基礎上,立足新時代下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內涵及特征,遵循指標設計的科學性、客觀性、系統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以農業農村現代化為目標層,以農業現代化、農村現代化、農民現代化為系統層,以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產出體系、支出保障、生態建設、基礎設施、生態文明、社會治理、物質保障、生活品質、文化素養為準則層,將上述準則層拆分為35 個指標,以此構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指標體系。同時,為了體現農業農村發展的可持續性、包容性和高效性,從林業經濟的視角出發,將森林覆蓋率和林業產業總產值納入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指標體系中,豐富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物質保障的內涵。森林覆蓋率直接反映了農業農村發展中對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程度及生態環境的健康狀況;林業產業總產值,則是從林業經濟的角度出發,評估其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通過對林業產業總產值的深入分析,可以進一步探索林業資源高效利用的路徑,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雙贏局面。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由于影響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因素眾多,為避免指標權重構建的主觀性,本文采用熵權-TOPSIS模型對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進行測度。考慮到各個系統指標數據的不一致,需要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使用極差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2)被解釋變量:林業現代化(MF)。對于被解釋變量林業現代化的測度,借鑒徐瑋等(2018)的研究,從生態資源、產業發展、社會文化和建設保障等四個維度構建多元指標體系,考慮到前文在度量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標時用到森林覆蓋率這一指標,因此沒有在準則層中加入該指標,并采用熵權法對中國31個省份進行測算。
(3)解釋變量:數字技術(DTD)。為度量數字技術水平,借鑒趙濤等(2020)、任轉轉等(2022)構建城市層面的數字技術發展指數,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省級層面及研究對象為數字技術,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合理性和客觀性,本文從數字覆蓋、數字保障、數字基礎、數字金融和數字人才等5 個角度選擇數字技術的相關指標,具體指標設計如表2 所示。在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使用熵權法對各個系統的指標進行權重賦值,然后根據計算出的指標權重,計算各省份數字技術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
在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使用熵權法對各個系統的指標進行權重賦值,最后直接利用權重與指標計算各省份數字技術水平的綜合得分。
(4)中介變量:除測度數字技術水平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程度外,為實證研究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作用機制,本文還分別構建了度量結構效應和勞動效應的指標。其中,勞動效應采用各省份的勞動生產率(LP)來度量,而結構效應采用各省份的產業結構(IS)指標如式(8)所示。
(5)控制變量:結合王平(2023)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相關研究,本文加入了地區創新水平(用Ramp;D強度的自然對數ln RD表示)、地方財政支出的自然對數(LFE)、GDP 平減指數(GDPG)和基礎設施水平(人均公鐵路里程PRM)作為控制變量,分別反映區域創新、政策支持及基礎條件對區域現代化的影響。另外,后文的異質變量分別采用地區經濟規模(用GDP的自然對數ln GDP來表示)和農村電商規模(用農村電商市場的交易額ESR來度量)進行研究。
4.3 描述性統計
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3 所示。
從表3 可以看出,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均值為0.36,最大值為0.88,最小值為0.06,二者存在一定差距,表明我國各省份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整體不高,不同省份發展水平有一定差距;數字技術均值為0.25,最大值和最小值具有一定差距,表明各省份數字技術水平不均衡,東西部差距明顯;另外,林業現代化水平均值為0.27,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差距較大,表明我國各省份林業現代化水平差距較大。各控制變量的數據較為平穩,說明較為適合后面進行的計量檢驗。
5 實證結果分析
依據前文計量模型的構建,本部分實證分析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對模型結論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并對二者關系進行機制性分析、異質性分析和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5.1 面板數據的相關檢驗
為更加準確地選擇合適的計量模型,本文進行F 檢驗和豪斯曼(Hausman)檢驗,結果如表4 所示。固定效應模型內生性檢驗的p 值為0.00,強烈拒絕了變量外生的原假設,故采用面板估計效應模型進行計量回歸分析,并與采用最小二乘、面板隨機效應的回歸結果進行比對,且采用動態面板廣義矩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以確保結果的穩健性。
5.2 基準回歸結果
為驗證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及林業現代化的影響,基于前文的計量模型式(1),本文分別采用最小二乘、面板隨機效應和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其中式(5)選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
由表5 可以看出,在式(1)選用的三種計量模型中,數字技術的回歸系數都為正,且在相應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尤以面板固定效應模型的擬合優度最大,故采用此模型的計量結果進行說明。從列(3)可以發現,數字技術的估計系數為0.19,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會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這與前文的機理分析是一致的,驗證了假設H1 的前半句。
從表5 列(4)可以看出,數字技術的回歸系數為0.04,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林業現代化進程;而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交互項的估計系數為0.18,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促進作用能夠進一步助推林業現代化。可能原因是:由于數字技術在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后,改善了農業農村面貌,優化了農業生態環境,加速了林業的數字化和信息化進程,提高了農村林業生態資源總量,提升了森林治理,促進了林業產業的發展,從而加快了整個區域林業現代化的進程。
控制變量方面,地方財政支出的自然對數(LFE)、GDP 平減指數(GDPG)和基礎設施水平(人均公鐵路里程PRM)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6、0.18 和0.07,且在相應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這些控制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另外,地區創新水平(用Ramp;D強度的自然對數ln RD表示)對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影響不顯著,創新能力在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上的作用不強。
5.3 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用的穩健性,對本文的研究結果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6 所示。
5.3.1 重新度量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數字技術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重新對已構建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標進行測算。同時采用熵權-TOPSIS 方法對數字技術進行重新測度。表6 列(1)為重測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計量估計結果,列(2)為重測數字技術的計量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更換掉兩個關鍵變量測度方法后,數字技術的估計系數為正,且在相應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顯著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研究結果是穩健的。
5.3.2 基于動態面板廣義矩檢驗
考慮到普通的固定面板效應模型可能會遺漏影響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相關因素,造成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動態面板廣義矩(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進行檢驗,結果如表6 列(3)所示。可以看出,數字技術的估計系數為0.37,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在采用系統GMM進行檢驗時,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影響與前文一樣,說明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數字技術依然會顯著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進一步驗證了假設H1,即數字技術會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5.4 機制檢驗
為分析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作用機制,本部分對前文的計量模型式(3)和式(4)進行檢驗,即分析數字技術是否會通過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升級作用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結果如表7 所示。
表7 列(1)中數字技術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系數為1.72,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顯著提升了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增強了勞動投入效率。列(2)在加入勞動生產率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沒有發生顯著變化,但估計系數由0.19 減小到0.09;而勞動生產率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之間的系數為0.05,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勞動生產率在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應占比約為40%,說明數字技術會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表7列(3)中數字技術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系數為0.18,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顯著提升地區產業結構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列(4)在加入產業結構變量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也沒有發生顯著變化,但估計系數由0.19 減小為0.12。產業結構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之間的估計系數為0.24,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產業結構在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比為20%,說明數字技術會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來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
5.5 異質性檢驗
前文分析了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二者的相互關系,并采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了數字技術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作用機制。但對不同區域屬性而言,這種影響是否存在?若存在,影響程度是否一致?本文從省份所屬區域、經濟規模和農村電商規模3 個角度分析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進行異質性檢驗,結果如表8 所示。
表8 中列(1)、列(2)、列(3)是將樣本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計量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數字技術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7、0.42、0.27,且都在相應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在不同區域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都顯著為正,但影響程度略有不同,中部地區最強、東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弱。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區農業發展和數字技術創新發展協同性較高,數字技術能較快應用到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中,如綠色發展、質量興農和品牌興農等,數字技術作用得以充分體現;東部地區由于重點發展第二和第三產業,導致數字技術更多應用在二三產業,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應用不多;而西部地區由于歷史原因,數字技術和農業農村現代化都相對較為落后,二者相關性最小。從列(4)可以看出,數字技術與經濟規模DTD×ln GDP的回歸系數為0.28,且在相應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影響程度,在經濟規模越大的省份越大。數字技術離不開經濟市場的支持,越大的經濟規模越能助推數字技術的應用,也更能發揮數字技術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作用。從列(5)可以看出,數字技術與農村電商規模DTD ×ESR的估計系數為0.38,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程度在農村電商規模大的省份更大。數字技術更多借助相應的平臺才能發揮顯著作用,電商規模越大,數字技術在農村的應用領域就越廣,數字技術與電商規模在農村場景的應用具有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作用,而農村電商規模的發展使得數字技術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更快。
5.6 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在實證分析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影響之后,本部分先采用全局莫蘭指數分析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空間相關性,使用空間杜賓模型(SDM)檢驗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探究影響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因素。
5.6.1 空間相關性檢驗
為分析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空間溢出效應,先采用全局莫蘭指數檢驗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空間自相關性,如表9 所示。
由表9 可知,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全局莫蘭指數除2013 年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外,其余年份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且指數都大于0,表明不同省份的農業農村現代化之間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產生了正向的溢出效應,帶動周邊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同樣,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較低的省份產生了負向溢出效應,抑制了周邊區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
5.6.2 空間計量分析
在驗證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具有空間相關性的基礎上,為選擇適合的空間計量模型,本文又進行一系列檢驗,結果如表10 所示。
從表10 可以看出,在進行事前的LM-err、LM-lag 和穩健LM-err 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與前文的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一致,即各省份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存在空間相關性。同時事后的Wald 檢驗和LR檢驗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表明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空間杜賓模型(SDM)比空間滯后模型(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EM)更為適合。
依據上面的檢驗結果,本文采用空間相鄰矩陣和地理距離矩陣對式(6)和式(7)進行計量,結果如表11 所示。
表11 中列(1)、列(2)分別為采用空間相鄰矩陣和地理距離矩陣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相較于前面的普通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二者結果較為一致。數字技術估計系數分別為0.69 和0.74,且分別在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與前文檢驗結果一致,即數字技術會顯著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相關系數ρ 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10 和0.16,且在相應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各省份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具有正向溢出效應,數字技術會通過空間溢出效應正向推動鄰近區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除了帶動本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外,周邊區域會相互模仿,從而通過知識溢出效應來推動臨近區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
為進一步研究空間溢出效應的形成過程,本文對上述SDM模型進行相應的相鄰矩陣和經濟地理矩陣的效應分解,得到具體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結果如表12 所示。
從表12 列(5)、列(6)發現,總效用與前文計量結果一致,列(1)、列(2)中直接效應的估計系數為0.41 和0.51,且在相應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同時列(3)、列(4)中間接效應的估計系數為0.13 和0.20,也在相應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技術不僅直接帶動了周邊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而且也會通過人才、技術和資本的優勢帶動周邊區域數字技術進步,進而間接推動周邊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發展。控制變量方面,GDP 平減指數和基礎設施水平也會顯著帶動周邊省份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表明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水平對臨近區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有正向溢出效應。
6 研究結論、討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從理論上分析數字技術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作用機制,構建數字技術、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林業現代化的指標體系,采用2013—2022 年我國省際層面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相關研究結論,并據此討論后提出政策啟示。
6.1 研究結論
通過對2013—2022 年我國31 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5 點研究結論。
(1)數字技術會顯著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且該結論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
(2)數字技術會通過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來提升林業現代化發展水平。
(3)機制檢驗表明,數字技術會通過增強勞動生產率、提高產業結構發展水平,進而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
(4)異質性檢驗表明,在中部地區及經濟規模較大和電商規模較大的省份,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影響程度更大。
(5)進一步采用空間杜賓模型(SDM)實證分析發現,數字技術會通過技術溢出來促進周邊區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現階段要加快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應用,推動農業數字化轉型,加強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提供思路。加強數字技術帶來的社會效益,如在林業現代化領域的應用,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6.2 討論
本文基于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理論分析框架,揭示了二者之間的作用機理和空間溢出特征,基于現有結論開展進一步討論。
(1)研究結論證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這與蔡雪玲等(2024)研究數字經濟驅動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結論一致,表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具有建設意義,但優化建設仍需一定的發展空間。
(2)中介效應表明數字技術會通過提升產業結構、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這與王偉新等(2023)認為數字經濟通過促進農村資本深化和提高市場化進程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提升結果有相似性,表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提升是一個多維度的提高。
(3)空間溢出效應表明數字技術會通過技術溢出來推動周邊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這與趙敏等(2024)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強的空間溢出性觀點類似,只不過本文數字普惠金融是數字技術的一個方面,數字技術相關范圍較廣,對周邊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輻射作用更強。
(4)研究結論表明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促進作用能夠進一步助推林業現代化,這與許琴琴等(2023)研究數字技術會正向推動林業發展的結論一致。數字技術能改善整個農業農村生態,提高整個林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從而提升林業現代化水平。同時,林業現代化的發展也將反哺農業農村現代化,形成良性互動,共同推動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的不足之處:一方面,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范圍很廣的概念,如何合理構建度量指標并合理測度,值得深入探討;另一方面,礙于數據的可得性,采用的是省級層面數據,在刻畫農業農村現代化及林業現代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未來可進一步使用地市乃至縣域層面數據進行更為細致深刻地分析。
6.3 政策啟示
基于研究結論和討論分析,結合“十四五”時期數字經濟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趨勢,本文提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6 點政策啟示。
(1)加快農業數字化轉型,提升數字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當前,我國農業發展水平比較落后,傳統農業占比仍然較大,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促進農業的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用數字技術來推動農業現代化。因此,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加強頂層設計,加快人工智能、AI 算法、大數據及區塊鏈對農業數據的提取及應用,加快農業科技研發,擴大數字應用試點。
(2)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數字技術環境。當前,雖然移動互聯網和網絡寬帶在農村地區大力普及,但相較于城市的數字基建還有一定的差距。為縮小城鄉間的數字鴻溝,應加快城鄉間、區域間的信息互聯互通,需加快農村數字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使得農村能快速實現網絡全覆蓋,讓農民能享受到數字社會帶來的好處,提升農民生活的數字環境,真正把數字技術應用到農民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
(3)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數字人才培養。數字技術會通過提升產業結構、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地區產業結構水平越高,越能發揮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現代化中的應用。各省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突出數字化轉型在其中的貢獻,同時勞動生產率提升離不開人的能力提高,需加快數字技術人才的培養。當地政府要積極與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業等展開合作,培育新型農業數字技術人才,提升農民勞動生產率,加快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應用。
(4)不同地區要實行差異化的涉農政策。數字技術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在不同規模、不同區域發揮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各省在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要結合本省的經濟、電商規模和所屬區域的特點,分層次地推動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中的應用。同時,國家在政策層面上要給予各省更多自主決策權,使各省能結合自身特點,充分利用數字優勢,提升各自區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
(5)由于空間溢出效應的存在,要加強各省尤其是相鄰省份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優化數字要素在各省農業農村領域的配置,數字技術對其他區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具有正向溢出效應,因此,不用形成惡性競爭,要相互促進,優先發展數字技術能最大發揮農業農村作用的地區,先富帶動后富,最后整體提升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全力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力量。
(6)提升農村居民尤其是林農的數字素養,為數字技術帶動林業現代化積蓄人力資本,無論是林業產業的發展還是數字化護林員,林農都是直接參與者。可以利用先進數字技術和數字教育資源提升林農的專業水準,推動林業作為綠色和民生主體產業的重要作用,發揮鄉村經濟中林業的經濟和生態雙重作用。
參考文獻
蔡雪玲, 龐智強. 數字經濟驅動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理論機制與路徑選擇[J]. 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 2024(4):51-56.
陳燦, 高建中, 李善美, 等. 數字普惠金融、家庭借貸對農戶林業收入的影響研究[J]. 林業經濟問題, 2022, 42(3):269-277.
陳飛, 劉宣宣, 王友軍. 數字經濟緩解了農村多維相對貧困?——基于收入導向型視角[J]. 浙江社會科學, 2022(10):25-36, 155-156.
陳弘, 馮大祥. 數字賦能助推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思路與進路[J]. 世界農業, 2022(2):55-65.
陳衛洪, 王瑩. 數字化賦能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構建研究——“智農通”的實踐與啟示[J]. 農業經濟問題, 2022(9):86-99.
陳亞軍. 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振興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J]. 現代經濟探討, 2022(6):121-132.
程聰, 謬澤鋒, 嚴璐璐, 等. 數字技術可供性與企業創新價值關系研究[J]. 科學學研究, 2022, 40(5):915-926.
程名望, 黃甜甜, 劉雅娟. 農村勞動力外流對糧食生產的影響:來自中國的證據[J]. 中國農村觀察, 2015(6):15-21.
杜志熊. 農業農村現代化:內涵辨析、問題挑戰與實現路徑[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21(5):1-10.
樊勝岳, 李耀龍, 馬曉杰, 等. 數字化水平對農業綠色發展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中國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J]. 世界農業,2021 (12):4-16.
樊軼俠, 徐昊, 馬麗君. 數字經濟影響居民收入差距的特征與機制[J]. 中國軟科學, 2022 (6):181-192.
封思賢, 宋秋韻. 數字金融發展對我國居民生活質量的影響研究[J]. 經濟與管理評論, 2021, 37(1):101-113.
高強, 曾恒源. “十四五”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重點與政策趨向[J]. 中州學刊, 2020(12):1-8.
管輝, 雷娟利. 數據要素賦能農業現代化:機理、挑戰與對策[J]. 中國流通經濟, 2022, 36(6):72-84.
韓晶, 陳曦, 馮曉虎. 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的現實挑戰和路徑選擇[J]. 改革, 2022(9):11-23.
何正燕, 張艷榮. 甘肅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測度及障礙因子研究[J]. 中國農機化學報, 2022, 43(2):1588-1599.
華中昱, 林萬龍, 徐娜. 數字鴻溝還是數字紅利?——數字技術使用對農村低收入戶收入的影響[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 39(5):133-154.
姜長云, 姜惠宸. 論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任務的三個層次[J]. 東岳論叢, 2021, 42(7):130-140, 192.
蔣永穆, 李明星. 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要求、問題挑戰與路徑策略[J]. 社會科學輯刊, 2024(5):1-12.
李靜, 陳亞坤. 農業公司化是農業現代化必由之路[J]. 中國農村經濟, 2022(8):52-69.
李文. 經濟社會雙輪驅動農業農村現代化[J]. 人民論壇, 2023 (4):36-39.
梁俊芬, 蔡勛, 馮珊珊, 等. 珠三角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程度評價及制約因子研究[J]. 生態環境學報, 2022, 31(8):1680-1689.
梁琳. 數字經濟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路徑研究[J]. 經濟縱橫, 2022(9):113-120.
劉蕾, 王軼. 數字化經營何以促進農民增收?——基于全國返鄉創業企業的調查數據[J]. 中國流通經濟, 2022, 36(1):9-19.
劉鵬飛, 韓曉琳, 李羚銳. 數字經濟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J]. 商學研究, 2022, 29(4):5-15.
陸益龍. 鄉村振興中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2018, 35(3):48-56.
羅浚文, 李榮福, 盧波. 數字經濟, 農業數字要素與賦能產值——基于GAPP 和SFA的實證分析[J]. 農村經濟, 2020(6):16-23.
羅千峰, 趙奇鋒, 張利庠. 數字技術賦能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框架、增效機制及實現路徑[J]. 當代經濟管理, 2022, 44(7):49-56.
彭艷玲, 周紅利, 蘇嵐嵐. 數字經濟參與增進了農民社會階層認同嗎?——基于寧、渝、川三省份調查數據的實證[J]. 中國農村經濟, 2022(10):59-81.
錢佰慧, 陳思霖, 徐洋, 等. 農村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測度分析[J]. 農業經濟與管理, 2021(6):39-49.
錢明輝, 潘菲, 齊悅. 后新冠疫情下我國農業農村數字經濟發展——問題、趨勢與對策[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21, 42(11):62-71.
覃誠, 汪寶, 陳典, 等. 中國分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評價[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22, 43(4):173-182.
任轉轉, 鄧峰. 數字技術, 要素結構轉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J]. 軟科學, 2022(4):51-61.
史常亮. 數字經濟賦能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效應與機制[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 2024, 23(9):94-109.
孫德超, 李揚. 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邏輯進路與實現路徑[J]. 社會科學, 2022(7):143-150.
孫賀, 傅孝天. 農業農村現代化一體推進的政治經濟學邏輯[J]. 求是學刊, 2021, 48(1):81-89.
唐慧敏. 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的理論闡釋和實踐發展[J]. 農村經濟, 2022(9):42-51.
唐建軍, 龔教偉, 宋清華. 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要素流動與技術擴散的視角[J]. 中國農村經濟, 2022(7):81-102.
唐文浩. 數字技術驅動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理論闡釋與實踐路徑[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 22(2):1-9.
王彬, 高敬峰, 宋玉潔. 數字技術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來自中國細分行業的經驗證據[J]. 2021(12):115-125.
王春光. 邁向共同富裕——農業農村現代化實踐行動和路徑的社會學思考[J]. 社會學研究, 2021, 36(2):29-45, 226.
王定祥, 彭政欽, 李伶俐. 中國數字經濟與農業融合發展水平測度與評價[J]. 中國農村經濟, 2023 (6):48-71.
王定祥, 冉希美. 農村數字化、人力資本與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基于中國省域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 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 28(2):1-14.
王海艷, 林云舟, 騰忠銘.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因素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 2022(3):123-132.
王火根, 鄧子玲, 汪鈺婷. 數字金融對林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制[J]. 林業經濟問題, 2023, 43(6):561-569.
王平. 基要性變革中數字金融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研究[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24, 45(5):183-193.
王偉新, 殷徐康, 王晨光. 數字經濟助推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測度、機制與啟示[J]. 農業現代化研究, 2023, 44(4):609-623.
王笑涵, 陳妮, 甘林針, 等. 美國鄉村林業發展經驗借鑒[J]. 世界林業研究, 2020, 33(5):113-117.
王兆華. 新時代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再認識[J]. 農業經濟問題, 2019 (8):76-83.
魏后凱. 深刻把握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科學內涵[J]. 農村工作通訊, 2019(2):1.
溫湖煒, 王圣云. 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研究[J]. 科研管理, 2022, 43(4):66-74.
溫濤, 陳一明. 數字經濟與農業農村融合發展:實踐模式、現實障礙與突破路徑[J]. 農業經濟問題, 2020(7):118-129.
肖冰, 吳詩翩. 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影響因素分析[J]. 江蘇農業科學, 2021, 49(4):231-236.
徐瑋, 孔祥慧, 包慶豐. 中國林業現代化水平的地區差異及動態演進研究[J]. 林業經濟問題, 2018, 38(4):86-91.
許琴琴, 舒斯亮. 數字經濟對林業產業發展的影響——基于門檻效應分析[J]. 林業經濟, 2023, 45(10):82-96.
葉興慶, 程郁. 新發展階段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特征和評價體系[J]. 改革, 2021 (9):1-15.
張兵, 李娜. 數字普惠金融、非農就業與農戶增收——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的實證分析[J]. 農業現代化研究, 2022, 43(2):249-260.
張瀚丹, 李婭. 數字經濟與林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研究[J]. 林業經濟, 2023, 45(11):50-72.
張旺, 白永秀. 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耦合的理論構建、實證分析與優化路徑[J]. 中國軟科學, 2022(1):132-146.
張衛東, 卜偲琦, 彭旭輝. 互聯網技能, 信息優勢與農民工非農就業[J]. 財經科學, 2022(1):118-132.
張小允, 許世衛. 我國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 農業現代化研究, 2022, 43(5):1-10.
張岳, 周應恒. 數字普惠金融、傳統金融競爭與農村產業融合[J]. 農業技術經濟, 2021(9):68-82.
翟郡, 楊紅強, 徐彩瑤, 等. 浙江省數字經濟與林業產融融合水平測度及影響因素[J]. 林業科學, 2024, 60(5):22-34.
趙敏, 郭偉建. 數字普惠金融能否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兼論影響機制與空間效應[J]. 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4, 26(2):79-94.
趙濤, 張智, 梁上坤. 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J]. 管理世界, 2020, 36(10):65-76.
趙星, 李若彤, 賀慧圓. 數字技術可以促進創新效率提升嗎?[J]. 科學學研究, 2022(11):4-18.
Acemoglu D, Restrepo 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Work [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 10(24):197-236.
Asongu S.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penetration on African inequal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15, 42(8):706-716.
Dunleavy P, Margetts H, Tinkler J, et al. Digital Era Governance: IT Corporations, 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Florian E S, Ferdinand H, Christoph G, et al. Sensor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mart forestry [J]. Sensors, 2024, 24(3):1424-1453.
Gabriela L G, Simon L L, Mark B, et al. Forestplots. net: a web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tool to manage and analyse tropical forest plot data [J]. Journal of Vegetation Science, 2011, 22(6):610-613.
Huttunen S. Revisiting Agriculture Modernisation: Interconnected Farming Practices Driving Rural Development at the Farm Level Author Links Open Panel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71(10):36-45.
Issahaku H, Abu B M, Nkegbe P K. Does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by Smallholder Maize Farmers Affect Productivity in Ghana?[J]. Journal of African Business, 2018, 19(3):302-322.
Kansanga M, Andersen P, Kpienbaareh D, et al.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transition: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n smallholder farming in Ghana under the new Green Revolu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p; World Ecology, 2019, 26(1):11-24.
Kleis L, Chwelos P, Ramirez R V, et 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angible output:The impact of IT investment on information productivity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2, 23(1):42-59.
Klerkx L, Jakku E, Labarthe P. A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 on Digital Agriculture, Smart Farming and Agriculture 4.0: New Contributions and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J]. NJAS: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2019, 90-91(C):100315.
Lee J Y. Contes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ultur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Music in Korea [J].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09, 10(4):489-506.
Ralandi S, Brunori G, Bacco M. The Dig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owards a taxonomy of the Impacts [J]. Sustainability,2021, 13(9):5172.
Srinivasan A, Venkatraman N. Entrepreneurship in Digital Platforms: A Network- centric View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8, 12(1):54-71.
(責任編輯 韓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