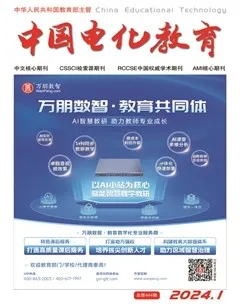我國(guó)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困境與戰(zhàn)略選擇
李森 王雪瑋
摘要: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是我國(guó)義務(wù)教育發(fā)展的新目標(biāo)、新任務(wù)。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和城鄉(xiāng)一體化是兩個(gè)緊密相連的動(dòng)態(tài)過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jìn)、相互融合。由于城鄉(xiāng)之間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體制機(jī)制、社會(huì)文化和資源配置等方面長(zhǎng)期以來(lái)存在較大差距,我國(guó)在推動(dòng)實(shí)現(xiàn)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進(jìn)程中,仍然面臨義務(wù)教育評(píng)價(jià)功利化、多主體協(xié)作淺表化、鄉(xiāng)村文化底蘊(yùn)流失、軟硬件資源投入不均等困境。為解決這些困境,需要從價(jià)值引導(dǎo)、政策推動(dòng)、文化認(rèn)同和歷史趨向的角度厘清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理路,進(jìn)而搭建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邏輯架構(gòu),為我國(guó)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提供戰(zhàn)略選擇。
關(guān)鍵詞: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城鄉(xiāng)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hào):G43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huì)精神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重點(diǎn)項(xiàng)目“推進(jìn)我國(guó)義務(wù)教育均衡發(fā)展和城鄉(xiāng)一體化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2AZD081)研究成果。
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提出“加快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和城鄉(xiāng)一體化”[1]。這意味著義務(wù)教育進(jìn)入新的發(fā)展階段:從基本均衡走向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從重“量”到提“質(zhì)”的方向轉(zhuǎn)變。優(yōu)質(zhì)均衡的義務(wù)教育既是對(duì)全面建設(shè)公平優(yōu)質(zhì)義務(wù)教育的新要求,也是強(qiáng)化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重要舉措,更是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關(guān)鍵。早在2010年頒布的《國(guó)家中長(zhǎng)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中就提出“把提高教育質(zhì)量作為教育改革發(fā)展的核心任務(wù)”,明確了優(yōu)質(zhì)均衡的義務(wù)教育是中國(guó)教育自我調(diào)整和不斷前進(jìn)的必經(jīng)過程。2019年中共中央、國(guó)務(wù)院印發(fā)的《中國(guó)教育現(xiàn)代化2035》中也將實(shí)現(xiàn)優(yōu)質(zhì)均衡的義務(wù)教育納入面向2035年的教育目標(biāo)[2]。2022年初全國(guó)教育工作會(huì)議提出“實(shí)施教育數(shù)字化戰(zhàn)略行動(dòng)”并列入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點(diǎn)。數(shù)字化作為教育轉(zhuǎn)型的載體和方向,已成為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改革和發(fā)展的重要驅(qū)動(dòng)力。然而,在推動(dòng)實(shí)現(xiàn)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進(jìn)程中,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不優(yōu)質(zhì)、不均衡成為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的一大痛點(diǎn),具體表現(xiàn)為教育評(píng)價(jià)功利化、多主體協(xié)作淺表化、鄉(xiāng)村文化底蘊(yùn)流失、軟硬件資源投入不均等問題。誠(chéng)然,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和城鄉(xiāng)一體化推進(jìn)是兩個(gè)緊密相連的動(dòng)態(tài)過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jìn)、相互融合。為此,需要從價(jià)值引導(dǎo)、政策推動(dòng)、文化認(rèn)同、歷史趨向的角度厘清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理路,進(jìn)而搭建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邏輯架構(gòu),從整體上全面把握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內(nèi)在機(jī)制,為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提供戰(zhàn)略選擇。
一、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意蘊(yùn)詮釋
在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的指引下,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美美與共,離不開全面育人的價(jià)值導(dǎo)向、與時(shí)俱進(jìn)的政策引擎、扎根本土的文化內(nèi)核和穩(wěn)中求進(jìn)的發(fā)展理路。立足時(shí)代背景,從價(jià)值邏輯、政策邏輯、文化邏輯和歷史邏輯四個(gè)互為依托、相互嵌入、融合共生的維度,深入剖析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邏輯架構(gòu),有助于形成全方位目標(biāo)共識(shí),凝聚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內(nèi)外部動(dòng)力。
(一)價(jià)值邏輯: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理念從外在功能回歸全面育人
義務(wù)教育的價(jià)值邏輯是實(shí)現(xiàn)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先導(dǎo),不僅承載了國(guó)家對(duì)于義務(wù)教育的核心思想和精神,也映射了社會(huì)對(duì)于義務(wù)教育的期望和需求。改革開放以來(lái),我國(guó)義務(wù)教育理念經(jīng)歷了從“效率為先”到“以人為本”的變革,義務(wù)教育價(jià)值取向也從以國(guó)家發(fā)展為主體、以人才供給為客體的工具取向,轉(zhuǎn)變?yōu)橥癸@人的主體性價(jià)值的人本主義取向。審視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價(jià)值取向的變遷,有助于從更大視野認(rèn)識(shí)優(yōu)質(zhì)均衡的深層價(jià)值意涵,進(jìn)而推動(dòng)義務(wù)教育朝著實(shí)質(zhì)性的目標(biāo)邁進(jìn)。
受外延式發(fā)展觀念的影響,在義務(wù)教育發(fā)展前期,我國(guó)義務(wù)教育發(fā)展的價(jià)值取向更多以工具主義為主。改革開放初期,為使國(guó)力迅速恢復(fù),教育秉承“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理念服務(wù)于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發(fā)展,“效率本位”成為義務(wù)教育的首要價(jià)值取向。1985年5月,鄧小平在全國(guó)教育工作會(huì)議上發(fā)表講話,強(qiáng)調(diào)教育與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互相依賴的關(guān)系,并在同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確立“教育必須為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服務(wù),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必須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導(dǎo)思想。這一時(shí)期的“工具主義教育觀”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確立了教育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之間的關(guān)系,認(rèn)識(shí)到必須建設(shè)教育強(qiáng)國(guó)進(jìn)而推動(dòng)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強(qiáng)國(guó)建設(shè);二是注重人才的功利化價(jià)值及其為社會(huì)發(fā)展帶來(lái)的實(shí)質(zhì)性效益。誠(chéng)然,工具主義的價(jià)值取向具有較強(qiáng)的實(shí)用性和功能性的優(yōu)勢(shì),使這一階段國(guó)家的綜合實(shí)力實(shí)現(xiàn)飛速發(fā)展,但是,也同時(shí)加深了城鄉(xiāng)資源分配不均等弊病,拉大了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差距。
進(jìn)入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義務(wù)教育著力推進(jìn)內(nèi)涵式發(fā)展,價(jià)值取向也由工具主義轉(zhuǎn)化為人本主義。這一轉(zhuǎn)向過程中,國(guó)家抓住教育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機(jī)遇,著眼于實(shí)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并將五育并舉上升為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的育人要求,主張的“優(yōu)質(zhì)”凸顯出應(yīng)始終聚焦于“人”的全面發(fā)展本身,回到培養(yǎng)“完整的人”的出發(fā)點(diǎn),體現(xiàn)對(duì)人的本體性價(jià)值的認(rèn)同[3]。2018年,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全國(guó)教育大會(huì)上講話中指出“教育的根本問題是培養(yǎng)什么人、怎樣培養(yǎng)人、為誰(shuí)培養(yǎng)人”,而這些根本性的最優(yōu)解都是建立在實(shí)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基礎(chǔ)之上。由此可見,義務(wù)教育不再僅僅局限于“量”的普及,還須實(shí)現(xiàn)“質(zhì)”的均衡。自20世紀(jì)90年代起,國(guó)家取消義務(wù)教育重點(diǎn)學(xué)校,科學(xué)規(guī)劃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學(xué)校布局。通過“特崗計(jì)劃”“優(yōu)師計(jì)劃”“國(guó)培計(jì)劃”等政策,優(yōu)先向農(nóng)村地區(qū)、邊疆民族地區(qū)、革命老區(qū)、邊遠(yuǎn)貧困地區(qū)提供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致力于彌合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差距,提高義務(wù)教育的整體質(zhì)量。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中強(qiáng)調(diào)“推進(jìn)教育數(shù)字化”,就是以數(shù)字技術(shù)為“抓手”,將數(shù)字優(yōu)勢(shì)轉(zhuǎn)化為數(shù)字價(jià)值,驅(qū)動(dòng)我國(guó)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優(yōu)化,來(lái)確保每個(gè)學(xué)生皆能獲得個(gè)性化、靈活化的教育資源。馬克思曾言“任何人類歷史的一個(gè)前提無(wú)疑是有生命的個(gè)人的存在”[4]。因此,只有走向“整體人”的義務(wù)教育,才能實(shí)現(xiàn)個(gè)體發(fā)展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有機(jī)結(jié)合。
(二)政策邏輯: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主體從政府主導(dǎo)走向多元聯(lián)動(dòng)
教育政策是連接教育理念與實(shí)踐的“橋梁”[5],義務(wù)教育的發(fā)展離不開政策的牽引和驅(qū)動(dòng)。義務(wù)教育在七十余年的政策引導(dǎo)下,責(zé)任主體經(jīng)歷了由地方分權(quán)到中央統(tǒng)一管理,再到責(zé)任重心下移的演變過程。對(duì)義務(wù)教育政策嬗變進(jìn)行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找準(zhǔn)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深層話語(yǔ)邏輯,從而為其發(fā)展提供相應(yīng)的策略參考。
1951年8月,《政務(wù)院關(guān)于改革學(xué)制的決定》中提出“應(yīng)給兒童以全面的義務(wù)教育”,但當(dāng)時(shí)國(guó)力尚在恢復(fù),國(guó)家也僅限于對(duì)城市教育的扶持,鄉(xiāng)村教育只能依靠集體。文革十年,義務(wù)教育的普及延滯,未取得實(shí)質(zhì)性的發(fā)展。改革開放初期,依據(jù)1986年頒布的《義務(wù)教育法》,我國(guó)義務(wù)教育實(shí)行“地方負(fù)責(zé),分級(jí)管理”的模式。義務(wù)教育系列政策實(shí)施三十年余年,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dòng)了義務(wù)教育的向前發(fā)展,但也造成城鄉(xiāng)教育的極度不均衡。為此,2001年,黨和國(guó)家打出了“人民教育政府辦”的鮮明旗號(hào)。2003年國(guó)務(wù)院發(fā)布的《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農(nóng)村教育工作的決定》中正式提出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開始由政府主導(dǎo)承擔(dān),義務(wù)教育進(jìn)入政府主導(dǎo)時(shí)期。在經(jīng)費(fèi)投入方面,2005年,我國(guó)在貧困縣實(shí)行義務(wù)教育“兩免一補(bǔ)”政策。2006年出臺(tái)的《義務(wù)教育法》明確規(guī)定了義務(wù)教育的免費(fèi)政策,義務(wù)教育完全進(jìn)入政府公共財(cái)政的保障范圍。2010年《國(guó)家中長(zhǎng)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指出“提高國(guó)家財(cái)政性教育經(jīng)費(fèi)支出占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比例”。在鄉(xiāng)村教師支持方面,政策予以傾斜,2015年頒布的《鄉(xiāng)村教師支持計(jì)劃》系列政策不斷用補(bǔ)償性政策作為激勵(lì)杠桿,全面深化鄉(xiāng)村教師隊(duì)伍的建設(shè)。
邁入優(yōu)質(zhì)均衡階段后,政府“退居幕后”,主張多元主體協(xié)同推動(dòng)義務(wù)教育發(fā)展。這一階段,數(shù)字技術(shù)助力于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多主體聯(lián)動(dòng)下的跨區(qū)域協(xié)同、校際合作、名師共享等多元實(shí)踐路向。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強(qiáng)調(diào)要建立城鄉(xiāng)一體的義務(wù)教育發(fā)展機(jī)制,推動(dòng)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一體化發(fā)展。2018年2月,《中共中央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實(shí)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意見》明確提出要“高度重視發(fā)展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推動(dòng)建立以城帶鄉(xiāng)、整體推進(jìn)、城鄉(xiāng)一體、均衡發(fā)展的義務(wù)教育發(fā)展機(jī)制”。2023年6月,在《關(guān)于構(gòu)建優(yōu)質(zhì)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wù)體系的意見》中提到要“全面推進(jìn)城鄉(xiāng)學(xué)校共同體建設(shè),健全城鄉(xiāng)學(xué)校幫扶激勵(lì)機(jī)制”,其中也指出要通過“加強(qiáng)國(guó)家數(shù)字化平臺(tái)建設(shè),構(gòu)建互聯(lián)互通、共建共享的數(shù)字教育資源平臺(tái)體系”,體現(xiàn)出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發(fā)展邏輯從政府主導(dǎo)走向多主體共治的轉(zhuǎn)向。
(三)文化邏輯: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文化從“復(fù)制”轉(zhuǎn)向特色再生產(chǎn)
文化功能是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系統(tǒng)內(nèi)在價(jià)值的演繹。義務(wù)教育承擔(dān)著孕育、傳承和創(chuàng)新文化的責(zé)任,文化作為義務(wù)教育的核心力量也在締造特色的義務(wù)教育。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是底線均衡基礎(chǔ)上的差異均衡,其發(fā)展是注重質(zhì)量提升的內(nèi)涵發(fā)展,是基本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基礎(chǔ)上的特色發(fā)展[6],而本土文化恰好為“優(yōu)質(zhì)均衡”提供了特色化的生長(zhǎng)土壤。為此,探析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背后的文化邏輯,可以更好地把握“優(yōu)質(zhì)均衡”的內(nèi)在機(jī)理,從而推動(dòng)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特色發(fā)展。
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發(fā)展過程中,鄉(xiāng)村文化經(jīng)歷了“復(fù)制”轉(zhuǎn)向特色再生產(chǎn)的過程。相應(yīng)地人們對(duì)待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觀念也從“城市為優(yōu)”轉(zhuǎn)變?yōu)椤氨就琳J(rèn)同”。在城鎮(zhèn)化的迅速發(fā)展過程中,鄉(xiāng)村教育在實(shí)踐中具有明顯的“城市偏向”,并以城市化的辦學(xué)標(biāo)準(zhǔn)創(chuàng)建鄉(xiāng)村學(xué)校教育,在校園校風(fēng)建設(shè)上也以模仿城市中小學(xué)為主。部分鄉(xiāng)村學(xué)校也一度復(fù)刻杜郎口中學(xué)、洋思中學(xué)以及十一學(xué)校等辦學(xué)模式。而鄉(xiāng)村學(xué)校在套用這些模式時(shí),學(xué)校的教師和學(xué)生也在學(xué)習(xí)和體驗(yàn)新型的教學(xué)模式。與此同時(shí),“城市偏向”的潛在思想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鄉(xiāng)村文化的封閉壁壘,促進(jìn)文化間的交流。
2021年,《中共中央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全面推進(jìn)鄉(xiāng)村振興加快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的意見》提出“深入挖掘、繼承創(chuàng)新優(yōu)秀傳統(tǒng)鄉(xiāng)土文化”。在新的發(fā)展形勢(shì)下,我國(guó)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也由“離農(nóng)”演化為“為農(nóng)”。當(dāng)下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要重新扎根優(yōu)秀鄉(xiāng)村文化,與優(yōu)秀鄉(xiāng)土文化進(jìn)行深度融合,汲取鄉(xiāng)土文化中的精髓,使鄉(xiāng)土文化逐步回歸并滲入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中,為鄉(xiāng)村的特色義務(wù)教育辦學(xué)提供核心教育內(nèi)容。2019年,《數(shù)字鄉(xiāng)村發(fā)展戰(zhàn)略綱要》提出“推進(jìn)鄉(xiāng)村優(yōu)秀文化資源數(shù)字化”,以此來(lái)加強(qiáng)鄉(xiāng)村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hù)與傳承。為鼓勵(lì)發(fā)展鄉(xiāng)村學(xué)校扎根鄉(xiāng)土特色辦學(xué),2020年教育部發(fā)布的《教育部辦公廳關(guān)于推進(jìn)鄉(xiāng)村溫馨校園建設(shè)工作的通知》中確定了第一批100所鄉(xiāng)村溫馨校園典型案例學(xué)校予以示范。這些鄉(xiāng)村學(xué)校將優(yōu)秀的鄉(xiāng)村文化轉(zhuǎn)化為適應(yīng)教育目的的語(yǔ)言和符號(hào),讓青少年一代在認(rèn)知和心理上逐漸認(rèn)同本土文化,激發(fā)其“文化獲得感”和“文化自豪感”,從而在自覺繼承并發(fā)揚(yáng)優(yōu)秀鄉(xiāng)土文化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鄉(xiāng)村文化的特色再生產(chǎn)。而在推進(jìn)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過程中,鄉(xiāng)村教育承載特色的鄉(xiāng)土文化,也在扭轉(zhuǎn)工業(yè)化背景下的教育功利傾向,實(shí)現(xiàn)本土文化創(chuàng)新的同時(shí)助力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融合發(fā)展。
(四)歷史邏輯: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水平從不均衡邁向一體化
建國(guó)以來(lái),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從初始的背景不均衡、投入不均衡、過程不均衡、結(jié)果不均衡,轉(zhuǎn)為注重投入的均衡、過程的均衡,再到關(guān)注結(jié)果的均衡。從時(shí)間上可以將當(dāng)下劃分為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不均衡期、基本均衡期、優(yōu)質(zhì)均衡期三個(gè)階段。預(yù)計(jì)未來(lái),我國(guó)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也必將走向一體化。
第一階段(1978—2000年):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不均衡期。改革開放初期,我國(guó)教育事業(yè)百?gòu)U待興,加快義務(wù)教育的恢復(fù)和發(fā)展已成為國(guó)家面臨的緊迫任務(wù)。為此,義務(wù)教育緊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步伐,分地區(qū)、有步驟地實(shí)施義務(wù)教育。鼓勵(lì)一部分地區(qū)先發(fā)展義務(wù)教育,而后幫助相對(duì)后進(jìn)地區(qū),最終實(shí)現(xiàn)義務(wù)教育的共同發(fā)展。這一階段,確立和保障人人平等的受教育權(quán)成為義務(wù)教育初始階段的目標(biāo),“兩基”攻堅(jiān)計(jì)劃的實(shí)施加快了這一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截止2000年底,我國(guó)已有85%的人口完成了九年義務(wù)教育,實(shí)現(xiàn)了義務(wù)教育的基本普及。
第二階段(2001—2019年):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基本均衡期。在義務(wù)教育普及率達(dá)標(biāo)后,其發(fā)展重心也正式轉(zhuǎn)移到基本均衡。這表明義務(wù)教育重心將從追求全覆蓋轉(zhuǎn)向確保義務(wù)教育資源分配的基本均衡。同時(shí),如何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就成為國(guó)家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一時(shí)期,國(guó)家以加大義務(wù)教育資源總體投入以及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的補(bǔ)償為主要策略,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投入均衡和過程均衡,核心內(nèi)容則是從經(jīng)費(fèi)、校舍、教學(xué)儀器、師資、學(xué)生資源和信息化建設(shè)等方面實(shí)現(xiàn)基本保障。截至2019年12月,全國(guó)累計(jì)2767個(gè)縣通過國(guó)家義務(wù)教育基本均衡的認(rèn)定,占比95.32%[7]。
第三階段(2019—2035年):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期。當(dāng)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實(shí)現(xiàn)基礎(chǔ)設(shè)施資源投入相對(duì)均衡后,義務(wù)教育結(jié)果均衡成為時(shí)代新的訴求。2019年,我國(guó)正式啟動(dòng)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督導(dǎo)評(píng)估認(rèn)定工作。就學(xué)生個(gè)體而言,優(yōu)質(zhì)均衡不再局限于“能上學(xué)”,而是要讓每個(gè)孩子“上好學(xué)”,“讓每個(gè)孩子實(shí)現(xiàn)類型上的差異化發(fā)展,而不是高低層級(jí)上的差異化發(fā)展”[8],最大限度地促進(jìn)學(xué)生潛能和個(gè)性的發(fā)展。就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而言,優(yōu)質(zhì)均衡就是要在底線均衡的基礎(chǔ)上尊重城鄉(xiāng)差異,并將其轉(zhuǎn)為特色,發(fā)揚(yáng)本土優(yōu)勢(shì),促進(jìn)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相互補(bǔ)充及資源共享。對(duì)國(guó)家而言,優(yōu)質(zhì)均衡就是要求義務(wù)教育的理念、政策、建設(shè)、教師隊(duì)伍有更高的提升,加大對(duì)義務(wù)教育條件和過程均衡的投入力度,關(guān)注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質(zhì)量均衡。
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期(2035— )。義務(wù)城鄉(xiāng)教育一體化的階段是指將來(lái)義務(wù)教育在城鄉(xiāng)背景不同的情況下,無(wú)論從投入、過程以及結(jié)果皆實(shí)現(xiàn)均衡發(fā)展。義務(wù)教育打破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束縛,通過數(shù)字技術(shù)整合城鄉(xiāng)教育資源,構(gòu)建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動(dòng)態(tài)均衡、雙向互通的體系和機(jī)制,使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在兼具差異的同時(shí),又能實(shí)現(xiàn)特色發(fā)展,在特色生長(zhǎng)時(shí)又相互融通。這有助于消除社會(huì)長(zhǎng)期以來(lái)形成的對(duì)城鄉(xiāng)教育不平等的觀念,轉(zhuǎn)為對(duì)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同等信賴,真正實(shí)現(xiàn)人民滿意的教育。
二、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困境
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強(qiáng)調(diào):“努力讓每個(gè)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zhì)量的教育”[9],優(yōu)質(zhì)均衡的義務(wù)教育成為我國(guó)新時(shí)代的當(dāng)下之需。然而,舊有觀念、文化的限制以及系統(tǒng)性變革的多重挑戰(zhàn),極易成為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中的堵點(diǎn)。優(yōu)質(zhì)均衡的落地必須緊扣這些困厄,準(zhǔn)確把握癥結(jié)所在,才能逐步清除義務(wù)教育發(fā)展道路上的阻礙。
(一)評(píng)價(jià)應(yīng)試化:以升學(xué)為導(dǎo)向的滯后觀念
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的實(shí)質(zhì)就是為學(xué)生打好扎實(shí)的基礎(chǔ),從而為滿足其全面發(fā)展與個(gè)性化發(fā)展提供平等的機(jī)會(huì),這是“優(yōu)質(zhì)”和“均衡”共同的價(jià)值核心。然而,長(zhǎng)期以來(lái),不少家長(zhǎng)把教育效率片面等同于升學(xué)率,為了高分和高升學(xué)率,寧愿放棄公平[10],義務(wù)教育在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道路上仍然受到評(píng)價(jià)應(yīng)試化、單一化、功利化的升學(xué)導(dǎo)向束縛,學(xué)校教育的工具功能被夸大,教育的本來(lái)意義被忽視[11]。由此,鄉(xiāng)村一度引發(fā)“進(jìn)城擇校”熱,部分鄉(xiāng)村家長(zhǎng)甚至?xí)M全力將孩子送在城市的重點(diǎn)學(xué)校讀書。在這樣的觀念下,造成城鎮(zhèn)“大班額建設(shè)不優(yōu)”和鄉(xiāng)村“空校化”的兩級(jí)化現(xiàn)象。一些基礎(chǔ)弱的鄉(xiāng)村學(xué)校在面對(duì)人民滿意教育與家長(zhǎng)滿意教育的矛盾中,將提高升學(xué)率選定為學(xué)校的主要教學(xué)目的。教師僅圍繞考試大綱制定課程和教學(xué)計(jì)劃,多數(shù)“副課”也被考試科目占用。有些教師過分看重投入產(chǎn)出比,認(rèn)為推進(jìn)教學(xué)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需要投入大量的時(shí)間與精力,短期內(nèi)難以產(chǎn)出較為顯性的成果[12],導(dǎo)致教師自身對(duì)數(shù)字化素養(yǎng)的提升比較排斥。一定程度上,以升學(xué)為導(dǎo)向觀念,不僅抑制了地方課程、校本課程等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也阻礙了教師的專業(yè)發(fā)展。當(dāng)分?jǐn)?shù)不斷被推崇和發(fā)揚(yáng),義務(wù)教育評(píng)價(jià)也將異化為壓制學(xué)生自身差異發(fā)展的工具,成為學(xué)生興趣和創(chuàng)造力的桎梏,迫使學(xué)生“削足適履”,這種以甄別和選拔為導(dǎo)向的義務(wù)教育也就偏離了優(yōu)質(zhì)均衡的內(nèi)在深意。
(二)協(xié)作淺顯化:以遷移模式為主的交流互動(dòng)
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多主體合作的一體化發(fā)展本質(zhì)是協(xié)調(diào)系統(tǒng)中諸要素的有機(jī)聯(lián)系,從而促進(jìn)系統(tǒng)整體穩(wěn)步發(fā)展。當(dāng)下,伴隨我國(guó)社會(huì)對(duì)優(yōu)質(zhì)義務(wù)教育需求浪潮的高漲,不少地區(qū)也大膽嘗試并開創(chuàng)了名校集團(tuán)化、學(xué)區(qū)管理、捆綁發(fā)展、學(xué)校托管等合作模式。然而,在處理城市要素和鄉(xiāng)村要素的關(guān)系上,要素間的差異性問題難以解決。實(shí)際的合作模式也主要集中于“以城帶鄉(xiāng)”,遷移城市義務(wù)教育要素資源到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要素上為主,造成了同質(zhì)化的發(fā)展模式,城鄉(xiāng)學(xué)校都很難找準(zhǔn)自己的辦學(xué)定位。一方面,對(duì)于相對(duì)薄弱的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而言,在集團(tuán)化、托管、“兩校一長(zhǎng)”等模式的實(shí)踐過程中,城市義務(wù)教育的強(qiáng)加和灌輸使得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被迫接受同化和改造,忽視了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差異性。有調(diào)查顯示,在集團(tuán)化模式中,教育質(zhì)量的提高僅僅在城市的參與校中,鄉(xiāng)村參與校的義務(wù)教育質(zhì)量并未因集團(tuán)化辦學(xué)得到改善,反而可能因此下降[13]。當(dāng)“整合”被異化為“統(tǒng)一”,就會(huì)過度追求要素之間的一致性,否定要素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對(duì)于城市義務(wù)教育而言,合作模式更多是城市義務(wù)教育在資源上對(duì)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的幫扶,為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輸血”。由于幫扶的不斷擴(kuò)展和深入,慢慢使城市義務(wù)教育也面臨優(yōu)質(zhì)資源被“稀釋”的問題,出現(xiàn)自我“貧血”現(xiàn)象。尤其體現(xiàn)在教師資源輸出上,骨干教師的調(diào)配,使城市學(xué)校師資缺乏,極大影響教學(xué)質(zhì)量。當(dāng)“協(xié)作”成為單方面的“移植”,義務(wù)教育就會(huì)過度追求平均,掩蓋其自身特色。
(三)文化表層化:以效仿為基準(zhǔn)的“本色迷失”
為提高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質(zhì)量,鄉(xiāng)村學(xué)校試圖通過效仿城市學(xué)校的校風(fēng)建設(shè)、教學(xué)理念、教學(xué)模式等實(shí)現(xiàn)這一目的。然而,“效仿”對(duì)鄉(xiāng)村學(xué)校的教學(xué)質(zhì)量并沒有實(shí)質(zhì)性的提升,反而造成“水土不服”。其深層原因便是城市文化無(wú)法在鄉(xiāng)村教育扎根,同時(shí)鄉(xiāng)土文化也漸趨被鄉(xiāng)村教育淘汰。在城鄉(xiāng)一體化的迅猛發(fā)展中,受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制約,鄉(xiāng)村文化成為落后的代名詞。鄉(xiāng)村教育與鄉(xiāng)土文化的結(jié)構(gòu)上,鄉(xiāng)村教育逐漸遠(yuǎn)離鄉(xiāng)土文化,淪為了鄉(xiāng)土文化的“他者”和“陌路人”[14]。鄉(xiāng)村文化與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的斷裂和分離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層面:首先,在鄉(xiāng)村生源上,最新報(bào)告顯示,義務(wù)教育總體城鎮(zhèn)化率達(dá)81.91%,比2012年增加13.91個(gè)百分點(diǎn)[15]。鄉(xiāng)村學(xué)生的銳減,使年輕一代的鄉(xiāng)土文化傳播者和再生產(chǎn)者減少,導(dǎo)致鄉(xiāng)土文化的衰弱和失傳。其次,在課程體系和教學(xué)內(nèi)容上也有以城市文化為背景的傾向,學(xué)生不得已以習(xí)得城市文化為主,拉大了鄉(xiāng)村教育和鄉(xiāng)村文化的鴻溝。最后,學(xué)校建設(shè)上,作為承載文化的重要場(chǎng)域,鄉(xiāng)村學(xué)校一味學(xué)習(xí)模仿城市學(xué)校建設(shè),淡化與鄉(xiāng)土文化的聯(lián)系,無(wú)形中滲透著對(duì)鄉(xiāng)村教育獨(dú)特性價(jià)值的否定,扭曲了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本質(zhì)。
(四)資源物質(zhì)化:以基礎(chǔ)設(shè)施為重心的投入不均
相較于以依附外部投入為主要手段的基本均衡,優(yōu)質(zhì)均衡則更加強(qiáng)調(diào)內(nèi)部的自主發(fā)展。然而,當(dāng)前我國(guó)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顯著投入還是局限于外部硬件設(shè)施。截至2021年,義務(wù)教育小學(xué)階段共有校舍建筑面積87128.98萬(wàn)平方米,比上年增加2551.73萬(wàn)平方米。設(shè)施設(shè)備配備總體達(dá)標(biāo)的學(xué)校比例在90%以上。初中階段共有校舍建筑面積75593.70萬(wàn)平方米,比上年增加3751.09萬(wàn)平方米。設(shè)施設(shè)備配備總體達(dá)標(biāo)的學(xué)校比例在95%以上[16]。在信息化建設(shè)上,根據(jù)2018年的數(shù)據(jù)表明,城鄉(xiāng)每百名學(xué)生擁有計(jì)算機(jī)臺(tái)數(shù)不斷增加,鄉(xiāng)村甚至反超城市[17]。雖然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在硬件設(shè)施的配置上不斷均衡,但各學(xué)校新配置的標(biāo)準(zhǔn)化教學(xué)儀器和技術(shù)設(shè)備,利用率普遍不足,鄉(xiāng)村學(xué)校更為突出,甚至造成資源的浪費(fèi)。反觀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軟實(shí)力,差距較為明顯,集中體現(xiàn)在辦學(xué)水平和教師隊(duì)伍。同時(shí),鄉(xiāng)村學(xué)校的創(chuàng)造力和內(nèi)生力不足的弊病依舊存在,教學(xué)管理、教學(xué)模式、教學(xué)研究、自身特色建構(gòu)等方面依舊滯后。在教師結(jié)構(gòu)方面,鄉(xiāng)村學(xué)校教師還存在結(jié)構(gòu)性失衡的問題。如鄉(xiāng)村學(xué)校較為集中的西部地區(qū),“體育教師占總數(shù)的6.18%,美術(shù)教師占總數(shù)的4.12%,音樂教師占總數(shù)的4.12%,道德與法治教師占總數(shù)的1.54%” [18]。在教師專業(yè)素養(yǎng)方面,鄉(xiāng)村教師的學(xué)歷普遍低于城市教師,而學(xué)歷又直接影響著教師的專業(yè)知識(shí)和專業(yè)技能。當(dāng)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只注重基礎(chǔ)資源的配置而忽視軟實(shí)力的提升時(shí),優(yōu)質(zhì)均衡的義務(wù)教育也將“華而不實(shí)”。
三、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戰(zhàn)略選擇
當(dāng)前,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面臨諸多困境,找準(zhǔn)落實(shí)好這一政策的切入點(diǎn),既要依賴于國(guó)家層面的頂層設(shè)計(jì)做統(tǒng)籌,需要利益相關(guān)者的深入?yún)f(xié)同,也要堅(jiān)持城鄉(xiāng)自發(fā)的特色開創(chuàng),還要有社會(huì)認(rèn)同的育人理念,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我國(guó)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
(一)國(guó)家調(diào)控戰(zhàn)略:堅(jiān)持扶弱頂層設(shè)計(jì),加快義務(wù)教育轉(zhuǎn)型
問題定義的目的在于將同一認(rèn)知達(dá)成共識(shí)[19]。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重在高層次的統(tǒng)籌規(guī)劃,政府要明確重點(diǎn)、強(qiáng)化職能,以問題為導(dǎo)向,在國(guó)家宏觀政策框架內(nèi),調(diào)整制度和策略,做好戰(zhàn)略選擇與操作執(zhí)行的動(dòng)態(tài)耦合,確保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
從政策層面看,國(guó)家要持續(xù)加大對(duì)義務(wù)教育的經(jīng)費(fèi)投入,尤其要對(duì)鄉(xiāng)村教育實(shí)行傾斜。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一直處于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劣勢(shì)地位,想要扭轉(zhuǎn)局面,必須依靠外部力量抬升底部,所以政府要承擔(dān)義務(wù)教育投入的主要責(zé)任。一方面,明晰中央與地方義務(wù)教育財(cái)政事權(quán)和支出責(zé)任劃分范圍,保障教育經(jīng)費(fèi)真正落實(shí)到義務(wù)教育健康發(fā)展。另一方面,在制定調(diào)整政策和制度時(shí),要建立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數(shù)字化考察機(jī)制。大量實(shí)地調(diào)查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實(shí)際情況,通過智能算法,精準(zhǔn)數(shù)據(jù)追溯,精確匹配區(qū)域義務(wù)教育資源,以具體的數(shù)字呈現(xiàn)當(dāng)?shù)剞k學(xué)條件。改善投資方式,設(shè)定專項(xiàng)資金供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靈活使用。以便后期政府更好的明確重點(diǎn)、細(xì)化投入、機(jī)動(dòng)調(diào)配,做到精準(zhǔn)的“治薄扶弱”,避免資源浪費(fèi)。
從資源配置層面看,提高資源配置重心,是促成高質(zhì)量、高水平、高標(biāo)準(zhǔn)一體化發(fā)展的關(guān)鍵。目前我國(guó)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注重物質(zhì)性的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忽視義務(wù)教育內(nèi)涵意蘊(yùn)的發(fā)展。國(guó)家要將資源配置重心集中到軟實(shí)力的建設(shè)上來(lái),教師作為軟實(shí)力的核心要素,在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一體化中發(fā)揮不可或缺的作用。為此,健全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教師長(zhǎng)效機(jī)制勢(shì)在必行。在政策上,在已有的補(bǔ)償性政策上補(bǔ)充鄉(xiāng)村教師的發(fā)展性政策。通過不斷的激勵(lì),形成長(zhǎng)期的吸引力,提升鄉(xiāng)村教師的獲得感。在制度方面,設(shè)立評(píng)價(jià)考核制度,建立由教育局、專家、學(xué)校組成的評(píng)價(jià)團(tuán)隊(duì),負(fù)責(zé)對(duì)鄉(xiāng)村教師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考核,并定期向教師提供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和個(gè)人成長(zhǎng)的建議。評(píng)價(jià)考核的同時(shí),也要提供支持和培訓(xùn)機(jī)制,為鄉(xiāng)村教師提供專業(yè)發(fā)展的培訓(xùn)課程和資源,尤其是要常態(tài)化推進(jìn)教師素養(yǎng)的培育,幫助他們提升教學(xué)能力和專業(yè)素質(zhì)。
(二)區(qū)域驅(qū)動(dòng)戰(zhàn)略:建立城鄉(xiāng)多元聯(lián)盟,推動(dòng)深層互通共享
數(shù)字時(shí)代的核心價(jià)值理念為“自由、開放、共享”[20]。城鄉(xiāng)一體化是指一定區(qū)域范圍內(nèi)城市與鄉(xiāng)村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方面發(fā)展的有機(jī)結(jié)合,形成以城帶鄉(xiāng)、以鄉(xiāng)促城、相互依存、互補(bǔ)融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21],可見,數(shù)字化與義務(wù)教育城鄉(xiāng)一體化本質(zhì)上具有“同構(gòu)性”的關(guān)系。因此,要改變“城鄉(xiāng)兩策,重城抑鄉(xiāng)”的思路,就要從城鄉(xiāng)各自的小循環(huán)、小系統(tǒng)走向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大循環(huán)、大系統(tǒng)[22],城鄉(xiāng)間要建立多元聯(lián)盟機(jī)制,將數(shù)字技術(shù)與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治理主體深度融合,發(fā)揮數(shù)字效能,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多主體間的相互兼容和深入互通,合力打造雙強(qiáng)共榮的義務(wù)教育。
城鄉(xiāng)多元聯(lián)盟的深入建設(shè)不僅需要政府“牽引力”的助推,還需要城鄉(xiāng)之間“齊驅(qū)力”的共創(chuàng)。當(dāng)前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的合作,是以地區(qū)政府自發(fā)的模式為主,政府往往是以大局視角整合義務(wù)教育資源。而相對(duì)于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學(xué)校而言,學(xué)校作為一個(gè)組織,當(dāng)沒有利益作為前提條件時(shí),合作就變成流于形式的被迫配合。因而為了保障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聯(lián)盟的規(guī)范性和長(zhǎng)期性,一是要制定相關(guān)政策和法規(guī),明確促進(jìn)城鄉(xiāng)教育聯(lián)盟建設(shè)的目標(biāo)和原則。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政府要發(fā)揮組織協(xié)調(diào)的作用,要求相關(guān)部門和機(jī)構(gòu)履行推進(jìn)城鄉(xiāng)教育聯(lián)盟的責(zé)任和義務(wù),促使多元主體參與城鄉(xiāng)教育聯(lián)盟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協(xié)同落實(shí)城鄉(xiāng)教育聯(lián)盟的各項(xiàng)措施。二是政府要通過財(cái)政投入、教育基金設(shè)立等方式,為城鄉(xiāng)教育聯(lián)盟提供資金支持,推動(dòng)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三是要?jiǎng)?chuàng)建深度互通共享機(jī)制,設(shè)置城鄉(xiāng)教育資源數(shù)字化共享平臺(tái),用于城鄉(xiāng)學(xué)校之間的資源共享,為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多主體對(duì)話營(yíng)造有利條件,學(xué)校和師生可以通過線上進(jìn)行教學(xué)資源的共建共享。四是在城鄉(xiāng)教師要素層面上,促進(jìn)城鄉(xiāng)教師的雙向流動(dòng)和合理分配。要構(gòu)建好師資支持系統(tǒng),提供專業(yè)的培訓(xùn)和指導(dǎo),調(diào)配優(yōu)秀的城市教師到農(nóng)村學(xué)校進(jìn)行支教。在此基礎(chǔ)上,還要搭建教師共享中心將城市名校教師與鄉(xiāng)村學(xué)校教師設(shè)立結(jié)對(duì)幫扶,以促進(jìn)師資隊(duì)伍的均衡發(fā)展。
(三)學(xué)校發(fā)展戰(zhàn)略:厚植本土校園文化,打造特色辦學(xué)品牌
學(xué)校文化是激發(fā)辦學(xué)活力的內(nèi)生動(dòng)力[23]。學(xué)校作為義務(wù)教育的實(shí)踐主體,決定著義務(wù)教育自主發(fā)展的質(zhì)量和水平。而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深刻內(nèi)涵詮釋了本土文化平等發(fā)展意蘊(yùn)的同時(shí),數(shù)字技術(shù)也為學(xué)校特色化辦學(xué)提供了強(qiáng)有力的后盾和創(chuàng)造力。因此,城鄉(xiāng)學(xué)校根植特色本土文化,打造特色辦學(xué)品牌勢(shì)在必行。
堅(jiān)持本土化的辦學(xué)道路,形成共生性文化認(rèn)同。城鄉(xiāng)一體化不等于城鄉(xiāng)一樣化,不同地區(qū)、學(xué)校之間各有差異。而在承認(rèn)差異的基礎(chǔ)上,鄉(xiāng)村學(xué)校應(yīng)扎根鄉(xiāng)土地域,突出自身的本土特性,凝練和融合鄉(xiāng)土文化內(nèi)涵,將差異轉(zhuǎn)為辦學(xué)的特色點(diǎn)和創(chuàng)新點(diǎn),從而走出個(gè)性化辦學(xué)道路。鄉(xiāng)村學(xué)校要借助數(shù)字技術(shù)聯(lián)通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和本土文化,運(yùn)用好數(shù)字技術(shù)保存和傳承鄉(xiāng)土文化來(lái)開展學(xué)校特色文化。鄉(xiāng)村學(xué)校要明確“主人翁”辦學(xué)理念,辦學(xué)理念是學(xué)校內(nèi)部的核心價(jià)值觀、共同信仰和行為準(zhǔn)則的集合體。受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影響,鄉(xiāng)村教師、學(xué)生普遍存在“自卑”心理。為解決這一問題,一是在人才觀層面,明確鄉(xiāng)村教育目的是要培育熱愛鄉(xiāng)村、扎根鄉(xiāng)村、建設(shè)鄉(xiāng)村和振興鄉(xiāng)村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讓學(xué)生意識(shí)到自己的發(fā)展與鄉(xiāng)村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使其學(xué)習(xí)目標(biāo)具有更深層次的意義感和使命感。二是在教師層面,教師應(yīng)為學(xué)校的主人,參與到學(xué)校的管理、決策等過程中,增強(qiáng)教師的責(zé)任感,更好地發(fā)揮創(chuàng)造力。教師個(gè)人也要主動(dòng)接受教育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積極參與研修和培訓(xùn)活動(dòng),提升信息素養(yǎng),提高信息化教學(xué)應(yīng)用能力[24]。
挖掘地方教育資源,創(chuàng)設(shè)綜合育人課程。每所學(xué)校都面臨不同的內(nèi)外環(huán)境,如果能夠基于自身時(shí)空和境遇的分析確定戰(zhàn)略發(fā)展方向和路徑,任何學(xué)校都具有通過特色發(fā)展實(shí)現(xiàn)優(yōu)質(zhì)資源創(chuàng)生的可能性[25]。因此,城鄉(xiāng)學(xué)校都應(yīng)秉承五育融合理念,利用數(shù)字技術(shù),結(jié)合所在地的自然、人文和經(jīng)濟(jì)資源,發(fā)現(xiàn)當(dāng)?shù)氐奶厣蛢?yōu)勢(shì),整合跨學(xué)科教學(xué)內(nèi)容,為綜合育人課程的創(chuàng)設(shè)提供依據(jù)。具體而言,一是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學(xué)校以數(shù)字技術(shù)為中介建立校地合作伙伴關(guān)系,城市學(xué)校與當(dāng)?shù)厣鐓^(qū)、企業(yè)、非營(yíng)利組織等攜手,將課程內(nèi)容與學(xué)生社會(huì)生活相聯(lián)系,形成以學(xué)校為中心的區(qū)塊鏈模式的育人時(shí)空,以智慧課堂實(shí)現(xiàn)虛擬仿真實(shí)訓(xùn),構(gòu)建數(shù)字化育人場(chǎng)域,增強(qiáng)學(xué)生虛實(shí)融合的體驗(yàn)[26]。鄉(xiāng)村學(xué)校可以與當(dāng)?shù)貍鹘y(tǒng)產(chǎn)業(yè)聯(lián)手,建設(shè)有根性鄉(xiāng)土課程。如靜寧縣大寨小學(xué)基于鄉(xiāng)土鄉(xiāng)情以及“平?jīng)鼋鸸敝鳟a(chǎn)地的區(qū)位優(yōu)勢(shì),設(shè)立“蘋果谷”課程體系,以此培養(yǎng)學(xué)生跨學(xué)科的知識(shí)融合應(yīng)用能力,“發(fā)揮不同學(xué)科與學(xué)科組織要素間聯(lián)動(dòng)共生效應(yīng),形成可持續(xù)的學(xué)科交叉群落”[27]。同時(shí)學(xué)生也更加了解鄉(xiāng)村社會(huì)需求,為未來(lái)鄉(xiāng)村發(fā)展打下基礎(chǔ)。二是城鄉(xiāng)學(xué)校可以招募當(dāng)?shù)貙I(yè)技能人才建設(shè)課程。在面對(duì)城鄉(xiāng)學(xué)校整體缺乏專業(yè)學(xué)科教師窘境時(shí),城鄉(xiāng)學(xué)校可以向下深度探尋。如懷柔區(qū)九渡河鄉(xiāng)村小學(xué),校長(zhǎng)提出“鄉(xiāng)村合伙人”計(jì)劃,讓當(dāng)?shù)啬芄で山车娜藚⑴c到學(xué)校課程建設(shè)中來(lái),豐富了學(xué)校的綜合課程。
(四)家校社共育戰(zhàn)略:加強(qiáng)家校社協(xié)同育人,關(guān)注個(gè)體個(gè)性發(fā)展
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需要內(nèi)外部共同合力推進(jìn),家庭教育作為內(nèi)部教育的第一生長(zhǎng)點(diǎn),潛移默化地影響學(xué)生的思想道德和價(jià)值觀的樹立;學(xué)校教育作為外部教育的首要催化器,在于通過促進(jìn)人的社會(huì)化,為個(gè)體的個(gè)性發(fā)展打下基礎(chǔ);社會(huì)教育作為外部教育的“第二責(zé)任田”,對(duì)家庭教育和學(xué)校教育起著監(jiān)督和補(bǔ)充的作用。2021年,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在《一起重新構(gòu)想我們的未來(lái):一種新的教育社會(huì)契約》的報(bào)告中指出,重新構(gòu)想學(xué)校,使人在不同文化和社會(huì)空間中接受教育的機(jī)會(huì)。因此,建構(gòu)家校社育人共同體,健全多方面育人體系,是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重要舉措。
第一,校社推動(dòng)家長(zhǎng)育人理念更新。家長(zhǎng)的育人理念更新是學(xué)生得以實(shí)現(xiàn)全面發(fā)展的關(guān)鍵,然而城鄉(xiāng)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水平存在較大差異[28]。學(xué)校應(yīng)開設(shè)家庭教育指導(dǎo)服務(wù)的數(shù)字化平臺(tái),配備專業(yè)型家庭指導(dǎo)教師,針對(duì)城鄉(xiāng)家庭提供相應(yīng)的教育內(nèi)容。城鄉(xiāng)社區(qū)要建立專門的家庭教育網(wǎng)站。城市社區(qū)可以邀請(qǐng)專家、教育者和成功家長(zhǎng)開展線上講座。鄉(xiāng)村社區(qū)可以組織家庭教育相關(guān)的比賽和活動(dòng),鼓勵(lì)家庭參與,激發(fā)家長(zhǎng)和孩子的興趣和參與度,以此實(shí)現(xiàn)家庭育人理念的更新。
第二,學(xué)校建全家校育人制度。為使家校合作更加規(guī)范化,城鄉(xiāng)義務(wù)學(xué)校要建立家校協(xié)同制度。一方面,學(xué)校要允許家長(zhǎng)參與到學(xué)校管理、制度、文化和課程的建設(shè),幫助家長(zhǎng)了解學(xué)校的教育目標(biāo)和方法,學(xué)習(xí)先進(jìn)育人思想。另一方面,學(xué)校要做好家長(zhǎng)委員會(huì)的指導(dǎo)工作,搭建好溝通渠道,確保學(xué)校與家長(zhǎng)之間的雙向及時(shí)有效的反饋暢通。
第三,政府設(shè)立協(xié)同育人評(píng)估機(jī)制。首先,政府要建立健全家校社協(xié)同育人評(píng)估的政策文件和指導(dǎo)方針,提供具體的實(shí)施指導(dǎo)。其次,要成立專門的家校社協(xié)同育人評(píng)估機(jī)構(gòu)或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規(guī)劃、組織評(píng)估工作開展。綜合性的評(píng)估工作涵蓋學(xué)校、家庭和社會(huì)三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包括學(xué)生五育的發(fā)展、家庭的支持、社區(qū)資源等多個(gè)方面的指標(biāo)和維度。最后,政府要完善數(shù)據(jù)收集和分析系統(tǒng),及時(shí)獲取評(píng)估結(jié)果,為政府決策、學(xué)校改進(jìn)和家庭教育提供依據(jù)。
參考文獻(xiàn):
[1] 習(xí)近平.高舉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國(guó)家而團(tuán)結(jié)奮斗[N].人民日?qǐng)?bào),2022-10-26(01).
[2] 中共中央國(guó)務(wù)院.中共中央國(guó)務(wù)院印發(fā)中國(guó)教育現(xiàn)代化2035[N].人民日?qǐng)?bào),2019-02-24(01).
[3] 周海濤,王藝鑫等.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的多維思考(筆談)[J].吉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2,43(4):72-89.
[4]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5] 胡耀宗,馬立超.基于系統(tǒng)分析的教育政策工具配置模型構(gòu)建[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21,(2):48-54.
[6] 馮建軍.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的理論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3,42, (1):84-94+61.
[7]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教育部.2019年全國(guó)義務(wù)教育均衡發(fā)展督導(dǎo)評(píng)估工作報(bào)告[EB/O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1997/sfcl/202005/ t20200519_456057.html,2020-05-19.
[8] 教育部課題組.深入學(xué)習(xí)習(xí)近平關(guān)于教育的重要論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9] 習(xí)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奪取新時(shí)代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偉大勝利[N].人民日?qǐng)?bào),2017-10-28(01).
[10] 張志勇,任晶惠.轉(zhuǎn)型中的治理與治理的轉(zhuǎn)型——民辦義務(wù)教育發(fā)展難題及其破解[J].貴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2,(4):48-58.
[11] 石鷗,何孟珂.“雙減”背景下中考改革的目標(biāo)訴求與行動(dòng)框架[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22,(11):1-9.
[12] 周劉波,張夢(mèng)瑤等.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背景下教師數(shù)字素養(yǎng)培育:時(shí)代價(jià)值、現(xiàn)實(shí)困境與突破路徑[J].中國(guó)電化教育,2023,(10):98-105.
[13] 成剛,杜思慧等.集團(tuán)化辦學(xué)對(duì)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質(zhì)量的影響研究——基于中國(guó)教育追蹤調(diào)查的實(shí)證分析[J].教育經(jīng)濟(jì)評(píng)論,2022,7(2):65-84.
[14] 李森.新型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我國(guó)鄉(xiāng)村教育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困境與戰(zhàn)略選擇[J].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41(4):98-105+191.
[15] 鄔志輝.中國(guó)農(nóng)村教育發(fā)展報(bào)告2020-2022[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22.12.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教育部.2021年全國(guó)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EB/OL].2022-09-14.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209/t20220914_660850.html.
[17] 白文倩,徐晶晶.義務(wù)教育信息化資源配置均衡性研究——基于2001~2018年《中國(guó)教育統(tǒng)計(jì)年鑒》數(shù)據(jù)分析[J].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2019,29 (10):108-114.
[18] 張鴻翼,李森.西部地區(qū)農(nóng)村小學(xué)教師結(jié)構(gòu)性缺編現(xiàn)狀調(diào)查研究——基于川、渝、滇、黔等六省市區(qū)的實(shí)證分析[J].云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51(3):100-109.
[19] 陳亮,商一杰.大學(xué)超學(xué)科研究:理論內(nèi)涵、實(shí)踐路徑與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J].西北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2,(3):43-54.
[20] 孫偉平,趙寶軍.信息社會(huì)的核心價(jià)值理念與信息社會(huì)的建構(gòu)[J].哲學(xué)研究,2016,(9):120-126+129.
[21] 褚宏啟.城鄉(xiāng)教育一體化:體系重構(gòu)與制度創(chuàng)新——中國(guó)教育二元結(jié)構(gòu)及其破解[J].教育研究,2009,30(11):3-10+26.
[22] 李廣舜.國(guó)內(nèi)外城鄉(xiāng)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研究成果綜述[J].地方財(cái)政研究,2006,(2):22-25.
[23] 岳偉,王仙紅.校長(zhǎng)文化建設(shè)焦慮:表征、成因與調(diào)適路徑[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22,(5):74-81.
[24] 張妮,穆佳男等.智能時(shí)代義務(wù)教育優(yōu)質(zhì)均衡發(fā)展路徑研究——以“三個(gè)課堂”為支撐[J].中國(guó)電化教育,2022,(12):18-26.
[25] 范涌峰,張輝蓉.學(xué)校特色發(fā)展:新時(shí)期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一體化的內(nèi)生路徑與發(fā)展策略[J].教育研究與實(shí)驗(yàn),2019,(5):70-75.
[26] 曲嬌嬌,高春梅.數(shù)字化賦能:校長(zhǎng)信息化領(lǐng)導(dǎo)力的時(shí)代指向與提升策略[J].中國(guó)電化教育,2022,(12):129-135.
[27] 陳亮,李文健.學(xué)科集群與城市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沖突限制與優(yōu)化策略——互動(dòng)式治理理論視角[J].高校教育管理,2023,(4):24-37.
[28] 廖婧茜,龔洪.家校社協(xié)同育人的責(zé)任倫理[J].民族教育研究,2023,34 (1):13-20.
作者簡(jiǎn)介:
李森: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yàn)檎n程與教學(xué)論、教師教育、鄉(xiāng)村教育。
王雪瑋:在讀碩士,研究方向?yàn)檎n程與教學(xué)論。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Strategic Choice of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Li Sen, Wang Xuewei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Abstract: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a new goal and a new task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 two closely linked dynamic processes that are interdependent,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integrated. Due to the long-standing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social cultur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China is still facing the dilemmas of utilitarian evalu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superficial collaborat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los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unequal input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dilemma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lue guidance, policy promo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tendency, and then build a logical structure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 as to provide strategic choice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s compulsory education.
Key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11日
責(zé)任編輯:趙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