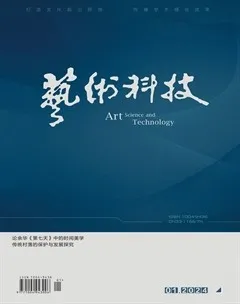論王小帥現(xiàn)代化主題影像空間建構(gòu)
摘要:目的:作為“第六代導演”之一的王小帥,其電影作品有著鮮明的個人印記和空間意識。例如,很少采用三段體敘事、零散化敘事和主客觀視點自由轉(zhuǎn)換等敘事手法,從不讓技巧脫離故事內(nèi)容,形成喧賓奪主的場面,而是依托起伏較大的故事情節(jié)和意想不到的節(jié)奏切分來講述故事。同時,他的電影熱衷于表達個人和時代記憶。王小帥的電影敘事模式,著重通過人與人、人與城市之間的沖突來表現(xiàn)底層邊緣群體與社會環(huán)境的格格不入,并由此揭示邊緣人群與社會環(huán)境難以協(xié)調(diào)的深層原因。在他的《青紅》《我11》和《闖入者》三部曲中,通過多重空間的疊加,表征了早期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進程中存在的貧富差距大、城市異化和城鄉(xiāng)矛盾等問題。方法:文章通過分析記憶空間、社會空間和城鄉(xiāng)空間,觀照中國式現(xiàn)代化之路的發(fā)展歷程。結(jié)果:通過分析王小帥電影所表征的社會問題,揭示現(xiàn)代化繁華背后的創(chuàng)痛和生活的殘酷,將隱匿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背后的矛盾以原生態(tài)的方式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結(jié)論:王小帥在電影里通過對記憶空間、社會空間和城鄉(xiāng)空間的建構(gòu),書寫了社會底層邊緣群體孤獨和迷茫的精神狀態(tài),表現(xiàn)了城市底層民眾頑強的生命力,其影像空間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意蘊。
關(guān)鍵詞:王小帥;電影;記憶空間;權(quán)力空間;城市空間;現(xiàn)代性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1-0-03
伴隨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一方面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水平、人民的物質(zhì)生活水平顯著提升,城市面貌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另一方面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和題材選擇也受到影響。王小帥的電影堅持“以人民為創(chuàng)作導向”的理念,以人民為主體,觀照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1]。他的電影在書寫人民性的同時,還注重建構(gòu)影像空間。在其電影作品中,空間不僅是生產(chǎn)資料的對象和載體,也是社會實踐的產(chǎn)物,它既是社會關(guān)系的容器,又是能夠被感知的生活空間,具有人的屬性,是蘊含精神屬性的物質(zhì)空間。
1 記憶空間:集體記憶的建構(gòu)與消解
“集體記憶又稱群體記憶”[2],哈布瓦赫指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gòu)的概念”[3]。王小帥的父母是“三線建設”的一員,他一出生就隨父母來到貴州進行“三線建設”。作為“三線建設”群體成員的王小帥,對過去回憶的再現(xiàn)是對“三線”集體記憶的一種懷舊和建構(gòu)。電影
《我11》中通過煤球爐子和爐上的鋁制水壺、穿著中山裝的男主人公和戴著碎花套袖的女主人公、鳳凰牌自行車、臺式收音機等,真切還原了過去家庭空間的生活場景。工廠墻面上的標語和廣播、對人們行為的規(guī)訓還原了以前工人工作的日常。王小帥立足當下,通過復刻過去工業(yè)廠區(qū)空間和再現(xiàn)工人日常家庭生活,還原了一段遠去的集體記憶。老物件的出現(xiàn)營造了電影的真實感,也使電影故事敘事變得更加可靠。
工人的身份問題也在集體記憶的構(gòu)建中被反復呈現(xiàn),凸顯了他們對身份的焦慮。在《青紅》中,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工人的社會身份地位發(fā)生變化,失去了往日的榮光。老吳對自己的身份產(chǎn)生了焦慮,他迫切地想要回到上海,哪怕是失去工廠的“鐵飯碗”。《我11》里,當“三線建設”的榮光褪去后,謝覺強的父親同樣產(chǎn)生了想要調(diào)回上海的迫切渴望。產(chǎn)生身份焦慮的深層原因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出現(xiàn)了問題,三線建設者一般來自經(jīng)濟較發(fā)達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初到建設地產(chǎn)生的心理落差,加上氣候、語言和飲食等差異,造成了三線建設者和當?shù)鼐用裰g的區(qū)隔。在電影中,很少看到三線建設者與當?shù)鼐用窠煌麄兓径际呛屯后w展開交流。王小帥的電影主要表現(xiàn)的是隨著改革開放和國家經(jīng)濟政策調(diào)整,“三線建設”不再受到大幅度的宣傳和頌揚,大量三線工廠開始面臨虧損甚至破產(chǎn)的命運,因此很多三線建設者紛紛想回歸大城市。個體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變動和主觀階級認同,都是電影中三線建設者難以產(chǎn)生身份認同的原因。
王小帥的“三線”電影營造出種種近乎真實的歷史幻象,重現(xiàn)了過去“三線建設”的歷史給觀眾帶來的懷舊體驗。在懷舊中王小帥再現(xiàn)了曾經(jīng)三線建設者的艱苦奮斗和社會轉(zhuǎn)型下個體產(chǎn)生的身份問題及其精神上的迷惘與痛苦,也讓“三線”歷史得以流傳和被銘記。
2 社會空間:社會秩序的建構(gòu)
空間是權(quán)力運作的基礎,也是對個人進行規(guī)訓的執(zhí)行場所。規(guī)訓是一種社會權(quán)力,在王小帥建構(gòu)的社會權(quán)力空間中,充滿了集體規(guī)訓個人的符號。在
《我11》中,王憨一家因“三線建設”從上海來到西南山區(qū),電影從王憨這個無憂無慮的11歲小孩的視角,講述了一起“殺人事件”。電影開頭的十字路口有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畫像,在王憨父親送王憨上學途中經(jīng)過的墻上寫著“為人民服務”的標語;工廠大門上寫著“聽毛主席話,跟共產(chǎn)黨走”的對聯(lián),這些符號都在暗示當時是紅色革命年代。《地久天長》中,廠里的“為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的標語,“優(yōu)生優(yōu)育”的宣傳告示,以及劉耀軍和王麗云害怕懷二胎被發(fā)現(xiàn)的對話,都在告訴觀眾當時正處于嚴格實行計劃生育的年代,擁有屬于自己的孩子需要國家政策同意。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人們的活動以工廠大院的集體為單位,個人的任何活動都要服從集體的安排,工廠大院規(guī)訓著人們的行為和作息時間。在電影《青紅》和《我11》中,工廠以廣播為媒介,嚴格管控個體的工作和學習時間。時間的規(guī)劃是對人們?nèi)粘P袨榱晳T和生活方式的規(guī)訓,人們的任何行為都要服從工廠的軍事化管理,個人的行為習慣和私人感情也要讓位于工廠的生產(chǎn)目標。
工廠嚴格的軍事化管理,產(chǎn)生于特定的時代背景,當時的中國正面臨緊張的國際局勢,而且工業(yè)結(jié)構(gòu)分布不均,大部分分布在東北和華北一帶,為了保障國防安全,國家開展了一場大規(guī)模推進西部工業(yè)化的運動,也就是“三線建設”運動。這場運動應用勞動密集型策略,動員許多工人參與建設。為了加強人員管理,按時完成生產(chǎn)任務,工廠會對工人進行任務劃分、行為規(guī)訓與監(jiān)督和時間的管控。
集體對個人行為的規(guī)訓,有利于整合分散的個人力量,提高群體的生產(chǎn)力,同時也有利于建構(gòu)社會秩序。“社會秩序表示社會有序狀態(tài)或動態(tài)平衡的社會學范疇”[4],“在馬克思的共同體思想中,社會秩序是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tǒng)一,共同體是對社會秩序的經(jīng)濟、政治特性進行總體性和關(guān)聯(lián)性的把握”[5]。在王小帥構(gòu)建的權(quán)力空間中,社會秩序的建構(gòu)不僅依靠集體規(guī)訓,更重要的還在于個體自覺。三線建設者基于國家需要,自覺投身祖國建設事業(yè),他們有共同的價值信仰規(guī)范,把集體目標當作自己的目標。來自五湖四海的三線建設者成為一個共同體,其對共同體的認知增強了群體凝聚力,有利于構(gòu)建和諧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
“權(quán)力可以通過一套精心設計的系統(tǒng)性空間知識形態(tài)(城市規(guī)劃話語的形成、空間建筑范式的塑造、空間建筑元素的象征性與符號性表達)來創(chuàng)建自身的話語機制,從而完成將空間、人口、生命技術(shù)、組織制度融為一體的社會治理。”[6]王小帥建構(gòu)的權(quán)力影像空間,呈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早期的工業(yè)化管理和監(jiān)督模式。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個人與集體的命運融為一體,集體對個人的權(quán)力規(guī)訓既是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又是達到生產(chǎn)目標的要求。
3 城鄉(xiāng)空間:現(xiàn)代化書寫與社會互嵌
工業(yè)化的出現(xiàn)打破了封閉的農(nóng)業(yè)社會組織,它要求人具有新的角色和功能。在變化和流動的工業(yè)社會中,個體不可能永遠待在一個封閉、僵化的環(huán)境里,鄉(xiāng)村中的家庭集體經(jīng)濟組織受到?jīng)_擊,加上城市化發(fā)展對鄉(xiāng)村土地的侵占以及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加速了鄉(xiāng)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王小帥的城市影像空間展示了農(nóng)村外出務工人員在城市遭受的種種不公待遇。例如影片《十七歲的單車》中的小貴,他從偏遠貧窮的鄉(xiāng)村來到城市務工,丟了公司配置的自行車,在尋找自行車的過程中遭受了來自城市的惡意和排擠。再如《扁擔·姑娘》中的高平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被騙錢,最后丟了性命。鄉(xiāng)村人員雖然進入了城市,但是很難真正融入城市,這是因為鄉(xiāng)村與城市之間存在隔閡,其中最明顯的便是身份隔閡。“1958年,我國新的戶籍制度建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被嚴格限制,這種充滿矛盾的、等級制的城鄉(xiāng)戶籍既分割了兩種社會生產(chǎn)和生活,也分割了權(quán)利。”[7]戶籍制度造成了資源向城市傾斜,城市居民擁有更多優(yōu)于農(nóng)村居民的權(quán)利,而這也造成了城市與鄉(xiāng)村居民身份權(quán)利的不平等。
身份權(quán)利上的不平等導致進城務工人員產(chǎn)生身份焦慮,如《扁擔·姑娘》中的高平來到城市打工,即使自己沒有錢也給自己買了一套西裝;《十七歲的單車》中周迅飾演的保姆,經(jīng)常趁主人不在時偷穿主人的裙子和高跟鞋。對他們來說,亮麗的衣服是城市身份的象征,可以掩蓋自己來自農(nóng)村的身份,從而建構(gòu)自我身份認同。王小帥電影中的人物在建構(gòu)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往往是以他者為鏡,而城市居民就是王小帥的城市影像空間中的“他者”。高平、阮紅和小貴等進城務工人員以城市居民為鏡,進行行為模仿和裝扮,達到自我身份認同。在王小帥呈現(xiàn)的城市影像空間中,這種身份焦慮不僅存在于農(nóng)村居民群體中,還存在于城市居民群體中。例如《十七歲的單車》中的小堅一直生活在城市,為了擁有其他伙伴也擁有的自行車,不惜偷錢買車。自行車在這里是家庭財富的象征,能遮掩小堅家庭并不富裕的現(xiàn)實,達到維護自我形象的目的。
工業(yè)主義催生的現(xiàn)代化大都市以貨幣經(jīng)濟為主導,這激發(fā)了都市人對貨幣的狂熱追逐。王小帥建構(gòu)的城市空間表征了金錢對人的異化。例如,《扁擔·姑娘》中,“扁擔”們?yōu)榱私疱X而互相殘殺;《十七歲的單車》中,小堅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偷錢買自行車。金錢對人的異化導致人們精神空間的疏離。“受貨幣經(jīng)濟工具理性的影響,現(xiàn)代主體的心靈也被物質(zhì)文明所‘異化’。主體的生活內(nèi)容由此發(fā)生改變,即排斥了非理性的、本能的特質(zhì)和主觀獨斷的沖動,也就排除了情緒化的體驗。”[8]理性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核心觀念,現(xiàn)代社會組織的內(nèi)在脈絡就是理性。理性強調(diào)效率,而效率是現(xiàn)代城市發(fā)展所追求的目標。在《十七歲的單車》中,小堅所工作的快遞公司為員工配備新自行車,就是為了更快地將信件送到收信人手中;《扁擔·姑娘》中的高平選擇不正當?shù)馁嶅X方式,也是因為這種方式來錢快。在快節(jié)奏生活的催壓下,城市空間中的人際關(guān)系變得膚淺、短暫和淡薄。當樸實、善良的農(nóng)村外出務工人員來到與鄉(xiāng)村環(huán)境截然相反的城市時,很難在城市中得到他人的幫助,遑論融入其中。他們基本都是同鄉(xiāng)間互幫互助,如《扁擔·姑娘》中冬子帶著一根扁擔,只身來到武漢,投奔先來此地的同鄉(xiāng)兼好友高平;《十七歲的單車》里,小貴與老鄉(xiāng)一起住;等等。
城市林立的高樓大廈和鮮明的區(qū)域分割,使得城市物理空間變得狹小,無形之中拉開了主體間的精神距離。城市中的人在空間上的距離雖近,但在心理與精神方面卻相隔甚遠。城市主體間的精神疏離與傳統(tǒng)鄉(xiāng)村和諧的人際交往恰恰相反,這導致進入城市的農(nóng)村居民很難適應這種人際交往方式。同時,城市快節(jié)奏的生活方式也很難讓農(nóng)村外出務工人員的心聲得到傾聽。因此,在王小帥建構(gòu)的城市空間中,農(nóng)村外出務工人員通常是沉默不語的,就算被誤會也不會開口解釋,沉默的外來人員成了城市里的“異鄉(xiāng)人”。
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的隔閡,主要源自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的對立矛盾。現(xiàn)代文明沖擊著傳統(tǒng)鄉(xiāng)村文化,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發(fā)展更是加深了城鄉(xiāng)隔閡。王小帥的城市空間電影表征了城市異化和城鄉(xiāng)發(fā)展失衡的問題。面對城市異化問題,需要遵循城市主體性原則,城市發(fā)展需要與自然共存、與環(huán)境共存。針對城鄉(xiāng)發(fā)展失衡問題,國家提出了多項問題解決對策,如實行免農(nóng)業(yè)稅、新農(nóng)村建設等措施,以此促進鄉(xiāng)村全面振興。城市和鄉(xiāng)村應是互相依存、和諧共生的關(guān)系,城鄉(xiāng)應實現(xiàn)融合發(fā)展。
4 結(jié)語
王小帥建構(gòu)的影像空間以現(xiàn)代化為主題,記錄了早期中國工業(yè)化建設運動——“三線建設”,再現(xiàn)了三線建設者在特定年代的心路歷程和面臨的人生困境。同時,他也關(guān)注到了城市化進程中城市邊緣群體和城市異鄉(xiāng)人的境遇和感受。王小帥的影像空間聚焦現(xiàn)代化進程中人的現(xiàn)代性感受,表征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進程中出現(xiàn)的社會問題和對人精神空間的忽略。其現(xiàn)代化主題影像空間敘事,是認識現(xiàn)代化的一種方式,即通過對現(xiàn)代化背景下個體生命的書寫,反思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過程中的現(xiàn)實問題。這些問題在電影中隨著沒有結(jié)尾的敘事而留置,促使人們?nèi)ニ伎荚鯓痈玫赝七M現(xiàn)代化發(fā)展。
參考文獻:
[1] 索杰.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陸揚,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7.
[2] 高萍.社會記憶理論研究綜述[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113.
[3] 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4] 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353.
[5] 磨胤伶,王坤.個人化社會的社會秩序何以可能:馬克思共同體視閾下的社會秩序建構(gòu)[J].廣西社會科學,2020(8):86.
[6] 張羽佳.權(quán)力、空間知識型與烏托邦[J].探索與爭鳴,2016(8):84.
[7] 姚尚建.城市身份的權(quán)利附加[J].行政論壇,2018,25(5):27.
[8] 鄧志文.城市精神空間的生態(tài)反思及其重塑的實踐路徑[J].云南社會科學,2021(2):182.
作者簡介:李婷婷(1998—),女,江西南昌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當代文學與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