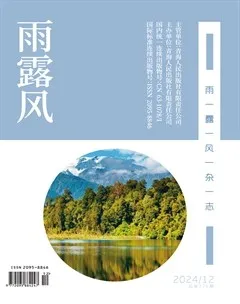一段酣暢淋漓的夢游

魯迅的《死火》是其1925年創(chuàng)作的散文詩,后收入《野草》。《野草》是中國現(xiàn)代散文詩走向成熟的第一個里程碑,是在中國現(xiàn)代散文詩的發(fā)展中具有開山意義的作品。魯迅的《死火》是一篇充滿象征和隱喻的散文詩,通過描述一個夢境中的場景,魯迅以“死火”為象征,表達(dá)了他對生命、熱情、希望以及革命理想的獨(dú)特思考。在《死火》中,魯迅描繪了一個冰冷、荒蕪的冰山冰谷,這個環(huán)境象征著冷酷、絕望的外部世界,同時也映射出作者內(nèi)心深處對于現(xiàn)實(shí)的感受。在這個環(huán)境中,主人公發(fā)現(xiàn)了一團(tuán)“死火”,這團(tuán)火雖然被冰封,但仍然保持著火焰的形態(tài),這象征著被遺忘、被遺棄的革命力量,雖然暫時處于低潮,但它的本質(zhì)并未改變,仍然具有燃燒的熱情和力量。《死火》描寫了兩個孤獨(dú)的靈魂一次短暫的相遇,暗含著三種不同的內(nèi)涵。
一、一次短暫的相遇
魯迅的《死火》最開始以散文詩中主人公“我”的夢為發(fā)端,夢見自己在冰山間奔馳。夢境是作者寄托心志的一種方式,在夢境中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夢境也能在無意識中滿足人們現(xiàn)實(shí)中的遺憾。在我國諸多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中,夢境作為一種特有的情節(jié)連接著現(xiàn)實(shí)生活。比如湯顯祖在《牡丹亭》中,就將做夢發(fā)揮到極致,杜麗娘通過夢發(fā)現(xiàn)了情。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中有許多緣起來自一場夢,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等,都使整個《紅樓夢》籠罩在一種如夢似幻、半假半真、半虛半實(shí)的氛圍中。作為能將古代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巧妙融為一體的作家,魯迅在創(chuàng)作《死火》時也利用夢作為發(fā)端,一開始就奠定了天馬行空、真假難辨的環(huán)境基調(diào)。
中西方對夢都進(jìn)行過研究。中國古代關(guān)于夢境意象解讀的書籍就有《周公解夢》《敦煌解夢書》等,而西方關(guān)于夢境意象解讀的書籍有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等。弗洛伊德認(rèn)為:“夢,并不是空穴來風(fēng),它不是毫無意義的,不是荒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識的昏睡,而只有少部分是乍睡乍醒的產(chǎn)物。它完全是有意義的精神現(xiàn)象。實(shí)際上,是一種愿望的達(dá)成。它可以算作是一種情形狀態(tài)精神活動的延續(xù)。它是由高度錯綜復(fù)雜的智慧活動所產(chǎn)生的。”[1]弗洛伊德認(rèn)為夢是有意義的。《死火》中的夢也是如此,盡管作者以夢作為故事開篇的背景,但這個夢可以完全與現(xiàn)實(shí)相連。在《周公解夢》中,夢到冰山通常預(yù)示著人會碰到十分棘手的難題,也許是強(qiáng)大的對手,也許是工作中極大的阻礙,并且冰山遠(yuǎn)比人預(yù)想的還要可怕,形勢或許比人已知的還惡劣。所以《周公解夢》給出的建議是:人必須學(xué)會冷靜地思考,只要堅(jiān)定明確和小心謹(jǐn)慎地處理,人們是有可能繞過它的。
冰山的意象本應(yīng)是冷漠而孤獨(dú)的,而“我”夢里的冰山跟普通的冰山又有所區(qū)別。冰山周圍的環(huán)境空曠且潔白,放眼望去,冰山卻并非一望無際的白,天空也并非一望無際的空,冰山的山麓會有冰樹林點(diǎn)綴,天空也有如魚鱗模樣的凍云,也因此減去了冷寒的特點(diǎn),更添了些生機(jī)和暖意。接下來是“我”與“死火”的相遇,“我”們相遇在冰谷中,冰谷給人的印象通常是絕望而又惶然的,尤其是在陌生環(huán)境中,環(huán)境又是如此冷寒。而在魯迅的描寫下,此時冰谷的環(huán)境仍舊冰冷且伴隨著青白,為什么是青白的呢?也許是由于冰谷反射的光導(dǎo)致“我”短暫性地患上雪盲癥,看到的紅影有可能是眼球經(jīng)過強(qiáng)大刺激后投射的陰影,青白與紅影共同營造出極具沖擊力的畫面。在這樣極具張力的環(huán)境中,“我”和“死火”相遇了。
死火和一般的火焰也不同。由于在冰谷中被凍結(jié),死火只有“炎炎的形”,尖端還有黑煙。火焰按理來說也是無法被凍結(jié)的,而死火被凍結(jié)違背了生活常識,魯迅用陌生化手法將火焰的熱和冰谷中的寒碰撞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纏綿狀態(tài)。死火經(jīng)歷了“如珊瑚網(wǎng)”“像珊瑚枝”“成紅珊瑚色”“如紅彗星”四個狀態(tài),也代表著死火的生命歷程,生命力由最開始的旺盛到最后的消逝,死火的顏色也由紅珊瑚色的濃烈轉(zhuǎn)變成紅彗星的寥落,歷史悠長的死火就在悄無聲息中隕落,就像“我”最后被碾死的結(jié)局一樣。死火醒來后面臨著凍滅和燒完的兩難選擇,而“我”不愿意接受這種必死的結(jié)局,并與這既定的結(jié)局抗?fàn)帲欢阑鹱詈筮€是為了拯救“我”燃燒自己,“我”雖被碾死,但依舊不服輸,將向命運(yùn)的抗?fàn)幘窨淘谧约旱墓撬枥铮詈蟀l(fā)出嘲弄。
二、兩個孤獨(dú)的靈魂
“我”與死火在對話中互相認(rèn)識。魯迅在“我”與死火相遇后描寫了我幼小時期的心境,幼小時“我”愛看快艦激起的浪花,洪爐噴出的火焰,因?yàn)樗鼈兪莿討B(tài)的,且轉(zhuǎn)瞬即逝又瞬息變化,可“我”如今長大了,對一切瞬息變化的事物都沒有像當(dāng)初那么喜愛,正因?yàn)槟切┦挛锼蚕⒆兓浴拔摇笨偸亲ゲ蛔∧切〇|西,也無法看清它們本來的樣子。而死火不同,因?yàn)樗阑鸨槐鶅鲎。运阑鹗遣蛔兊模耆梢钥吹狡湫螒B(tài),也很容易看到它的內(nèi)心,是“我”可以抓住的,這體現(xiàn)了“我”的成長,小時候孩子們大多會追求不可得之物,而長大后為了穩(wěn)定則會追求能夠掌握在手中之物。所以死火對“我”有著強(qiáng)烈的吸引力,這也是“我”拿走死火的原因。“我拾起死火,正要細(xì)看,那冷氣已使我的指頭焦灼”,在這一句話中,冷氣與焦灼搭配,魯迅用陌生化的手法強(qiáng)調(diào)這一焦灼的感受過程。陌生化理論是什克洛夫斯基1916年在其作品《作為手法的藝術(shù)》中提出的,是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理論。在《藝術(shù)作為手法》中,什克洛夫斯基指出:“為了恢復(fù)對生活的感覺,為了感覺到事物,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存在著一種名為藝術(shù)的東西。藝術(shù)的目的是提供作為視覺而不是作為識別的事物的感覺;藝術(shù)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變的模糊、增加感覺的困難和時間的手法,因?yàn)樗囆g(shù)中的感覺行為本身就是目的,應(yīng)該延長;藝術(shù)是一種體驗(yàn)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東西對藝術(shù)來說是無關(guān)重要的。”[2]他認(rèn)為:“藝術(shù)中的感覺行為本身就是目的。”[2]所以將文本進(jìn)行陌生化的處理有利于體現(xiàn)出其中的感覺行為,在《死火》中也就是突出“我”拾起死火的特殊感覺。這是冰與火融合在一起的特殊感覺,魯迅用一種細(xì)膩的語言、敏感的體驗(yàn)將這種特殊感覺清晰地表達(dá)出來,由此可以體現(xiàn)出魯迅高超的寫作筆法和敏感細(xì)膩的情感。
“我”將死火放入口袋,“我”的溫?zé)釂拘蚜怂阑穑阑鸫藭r正在燃燒,“我”身上的衣物也正在被死火燃燒,可“我”絲毫沒有要將死火放下的想法,“我”倔強(qiáng)地想著將死火帶出冰谷,貪戀死火帶來的新奇和溫暖,死火給予“我”出冰谷的極大渴望。
死火醒來后,給“我”講述了它的來歷,原來死火是被人遺棄在這的,可以想到死火原本只是普通的火,之前在冰谷中可能也有其他的人,他們使用了死火,渡過了難關(guān)并且將死火永遠(yuǎn)留在了冰谷中,或許他們沒有遺棄死火,可能遭遇了不幸,最后在冰谷中掩埋了一切,只有死火永遠(yuǎn)存在下來。“我”是掉進(jìn)冰谷中的,而“我”并沒有遺棄它,反而想要和它一起走出冰谷,這對被遺棄過的死火來說是非常動容的。此時,在寒冷的冰谷中,只剩下“我”和死火,死火陪伴著“我”,“我”也是死火在被遺棄后的年歲中唯一遇見的人,兩個孤獨(dú)的靈魂此時相遇,成為彼此唯一的慰藉。
此時“我”與死火的對話構(gòu)造出了一個悖論的世界:“那么,怎么辦呢?”“但你自己,又怎么辦呢?”“我說過了:我要出這冰谷……”這一類矛盾的對話可以明顯地看出“我”身處夢境中產(chǎn)生的暈眩和模糊的感受,包括前文死火的答非所問。死火的兩種結(jié)局:一種是被“我”帶走,它將被燒完;另一種是留在冰谷,它將被凍滅,兩種結(jié)局都是必然消亡的結(jié)局,而死火兩種結(jié)局都沒選擇,它選擇瞬間燃燒自己送“我”出冰谷。
這是兩個孤獨(dú)的靈魂在不正確的地點(diǎn)和時間正確地會面,“我”與死火都是世間孤獨(dú)的一分子,死火犧牲自己送“我”出冰谷,這不僅是對“我”身體上的拯救,也是對我精神上的拯救。
三、三種不同的內(nèi)涵
(一)革命的態(tài)度
“死火”可以被看作是革命精神的象征,這是目前被許多人解讀最多的內(nèi)涵。從創(chuàng)作時間來看,《死火》完稿于1925年4月23日,此時的中國正處于危難之際,遭受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的雙重夾擊,整個社會動蕩不安、搖搖欲墜。而魯迅作為思想先進(jìn)的知識分子,從社會現(xiàn)象中看到了中國革命事業(yè)的艱難曲折,于是他以筆為矛直刺社會軟肋,扛起了作為作家的偉大責(zé)任,在需要鼓舞人們積極反抗、堅(jiān)持革命的時候挺身而出。相較于“我”,魯迅更像是死火,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yè)不懈奮斗,甘于奉獻(xiàn)自身。魯迅通過描述主人公拯救死火的過程,表達(dá)了自己愿意為革命事業(yè)獻(xiàn)身的犧牲精神。死火雖然被冰封,但仍然保持著火焰的形態(tài),這象征著革命精神雖然暫時處于低潮,但其本質(zhì)并未改變,仍然具有燃燒的熱情和力量。
(二)生命與死亡
無論是在梭羅的筆下,還是在梁遇春的想象中,“火”都是“熊熊燃燒”的“生命”的象征;而魯迅寫的是“死火”:面臨死亡而終于停止燃燒的火。魯迅不是從單一的“生命”的視角,而是從“生命”與“死亡”的雙重視角去想象火。這幾乎是獨(dú)一無二的。[3]在《死火》中,“我”在一場夢境中遇見死火,并愿意將死火一起帶出冰谷。冰谷象征著一場未知的冒險,是突如其來的奇遇,在傳統(tǒng)意義上,掉入無人且環(huán)境惡劣的冰谷,會丟失性命死亡。然而,在冰谷中“我”遇見了死火,這種火居然能被冰塊凍住,這讓“我”感到驚奇,也讓“我”看到了死火奇異的美麗,正是在這看似不可能中,死火的存在更讓“我”看到了走出冰谷的可能。因?yàn)橛鲆娝阑穑笳髦厮赖慕^境——冰谷,表現(xiàn)出生命的希望,所以最后是死火犧牲自己將“我”帶出了冰谷。這樣絕處逢生的過程象征著生命的過程,生命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會經(jīng)歷許多坎坷和不幸,但是最后都有化險為夷的可能性,正是因?yàn)橛腥缢阑鹨粯訝奚约旱娜嘶蛭铮拍茏屘幱诶щy中的人看到希望,最終鼓起勇氣戰(zhàn)勝困難。魯迅以“死火”作為象征,表達(dá)了他對生命和死亡的理解。無論死火選擇留在冰谷還是走出冰谷,最終的結(jié)果都是死亡,然而,死亡的意義卻截然不同。留在冰谷的死火將無聲無息地耗盡生命,而幫助“我”走出冰谷的死火則能在燃燒自己中發(fā)出燦爛的余輝,給人們帶來光明,讓生命顯現(xiàn)出它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是魯迅用一生所踐行的宗旨。
(三)奉獻(xiàn)
首先,從整體結(jié)構(gòu)上來看,《死火》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夢入冰谷、拯救死火、與死火的對話。這三個部分緊密相連,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在夢中,“我”墜入了冰谷,發(fā)現(xiàn)了死火,試圖拯救它并與其展開對話,使得整個故事充滿了荒誕色彩和象征意義,讓人深思。魯迅運(yùn)用了豐富的意象和象征手法。用“高大的冰山”“天上凍云彌漫”“冰樹林”等意象,營造出一個冰冷、荒涼的氛圍。“死火”這一象征則代表了被遺忘、被遺棄的革命力量,它雖然被冰封,但仍然具有燃燒的熱情和力量。又通過對死火的形象描繪和與死火的對話,表達(dá)了自己對革命事業(yè)的堅(jiān)定信念和犧牲精神,死火即使被冰封,它的形態(tài)仍然具有火焰的特征,表明革命力量雖然暫時處于低潮,但它的本質(zhì)并未改變。而“我”與死火的對話則進(jìn)一步揭示了革命事業(yè)的艱辛和重要性,“我”愿意攜帶死火走出冰谷,讓它永不冰結(jié),永得燃燒,這體現(xiàn)了“我”對革命事業(yè)的執(zhí)著追求和奉獻(xiàn)精神。同時,文本內(nèi)部的語言、結(jié)構(gòu)、意象等元素也相互呼應(yīng),構(gòu)成了一個和諧統(tǒng)一的藝術(shù)整體,展現(xiàn)了魯迅作為偉大文學(xué)家的卓越才華和深厚的藝術(shù)造詣。
四、結(jié)語
魯迅在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尖銳的筆觸、先進(jìn)的思想和細(xì)膩的表達(dá)使得他的作品猶如一把鋒利的匕首狠狠插入封建倫理道德社會的核心。而《死火》蘊(yùn)含著多種內(nèi)涵,也正是因?yàn)檫@一特征,《死火》一直被人們不斷研究和品味,卻很難對其下具體的論斷,也因?yàn)槊總€讀者的經(jīng)歷都各不相同,所解讀出的含義也有不同,《死火》含義不斷豐富,也造就了這樣一篇經(jīng)典性的作品。《死火》這篇散文詩既具有散文的情感自由又有著詩一樣精準(zhǔn)的語言,魯迅將散文和詩巧妙結(jié)合,賦予了《死火》獨(dú)特的結(jié)構(gòu)美和語言美,使其成為他散文詩中的代表性作品。
作者簡介:鄭小艷(2000 —),女,仡佬族,貴州石阡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閷W(xué)科教學(xué)(語文)。
注釋:
〔1〕弗洛伊德(S.Freud).夢的解析[M].丹寧,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2〕茨維坦·托多羅夫.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M].蔡鴻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9.
〔3〕錢理群.對宇宙基本元素的個性化想象——讀魯迅《死火》《雪》《臘葉》[J].蘇州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3(1):76-80,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