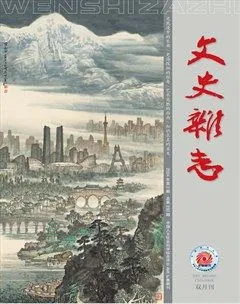司馬遷的“蒙太奇”
張昊蘇?陳熹
摘 要:《史記·刺客列傳》描寫(xiě)“荊軻刺秦王”一段,具有豐富的動(dòng)作細(xì)節(jié),猶如電影的“分鏡劇本”,給人極強(qiáng)的畫(huà)面感,可以視為文言寫(xiě)作的“蒙太奇”。司馬遷如果生在當(dāng)代,當(dāng)是善于營(yíng)造鏡頭場(chǎng)面的電影大師。
關(guān)鍵詞:《刺客列傳》;動(dòng)作信息;長(zhǎng)鏡頭;原始面貌
在162分鐘的電影大作《荊軻刺秦王》(1998年陳凱歌導(dǎo)演作品)中,陳凱歌以9分半的長(zhǎng)度表現(xiàn)荊軻在秦庭的刺殺經(jīng)過(guò)——這也許可以代表多數(shù)人的認(rèn)知:“刺殺”本身固然是《刺客列傳》“荊軻傳”的高潮,但因?yàn)樘^(guò)耳熟能詳,反而可以用簡(jiǎn)省的方式來(lái)講述。于是,司馬遷在文本原作描寫(xiě)這一段時(shí)所運(yùn)用的文章筆法,就容易在一般閱讀時(shí)被忽略。
讓我們重返《史記·刺客列傳》那刺殺高潮時(shí)刻的現(xiàn)場(chǎng):
秦王發(fā)圖,圖窮而匕首見(jiàn)。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zhǎng),操其室。時(shí)惶急,劍堅(jiān),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huán)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zhí)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shí),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
這一段描寫(xiě)千百年來(lái)為世所稱(chēng)道,今天重讀,仍然有如在目前的“即視感”。在司馬遷細(xì)致而富于節(jié)奏的筆調(diào)之下,我們?nèi)阅苊靼椎乩斫獗藭r(shí)的來(lái)龍去脈,感受到一時(shí)的緊張刺激。《史記》的善于“講故事”為人所熟知,然而在流傳兩千年的文字背后,我們需要更細(xì)致地考察,它“生動(dòng)”的秘密何在?
我們今天所謂“描寫(xiě)”,本來(lái)就是指用語(yǔ)言指引讀者還原事件,是文學(xué)寫(xiě)作的基本手段。《史記》的時(shí)代并沒(méi)有攝錄機(jī),這些生動(dòng)描寫(xiě)當(dāng)然多少有賴(lài)于歷史敘述者的主觀(guān)想象。從這個(gè)角度推想早期著作中“文”“史”之邊界,追究細(xì)節(jié)描寫(xiě)是否有確據(jù)可能未必重要(也缺乏操作性),關(guān)鍵是理解特定描寫(xiě)令人想來(lái)逼“真”的原理。
重讀荊軻刺秦王的描寫(xiě),一個(gè)鮮明的特色是連續(xù)的細(xì)碎的動(dòng)作。“秦王發(fā)圖,圖窮而匕首見(jiàn)。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zhǎng),操其室。”這一連串的描寫(xiě),都是連貫細(xì)致的動(dòng)作。《史記》前的中國(guó)史書(shū)雖然有豐富的敘事實(shí)踐,但《史記》似乎對(duì)敘事中的動(dòng)作有更深入的理解。
不妨粗略借用哲學(xué)分析中討論人的動(dòng)作的框架來(lái)觀(guān)察《史記》敘事。圍繞一個(gè)動(dòng)作事件有很多因素:有施行動(dòng)作之人,有動(dòng)作的意向,有具體動(dòng)作,有動(dòng)作效果,還有動(dòng)作的因果。《史記》前的傳統(tǒng)史書(shū)記事,在關(guān)注語(yǔ)言對(duì)話(huà)之外,主要給出事件中動(dòng)作的效果,關(guān)注人物在事件中的作用。而《史記》區(qū)別于傳統(tǒng)史傳之處,正是提供了更豐富的動(dòng)作信息。且看《刺客列傳》接下來(lái)一段——
左右乃曰:“王負(fù)劍!”負(fù)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
如果只從效果事件出發(fā),那么這幾句的描述重點(diǎn)應(yīng)該是“秦王負(fù)劍”和“荊軻擲秦王不中”兩個(gè)結(jié)果,不影響事件結(jié)果的信息如第二個(gè)“負(fù)劍”可以刪去。但在司馬遷的筆下,整個(gè)事件中動(dòng)作信息異常豐富完整:左右發(fā)出提醒的聲音后,我們看到了擊殺荊軻中間的重要一步,“負(fù)劍”(動(dòng)作);而秦王做出負(fù)劍動(dòng)作的因由,是因?yàn)橛凶笥姨嵝眩ㄒ蚬GG軻向秦王投出匕首(動(dòng)作),馬上給出“不中”的效果,以及“中銅柱”的余響。正是通過(guò)提供這些看似細(xì)碎但豐富連貫的動(dòng)作要素,司馬遷仿佛直接為讀者提供了一份“分鏡劇本”,予人極強(qiáng)的畫(huà)面感,也是后世“敘事文學(xué)”多從《史記》借鑒的重要原因。
《史記》的動(dòng)作特色還可以在其他篇目中發(fā)現(xiàn)。以有名的《李將軍列傳》中李廣出獵一段為例(括號(hào)中字是筆者所標(biāo)示的動(dòng)作要素,下同):“廣出獵,見(jiàn)草中石,以為虎(意向)而射之(動(dòng)作),中石沒(méi)鏃(效果),視之(動(dòng)作),石也。”若純就筆法簡(jiǎn)省這一角度看,“視之,石也”甚至“以為虎”都可以刪去,因“見(jiàn)草中石,射之”已經(jīng)將整個(gè)故事的結(jié)局呈現(xiàn)出來(lái)了。圍繞事件提供豐富完整的動(dòng)作要素,這正是司馬遷敘事的高明。讀者借由完整的動(dòng)作要素還原情景,由此得到生動(dòng)的體驗(yàn)。
我們不妨拿出和《史記》所敘內(nèi)容有重疊的兩部書(shū)——《左傳》和《漢書(shū)》,作為參照。《左傳·桓公十八年》記載魯莊公在齊國(guó)被彭生殺害于車(chē)上,直接寫(xiě)事件的結(jié)果:“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chē)(效果)”。根據(jù)同樣的材料,《史記·齊世家》則給出了更多的動(dòng)作細(xì)節(jié):“使力士彭生抱上(動(dòng)作)魯君車(chē),因拉殺(動(dòng)作—結(jié)果)魯桓公。”《魯世家》則用互見(jiàn)筆法寫(xiě)成:“因命彭公折其脅,公死于車(chē)”,這里的差異正是《史記》的特色。《史記·李將軍列傳》中記有李廣行軍戰(zhàn)陣的場(chǎng)面,司馬遷寫(xiě)道:“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漢書(shū)》則寫(xiě)成:“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僅從此句看,班固的處理方式當(dāng)然更加雅潔,且未損失任何核心信息,但讀者卻更容易從《史記》的描寫(xiě)體驗(yàn)到事件中的情景——僅僅一字之差,語(yǔ)言之“前”與動(dòng)作之“前”的動(dòng)作就如在目前。
明代茅坤《漢書(shū)評(píng)林序》中對(duì)《史記》有一段精彩的評(píng)價(jià)。他說(shuō)《史記》的描寫(xiě):“指次古今,出入《風(fēng)》《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zhàn)河山之間,當(dāng)其壁壘、部曲,施旗怔鼓,左提右挈,中權(quán)后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于曲旃之上,而無(wú)不如意者,西京以來(lái),千古絕調(diào)也。”這確實(shí)是千百年來(lái)讀者對(duì)《史記》的閱讀體驗(yàn),其中的“動(dòng)作”正是奧秘所在。在此之外,如果說(shuō)傳統(tǒng)史傳敘事關(guān)注事件的結(jié)果,使人明白地看清歷史現(xiàn)場(chǎng)的意義,《史記》對(duì)動(dòng)作的還原,則是將歷史事件根植于日常經(jīng)驗(yàn)之中,關(guān)注于事件中的人身上。
正如敘事電影和紀(jì)錄片不同,不以再現(xiàn)線(xiàn)性時(shí)間下的動(dòng)作為目的,《史記》也不是單純地再現(xiàn)動(dòng)作要素,而以更高超的手段調(diào)節(jié)動(dòng)作進(jìn)程的展示。這里不妨細(xì)玩《史記》荊軻刺秦王那段(見(jiàn)前引)的文意:荊軻左手把袖、右手持刃——司馬遷行文的語(yǔ)氣相對(duì)舒緩;而“未至身”以下連續(xù)的二三字?jǐn)嗑鋮s節(jié)奏極快極密,富有跌宕起伏之美。這種疾、徐的對(duì)比間,荊軻的刺殺似乎給人以慢動(dòng)作的感覺(jué),秦王的一系列躲閃卻是反應(yīng)迅捷。這一段中更有鏡頭景別的變化。如果用電影的分鏡語(yǔ)言來(lái)詮釋?zhuān)仁墙疤貙?xiě)荊軻與秦王的近身動(dòng)作,凸顯緊張的快速切換;忽然拉遠(yuǎn)呈現(xiàn)殿中人群像的遠(yuǎn)景鏡頭,乃至“而秦法”一句,又將畫(huà)面切換到殿下。司馬遷在不知不覺(jué)中引導(dǎo)著讀者想象這一事件的情境,讓讀者感知的并非荊軻與秦王的實(shí)際搏斗時(shí)間(或曰故事時(shí)間),而是《史記》為這一段搏殺提供的敘述時(shí)間。最激烈的打斗在一瞬間交換了大量動(dòng)作,隨后則進(jìn)入到秦王占據(jù)主動(dòng)、重創(chuàng)荊軻,又異常簡(jiǎn)練,一瞬之間“秦王復(fù)擊軻,軻被八創(chuàng)”。
再往前回溯,在荊軻怒叱太子丹,不待“客”到而入秦一段,司馬遷給世人留下一段記憶永恒的送別: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fēng)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fù)還!”復(fù)為羽聲伉慨,士皆瞋目,發(fā)盡上指冠。于是荊軻就車(chē)而去,終已不顧。
短長(zhǎng)句式的交錯(cuò),變徵、羽聲兩種音樂(lè)更替對(duì)送行者(或曰“觀(guān)眾”)情緒的直接沖擊,以及“就車(chē)而去,終已不顧”的告一段落,這一連串動(dòng)作事件不間斷地涌來(lái),可以稱(chēng)之為是一組古文中的“長(zhǎng)鏡頭”。在這樣的展示之下,司馬遷給讀者留下了綿長(zhǎng)的“敘事時(shí)間”,帶來(lái)異乎尋常的藝術(shù)震撼。
電影剪輯中的蒙太奇(Montage)手法,寬泛而言,指的是不同鏡頭重新組合可以生成新的含義,常常以視覺(jué)形象的象征性代替事件自身的因果邏輯,這也是電影從機(jī)械記錄變?yōu)樗囆g(shù)創(chuàng)造的重要技術(shù)依憑。這類(lèi)表現(xiàn)手法在文章寫(xiě)作中則更易實(shí)現(xiàn)。按金圣嘆《讀第五才子書(shū)法》的講法,《史記》屬于文人之史;“《史記》是以文運(yùn)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yùn)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jì)出一篇文字來(lái),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bǔ)低都由我。”傳統(tǒng)批評(píng)中的“事為文料”,也許可以看作是文言寫(xiě)作的蒙太奇——僅從技巧本身來(lái)說(shuō),文章家的剪裁與當(dāng)代的影視剪輯頗為同調(diào)。
在所有動(dòng)作、時(shí)間、景別、蒙太奇之外,必須認(rèn)識(shí)到,我們?cè)谒抉R遷筆下事件中讀到的生動(dòng),離不開(kāi)《史記》本身的史學(xué)框架。《史記》中幾乎出現(xiàn)在每篇結(jié)尾的“太史公曰”,是司馬遷相當(dāng)有標(biāo)志性的個(gè)人書(shū)寫(xiě),有些細(xì)節(jié)看似閑筆,卻有相當(dāng)深刻的史學(xué)屬性。《刺客列傳》最后的“太史公曰”探討了荊軻故事的史源——“世言荊軻,其稱(chēng)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guò)。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wú)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曾親用藥囊擊打荊軻的夏無(wú)且,將這段故事講給了公孫季功(弘,公元前200—前121)與董子(仲舒,前179—前104),隨后又傳遞到太史公(司馬遷,約前145—?)處,使這段記載區(qū)別于“世言”(大抵是《燕丹子》同類(lèi)的小說(shuō)家言)。從別人那聽(tīng)來(lái)故事,這似乎符合本雅明所謂講故事的傳統(tǒng)之一,即遠(yuǎn)方來(lái)人講述傳奇;然而不同的是,《史記》總是通過(guò)“太史公曰”以嚴(yán)謹(jǐn)?shù)膽B(tài)度檢視這些傳奇的源流和可信程度,這就脫離開(kāi)生動(dòng)的“故事”,而回到嚴(yán)肅的“史學(xué)”。比如,在記敘戰(zhàn)國(guó)四公子跌宕起伏的傳奇之后,太史公談起他的追索:“吾嘗過(guò)薛”(《孟嘗君列傳》),“吾過(guò)大梁之墟,求問(wèn)其所謂夷門(mén)”(《魏公子列傳》),“吾適楚,觀(guān)春申君故城”(《春申君列傳》),甚至是援引理論的批評(píng):“鄙語(yǔ)曰:‘利令智昏’”(《平原君列傳》)——“太史公曰”算是一段結(jié)尾旁白,也可說(shuō)是每段故事后“史學(xué)”的壓軸登場(chǎng),把傳奇拉回到歷史書(shū)寫(xiě)的框架中。后來(lái)的歷史學(xué)家,以及試圖用“實(shí)”飾“虛”的小說(shuō)家,都深深受益于這一框架。
在荊軻刺秦王這一故事的尾聲中,假如把《史記》原文里比較中立的“秦王不怡者良久”,改換為《戰(zhàn)國(guó)策》中的異文“秦王目眩良久”,則其文學(xué)性愈發(fā)地顯豁起來(lái):故事業(yè)已講完,只有一段秦王頭昏目眩的空鏡。考慮到今存《戰(zhàn)國(guó)策》“燕太子丹質(zhì)于秦”一段大概率是依托《史記·刺客列傳》而加以刪削的文本,我們甚至可以認(rèn)為,假如沒(méi)有“史”之客觀(guān)性的限制,司馬遷完全有能力寫(xiě)出更富有傳奇性的故事。區(qū)別于記載了更多道聽(tīng)途說(shuō)傳聞,但仍兼具雜傳文體特征的《燕丹子》,《史記》的筆墨顯然遠(yuǎn)勝之。文章可讀性的高低,并不必然地與所記錄事件是否“傳奇”掛鉤;嚴(yán)肅地表明史學(xué)的謹(jǐn)慎立場(chǎng),反而能給傳奇以現(xiàn)實(shí)參照,更增大傳奇的震撼力。
當(dāng)然,面對(duì)古代文本展開(kāi)細(xì)致解讀,可能時(shí)常要面對(duì)是否“原本”的問(wèn)題。考慮到今本《史記》的文字遠(yuǎn)少于司馬遷自稱(chēng)的“五十二萬(wàn)六千五百字”,則或許今本《史記》已被鈔者作了大量刪削,而原本《史記》的繁復(fù)程度可能遠(yuǎn)超今本。從今本中的長(zhǎng)篇文章本身所呈現(xiàn)的效果來(lái)看,《史記》的風(fēng)神是相當(dāng)鮮明而特出的,且正存在于易為忽略的“閑言碎語(yǔ)”之中。《史記》的原始面貌或許展示了更為生動(dòng)復(fù)雜的歷史場(chǎng)面。
最后,我們不妨下一帶有文學(xué)色彩的總結(jié)評(píng)論——對(duì)于太史公,人周知其乃“史家之絕唱”,是“小說(shuō)之教父”;同時(shí)也應(yīng)該相信,他如果生在當(dāng)代,必然也是熟諳口頭文學(xué)技藝的評(píng)書(shū)家,是善于營(yíng)造鏡頭場(chǎng)面的電影大師。前人批評(píng)太史公之好奇,其“奇”不在于“增益怪誕”,而在于敘事引人入勝,所謂“于起滅轉(zhuǎn)接之間,覺(jué)有不可測(cè)識(shí)處,便是奇氣”(劉大櫆《論文偶得》)。這些表現(xiàn)技巧至今仍然具有藝術(shù)教科書(shū)的意義。
作者 張昊蘇:南開(kāi)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師
陳 熹:美國(guó)斯坦福大學(xué)博士后
——以《在一起》中的《救護(hù)者》單元為例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