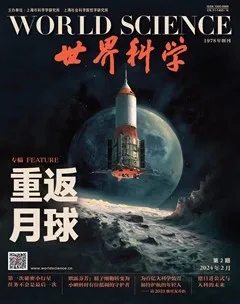默露芬芳:精子細胞轉變為小蝌蚪時有位低調的守護者

本篇報道圍繞2022年上海市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項目“RNA調控在精子發生及男性不育中的新功能機制研究”展開,該獎項由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劉默芳研究員領銜獲得。
2006年,劉默芳結束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研究生涯,回到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王恩多課題組擔任副組長。劉默芳已經和RNA打了很多年的交道,此刻的她十分渴望能獨自在RNA領域開拓出一片嶄新的天地。
正好在那一年,RNA領域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新突破。
包括華人科學家林海帆在內的多個研究團隊,分別在小鼠、果蠅等多種模式生物的生殖細胞中發現了一類全新的小RNA分子。由于這類新型小RNA分子在果蠅生殖細胞中與Piwi蛋白結合在一起發揮功能,因此研究者們將其命名為Piwi相互作用的RNA(Piwi-interacting RNA),簡稱piRNA。
piRNA在生物體內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低調”的一類分子了。首先,piRNA集中存在于生殖細胞,在其他絕大多數的體細胞中基本上都不表達;其次,即使是在生殖細胞中,piRNA也并不會進一步合成蛋白質分子,僅僅是以RNA分子的形式默默存在著。
但與此同時,piRNA卻有著很強的多樣性,以小鼠的生殖細胞為例,人們就發現了超過一百多萬種具有不同序列的piRNA。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在生殖細胞中會表達種類如此繁多的piRNA?piRNA究竟具有怎樣的生物學功能呢?
最初的幾項研究紛紛發現,許多piRNA序列都能匹配到一類名為轉座子的DNA元件,進而抑制這些轉座子序列的表達。
轉座子是一大類能在基因組不同序列之間“跳躍”的分子,轉座子的跳躍有一定的概率會導致基因突變,因此從長遠來看是推動生物演化的重要動力之一。但對于生物個體來說,過于活躍的轉座子并非好事,由此導致的基因突變會增加癌癥等疾病的風險。此前人們已經發現細胞演化出了專門將轉座子活性管控在一定頻率以下的分子機制。
當具體到以精子細胞為例的生殖細胞中,由于肩負著將遺傳信息完整、精確傳遞到下一代的重要使命,研究者推測,在這里對于轉座子活性的“管控”也會比其他細胞類型更加嚴格。
而piRNA的橫空出世,完美地印證了這一推測:piRNA就好像是一道專門為生殖細胞額外添加的“安檢門”,保證轉座子的活性在生殖細胞中被抑制在一個更低的水平。
但劉默芳卻留意到,并非所有piRNA分子都能匹配到轉座子序列。
那這些匹配不到轉座子序列的“例外”piRNA分子是否還具有未知的生物學功能呢?此外,科學家們在實驗室里對小鼠、果蠅等模式動物進行基因敲除操作,破壞piRNA生成或功能,都會導致模式動物不能繁育后代。那如果我們人的piRNA生成或功能出現故障,會導致怎樣的后果呢?
劉默芳決定將這些問題作為自己團隊的主要研究方向。
轉座子之外的靶點
2010年,一個法國研究團隊發現piRNA在果蠅胚胎發育的過程中參與對編碼發育因子Nanos的信使RNA的降解,破壞piRNA的結合蛋白Aub會導致Nanos信使RNA清除不及時,進而引起胚胎頭部的發育出現缺陷。
這一發現首次表明,除了轉座子序列之外,能夠編碼蛋白質的信使RNA也可以成為piRNA的靶點,并接受其調節。
果蠅中發現的這個案例進一步堅定了劉默芳在哺乳動物中系統地尋找piRNA新靶點和新功能的信心。
piRNA在小鼠精子形成過程中一個有趣的特殊性質為劉默芳提供了突破口:原來,在精子細胞最終形成蝌蚪形狀成熟精子的過程中,存在著兩波piRNA的表達高峰,其中匹配不到轉座子序列的piRNA主要存在于第二波表達高峰。
因此,劉默芳團隊首先從小鼠的睪丸組織中分離出處于第二波piRNA表達高峰中的精子細胞,進而純化出包含piRNA的復合物。經過深度測序,他們驚喜地發現,在分離出的復合物與piRNA配對的RNA分子中,雖然超過2/3都是匹配到轉座子序列的“經典”piRNA,但是仍然存在約20%是能夠編碼蛋白質的信使RNA。
接下來他們選擇出十對互相匹配的piRNA和信使RNA,對它們之間物理上的相互作用進行驗證,并通過功能學論證特異性piRNA的存在會促進對應信使RNA的降解。
如何理解這個發現的意義呢?
原來,piRNA促進信使RNA的降解主要發生在精子細胞從圓形向長桿形轉化的過渡階段。對于最終成熟的精子來說,為了能保證足夠的運動能力,要盡可能地拋除可能會增加負重的材料。打個比方說,就像是神州飛船,在發射升空的過程中會將帶有多余重量的助推器逐一脫落,最終只剩下一個裝載著宇航員的“大鐵球”進入太空。而在形成精子的過程中,細胞從最初的圓形先轉變為長桿形最終變為蝌蚪狀,細胞中的大部分信使RNA都需要被清除干凈。
而劉默芳團隊的工作表明,piRNA在幫助精子細胞減輕負荷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換而言之,在精子形成的特定階段,piRNA還扮演著“清潔工”的光榮使命。
能者多勞的piRNA
劉默芳團隊前后選取了超過100對piRNA和信使RNA進行驗證,其中絕大部分的piRNA都會促進信使RNA的降解,進而引起所編碼蛋白質水平的降低。
但其中卻出現了5對例外:研究者驚奇地發現,這些piRNA的表達并不影響對應信使RNA的含量;而對于所編碼的蛋白質,piRNA表達不僅不會引起蛋白水平的降低,反而會導致蛋白水平的升高!
這離奇的現象,究竟是源自實驗操作的失誤,還是背后隱藏著未知的全新生物學原理?
劉默芳團隊并沒有輕易放過這5對“例外現象”,通過對其進行深入挖掘,最終幸運地回答了精子發育領域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轉錄-翻譯解偶聯”現象是長期困擾精子發生領域研究者的一大謎團:精子細胞在發育的過程中,為了“瘦身”,首先要對攜帶著基因組信息的細胞核進行壓縮,而此操作卻終止了細胞核內信使RNA的轉錄;為了保證生產出精子在后續發育過程中所需的蛋白質,精子細胞會提前合成出所需的信使RNA,并將其儲存在一種名為“信使核糖核蛋白”(mRNP)的復合物中。mRNP就像是細胞臨時搭建的一個“倉庫”,保存在mRNP中的信使RNA處于“休眠”狀態,翻譯蛋白質的活性很低。
當精子發育推進到形狀由圓形向長桿形轉變時,保存在mRNP中的信使RNA會被有序釋放出來,進而快速翻譯產生精子發育后期所需要的蛋白質。
精子形成過程中這一先轉錄合成信使RNA,然后不立即翻譯出蛋白,而是先保存在mRNP復合物中,等到時機成熟后再恢復翻譯活性的機制被稱作“轉錄-翻譯解偶聯”現象。
而劉默芳團隊注意到,在能意外上調蛋白水平的5條piRNA中,恰好就有2條是對于精子發育后期非常重要的。
由此他們推測,piRNA是否就是推動mRNP釋放信使RNA、重新激活蛋白翻譯的關鍵分子呢?
事實也的確如他們所料!特定的piRNA能通過結合信使RNA末端的一段特殊序列,招募一系列的翻譯調節因子,激活該信使RNA的翻譯。
而且他們還發現,這一新機制不局限于此前發現的5個piRNA,進一步蛋白組學的實驗結果表明,這種依賴于piRNA通路的翻譯激活機制能推廣到超過數百個不同蛋白。
這一發現進一步確立了piRNA在生殖細胞中“勞模”的地位:它們首先能在精子發育全程抑制轉座子活性保證基因組的穩定性;其次還能重新激活保存于mRNP中信使RNA的翻譯活性;最后在精子發育后期確保信使RNA的清除,使得最終成熟的精子能輕裝上陣,具有較強的運動能力。這些發現分別發表在《細胞研究》(2014年)和《細胞》(2019年)期刊上。
概括起來,劉默芳團隊的這一系列研究工作,發現了piRNA對于精子細胞中的信使RNA存在著雙重調控作用。
激活翻譯的好幫手
伴隨著piRNA對于“轉錄-翻譯解偶聯”現象功能的闡明,劉默芳團隊對mRNP復合物在精子發育不同階段的動態變化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可精子細胞是如何知道,該在什么時候重新激活蛋白翻譯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劉默芳團隊從幼齡和成年小鼠睪丸中純化出處于高度活性狀態的核糖體復合物,利用蛋白組學手段鑒定出了12個在成年小鼠睪丸中富集的翻譯調控因子。其中,一個名為FXR1的蛋白格外引起了研究者們的興趣。
伴隨著精子細胞形狀的改變,FXR1蛋白的表達量也逐漸升高。而且FXR1能結合上千種不同序列的信使RNA分子,促進相應蛋白的翻譯。更有趣的是,FXR1的一個同源蛋白具有一種特殊的“相分離”性質——隨著其濃度的升高,能在細胞中形成一類聚集在一起的特殊結構。
那么FXR1是否也具有類似的相分離性質呢?
體外的實驗表明,隨著濃度升高,FXR1的確可以形成相分離特有的結構。同時,在生殖細胞中敲除FXR1,會導致雄性小鼠出現不育的表型。
劉默芳團隊由此做出一個大膽的猜想:在精子發育的過程中,FXR1蛋白水平的升高,可能會通過相分離的機制將分散存在的mRNP復合物聚攏在一起,從而解除mRNP復合物對于翻譯活動的抑制,推動精子發育進入下一個階段。
劉默芳(左三)與學生在實驗室
為了驗證這個猜想,他們設計了一個精彩的實驗:通過突變篩選,研究者鑒定出了一個FXR1突變體。這個突變體與原版的FXR1相比只在一個關鍵位點的氨基酸存在差異,結合RNA分子的能力不變,但卻失去了發生相分離的能力。當小鼠精子細胞中的FXR1蛋白被替換成突變體版本后,研究者驚喜地發現,mRNP復合物的翻譯激活能力顯著降低了。
看來,FXR1蛋白的確很可能是通過相分離的機制來調控精子細胞翻譯激活的。
這個發現開創性地闡釋了相分離在精子發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劉默芳團隊于2021年5月25日把論文投稿到《科學》雜志。
但正是因為這一發現的意義重大,審稿人對于論證的細節提出了許多謹慎的質疑。有趣的是,其中一位審稿人在審稿意見中寫道:“即使相分離模型今后被證明是錯誤的,這項工作的發現也是新穎而重要的。研究人員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是我的評論延后了該工作的發表,我表示道歉……”
歷經十個月時間的精心修改之后,劉默芳團隊在2022年3月23日將添加了更多補充實驗的論文重新遞交到《科學》送審,最終在2022年的8月12日正式發表。
結 語
從2006年到現在,劉默芳團隊在piRNA領域精耕細作,不斷地深化人們對于精子細胞發育調控機制的理解。
與此同時,他們也關心著基礎研究給臨床實踐帶來的幫助,其中發表在《細胞》上的一項工作就是課題組與上海市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合作成果。他們篩查了413例臨床無精、弱精癥患者,在3例病人中發現了Piwi基因存在突變。研究者通過敲入突變的小鼠模型論證病人攜帶的Piwi基因突變是導致不育的罪魁禍首,并揭示了此類突變的致病機理,且基于致病機理設計了干預策略,能夠一定程度上恢復突變小鼠精子的活力,為這類男性不育癥患者的治療提供了潛在的方法策略。這一工作首次證明了piRNA通路突變是男性不育的新病因。
繼這一奠基性研究之后,劉默芳團隊乘勝追擊,與湘雅生殖醫學中心合作,通過人類遺傳學方法在病人中篩選男性不育相關的piRNA通路的新型基因突變。研究發現,原來除了Piwi基因以外,piRNA通路的其他元件的突變也會導致精子發育的異常。piRNA加工酶PNLDC1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此前國際上的同行已經利用小鼠模型論證PNLDC1的異常會導致雄性不育,并在2021年也采用和劉默芳類似的人類遺傳學思路,從不育患者體內發現了多個導致PNLDC1功能缺失的突變。劉默芳團隊的發現與同行互相呼應,并且還在PNLDC1蛋白的活性位點上鑒定出了患者突變,進一步豐富了人們對于piRNA通路與精子發育關聯的認識。
近期,他們又從男性不育癥患者中鑒定到一個新的Piwi基因突變,該突變引起piRNA變短,從而導致piRNA消極怠工,不能很好地激活翻譯、生產精子發育必需的蛋白質,從而影響了男性生育力。
這些工作為將來不育患者的篩查、治療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piRNA通路,這一精子發育過程中的低調守護者,背后究竟還隱藏著多少未知的驚喜?
讓我們拭目以待。
————————
本文作者黃宇翔是密歇根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細胞自噬的調控機制”,科普作品主要圍繞生命科學及相關學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