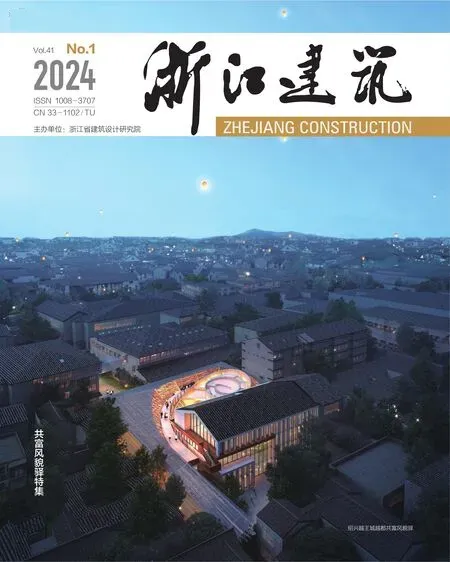浙江省鄉村書院空間探析
陶 倫
浙江工商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引言
浙江地處東南沿海,自古有耕讀傳家、重教興學的傳統,鄉村書院遍布鄉野。現存地方志、書院志記載了眾多的書院歷史發展與社會背景,大量的鄉村族譜更為細致地記載了鮮活個例,方志和家譜為研究浙江鄉村書院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傳統的農耕社會,一鄉一村同姓同宗聚族而居,家族興辦書院、私塾學堂現象普遍,即便是雜姓村也多有興辦鄉學、義塾、冬學的傳統。書院是鄉村典型的文教空間,起到了文化普及與教化鄉里的教育設施作用。與縣學、府學的辦學主體不同,宗族是興辦鄉村書院的主要力量。耕讀伴隨著宗族社會的發展、文教的需求進而催生了鄉村書院的興起和發展。自宋迄清,鄉村書院一直是鄉村教育的主要形式,承擔著廣大鄉村地區從蒙學階段直至科舉教育的重要功能。為蒙學發韌、知識傳播、孕育思想與普及社會道德標準、敦化社會風俗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土壤,涵養了具有文明主體性的文化傳統資源,并深遠影響了浙江地域性的文教氣象。作為文教功能空間載體的鄉村書院,如同壓艙石一般,對宗族、鄉村社會秩序的維護與穩定發揮著重大的“化育”作用,為孕育與傳播傳統文化觀念,維系中國上千年超大規模的文教傳承,提供了最為基礎且真實的文教空間載體。
1 浙江鄉村書院文教空間成因分析
建筑是文化的物質載體,建筑形式是文化的顯性反映。浙江鄉村書院包含了豐富的文化與教育資源,文教空間所呈現出的豐富性亦體現出受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包括人地關系(聚落生活)、經濟發展(生產技術)、社會觀念(鄉土風俗)、文化傳承(學派流脈)等。究其根本,首先是受限于地理氣候的影響而形成特定的人地關系,進而影響浙江鄉村聚落的格局,從而決定了鄉村書院的文教空間形態。從浙江地理空間格局來看,由于水域與丘陵的分割形成了若干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加之浙江“西南高北東低、多山少平原”的地理結構[1],使得農耕的前提必須進行成片的排澇疏浚與山地開墾。同時,浙江持續輸入型的人口壓力、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以及非躍遷型的農耕技術水平,決定了在傳統社會農業生產開發中,必須始終圍繞如何平衡人地間的矛盾,合理并靈活地利用自然資源,持續性地進行鄉村建設與生產生活、經濟發展與文化教育。
人類的建筑活動伴隨著人類自身的生活發展與文明進化[2],鄉村書院是人與空間持續進行文教互動的空間場所,是文化生成與傳播、教化普及與知識傳續的空間載體,具備文化性與教育性合一的內在屬性;教化功能的外化呈現則需要通過建筑的等級與形制得以彰顯明確,輔以裝飾性勸學意涵的字畫與雕刻浸潤默化,并在特定時段通過祭祀宗教儀式場景進而固化并強化,從而形成了一整套依附于實體空間的文教設施系統。人參與文教互動中賦予其完整的文教意義系統。整體系統中鄉村書院起到的是樞紐性的功能,多重身份人群共同的文教愿景凝結其中,包括宗族自身的發展意愿、鄉里后生的求學上進、文化精英的知識傳播、管理階層的敦化風俗、地域學派的化民成俗等。基于傳統耕讀觀念下的血緣宗族,其自身強烈的發展意愿與現實的科舉、事功路徑相統一,激發了鄉村基層社會的建設意愿,從而自下而上自發地積極興建書院,教化族人,耕讀傳家。與此同時,國家統治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治理的觀念主張相結合,糅合了地方管理與敦化民風的風俗建設,從而使得主流認可的意識觀念,自上而下地滲透到鄉村書院的文教活動中。除此之外,精英知識群體推動的化民成俗進程,以鄉村書院作為主陣地普及性傳播知識、開發民智,匯聚形成家與國、基層與社會、平民群體與知識精英相向而行的統一發展邏輯。
2 文教傳承的核心結構與演化推動力
從浙江現存眾多地方志與宗族家譜記載可以看出,“崇文重教→興建書院→負耒橫經→耕讀傳家”的衍化脈絡,始終是維系宗族世家發展的必要手段,也是賡續宗族興旺的必由之路。江南歷史上三次大的由北向南的人口遷徙,不僅帶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文化觀念[3],也使浙江的人地矛盾進一步凸顯。歷史時期人地關系演變的實質,就是這種沖突與對抗之具體表現形式及其內涵的演變[4]。村落選址、宗族發展、鄉里建設是同一時空背景下共同演化的互動過程,三者之間互相交織并共生衍化,形成“三元互嵌”的環狀結構,即:村落選址的地理面貌,約束著村落集聚的生產形式與生活形態;自組織特征的宗族,成為推動鄉村社會發展與建構的擔綱力量;禮俗觀念的鄉土社會關系,固化了鄉里人群的行為準則,維系著社會基層的平穩運行。“三元互嵌”回應了鄉村書院“在哪建—誰來建—為何建”的基本問題。環狀的中心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耕讀觀念根植其中,形成“中心+外環”的穩定結構。“三元一核”是解析鄉村書院發生并演化的基本機理。
儒學觀念規范的是農耕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倫理秩序,體現為在相對穩定的群居社會中,通過定居并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進而拓展大規模協作的人際網絡。鄧洪波提出鄉村書院的兩個界定:建于鄉村并進行公共性的教育[5],指出了鄉村書院由血緣型向地緣型的轉化特征。從現有浙江傳統村落分布的稠密程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村落聚落的形成不僅受限于地理空間的約束性條件,還因為人地關系的演化進程而被深刻地影響(圖1)。山區連綿、土地細碎又交通不便,中央的統治力量難以深入,宗族力量得以長期保存,根植于村落、宗族、鄉里之中的鄉村書院長期強韌。同時也應看到,這種強韌性折射出受社會歷史變遷中生產力與經濟發展的影響,文化傳播的加速與文化的下移呈現出來的總趨勢,以及社會進步與技術發展的疊加效益,合力加速推動了鄉村書院的演化進程。

圖1 浙江636個傳統村落核密度[6]與主要山脈分布關系[7]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在南北地域內耕地分布極為不平衡。北部為地勢平坦水網縱橫的杭嘉湖、寧紹平原,往南往西是連綿的山地丘陵地區(麗、臺、溫及金衢盆地),往東則是沿海地區的狹長細碎平原。山地丘陵地區較平原地區農業開發難度大,加之歷史上大規模的南遷人口使得糧食問題突出,有限的耕地不得不承載增長的人口,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尤為迫切,例如普及雙季稻種植技術與引進高產作物山地種植技術。浙江雙季稻最早出現在唐代之前,但推廣范圍很小。北宋處州有“稻再熟”的記載(光緒《處州府志》卷十二)。南宋時期溫嶺出現了“黃巖出谷半丹”(《蘇城志》卷三)。明《谷譜》所載:“浙江溫州歲稻兩熟。”隨著明代中期大規模地引進北美玉米、馬鈴薯、番薯種植,光緒《宣平縣志》卷十三說番薯“雖陡絕高崖,皆可栽種”[1],即便是在中南部山地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也極易推廣,山地型村落的人地矛盾與糧食緊缺問題大為緩和,村落分布與數目趨于定型。
農業生產技術的提升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帶來的是學習時間增加與教化意愿的不斷深入。浙江高度發達的印刷業與雕版印刷技術的普及,進一步促進了書籍在文化知識生產、傳播、積累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8]。宋代開始浙江的造紙已居全國之冠,越州竹紙、杭州藤紙、溫州蠲紙等產量巨大,紙張的普及降低了學習的門檻與成本。宋元以后統一規范了教材,清晰了從蒙學到科舉的努力方向。這些都從技術層面推動了鄉村書院的進一步發展;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自宋開始由豪族社會轉向平民化社會,科舉進一步普及,宗族的自身發展要求不斷拓展鄉村書院教育職能;南宋遷都臨安后,浙江政治、經濟、文化功能高度重合,江浙學子通過科舉參與國家治理的上升通道被完全打通;元明清帝國雖定都北京,然而大運河漕運的興盛將浙江與北方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江南仕子朝中為官參與治國比例全國最高;長時段來看,社會高度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撐起浙江鄉村書院亙古綿長的歷史進程。
3 從“家國同構”探尋文教空間的文化教育合一屬性
《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表述了古代教育的層級關系,蘊含著以宗法血緣為紐帶,把家、國、政治與倫理融為一體的觀念。作為傳統社會長期維系其低成本運行而形成的一整套觀念系統,不僅體現出自上而下的宏觀構架整合與自下而上的微觀秩序建構;還體現為家庭、宗族、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具有共同性與對應性,滲透在日常生活狀態中,“家國同構”觀念被反復地強化。反映在建筑禮制上,顯現為其軸線、朝向、前后、高低與建筑的等級呈現出強烈的對應關系,這樣的一種“同構”特質,使得不論是官式建筑與民居建筑,皆反映出其建筑等級的形制高低、軸線關系、尺度大小、色彩使用,都嚴格遵循等級規范。合院式是最為基礎的傳統建筑布局樣式,書院中的多個“合院空間”安排在主軸線上,前導性的祭祀與禮儀空間、主體性的教學與藏書空間、輔助性的起居與祈福空間等。文教功能通過空間的先后序列被組織起來,形成文化與教育統一實施的完整場景。作為合院式“外擴”形式的傳統官學建筑,通常遵循“左廟右學”雙軸線的布局樣式,大小形制遠遠高于鄉村書院。單從文教空間布局上講,與鄉村書院處理手法上均屬“同構”(圖2),在現存眾多的浙江地方志所記載的縣學、府學與鄉村書院的建筑布局樣式中屢見不鮮。

圖2 海寧州學宮圖與海寧安瀾書院圖對比[9]
聚焦到微觀層面的文教空間。鄉村書院分布于村莊鄉野,有些就是直接坐落在宗祠、家宅、園林中。規模雖不及官學建筑,卻能實現與周邊環境的靈活協調布置,并追求清幽淡泊、隱逸高雅的文化氛圍。環境和諧統一的自適應彈性、景觀綠化的勃勃生機以及精巧營造的“書卷氣息”,強烈透射出基于“文化傳續與知識傳承”的文教意愿,成為文化與教育意向表達的絕佳詮釋。傳旭元在《東明精舍記》中這樣描述:“……前為榮后為寢,東西分為四齋……其所問難曰敬軒,其所鼓琴曰琴軒,其所退休曰游泳軒。其琴軒少南有水一泓,不虧不盈,曰靈淵。之東百步許有泉泠,然老梅如龍橫蹲其上,曰梅花泉。匕北有壇,當時延景濂教授其中。”[10]從布局上極力保持明確的軸線關系,保持流線的通達與序列的完整。貫穿于書院的祭祀、教書、藏書的三大主體功能,與生活起居、園林綠化、水體造景、沉思冥想等空間充分融合。大則“盡善盡美”,盡可能將文教功能配置到極致;空間小則“求巧求雅”,使文教功能分布在單個建筑內的不同區域中,表達出文教功能的核心訴求,確保空間能盡可能多地為教學活動所使用。
4 鄉村書院是鄉村文教空間的典型代表
4.1 山水格局、自然風景與化民成俗融合潛移默化
浙江山水格局豐富多樣,鄉村書院亦呈現出極其豐富多樣的景觀圖景、民居樣式,地域材質與鄉土民情,展現出生機勃勃田園牧歌的景象,與自然山水環境相融為一體而又生生不息。宋代以來理學思想日漸豐盈并不斷向基層滲透,持續進行的哲學思考、倫理教育和民間風俗建設,對浙江鄉村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化民成俗的進程在客觀上使鄉村書院成為聯系心靈精神世界的紐帶,將文化精英的知識推廣與敦化社會風俗的基層建設相統一,以有教無類的方式滲入廣大鄉村。儒家經典“比德山水”觀念下的審美觀與鄉間樸素的“環農業”“適形”村落選址觀念相互糅合[11],“擇勝”環境觀、“形勝”風水觀、“文運”發展觀、“傳家”倫常觀等凝結匯聚成“生生不息”的生命狀態,于天地自然環境中參贊化育。
瀛山書院源于北宋熙寧間的詹氏族學,初期以本族子弟入學就讀為主,后因朱熹講學并作《題方塘詩》而影響深遠。瀛山書院的建設過程歷經宋元明清四代,“瀛山”的得名是由背山“銀山”而來,因取“登瀛”之義,遂改銀峰為瀛山,其書堂亦改名瀛山書院。《瀛山書院志·四刻瀛山書院志首卷》中的圖述記載(圖3):“嗚呼!東南冠蓋,春夢空憑,南渡風煙,冬青漫慨。先圣之化境,為終古之名區。萬笏山排,翠篠白云開別館,一環溪護,碧鷗紅蓼指遙村……”[12]書院選址充分考慮了背山、環水、依托地勢營造高點等綜合地形因素,書院整體映襯在竹翠與冬青、碧鷗與紅蓼之間,“別館”與“遙村”進一步說明書院建造不在村內,而是超脫于市井煙火氣之外,與自然景觀環境渾然融為一體。在自然的四季更替中滋養讀書的種子,在天地萬物間吐納思想的氣息,在山林幽靜之地怡情養性、潛心向學。

圖3 瀛山書院圖[12]
4.2 匠心營造、敦化鄉里與公共服務延展相輔相成
鄉村書院的首要職能是教育普及與人才培養,教育對象除宗族和鄉里子弟之外,甚至擴展到外姓子弟與非本村子弟。其建設規模與支持財力各有不同,個人籌建、宗族出資、鄉里集資、官府合辦等形式多樣。教學層次也不盡相同,有蒙學、冬學,有輸送縣、府學,有針對應試科舉等不同階段類目的教學形式。綜合來看,鄉村書院的衍化歷程實現了由血緣型向地緣型的轉化,由私學屬性向公共服務屬性的轉變,其文教空間亦成為鄉村公共服務延展的場所。由此,從公共性的文教服務視角切入觀察鄉村書院,可以看出,整體系統中不但包括建筑實體,如桅桿、魁坊、文峰塔、文昌閣、藏書樓、書院、文館等[13];還包括裝飾性質的教化內容,如室內的楹聯、匾額、雕刻、族訓、賢圣畫像、碑記等;以及儀式性較強的教化場景,如每日課的神位祭拜、每半月的文會受題作文、日常的書院講堂教授、大型的祭祖祭孔儀式等等。
建德新葉古村早期的重樂書院建于元初,兼收本姓與外姓子弟,北山四先生金履祥、許謙以及柳貫、章燮曾前后教學于此,雖明代頹敗,但葉氏宗族辦學則一直延續。至今村內保存大量的文教設施,建有旌表型(舉人桅桿、“耕讀人家”與進士第牌坊)、書齋型(華萼堂私塾,居敬軒官學堂等)、公共祭祀型(有序堂書房義塾)、祈福型(摶云塔、文昌閣、土地祠)等文教空間。有序堂位于村內核心區塊,為葉氏外宅派的總祠,面朝一半月形的泮池,極目遠眺朝山“文筆峰”,視野極為開闊。祠內設有大戲臺,義塾設在總祠東側書屋內。該區塊是新葉村公共空間屬性最為強烈的區域,承載了新葉村幾乎所有的公共性儀式場景,包括集會、祭祀、演出、文教、交往等。歷經明、清、民國的不同時期,在村落東南方位的水口位置,分別加建了摶云塔、文昌閣、土地祠三類建筑,功能上同為祈福文運的儀式性建筑(圖4)。高聳入云的摶云塔與造型飛揚的文昌閣組合在一起,形成了極富視覺張力的村落入口地標建筑,昭示出葉氏家族世代祈求文運、傳承文風、耕讀繼世的強烈意志。

圖4 新葉古村摶云塔、文昌閣、土地祠
4.3 因地而生、因時而興與文化地域交織共生共衍
文化總是具有地域性特點,文化的這種地域性是文化的本質屬性之一。但同時,文化也并不完全局限于地理環境,通過種種方式突破空間地域的限制,使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得到交流、融合,相融且互補的地域性文化現象亦反映在建筑樣式上。浙江的鄉村書院保持著較為清晰的浙派民居建筑譜系特征,呈現為既有吳越文化地域中典型的水鄉建筑特征,又兼具受相鄰地域性建筑文化的影響與滲透。在浙江南部、北部、中部、西部區域均呈現出眾多特征明顯的過渡型民居建筑特點:浙西地區鄉村書院建筑樣式與皖南民居同源;浙南地區建筑樣式雖原生性較強,也兼具閩東北大厝樣式特征;浙中金衢地區樣式則有較強的邊際效應,過渡性特征尤為明顯;東北部寧紹地區是越地文化發源核心區域,北部杭嘉湖地區與蘇吳太湖地區水鄉建筑樣式相近。
湖州地區是水網交錯型的平原水鄉,鄉村書院呈現出典型的浙江水鄉民居特征——建筑鄰水、院落進數多、朝向與河道成垂直關系、多布置花園等特點。如南潯荻港古村的積川書塾較為典型。具有上千年歷史的循環農業形態特征的“桑基魚塘”環繞荻港村落周邊,京杭大運河沿村穿流而過,至今往來船只汽鳴不絕[14]。積川書塾原為荻港大族章氏的私家書塾,后遷入具有道教文化背景的云怡堂中。乾隆34年(公元1769年),章氏家族出巨資擴建“南苕勝境”建筑群,形成多重進深的院落結構,主軸線上有八卦池、五孔架橋梁、文昌閣、純陽宮。積川書塾位于主軸西側,毗鄰花園與御碑亭(圖5),臨水且環水、園林與水景相融,營造出超然脫俗清新俊雅的水環境文教空間。

圖5 積川書塾平面
在清朝兩百年間,區區一村中的積川書塾共培養出兩位狀元,五十多位進士。文運如此昌盛,與當地高度發達的“農業+工商業”經濟形態,以及依托水網縱橫的便捷交通所形成的商貿繁榮有著莫大的關系。大運河聯通杭嘉湖一帶四通八達的水網,明清時期通過漕運高效聯系著國家南北方交通,交通便捷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前提。湖州素有“蘇湖熟,天下足”的美譽,稻桑棉麻開發較早,農業與桑絲生產基礎較強。早期資本主義在此萌芽,恰逢明清絲綢工商經濟更加發達,加速形成了以血緣、地緣、業緣為聯結紐帶的潯商群體。雄厚的經濟實力支撐起繼世教化、藏書、留學等文教事業,包括像嘉業堂、宜園(旁氏花園)藏書樓,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精致的園林、海量的藏書、精美的書畫足以例證。在明清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地域性的浙江文化精英知識群體,參與國家政治治理、浙派樸學研究、初級工商業萌發,以及近現代先進思想傳播等,均有尚佳展現。
4.4 文教傳承、文化傳播與人文流脈重合薪火賡續
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持著的社會共同經驗[15]。人是文化活動行為的主要載體,群體文化意識是文化共同經驗的集中表達。書院是人才培養與人才匯聚之地,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間互動交流與激發的平臺。文教空間與人文流脈的重合,使文教傳承呈現出縱向師承與橫向擴展的雙重意涵。成為書院傳教者的山長、先生、教師是文化傳承的主體角色,由于明確了師承關系,受教育的學子們往往繼承學統,進行跨地域性的傳播與生發。這是一個廣泛的文化精英知識群體,不僅代表了浙江地域文化的人文流脈,在遼闊的時空背景下將文教傳承事業薪火賡續,使之更具有深遠的地域文化穿透意義。浙江文教空間與人文流脈重合現象歷代延續,不勝枚舉。南宋朱熹與浙江書院交往之密切,不僅表現在直接講學于當時書院,也常因訪友、問學、論道而成為各地書院之常客[16];元代大儒金履祥一生也講學不輟,創辦了仁山書院,還先后執教于嚴陵釣臺書院、蘭溪齊芳書院與重樂精舍,廣授門徒,教育后進;元末明初大儒宋濂早年在東明書院求學,師從吳萊,后接任書院主講一職,斷斷續續在東明書院學習、執教,學習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也有二十多年[17]。這種基于鄉村書院的文化互動現象,既表現為橫向“跨地域”間的薪火賡續,又展現出縱向“互動變遷”歷時性的動態關聯,在此意義上,文化與教育合一的屬性已經突破了血緣、地緣、學緣、師承與學派的邊界,使得鄉村書院成為不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激蕩、融合的場所,鄉村書院成為文化傳承最為真切的空間載體,并成為浙江傳統社會中知識傳播與思想孕育的孵化器。
5 結論
代代相續傳承的浙江鄉村書院,穿越千年且生命力強韌,不僅展現出體系性的民居建筑譜系特征,而且體現出創造性極強的營建能力和環境相適應的彈性,更反映出地域性鮮明的鄉土情懷與傳統觀念傳續中的韌性特質;其所具有的血緣凝結與地緣拓展相融合、文教空間與文化流脈相重合、耕讀繼世與家國情懷相聚合等核心特征,更加凸顯了鄉村書院作為心靈與精神紐帶的強大黏性。首先,從空間維度上看,挖掘浙江鄉村書院的在地性研究價值,探尋浙江鄉村文教空間的生發機理與傳續成因,將有助于理解地域性的浙江在中國主體性建構貢獻中,所凝結形成的多元復合總特征的價值意義。其次,從時間維度上看,梳理浙江鄉村書院豐富的形態特色與演化現象、風俗建設與學派流脈的互動進程,也將能夠更為清晰地顯現出,文教繁榮的浙江在文明長河的滾滾洪流中,不斷地吸收、萃取、生發乃至反哺的互動進程。最后,從更廣闊的人文視野來看,以鄉村書院為載體的文教空間是一類融合了農業文明、儒家文化與商業文明、生態文明等多義文化載體,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化互動意識,使之真正成為浙江地域精神塑造的發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