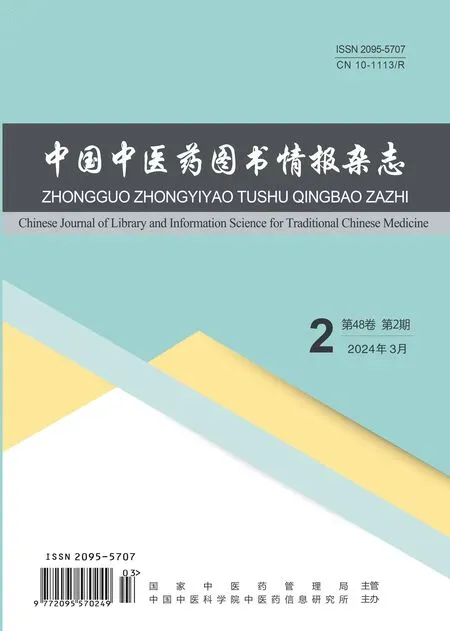含砷中藥復方為主治療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中醫證型及用藥規律研究
毛悅 ,靳楠 ,劉健 ,唐旭東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00;3.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北京 100091
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是一組起源于造血干細胞(HSC)的異質性髓系克隆性疾病,其特點是髓系細胞發育異常,主要表現為無效造血、難治性血細胞減少及向急性髓系白血病轉化[1]。本病主要發生于老年人,而我國患者發病中位年齡約56歲[2],西醫治療主要包括支持治療、免疫調節劑、免疫抑制劑及去甲基化藥物等[1]。異基因HSC移植為MDS唯一治愈性療法,但由于MDS異質性、患者特征及移植后并發癥,大部分患者可能在移植后出現移植相關性死亡與復發[3]。本病屬中醫學“髓毒勞”,主要病位在脾腎,病機主要為正氣虛損而感受邪毒,邪毒伏于骨髓且因毒致瘀、毒瘀互結,屬正虛邪實、虛實夾雜之證,治療多以補脾益腎、益氣養陰活血、解毒化瘀為治療法則[4-5]。中藥復方是適應現代藥物學認識范疇對多組分化學特征中藥方劑的通稱,現在方劑學復方有以二方或數方結合使用的含義[6]。砷制劑指含As2O3的砒霜及含As2S2、As4S4的雄黃[7]。青黃散始載于《奇效良方》,是由青黛、雄黃組成的含砷中藥古方[8],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血液科治療MDS應用多年,并在聯合健脾補腎中藥中取得良好療效[9]。除以健脾補腎為基礎外,病情不同,具體用藥也不同,但均屬青黃散與一方或二方加減變化而成,故可稱含砷中藥復方。本研究探索門診中含青黛、雄黃與其他中藥組合的含砷復方治療MDS的中醫證型與組方規律。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從醫院信息系統中提取2014年4月2日-2021年10月31日就診于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血液科門診并明確診斷為MDS的患者病案。
1.2 診斷標準
西醫診斷與分型標準參考《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10]與《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中國診斷與治療指南(2019年版)》[1]。中醫診斷標準參考《中西醫結合治療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專家共識》[11]與《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中西醫結合診療專家共識(2018年)》[4]。
1.3 納入標準
①中西醫診斷明確,按《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中西醫結合診療專家共識(2018年)》[4]辨證為氣陰兩虛、毒瘀阻滯證,脾腎兩虛、毒瘀阻滯證與邪熱熾盛、毒瘀阻滯證3種證型。②規律用院內制劑青黃散。③連續就診于本科室,其中2014-2019年就診次數≥60次且記錄明確者納入首末次處方2首;2020-2021年就診次數≥36次,若處方≥18首則納入首末處方2首,若處方記錄<18首或就診次數≥36次但僅有2~3首處方則納入末次就診處方1首。④藥物組成及劑量明確。
1.4 排除標準
①診斷中包含其他疾病;②藥物組成<4味;③患者、年齡、性別等基礎信息不全。
1.5 數據庫建立及整理
按照以上納排標準篩選處方,對2次納入證候一致者只記錄一次。采取雙人錄入,提取信息包含:①患者就診ID、性別、年齡、出生年月等基礎信息;②患者住院信息,如入院診斷、出院診斷、住院時長、住院用藥、住院次數、血型等;③患者就診于本院的心臟超聲、頭顱CT、心電圖、血常規、肝功能等檢驗及檢查結果;④門診處方、就診次數、就診時間、開具處方醫師等。將以上信息錄入Excel2019,并根據2020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12]對藥物名稱進行規范,“藥典”中未收錄者則參考《中華本草》[13]、《中藥大辭典》[14]及《中藥學》[15]進行規范,如生菟絲子規范為菟絲子,紅參片規范為紅參,北敗醬草規范為敗醬草。對炮制后藥物功效差異明顯者分別錄入,如生地黃、熟地黃,甘草、炙甘草,白術、麩炒白術,山萸肉、酒萸肉等。
1.6 數據規范及分析
將規范數據批量導入古今醫案云平臺2.3.5,將中藥處方導入“分析池”,對年齡、性別、中醫證候、中藥頻次、性味歸經進行頻次統計。設置支持度≥0.5、置信度≥0.8,對中藥-中藥進行關聯規則分析;設置支持度≥0.05、置信度≥0.6,對證型-中藥進行關聯規則分析。選擇lance距離,以最長距離法對頻次前30位中藥進行聚類分析。設置邊權重為418,進行中藥復雜網絡分析,并應用Cytoscape3.8.0軟件進行可視化。
2 結果
2.1 患者基本信息
2.1.1 性別與年齡
根據納入及排除標準,最終納入患者457例,其中男性207例、女性250例,未見明顯差異。年齡<10歲1例,10~19歲14例,20~29歲19例,30~39歲67例,40~49歲65例,50~59歲74例,60~69歲91例,70~79歲67例,80~89歲57例,≥90歲2例,中位年齡為58歲,以60~69歲占比最大。
2.1.2 中醫證型
457例患者證型結果為脾腎兩虛、毒瘀阻滯證413例,氣陰兩虛、毒瘀阻滯證44例。
2.2 方劑分析
2.2.1 高頻中藥分布
819首治療MDS處方中涉及346味中藥,統計排名前20位中藥,青黛與雄黃共列首位,其后為茯苓、麩炒白術、熟地黃、菟絲子、山藥,見表1。

表1 819首治療MDS處方高頻中藥頻次(前20位)
2.2.2 性味歸經分析
346味中藥藥性以平、溫、寒為主,藥味以甘、辛、苦為主,歸經多屬腎經、肝經、脾經,見表2~表4。

表2 819首治療MDS處方中藥藥性分布

表3 819首治療MDS處方中藥藥味分布

表4 819首治療MDS處方中藥歸經分布
2.2.3 中藥關聯規則分析
對819首處方進行關聯規則分析,支持度≥0.5、置信度≥0.8,得到中藥關聯規則51條,其中提升度排名前20位組合為菟絲子-補骨脂、山藥-酒萸肉、鎖陽-熟地黃、山藥-熟地黃、熟地黃-酒萸肉等,見表5、圖1。

圖1 819首治療MDS處方中藥關聯規則分析(支持度≥0.5,置信度≥0.8)

表5 819首治療MDS處方中藥關聯規則(支持度≥0.5,置信度≥0.8)
2.2.4 證型-中藥關聯規則分析
設置支持度≥0.05、置信度≥0.6,得到證型-中藥關聯規則9條,其中脾腎兩虛證代表脾腎兩虛、毒瘀阻滯證,氣陰兩虛證代表氣陰兩虛、毒瘀阻滯證,提升度前3位的組合為氣陰兩虛證-茯苓、脾腎兩虛證-菟絲子、脾腎兩虛證-熟地黃,見表6、圖2。

圖2 819首治療MDS處方證型-中藥關聯規則分析

表6 819首治療MDS處方證型-中藥關聯規則(支持度≥0.05,置信度≥0.6)
2.2.5 高頻藥物聚類分析
對使用頻次前30位中藥進行聚類分析,距離類型選擇Lance距離,聚類方法選擇最長距離法,得到4個處方組合,組1:炙黃芪、當歸、陳皮;組2:炙淫羊藿、黨參、炙甘草、桂枝、白芍;組3:生姜、大棗。組4所含藥味多,進一步分為3個小類,類1:太子參;類2:澤瀉、菟絲子、補骨脂、熟地黃、麩炒白術、茯苓、雄黃、青黛;類3:鎖陽、巴戟天、枸杞子、何首烏、生地黃、桑葚、綿萆薢、女貞子、牡丹皮、山藥、酒萸肉,見圖3。從聚類分析結果看,組成為青黃散、四君子湯、六味地黃湯等的類方。

圖3 819首治療MDS處方高頻藥物聚類分析
2.2.6 中藥復雜網絡分析
設置邊權重為418,網絡中節點代表中藥,“節點度”表示各節點中藥相連邊的數目,生成中藥復雜網絡,得到1個核心處方,包含青黛、雄黃、熟地黃、麩炒白術等22味中藥,見表7。利用Cytoscape3.8.0進行可視化,見圖4。

圖4 819首治療MDS處方中藥復雜網絡(邊權重≥418)

表7 819首治療MDS處方中藥-節點度
3 討論
3.1 正氣為本,助體抗邪
MDS以脾腎兩虛為本,正虛無以抗邪使邪毒內侵伏于骨髓,虛、毒、瘀并存,基本病機以正虛為主、毒瘀互結,表現出脾腎兩虛、氣陰兩虛、邪毒熾盛的不同證型。“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故扶正固本為治療MDS的重要策略。從中藥頻次統計結果可見,以麩炒白術、熟地黃、菟絲子、山藥、補骨脂等補脾益腎類中藥應用為多,從用藥性味可見,以補益之甘味居首,且多歸腎經、肝經及脾經,前30位中藥聚類所得4類組方以六味地黃湯、四君子湯類方為主,體現了治療MDS重視補益脾腎、扶助正氣。地黃經炮制后生熟異治,生地黃性寒,長于清熱涼血、養陰生津,熟地黃則寒性減弱,偏于溫補,長于滋陰補血、益精填髓。藥理研究表明,二者雖存在功效差異,但均可起到調節免疫、改善外周血象的作用[16-17]。白術可益氣健脾、燥濕利水、止汗安胎,臨床中常以麩炒后入藥,可減弱燥濕作用而增強健脾功效。藥理研究發現,麩炒白術可增加白術內酯Ⅰ、Ⅱ、Ⅲ含量,且以白術內酯Ⅰ含量升高最為明顯[18],而在白血病細胞中白術內酯Ⅰ可發揮細胞毒性作用,又可誘導細胞凋亡與分化[19]。
3.2 辨病辨證,整體調節
含砷中藥包括雄黃與砒霜兩類,MDS 為正虛邪實、虛實夾雜之證,雖正虛為本,但毒邪與瘀血貫穿疾病全程,且是病機演變的關鍵因素,是治療本病的關鍵切入點。青黃散可針對MDS毒邪用雄黃以毒攻毒,用青黛涼血、解毒、化瘀,兩藥合用共奏解毒祛瘀之效[8],切合MDS毒瘀互結的病機。藥理研究表明,青黃散可改善MDS異常甲基化[20],聯合應用補脾益腎中藥可通過影響DACT1基因甲基化及缺氧誘導因子-1α水平產生臨床療效[21-22]。用藥頻次中青黛與雄黃共居首位,中藥與證型關聯規則中青黛與雄黃分別與脾腎兩虛、毒瘀阻滯證及氣陰兩虛、毒瘀阻滯證密切相關,中藥復雜網絡分析中青黛與熟地黃共為核心節點,也驗證了青黃散治療MDS的重要作用。氣血以通調為和,聚類中可見桂枝、白芍、炙甘草等,其中以桂枝-白芍經典藥對調和營衛氣血、通達血管內外[23],解毒化瘀兼調和氣血、整合內外。
MDS存在多種基因突變共同作用驅動,由此導致異質性克隆性HSC疾病,而HSC主要存在于由破骨細胞、骨細胞、脂肪細胞、交感神經元、調節性T細胞、樹突狀細胞、自然殺傷細胞、單核細胞、巨噬細胞、T細胞、B細胞、漿細胞及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1等多種成分組成的高度有序化,且處于穩態的骨髓微環境(BMME)中,炎癥在其病程中起重要作用。在衰老、感染、化療等多種因素作用下引起BMME炎癥穩態的破壞,骨髓內形成炎癥微環境可引起功能受損HSC數量增加、自我更新減少及偏向于髓系分化[24-25],在BMME中NLRP3炎癥小體復合物、半胱氨酸蛋白酶-1與Wnt/β-catenin誘導增殖等多種炎癥因素的激活也成為MDS形成的重要驅動因素[26]。整體微環境變化增加了單靶點治療MDS的難度,中藥多靶點則具有重要優勢。用藥頻次統計中茯苓居第3位,且關聯規則分析中與不同證型均存在較強相關性,藥理研究中,經茯苓酸b處理的細胞內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1β與白細胞介素-6可產生劑量依賴性減少現象而產生抗炎作用[27]。此機制可能與中藥多靶點治療MDS有關。故在用藥中除針對毒瘀阻滯以青黃散解毒散瘀外,又多與補脾益腎、健脾化濕、益氣養血、調和氣血中藥配伍,多角度治療M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