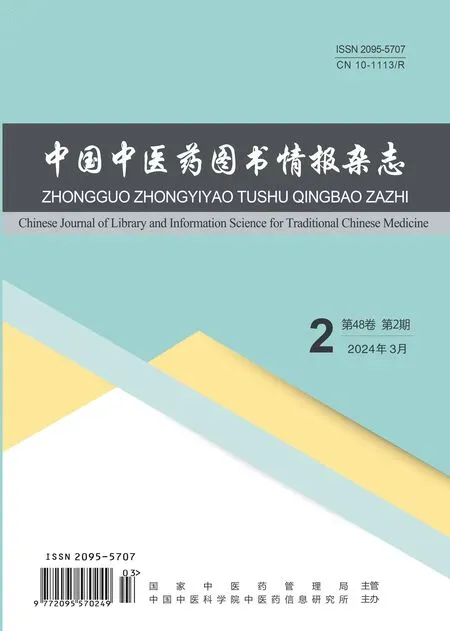艾灸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研究進展
楊燦燦,孫建華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 南京 210004
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種功能性胃腸道慢性疾病,我國發病率約為7.26%~11.5%[1],是常見的消化道疾病之一。IBS的主要癥狀為長期反復腹痛,同時可能伴有排便習慣改變、腸道形態異常等。根據排便習慣變化,IBS主要分便秘型(IBS-C)、腹瀉型(IBS-D)、混合型(IBS-M)、不確定型(IBS-U)4個亞型[2]。其中IBS-D發病率最高,約占40.83%[3]。IBS-D病程周期較長,腹瀉反復發作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甚至出現抑郁癥狀。現對國內外艾灸治療IBS-D研究進行綜述,以期啟發臨床。
1 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西醫認識
目前對IBS-D具體發病機制未完全闡明,主要將其歸因為神經-內分泌-免疫功能紊亂、內臟超敏反應、胃腸動力異常、腸道菌群失衡及精神心理因素等[4-6]。目前缺乏理想的治療方法,主要采用飲食療法、心理認知和行為學指導等,主要以解痙止痛藥、止瀉藥暫時緩解患者癥狀[7-8]。臨床主要為對癥治療手段,存在長期服藥依從性差、不良反應明顯、停藥后復發率高、缺乏整體緩解腸道癥狀及伴發情緒癥狀等問題。
2 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中醫認識
IBS-D主癥為瀉和痛,屬中醫學“泄瀉”“大腸瀉”范疇。《靈樞·邪氣臟腑病形》云:“大腸病者,腹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難經·五十七難》“泄凡有五……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臨證指南醫案》載“腹鳴溺少……向年陰分傷及陽位,每有腹滿便溏”,均提到明顯的腹部不適癥狀,與IBS-D癥狀相似。《腸易激綜合征中西醫結合診療共識意見(2017年)》將IBS-D分為肝氣乘脾、脾胃虛弱、脾腎陽虛、大腸濕熱4個證型[9]。臨床治療中,由于IBS-D病程較長,證型復雜,遷延難愈,增加了診治難度,亟需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艾灸作為中醫傳統外治法,治療IBS-D 療效顯著,但具體機制還需進一步闡明[10-11]。
3 艾灸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相關基礎研究
3.1 核因子-κB信號通路
核因子-κB(NF-κB)信號通路廣泛存在于哺乳動物細胞內,其主要功能與免疫炎癥相關。在腸上皮組織中NF-κB信號通路的激活可能帶來炎癥因子的釋放,從而引起腸道屏障通透性的改變,導致患者出現腹瀉癥狀[12-13]。王雪梅等[14]研究發現,IBS-D患者NF-κB陽性率顯著提高,同時Toll樣受體4(TLR4)表達量也顯著提升。Zhang等[15]研究發現,抑制脅迫法和醋酸灌腸法造模后的IBS-D 模型大鼠體內TLR4/MyD88/NF-κB表達量均顯著提高,同時白細胞介素(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等炎癥因子水平也明顯增加。儲浩然等[16]研究發現,艾灸“天樞”“上巨虛”可明顯緩解IBS-D 模型大鼠癥狀,其通過抑制TLR4/MyD88/NF-κB通路從而降低下游免疫炎癥因子表達,以達到治療腹痛、腹瀉的目的。同時艾灸“天樞”“上巨虛”還可以提高IBS-D模型大鼠結腸組織miR-345-3p/miR-216a-5p表達,并降低NF-κB p65表達來抑制炎癥水平[17]。由此可見,通過艾灸抑制NF-κB通路激活可能是緩解IBS-D癥狀的主要作用機制之一。
3.2 5-羥色胺
5-羥色胺(5-HT)是一種廣泛存在于人體各種組織與器官中的重要神經遞質,約95%分布于胃腸道中,與不同受體相結合產生相互作用,與胃腸道蠕動、激素分泌及內臟感覺相關[18-20]。5-HT作為一種活性肽物質,易受神經和心理功能影響。當機體感受外界強烈刺激時,腸嗜鉻細胞分泌大量5-HT,腸黏膜上的5-HT受體與5-HT結合,即可引起內臟超敏反應,從而導致腹痛與腹瀉[21]。Zheng 等[22]和Wohlfarth 等[23]研究發現,5-羥色胺受體4(5-HT4R)和5-羥色胺受體3(5-HT3R)與IBS-D關系最為密切,激活后可導致腸道平滑肌收縮,從而加重IBS-D患者癥狀。曹佳男等[24]發現,艾灸“肝俞”“脾俞”“足三里”“章門”等穴位可有效降低IBS-D大鼠結腸組織5-HT含量及5-HT3R含量,從而降低內臟超敏反應發生率。仝理等[25]研究發現,艾灸天樞、上巨虛可降低結腸組織色氨酸羥化酶1(TPH1)、5-HT3R含量,提高5-HT轉運體水平,從而干預5-HT合成和重攝取過程,以降低稀便率和改善內臟超敏。5-HT與腸道不同亞型受體結合可對腸道產生多種影響,可能是IBS-D的重要發病機制,5-HT及其亞型受體可能是艾灸臨床治療IBS-D的重要靶點。
3.3 P物質和血管活性腸肽
P 物質(SP)是一種神經肽,作為神經遞質和神經調節劑發揮作用,其主要作用于疼痛和炎癥反應。在胃腸道中參與調控平滑肌收縮、血管通透性和炎癥,研究表明,IBS-D患者小腸黏膜SP水平升高,可能是腸道形態改變和腹痛的原因之一。廖路敏等[26]研究發現,艾灸天樞、上巨虛可通過抑制降鈣素基因相關肽抑制SP,從而緩解IBS-D癥狀。血管活性腸肽(VIP)也是一種影響廣泛的堿基多肽,主要對胃腸道平滑肌有松弛作用,并影響水分和電解質平衡,與SP不同的是其主要顯示抗炎特性。但有研究發現,IBS-D患者血漿中VIP水平顯著升高,這可能是導致腹痛、腹瀉的主要因素[27]。SP和VIP共同作用可以促進胃腸道蠕動,調節水、電解質平衡,而其平衡的破壞可能是導致IBS-D患者出現胃腸道癥狀的誘因之一。許向前[28]研究發現,艾灸與補脾益腸丸聯合用藥可緩解大鼠腹瀉,降低內臟敏感度,降低血清、十二指腸和下丘腦SP、VIP水平。陳霞等[29]研究發現,單純艾灸“天樞”“上巨虛”同樣可降低IBS-D模型大鼠結腸和下丘腦SP、VIP含量,其與艾灸治療IBS-D的神經生理學機制密切相關。
3.4 c-Kit/SCF信號軸
c-Kit又稱CD117,是一種Ⅱ型受體酪氨酸激酶,參與細胞內信號傳導。c-Kit/SCF信號軸在免疫調節過程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抑制c-Kit/SCF可導致體內T淋巴細胞分化異常,從而使免疫球蛋白表達異常[30]。武志娟等[31]研究發現,IBS-D患者體內存在免疫細胞數量增多、免疫激活增強,主要表現為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提高,二者可能存在相關性。c-Kit與其配體干細胞因子(SCF)特異性結合后可觸發信號級聯,在胃腸道中主要影響Cajal間質細胞(ICCs)。ICCs數量和功能異常會導致腸道屏障受損、胃腸道運動功能異常,這是IBS-D的主要特征之一[32-33]。Xie等[32]研究發現,調控SCF/c-Kit信號軸可減少炎癥并延緩腸道屏障損傷。李奎武等[34]研究發現,艾灸“天樞”“上巨虛”可升高IBS-D模型大鼠結腸組織SCF、c-Kit表達,同時降低大鼠血清中免疫球蛋白水平,且對大鼠內臟高敏感性,腹痛、腹瀉等癥狀有改善作用。c-Kit/SCF信號軸可能是IBS-D患者出現免疫功能失常和胃腸道功能異常的關鍵因素,通過艾灸刺激腧穴進而調節這一通路可能是緩解IBS-D癥狀的重要手段。
3.5 腸道菌群
近年研究發現,腸道菌群在IBS-D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超過1013個微生物存在于胃腸道中,與宿主處于互惠關系,從飲食中獲取能量和營養,同時保護宿主免受病原體的侵害[35]。人體胃腸道內主要存在的菌屬有厚壁菌、放線菌、擬桿菌和變形桿菌等,但個體間的菌群組成均存在差異。IBS-D患者腸道菌群變化主要表現為腸道中優勢菌種數量減少、菌群多樣性減少,且有益菌種數量減少、有害菌數量增加。通過調控腸道菌群來治療IBS-D也是目前常用手段之一[36]。梭菌屬細菌Clostridiabacteria可在一定程度上逆轉IBS-D患者糞便膽汁酸過量的狀況,從而緩解患者的腹瀉癥狀[37]。靶向清除活潑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gnavus可降低IBS-D患者腸嗜鉻細胞中血清素生物生成,進而起到治療效果[38]。四君子湯可恢復IBS-D患者腸道菌群離體實驗中的鏈球菌Streptococcus和志賀氏埃氏菌E.Shigella失衡,改善IBS-D患者的神經遞質代謝[39]。Zhen等[40]研究發現,附子理中丸可提高乳酸桿菌含量,保護腸道免疫屏障。糞菌移植療法也被發現除恢復IBS-D患者失衡的腸道菌群外,還可緩解患者的抑郁癥狀[41]。雖然腸道菌群在治療IBS-D中已經展現出優勢,但由于不同患者之間腸道菌群特異性及單獨針對特定菌在臨床治療的復雜性,作為無創外治法和多靶點干預的艾灸也成為通過干預腸道菌群治療IBS-D的研究熱點方向。王樹東等[42]研究發現,艾灸關元可增加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數量,艾灸天樞可使腸桿菌和腸球菌數量增加,艾灸可選擇性調控腸道菌群類型,從而恢復穩態。鄭潔等[43]研究發現,艾灸配合針灸治療IBS-D可提高患者體內雙歧桿菌、乳酸桿菌、擬桿菌數量并恢復腸道菌群多樣性。腸道菌群調控已被證明是治療IBS-D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因其復雜性和特異性,具體機制還需深入研究。
4 結語
本病系因感受外邪,飲食所傷,情志不調,稟賦不足或久病致臟腑虛弱而發。由《景岳全書·泄瀉論證》“泄瀉之本,無不由于脾胃”可知,本病主要與脾胃相關,治療當以脾胃為根。
艾灸治療IBS-D療效較好,其作用機制復雜。然而,目前研究仍存在樣本量小、研究質量不高、缺乏長期隨訪等問題。因此,今后需要開展大樣本、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以探究艾灸治療IBS-D的遠期療效。此外,考慮到艾灸技術、相關理論的差異性,需要建立標準化、規范化的艾灸治療方法,以提高治療效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