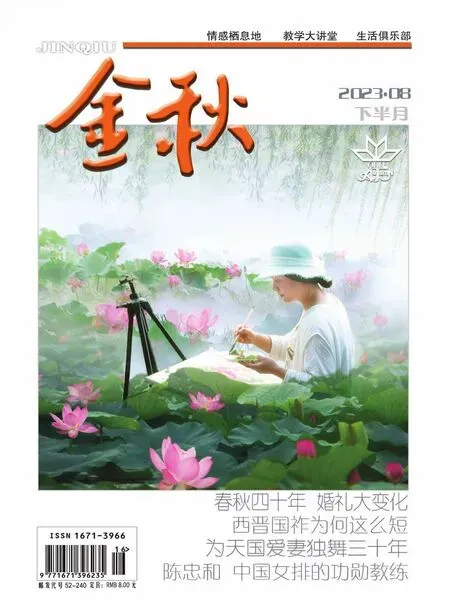傷肝的保健品
◎文/上海·李波

有別于受到嚴(yán)格管制的處方藥物,全世界各國(guó)對(duì)保健品行業(yè)管制有限。近日,世衛(wèi)組織一項(xiàng)調(diào)查顯示,因藥物引起的肝臟損傷病例中,首禍?zhǔn)潜=∑罚剂瞬±齼沙桑渲幸蕴?hào)稱能增強(qiáng)能量和消除脂肪的保健品危害最大。其它導(dǎo)致肝損傷的藥物依次為治療癌癥、糖尿病、心臟病的處方藥物。
這個(gè)肝臟專家小組近十年來(lái),調(diào)查了近千名因保健品導(dǎo)致肝臟嚴(yán)重受損的研究對(duì)象,發(fā)現(xiàn)受害者大都是想要減肥和想要增肌人群。其中,三分之一受害人群是服用了含有過(guò)量類固醇的保健品。類固醇是一類在結(jié)構(gòu)及活性上與人體睪酮相似的化學(xué)合成衍生物。因?yàn)樗c雄性激素相似,使用它可以使肌肉生長(zhǎng)的速度加快,還可以加快健身訓(xùn)練后的肌肉恢復(fù)。單憑這兩個(gè)用處,就獲得了很多健身增肌者的追捧。然而,過(guò)量的類固醇破壞了體內(nèi)荷爾蒙系統(tǒng),嚴(yán)重地?cái)_亂體內(nèi)正常的荷爾蒙的產(chǎn)生,對(duì)肝臟、心臟都有損害。
其余三分之二受害者多為中年婦女,她們以為服食保健品可達(dá)到瘦身或增強(qiáng)體力的效果。47歲的雷斯就診時(shí)眼、臉、胸呈現(xiàn)“近乎熒光黃的顏色”。經(jīng)醫(yī)生診斷,她的肝臟嚴(yán)重受損,罪魁禍?zhǔn)资欠玫囊环N標(biāo)榜能燃燒脂肪的綠茶精華素。后經(jīng)醫(yī)生治療,最終保住了雷斯的肝臟,但由于肝功能受損,她再也無(wú)法從事體育活動(dòng),也不能過(guò)度勞累,以后每個(gè)月還必須到醫(yī)院定期檢查。
綠茶精華素是一個(gè)廣受歡迎的保健品,含有兒茶素,它是一種會(huì)增加新陳代謝、可以瘦身的抗氧化劑。一小粒綠茶精華素所含的兒茶素是一杯綠茶的幾十倍,消費(fèi)者并不知道攝取過(guò)量?jī)翰杷貢?huì)傷害肝臟。
調(diào)查人員指出,多數(shù)國(guó)家保健品無(wú)須獲得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鑒定批準(zhǔn),就可上市。當(dāng)局只在消費(fèi)者服用健康受損后,才會(huì)采取行動(dòng)將相關(guān)保健品拉下架。以美國(guó)為例,美國(guó)人每年花費(fèi)320億美元購(gòu)買保健品,平均每?jī)蓚€(gè)美國(guó)人就有一個(gè)服用保健品,而且不少人在同一時(shí)間服食超過(guò)一種保健品。火熱的買方市場(chǎng),使得七成的保健品制造商不遵守基本的品質(zhì)管理標(biāo)準(zhǔn),市面上銷售的近六萬(wàn)種保健品中,僅有0.3%產(chǎn)品進(jìn)行過(guò)是否有副作用的測(cè)試。所以這次調(diào)查結(jié)果只不過(guò)是保健品危害健康事件中的冰山一角。不過(guò),此次調(diào)查也發(fā)現(xiàn),市場(chǎng)上較受歡迎的保健品,如維生素丸、礦物質(zhì)營(yíng)養(yǎng)品、益生菌產(chǎn)品、魚肝油并未呈現(xiàn)不良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