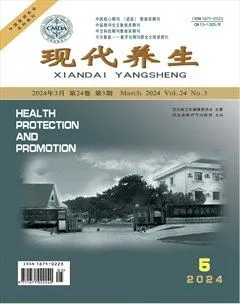基于“心腦共主神明”理論探討微生物-腸-腦軸與卒中后抑郁
王楠 陳炯華
【摘要】? 微生物-腸-腦軸認(rèn)為,大腦和腸道之間存在一種雙向調(diào)節(jié)途徑,生理病理狀態(tài)下二者相互作用,基于腦腸軸治療神經(jīng)精神并發(fā)癥依舊是目前的研究焦點(diǎn)。卒中后抑郁(PSD)是腦卒中最常見的并發(fā)癥之一,其治療預(yù)后的不確定性嚴(yán)重影響患者的功能康復(fù)、生活質(zhì)量。近年來,隨著對腸道微生物調(diào)控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作用的深入研究,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將目光立足于微生物-腸-腦軸對PSD的探討。因此,基于微生物-腸-腦軸,結(jié)合中醫(yī)經(jīng)典“心腦共主神明”理論闡述神明孰主與腸道微生物及卒中后抑郁之間的關(guān)系,并運(yùn)用“心腦同治”“腦病腸治”的理論框架,為PSD的診斷和治療提供有力的參考。
【關(guān)鍵詞】? 心腦共主神明;微生物-腸-腦軸;腸道微生物;卒中后抑郁;腸道穩(wěn)態(tài)
中圖分類號? R277.7?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 ? 文章編號? 1671-0223(2024)05--03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指一種發(fā)生于卒中后,表現(xiàn)出除卒中癥狀以外的復(fù)雜的心理障礙[1],以及常伴有相應(yīng)軀體癥狀的綜合征,是卒中常見且嚴(yán)重的并發(fā)癥之一。據(jù)最新研究,18%~33%的腦卒中患者會出現(xiàn)持續(xù)性的抑郁癥狀[2]。PSD會對腦卒中病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功能造成嚴(yán)重的損傷,使得疾病痊愈進(jìn)程減慢,從而導(dǎo)致卒中患者殘疾、死亡及復(fù)發(fā)的風(fēng)險顯著提高。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腸道和大腦之間存在相互交流和雙向作用,有學(xué)者將這種聯(lián)系稱為微生物群-腸-腦軸,亦稱作腦腸軸[3]。隨著腦腸軸的提出,卒中-腸道微生物-抑郁已成為新的研究熱點(diǎn),有證據(jù)表明腸道微生物可能是卒中后并發(fā)抑郁癥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4]。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xué)認(rèn)為,PSD尚無對應(yīng)的具體病名,根據(jù)其具體表現(xiàn)將其歸屬于“中風(fēng)”“郁證”二者合病范圍[5]。中醫(yī)藥治療中風(fēng)及郁證歷史悠久,歷代醫(yī)家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jīng)驗(yàn)和有效的治療手段。因此,基于“心腦共主神明”理論,深入探討PSD與腸道微生物群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1? “心腦共主神明”與微生物-腸-腦軸的傳統(tǒng)醫(yī)學(xué)理論依據(jù)
1.1? “心腦共主神明”理論溯源
在中醫(yī)基礎(chǔ)理論中[6],神的概念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之神是對人體生命活動的主宰及其外在總體表現(xiàn)的統(tǒng)稱,即人的生理、心理及生命活動的外在表現(xiàn)的總和,而狹義之神定義為意識、思維、情感等精神心理活動。從古至今,對于孰主神明一直呈現(xiàn)出“心主神明”“腦主神明”“心腦共主神明”等多種理論相互爭鳴的現(xiàn)象。“心主神明”最早見于《黃帝內(nèi)經(jīng)》,“心者,生之本,神明出焉。”《荀子·解蔽》亦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人的精神意識活動分屬于五臟,而主要?dú)w屬于心,人的思維活動、情感變化主要由“心”完成。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血脈和主神志,心主一身之血脈為基礎(chǔ),血液充盈、脈道流利,則血液運(yùn)行于周身,使機(jī)體氣血調(diào)和,神明清醒,才能更好地主導(dǎo)人體思維意識活動。“腦為元神之府”是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辛夷條》中最早闡明的論點(diǎn),其中指出:“腦為元神之府,而鼻為命門之竅。” 清·王清任《醫(yī)林改錯·腦髓說》則明確提出“腦主神明”一說[7]。張錫純先生深入研究、博采眾長,在《醫(yī)學(xué)衷中參西錄》中指出:“神明之體藏于腦,神明之用藏于心。”“人之神明,原在心、腦處,神明之功用,原在心、腦相輔而成。”更進(jìn)一步指出心主神明,腦為元神之府,心主血脈,心氣充沛,血液充盈,上行于腦,血足則腦髓充盈,故“心腦相通”“心腦共主神明”[8]。
1.2? 心腦與腸道微生物的關(guān)系
1.2.1? 心與腸道微生物相關(guān)? 人體是一個以心為主導(dǎo)、各臟腑相互為用、密不可分的有機(jī)整體,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與其他臟腑關(guān)系十分之密切。中醫(yī)學(xué)認(rèn)為,心與小腸相表里,小腸主受盛化物、分清泌濁,涵蓋了現(xiàn)代醫(yī)學(xué)中腸道的部分功能[9],與腸道微生態(tài)系統(tǒng)對物質(zhì)的消化、吸收功能相吻合。《靈樞·經(jīng)脈》記載:“心手少陰之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luò)小腸”“小腸手太陽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入缺盆絡(luò)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表明心與小腸經(jīng)絡(luò)循行中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中醫(yī)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整體觀念,不只是體現(xiàn)在臟腑之間表里相合,亦認(rèn)為互為表里的臟腑之間病理生理相通[10]。《素問·靈蘭秘典論篇》中有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心為任物之主,臟腑百骸功能皆與“心主神明”功能息息相關(guān),小腸亦如此。心的功能正常,心陽溫煦,則小腸得安,能夠維持正常的受盛化物、泌別清濁的功能;而小腸通過消化食糜后攝取水谷精微,精微物質(zhì)化赤為血,以滋養(yǎng)心脈,此即心與小腸生理上相通。病理上,心與小腸亦可互相累及,一則如《諸病源候論·小便血候》所謂:“心主于血,與小腸合。若心家有熱,結(jié)于小腸,故小便血也”[11],心與小腸以陽氣為用,但萬物不可過極,若心營熱甚,則心火下移小腸,熱灼膀胱血絡(luò),迫血妄行,可以導(dǎo)致小便短赤、灼熱澀痛等一系列癥狀,進(jìn)而使腸道微生態(tài)環(huán)境進(jìn)一步惡化,并使相關(guān)心系疾病的情況更加復(fù)雜。二則如《備急千金要方·心藏》言:“病苦頭痛身熱,大便難,心腹煩滿不得臥,以胃氣不轉(zhuǎn)水谷實(shí)也,名曰心小腸俱實(shí)。”此即小腸病傳變致心病,胃氣不能腐熟水谷,則化為實(shí)邪干于小腸,腸道微生物寄居于人體腸道內(nèi),小腸受邪,則腸道微生物群紊亂,小腸合于心,中焦?jié)釟馍瞎ビ谛膭t心胸?zé)M,心神不寧則夜寐不安。
1.2.2? 腦與腸道微生物相關(guān)? 腦為身之元首,乃奇恒之府,《靈樞·天年》述:“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五臟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說明腦與胃腸及腸道菌群在生理、臟腑功能上聯(lián)系緊密[12]。大量研究表明,腦與腸道微生物的相關(guān)性主要表現(xiàn)在:①腦與腸經(jīng)絡(luò)相通,《靈樞·經(jīng)脈》記載:“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之交頞中……循發(fā)際,至額顱”“大腸手陽明之脈……其支者,從缺盆上頸……上挾鼻孔”。由此可見,足陽明胃經(jīng)與手陽明大腸經(jīng)在經(jīng)絡(luò)循行過程中都經(jīng)過頭面部,通過經(jīng)脈與絡(luò)脈緊密聯(lián)系。②生理方面,脾主運(yùn)化,胃主受納腐熟,為水谷之海;小腸主液,大腸主津,脾、胃、大腸、小腸協(xié)同運(yùn)作以吸收、布散水谷精微,相輔相成,共同完成對五谷的消化、吸收和輸送,為大腦的正常生理功能提供養(yǎng)分[13]。《素問·靈蘭秘典論》中亦對脾胃、腸腑的生理機(jī)能做了詳細(xì)的記載:“脾胃者,食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頭為精明之腑,腦髓之海。《靈樞·五癃津液別》云:“五谷之津液,和合而為膏者,內(nèi)滲入于骨空,補(bǔ)益腦髓。”由此可見,脾胃中焦運(yùn)化水谷精微,氣血精微生化有源,腦髓得以充養(yǎng),這與腸道菌群可以促進(jìn)大腦生長及維持大腦正常生理功能的理論相似。
2? PSD與微生物-腸-腦軸的現(xiàn)代理論及依據(jù)
2.1? 微生物-腸-腦軸相關(guān)概述
大腦和腸道之間存在雙向通信交流和相互作用已成為廣泛共識[15],其中被稱為人類“第二大腦”的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ENS)與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CNS)、自主神經(jīng)系統(tǒng)、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等結(jié)構(gòu)相互作用,形成雙向調(diào)節(jié)軸,即腦腸軸[14]。研究發(fā)現(xiàn),腸道微生物群在該調(diào)節(jié)通路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是腦腸互動的核心角色,通過刺激神經(jīng)內(nèi)分泌和傳導(dǎo)通路,形成雙向通信交換的神經(jīng)-免疫-內(nèi)分泌網(wǎng)絡(luò),稱作微生物群-腸-腦軸(microbial-gut-brain axis,MGBA)。
人體腸道微生物群包括細(xì)菌、病毒、真菌、酵母和噬菌體,其中細(xì)菌是主要組成部分。調(diào)查顯示[16],腸道微生物群和宿主從胚胎生命的最早階段開始,通過母體相連,具有互惠互利的關(guān)系,影響嬰兒大腦發(fā)育和心理健康。腸道微生物群作為一個相對獨(dú)立且可變的人體組成部分,它的活動影響全身多個器官功能的生理運(yùn)動,對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影響尤甚,從而參與神經(jīng)精神疾病的發(fā)病過程[17],如自閉癥、抑郁癥、焦慮癥、腦卒中、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一系列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劉蘭香等[18]研究顯示腸道內(nèi)的微生物群落可通過神經(jīng)內(nèi)分泌、單胺類神經(jīng)遞質(zhì)、免疫炎癥、細(xì)胞信號通路、代謝通路等多種途徑影響大腦,證實(shí)腸道微生態(tài)失衡,則導(dǎo)致微生物-腸-腦軸功能紊亂,進(jìn)而誘導(dǎo)情緒、行為障礙。隨著MGBA獨(dú)特的調(diào)控機(jī)制被深入研究證實(shí),腸道微生物群治療PSD也成為當(dāng)前研究熱點(diǎn)。
2.2? ?PSD與腸道微生物群的相關(guān)研究
現(xiàn)代研究認(rèn)為,抑郁與腦卒中之間存在雙向聯(lián)系,腦卒中增加了抑郁的發(fā)生風(fēng)險,而抑郁作為腦卒中的獨(dú)立危險因素,亦加大了腦卒中復(fù)發(fā)及死亡的風(fēng)險率。近年來,PSD的發(fā)病率顯著提高,目前認(rèn)為PSD的發(fā)病機(jī)制繁多,尚不明確,涉及病理學(xué)相關(guān)機(jī)制和生物學(xué)機(jī)制等多個方面[19]。基于微生物-腸-腦-軸在神經(jīng)精神疾病的大量研究可推測,腸道微生物群的紊亂可使腸道屏障功能損傷、血腦屏障通透性改變,激活各類炎癥因子,介導(dǎo)免疫反應(yīng),從而調(diào)節(jié)神經(jīng)內(nèi)分泌及神經(jīng)遞質(zhì)的釋放,最終影響大腦功能,加快抑郁障礙的發(fā)生發(fā)展。如黃維翠等[20]研究發(fā)現(xiàn)PSD患者腸道菌群與單純腦卒中患者存在差異,腸道菌群紊亂影響血清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腦源性神經(jīng)營養(yǎng)因子(BDNF)、神經(jīng)生長因子(NGF)和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進(jìn)而影響PSD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妙煒等[21]認(rèn)為腸道微生物穩(wěn)態(tài)失衡導(dǎo)致VB12及FA的合成下降,進(jìn)而加重了卒中后抑郁障礙的程度。鄭舒等[22]通過實(shí)驗(yàn)驗(yàn)證血府逐瘀膠囊可上調(diào)腸緊密連接蛋白表達(dá),改善PSD引起的腸屏障功能損傷。綜上,腸道微生物群在PSD疾病發(fā)展過程中擔(dān)任了重要一環(huán),使得維持腸道微生物群穩(wěn)態(tài)有望成為干預(yù)PSD的新靶點(diǎn)。
3? 從心腦論治PSD
從中醫(yī)角度來講,PSD歸屬“中風(fēng)”“郁證”二者合病[23],總屬“因病而郁”。PSD是中風(fēng)的常見并發(fā)癥,其病機(jī)以中風(fēng)為主,并兼有郁證的一般特征。卒中后抑郁患者素體肝腎虧虛或痰濕內(nèi)熱,加之情緒過極,或外中風(fēng)邪,或肝風(fēng)內(nèi)動,以致風(fēng)痰瘀絡(luò),氣機(jī)升降失常,氣血逆亂,上擾心腦。其病位在腦,與心、肝、脾、腎相關(guān)。現(xiàn)代研究者發(fā)現(xiàn)的腸道微生物與心、腦及中樞神經(jīng)之間存在著較為復(fù)雜的相互作用,并在生理病理上相互影響,腸道微生物亦被證實(shí)介導(dǎo)抑郁障礙的發(fā)病[24]。因此,中醫(yī)可基于腦腸軸從心腦著手論治卒中后抑郁。
3.1? 從心論治
《類經(jīng)·藏象類》指出:“人身之神,惟心所主,故本經(jīng)曰:心藏神。”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亦主神明。首先,心藏神,主司意識思維、情志精神等正常活動,而氣為血之母,心亦主血脈,心氣不足則心主神明功能失常,即“心氣虛則悲”,正如《諸病源候論》[25]云:“心氣不足,其病苦驚悸,汗出,心中煩悶,短氣,喜怒悲憂,悉不自知”,心氣不足則出現(xiàn)憂愁悲傷、心悸煩躁等一系列郁證表現(xiàn)。其次,憂傷思慮等抑郁情緒亦會影響心的生理活動。如《黃帝內(nèi)經(jīng)》云:“人憂愁思慮則傷心”,人的情志會對心之氣血平衡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導(dǎo)致血行不暢,氣滯血瘀,出現(xiàn)胸痹胸痛等不適癥狀。
目前大量現(xiàn)代研究證實(shí),腸道菌群紊亂參與抑郁癥發(fā)病的環(huán)節(jié),抑郁癥患者腸道微生物多樣性和結(jié)構(gòu)改變。此外,一系列研究表明,心氣不足與卒中后抑郁及腸道菌群紊亂之間關(guān)系密切。馬永盛等[26]對65歲以上PSD患者的中醫(yī)證候分型進(jìn)行分析,結(jié)果顯示,PSD患者中脾陽虛證候出現(xiàn)頻率最高;PSD患者的胃腸道癥狀及其他軀體癥狀與心陽虛、肝陰虛證候關(guān)系密切。陳爽[27]運(yùn)用“調(diào)心健脾、益氣化瘀”針刺法聯(lián)合綜合康復(fù)治療心脾氣虛血瘀型缺血性腦卒中后抑郁患者,研究表明,針刺法可改善卒中癥狀,調(diào)節(jié)HPA軸,抑制炎癥反應(yīng),促進(jìn)神經(jīng)遞質(zhì)釋放和功能恢復(fù),進(jìn)而改善腸道微生態(tài)失衡。綜上,可以考慮從心論治PSD,通過益氣養(yǎng)心恢復(fù)腸道菌群平衡,進(jìn)而改善抑郁障礙癥狀。
3.2? 從腦論治
中風(fēng)之病,病位在腦。腦者,主神明,總統(tǒng)神、魂、魄、意、志諸神。《靈樞·海論》記載:“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于蓋,下在風(fēng)府。”《靈樞·經(jīng)脈》又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28],中醫(yī)角度上,腦髓化生正常,則人的意識、記憶、情志活動則正常運(yùn)轉(zhuǎn);若髓竅受損,則精神活動失常,神明無主,思想意識、運(yùn)動知覺失靈,發(fā)為中風(fēng),五志受累,逐漸發(fā)為郁病。隨著微生物-腸-腦軸在神經(jīng)精神疾病領(lǐng)域的研究發(fā)展,大量調(diào)查表現(xiàn),腸道微生物在促進(jìn)大腦發(fā)育、維護(hù)正常生理功能及導(dǎo)致病理狀態(tài)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冀旭艷等[29]基于“微生物-腸-腦軸”理論,采用隨機(jī)對照法觀察口服疏腦解郁湯對PSD患者的療效及腸道菌群影響,結(jié)果提示該方能通過調(diào)節(jié)患者腸道菌群的活性及多樣性來改善患者中醫(yī)臨床癥狀、神經(jīng)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趙子珺等[30]認(rèn)為頤腦解郁復(fù)方可通過增加乳桿菌屬和擬桿菌屬的含量促進(jìn)腸道微生物動態(tài)平衡的恢復(fù),維護(hù)腸道穩(wěn)定性,從而有效緩解大鼠的抑郁癥狀。因此,亦可考慮從腦論治,通過維持腦髓充盈,以期維持腦與腸道微生態(tài)的平衡從而改善卒中后抑郁的臨床癥狀。
4? 小結(jié)
PSD與微生物-腸-腦軸的關(guān)系一直是中西醫(yī)學(xué)研究的焦點(diǎn),基于“心腦共主神明”在卒中后抑郁的傳統(tǒng)及現(xiàn)代理論依據(jù),以腸道微生態(tài)平衡為基礎(chǔ),深入探討OSD的本質(zhì)及中醫(yī)病因病機(jī),為中醫(yī)藥在PSD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
5? 參考文獻(xiàn)
[1] 王少石,周新雨,朱春燕.卒中后抑郁臨床實(shí)踐的中國專家共識[J].中國卒中雜志,2016,11(8):685-693.
[2] Chun Yvonne Ho Yan,F(xiàn)ord Andrew,Kutlubaev A. Mansur,et al.Depression, anxiety, and suicide after stroke:A narrative review of the best available evidence[J].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22(4):53.
[3] 冉淦僑,戴佳錕,肖瀟,等."腸道微生物-腸道-腦軸"機(jī)制——腸道微生物干預(yù)神經(jīng)退行性病變研究進(jìn)展[J].現(xiàn)代生物醫(yī)學(xué)進(jìn)展,2018,18(14):2792-2796,2783.
[4] 劉莉.基于菌-腸-腦軸的腸肽與焦慮抑郁關(guān)系的研究進(jìn)展[J].中華全科醫(yī)學(xué),2022,20(8):1388-1391,1399.
[5] 吳雪利,王友剛.王友剛治療腦卒中后抑郁的臨床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J].內(nèi)蒙古中醫(yī)藥,2023,42(2):29-31.
[6] 郭霞珍主編.中醫(yī)基礎(chǔ)理論[M].上海: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6:8.
[7] 王清任·清.醫(yī)林改錯[M].上海:上海衛(wèi)生出版社,1956:9.
[8] 徐敏杰,常靜玲.論“腦心同治”理論對腦卒中康復(fù)的指導(dǎo)作用[J].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2022,45(10):1066-1070.
[9] 王世榮,岳壽松.微生態(tài)學(xué)與中醫(yī)“心與小腸相表里”新論[J].中國微生態(tài)學(xué)雜志,2018,30(7):847-848.
[10] 程艷,張苗苗,國嵩,等.“心與小腸相表里”理論的歷史源流及發(fā)展脈絡(luò)[J].中醫(yī)雜志,2023,64(13):1302-1307.
[11] 南京中醫(yī)學(xué)院編著.諸病源候論校釋[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9.
[12] 云小雯,吳鳳芝,徐一菲,等.基于“腸道菌群-腸-腦軸”探討肝郁脾虛證失眠[J].現(xiàn)代中醫(yī)臨床,2023,30(3):31-36,42.
[13] 曹文博,黃天琳,王慧萍.基于“腸道菌群-腸腦軸”理論探討中醫(yī)從胃腸論治偏頭痛[J].中國民族民間醫(yī)藥,2022,31(23):9-12.
[14] Hu W, Kong X, Wang H, et al.Ischemic stroke and intestinal flora: An insight into brain-gut axis[J].Eur J Med Res,2022,27(1):73.
[15] 熊林林,舒青龍,唐芳瑞,等.基于“腦腸軸”的中醫(yī)藥微生態(tài)研究進(jìn)展[J].時珍國醫(yī)國藥,2021,32(6):1438-1443.
[16] Codagnone M G , Simon S ,OMahony Siobhain M,et al.Programming bugs: Microbiota and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brain health and disease[J].Biological Psychiatry,2018,85:150-163.
[17] 崔佳瞿,陳啟儀,李寧.腸道微生物群-腸-腦軸在神經(jīng)精神系統(tǒng)疾病中的研究進(jìn)展[J].上海醫(yī)藥,2023,44(1):14-18.
[18] 劉蘭香,王海洋,謝鵬.腸道微生物紊亂誘導(dǎo)抑郁的腸-腦分子機(jī)制研究[J].重慶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2021,46(9):1003-1007.
[19] 王巖,彭顏暉.卒中后抑郁的發(fā)病機(jī)制和治療研究進(jìn)展[J].浙江醫(yī)學(xué),2023,45(2):220-224.
[20] 黃維翠,李柏新,劉振寧.腦卒中后抑郁患者腸道菌群分布及其與血清IGF-1、BDNF、NGF、hcy水平的關(guān)系[J].中國病原生物學(xué)雜志,2022,17(11):1341-1344.
[21] 妙煒,段昌嶸,謝雨萌,等.移植卒中患者腸道菌群后大鼠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變化對抑郁障礙的影響及機(jī)制[J].貴州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2021,46(9):1005-1010.
[22] 鄭舒,金博文,李東娜,等.基于腸屏障功能探討血府逐瘀膠囊防治卒中后抑郁作用研究[J].中南藥學(xué),2022,20(12):2823-2830.
[23] 吳雪利,王友剛.王友剛治療腦卒中后抑郁的臨床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J].內(nèi)蒙古中醫(yī)藥,2023,42(2):29-31.
[24] 茍梅麗,茍明慧,張靜,等.基于腦腸軸探討中藥治療卒中后抑郁的作用機(jī)制[J].中醫(yī)藥信息,2023,40(5):51-57.
[25] (隋)巢元方撰,黃作陣點(diǎn)校.諸病源候論[M].沈陽:遼寧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7.
[26] 馬永盛,陳國華,潘光輝,等.老年卒中后抑郁中醫(yī)證候分布特點(diǎn)分析[J].世界最新醫(yī)學(xué)信息文摘,2018,18(43):221-222.
[27] 陳爽.“調(diào)心健脾,益氣化瘀”針刺法聯(lián)合綜合康復(fù)治療氣虛血瘀型缺血性卒中后抑郁的臨床研究[D].天津:天津中醫(yī)藥大學(xué),2022.
[28] 王頤芳,龍華君,柏正平.基于微生物-腸-腦軸從“脾腎互贊”探討卒中后抑郁[J].中國醫(yī)學(xué)創(chuàng)新,2022,19(33):166-170.
[29] 冀旭艷,張恒嘉,李濤,等.疏腦解郁湯對卒中后抑郁患者腸道菌群的影響[J].中國實(shí)驗(yàn)方劑學(xué)雜志,2022,28(6):107-113.
[30] 趙子珺,趙瑞珍,張媛,等.頤腦解郁方對缺血性腦卒中及卒中后抑郁、焦慮、癡呆大鼠宏觀表征變化的干預(yù)作用[J].世界中醫(yī)藥,2018,13(12):3085-3090,3094.
[2023-11-16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