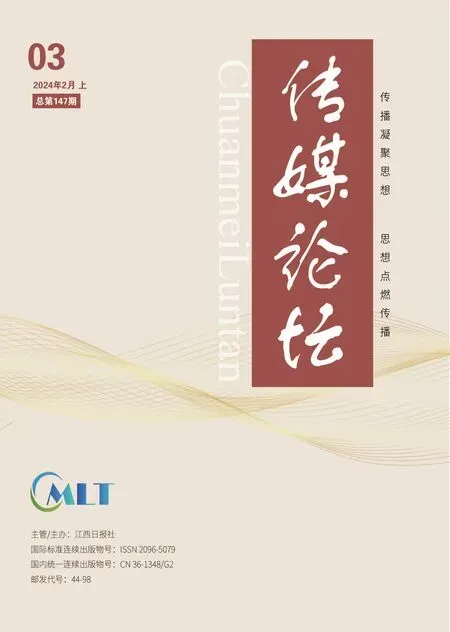抵近民眾:抗戰(zhàn)時(shí)期廣西學(xué)生軍的報(bào)刊活動
李時(shí)新 張佩琪
廣西學(xué)生軍系新桂系以知識青年為主體的半軍事的抗日救亡團(tuán)體,目的在于“培訓(xùn)抗日干部,宣傳民眾,組織群眾,配合正規(guī)軍作戰(zhàn)”[1],前后共有三屆。第一屆成立于1936年,存續(xù)僅月余;第二屆于1937年10月組建,奔赴湖北和安徽等地配合第五戰(zhàn)區(qū)作戰(zhàn),1940年結(jié)束;1938年10月日軍占領(lǐng)廣州后對廣西形成威脅,新桂系又于11月組織第三屆學(xué)生軍,動員民眾保衛(wèi)廣西,時(shí)稱“廣西學(xué)生軍”。第三屆學(xué)生軍組建之初先后成立了第一團(tuán)、第二團(tuán)、第三團(tuán)以及女生隊(duì)(后分配到三個(gè)團(tuán)),于1939年1月開赴桂林集訓(xùn)。2月初,由于日軍在海南島登陸,軍訓(xùn)提前一月結(jié)束,分派到桂東、桂東南各縣開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春,第一、二團(tuán)疏散到隆安下顏整編,建立學(xué)生軍團(tuán);7月整編結(jié)束,分派到左右江前線和敵后工作,1941年8月解散。本文主要探析第三屆學(xué)生軍(團(tuán))的辦報(bào)活動以及如何抵近民眾,進(jìn)行抗日救亡宣傳的。
一、廣西學(xué)生軍的工作區(qū)域與辦報(bào)活動
廣西學(xué)生軍從桂林集訓(xùn)到下顏整編直至最終解散,辦報(bào)是其工作的重要方面。廣西學(xué)生軍工作的區(qū)域和移動的軌跡也就是其辦報(bào)活動的范圍。為了有效地完成“宣傳民眾,組織民眾,訓(xùn)練民眾”的任務(wù),廣西學(xué)生軍被分配到其來源地工作。具體來說,第一團(tuán)團(tuán)部設(shè)在平樂,其工作區(qū)包括懷集、信都、鐘山、賀縣、八部、富川、蒙山、荔浦;第二團(tuán)團(tuán)部設(shè)在桂平,其工作區(qū)包括梧州、岑溪、容縣、北流、郁林、陸川、博白、興業(yè)、平南、貴縣;第三團(tuán)團(tuán)部設(shè)在賓陽,其工作區(qū)包括南寧、來賓、遷江、橫縣、永淳、武鳴、扶南、綏淥。[2]
據(jù)相關(guān)研究,學(xué)生軍創(chuàng)辦的報(bào)刊在1940年有85種,每期發(fā)行24252份。[3]1941年上半年總共有87種,其中日報(bào)11種,三日刊26種,五日刊8種,周刊21種,旬刊11種,半月刊10種,每期達(dá)三萬多份。這些報(bào)刊分布在桂東和桂南的25個(gè)縣,包括貴縣、平樂、蒙山、賀縣、鐘山、懷集、梧州、藤縣、蒼梧、玉林、興業(yè)、陸川、平南、信都、桂平、博白、岑溪、賓陽、邕寧、橫縣、永淳、隆安、北流、武鳴、上思等,占學(xué)生軍到達(dá)并活動的55個(gè)縣的45.5%,占當(dāng)時(shí)廣西全省99個(gè)縣市的四分之一。[4]辦報(bào)單位從學(xué)生軍司令部到各團(tuán)、各大隊(duì)和女生隊(duì),每級單位都辦有一種或數(shù)種報(bào)刊。[5]學(xué)生軍的抗日工作推動了報(bào)刊的廣泛的地域分布。
同樣以1941年的統(tǒng)計(jì)數(shù)字來看,這些報(bào)刊,一類是以學(xué)生軍為對象的內(nèi)部報(bào)刊,約占30%;一類完全面向社會,占25%;還有一類內(nèi)外兼顧,占45%。[6]也就是說,接近一半以上的報(bào)刊以社會各階層人士為讀者對象,這無疑促進(jìn)了報(bào)刊的下沉和對社會各階層的滲透力。
由上可知,廣西學(xué)生軍特別重視且善于運(yùn)用報(bào)刊這種現(xiàn)代傳播媒介,報(bào)刊的數(shù)量和發(fā)行量不斷推升,在廣袤的桂東、桂南農(nóng)村以及戰(zhàn)地廣泛分布,走向民眾。
二、凸顯地方性與加強(qiáng)讀者黏性
據(jù)《桂政紀(jì)實(shí)》記載:“廣西新聞事業(yè),在文化建設(shè)中,發(fā)展較遲。在抗戰(zhàn)以前,除省會所在地有一規(guī)模較大、設(shè)備較良之日報(bào)外,省內(nèi)各重要城市,為柳州、梧州、龍州等,所出日報(bào),大都因陋就簡;其他各縣,更無論矣。”[7]如在懷集鄉(xiāng)村,除了來自外縣的一份三日刊《平民》外,“其余根本就看不見廣大的工作者,因而民眾也得不到適當(dāng)?shù)木窦Z食”[8]。不僅報(bào)紙稀缺,即便有報(bào),投寄時(shí)間也是嚴(yán)重滯后。如桂平縣的潯旺鄉(xiāng)離縣城幾十里,消息較為閉塞,《桂平日報(bào)》從縣城寄到當(dāng)?shù)匾话阋欤鹆趾椭貞c的報(bào)紙所用時(shí)間更長。[9]學(xué)生軍創(chuàng)辦的報(bào)刊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工作地區(qū)缺報(bào)或少報(bào)的狀況,鄉(xiāng)民也能接觸報(bào)刊,了解抗戰(zhàn)形勢,汲取各類知識。至1940年,有的報(bào)紙已出版三百多期,有的達(dá)百余期,有的有十期或者幾十期,有的僅五期左右,各報(bào)存續(xù)時(shí)間不同,但累計(jì)“已有成百多萬份的報(bào)刊散布在城市、鄉(xiāng)村、戰(zhàn)場、敵后去了”[10]。
(一)編輯方針貼合地方和民眾
一是注重地方性。報(bào)紙的地方性或曰地方報(bào)紙不發(fā)達(dá),“大部分鄉(xiāng)村民眾不知道世界大事,不知抗戰(zhàn)的各種情況,另一方面,政府的命令也無由下達(dá),無由使民眾徹底了解,少數(shù)不良官吏可以任意曲解政令,作出與抗戰(zhàn)不利的事情”。[11]因此,“一個(gè)地方報(bào)紙,只要不失其地方性,總有它們存在的價(jià)值的”。[12]學(xué)生軍報(bào)刊總是將地方新聞安排在第一版。社論也以討論地方問題為主,在批評地方問題時(shí)不是消極指摘而是提出建設(shè)性的意見。[13]如信都的《火把》五日刊和《迎擊隊(duì)》三日刊以及懷集的《大眾報(bào)》三日刊和《懷集日報(bào)》都刊有本地當(dāng)天的新聞,社論等文章也具體針對讀者生活上的需要,因而頗能吸引讀者。《曙光報(bào)》自遷至左右江地區(qū)也相當(dāng)重視本地新聞,博得讀者的歡迎。
二是適應(yīng)讀者的文化程度和閱讀興趣。針對文化水平較低的讀者,將本戰(zhàn)區(qū)戰(zhàn)訊、地方新聞或一些與民眾關(guān)系密切的突發(fā)事件放在重要的版面;同時(shí),對電訊采取精編主義,根據(jù)其重要性進(jìn)行綜合或刪減;最后,副刊注意反映民眾的生活和其他切身問題,指導(dǎo)廣大的讀者練習(xí)寫作,成為報(bào)道本地新聞的投稿者或通訊員。[14]如,鑒于市面缺少適合大眾口味的刊物,駐梧州的學(xué)生軍除了出版免費(fèi)訂閱的油印《大眾小報(bào)》,還創(chuàng)辦鉛印的《好好睇》半月刊,“使大眾普遍得到精神糧食”[15]。而第一團(tuán)第三大隊(duì)的《大眾報(bào)》“內(nèi)容方面比較特色的有‘好好睇’一欄,專為一般勞苦大眾而設(shè),特用廣東俗語寫作”[16]。駐平南縣大安鎮(zhèn)的第二團(tuán)第一大隊(duì)學(xué)生軍出版的油印《大安報(bào)》三日刊主要針對窮苦的群眾讀者,“內(nèi)容和形式均遠(yuǎn)勝于《平南報(bào)》”[17]。有的專請名醫(yī)開辟“醫(yī)藥顧問”專欄,為病友服務(wù)。[18]
三是語言力求通俗易懂。這一點(diǎn)也是針對當(dāng)?shù)孛癖娢幕潭鹊汀⒆R字不多的實(shí)際情況。如,編輯電訊轉(zhuǎn)換成易于接受的白話或方言,發(fā)表的評論也力求通俗、簡潔、精練。如《火把》注意用廣東俗語寫文章,還開辟“老百姓”專欄,用淺近的語言解釋與農(nóng)民的生活有關(guān)的法令;《曙光報(bào)》 則提倡寫篇幅短小的文章,“在內(nèi)容上努力滿足讀者多方面的需要”[19]。
(二)建立穩(wěn)固的編讀關(guān)系
為了加強(qiáng)對本地情況的報(bào)道,更好地服務(wù)讀者,同時(shí)提升報(bào)紙的訂閱量,學(xué)生軍報(bào)刊十分注意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如《懷集日報(bào)》認(rèn)為“編者與讀者的聯(lián)系非常重要”,因而特別重視讀者來信,盡量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這樣,一方面報(bào)紙能夠貼近本地實(shí)際,體現(xiàn)出鮮明的地方性,“本報(bào)對地方上任何突發(fā)事件都加以詳細(xì)的分析與提供意見……因?yàn)樗茚槍δ骋坏胤酱蟮氖录M了輿論的責(zé)任,所以甚能引起讀者之注意”;另一方面也受到讀者的愛護(hù)和支持。“我們每當(dāng)發(fā)報(bào)之后,隨時(shí)都可看到許多讀者在街頭巷尾詳細(xì)的閱讀。”當(dāng)報(bào)紙?jiān)庥鲐?cái)力困難時(shí),有讀者慨然相助。如中洲鄉(xiāng)一位讀者就向報(bào)社捐助桂鈔十元,還熱心地請鄉(xiāng)參議員在參議會上提議為報(bào)紙撥款。旅居外縣的懷集人也經(jīng)常寫信詢問報(bào)社的情況,并提供改進(jìn)的意見。由于編讀聯(lián)系緊密,“我們各鄉(xiāng)的投稿者,都是盡義務(wù)的,然而他們?nèi)允遣婚g斷的投稿”。[20]
如果說民眾主動投稿在無形中形成了一個(gè)自發(fā)的通訊網(wǎng),那么許多報(bào)紙則有計(jì)劃地鋪設(shè)自己的通訊網(wǎng)。《懷集日報(bào)》的辦法是在每個(gè)鄉(xiāng)都聘請一位通訊員,這樣組成一個(gè)覆蓋全縣的網(wǎng)絡(luò),也因此“我們的地方新聞,并不見得怎樣缺乏”[21]。同樣,《火把》 也比較注重組建通訊網(wǎng),“由深入每一個(gè)山腳的工作小組的手里,報(bào)道出農(nóng)村最底層的生活來”[22]。
(三)擴(kuò)大發(fā)行量和讀報(bào)人數(shù)
學(xué)生軍創(chuàng)辦報(bào)刊主要在于交流工作經(jīng)驗(yàn)和宣傳抗戰(zhàn),發(fā)揮動員和組織民眾的作用。因此,提高發(fā)行量不在營利而在益智,而前提就是保證報(bào)紙質(zhì)量。由學(xué)生軍第二團(tuán)辦的《曙光日報(bào)》(后改為兩日刊)因其內(nèi)容豐富精彩,“握三區(qū)(即潯州、玉林和梧州)新型報(bào)的牛耳,也就是青年們所最熱愛的”,成為“西南新型油印報(bào)的模范”,每天銷量都在1000份以上。學(xué)生軍報(bào)刊擴(kuò)大發(fā)行量的方式一般有兩種:一是贈閱或張貼,二是售賣。《曙光報(bào)》創(chuàng)刊后在附近各鄉(xiāng)村張貼,應(yīng)學(xué)生軍、駐地附近的鄉(xiāng)村政府、學(xué)校、民眾和臨近駐軍的要求,免費(fèi)贈閱;后來需要者越來越多,乃改為正式訂閱,對外發(fā)行,僅收取成本費(fèi)。桂平縣的生活書店成為《曙光報(bào)》的寄售處,每天銷售數(shù)十份。[23]1940年五六月間,《曙光報(bào)》隨軍轉(zhuǎn)移到下顏繼續(xù)出版,發(fā)行至左右江沿岸以至賓陽、武鳴一帶十多個(gè)縣。[24]據(jù)統(tǒng)計(jì),《曙光報(bào)》在油印階段最高發(fā)行量達(dá)四千余份,在南寧改為鉛印日報(bào)后保持在四五千份。“一個(gè)地方小報(bào),當(dāng)時(shí)能夠達(dá)到這樣的銷售量,是很少的。”[25]
在七七事變爆發(fā)二周年紀(jì)念之際(即1939年),信都的《火把》發(fā)動義賣獻(xiàn)金運(yùn)動,三天之中在九鄉(xiāng)一鎮(zhèn)共售出七百多份,收得五百多元的獻(xiàn)款[26];容縣的《容縣日報(bào)》、博白的《大家看》三日刊、陸川的《大眾之友》三日刊、郁林的《好百姓》三日刊和《玉林青年》也發(fā)起義賣,平均收入在四五百元[27],既支持了抗戰(zhàn),又?jǐn)U大了報(bào)紙的影響和發(fā)行渠道。
三、克服業(yè)務(wù)、物質(zhì)和技術(shù)問題
廣西學(xué)生軍大多來自大學(xué)和中學(xué)等單位,并無多少新聞專業(yè)知識和技能。由于日軍封鎖和地理阻隔,紙張、蠟紙、油墨等印刷所需物資匱乏。在“青記”襄助以及自身勉力之下,廣西學(xué)生軍克服了辦報(bào)中的難關(guān)。
(一)“青記”和國新社幫助提升業(yè)務(wù)水平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xué)會(簡稱“青記”)和以“青記”骨干為基礎(chǔ)組建的國際新聞社(簡稱“國新社”)是中共領(lǐng)導(dǎo)下的全國性新聞記者組織和通訊社,由范長江、陳同生、孟秋江等創(chuàng)辦。由于新桂系對中共保持友善合作的態(tài)度,兩個(gè)組織于1938年先后遷到桂林辦公。學(xué)生軍由新桂系組建,但有不少中共黨員參加,他們在學(xué)生軍中發(fā)揮領(lǐng)導(dǎo)作用。“青記”和國新社為學(xué)生軍報(bào)刊培養(yǎng)骨干力量提供了許多支持。學(xué)生軍在桂林集訓(xùn)、分派到各地之前,國新社挑選一部分學(xué)生擔(dān)任通訊員。這些學(xué)生在每個(gè)星期日前往國新社聽社長范長江講授新聞報(bào)道與寫作知識,范長江建議大家訂閱《新華日報(bào)》和《救亡日報(bào)》,提高業(yè)務(wù)水平。這兩種報(bào)紙也支持各大隊(duì)的報(bào)刊。不少大隊(duì)的報(bào)刊的電訊和稿件都剪輯或轉(zhuǎn)載于這兩份報(bào)紙。“青記”還在桂林舉辦戰(zhàn)時(shí)新聞干部培訓(xùn)班,為學(xué)生軍培訓(xùn)新聞干部五十余人。[28]“青記”還指導(dǎo)成立曙光報(bào)分社,由中共地下黨員負(fù)責(zé),發(fā)展和培養(yǎng)了一些年輕有才能的記者和編輯人員。[29]范長江和陳同生等得知《曙光報(bào)》工作人員編報(bào)艱辛,寄來熱情的慰問信,一期不落地寄送他們主辦的國際新聞社的稿件,表示支持。[30]
(二)就地取材,自產(chǎn)油墨和紙張
由于學(xué)生軍工作任務(wù)的關(guān)系,學(xué)生軍報(bào)刊大多創(chuàng)辦于崇山峻嶺、竹木幽深的縣城墟鎮(zhèn),這里尚處于自給自足的社會經(jīng)濟(jì)狀態(tài),通往外界的道路時(shí)通時(shí)阻,各類物質(zhì)匱乏,文化閉塞,辦報(bào)困難重重。“因材料的困難,也就有許多(報(bào)刊)夭折了”[31];但報(bào)刊工作人員肩負(fù)抗戰(zhàn)宣傳的使命,工作熱情高昂,想方設(shè)法維持和鞏固報(bào)刊的出版。
在岑溪,學(xué)生軍積極推動,再加上當(dāng)?shù)貦C(jī)關(guān)贊助和合作,創(chuàng)辦了《岑溪日報(bào)》。學(xué)生軍接著創(chuàng)辦《號角》旬刊和《哨兵》三日刊,但由于材料貧乏,幾乎都停刊了,“但他們并不因此而灰心,他們還在困苦中奮斗著”[32]。
在桂東南地區(qū),以前辦報(bào)使用的紙張和油墨等都從香港經(jīng)陸路運(yùn)輸,廣州失陷后改由廣州灣(今北部灣)運(yùn)入,不僅交通不便,而且成本猛增,如80張一刀的紙張漲至國幣6元。感于經(jīng)費(fèi)捉襟見肘,報(bào)刊工作人員將一部分伙食費(fèi)和餉項(xiàng)(按百分之幾列支)充作辦報(bào)經(jīng)費(fèi)(許多紳士也自動捐助)。他們又就地取材,發(fā)明了用土材料配置的油墨,改用土紙。[33]
在平南縣大安鎮(zhèn),學(xué)生軍依靠每人每月節(jié)省的3元膳余,加上一小筆捐款和區(qū)公所提供的刻寫鋼板,辦起了一份刊物——《大安》,主要贈送給各機(jī)關(guān)團(tuán)體,打破了大安無報(bào)的歷史。后來,他們獲得廣西銀行大安辦事處負(fù)責(zé)人10元桂鈔的支持,將刊物改為《大安報(bào)》三日刊。他們遇到的主要問題是設(shè)備和經(jīng)費(fèi)。由于印刷工具和技術(shù)不好,幾次險(xiǎn)些停刊;他們修理一個(gè)廢棄的皮轆替換使用才渡過難關(guān)。洋紙、蠟紙、油墨價(jià)格飛漲,每月不到40元的辦報(bào)經(jīng)費(fèi)非常窘迫;同時(shí),膳余透支,伙食要靠賒賬才能維持。由于資金短缺,每期只能發(fā)行一百多份。即便如此,每逢紀(jì)念日,報(bào)紙都要加印兩版,并配上木刻漫畫。如何紓解經(jīng)費(fèi)窘迫問題?一是征求訂戶,每月每份2角,獲得二十多個(gè)訂戶;二是募捐,經(jīng)過動員,銀行以及區(qū)長、稽征局局長、郵政局局長、商會會長、平南縣副縣長和社會人士都參與捐款,總計(jì)有70多元。慶群劇社在“七七”二周年公演,將所得120元款項(xiàng)一半作為獻(xiàn)金,一半捐給《大安報(bào)》。[34]
(三)改進(jìn)蠟紙刻寫和油印技術(shù)
由于條件所限,鉛字和印刷機(jī)不易獲得,再加上隊(duì)伍經(jīng)常移動,學(xué)生軍報(bào)刊大多采用油印的方式,“將近90%都是只憑一筒蠟紙、一塊鋼板、幾枝椎子或留聲機(jī)的廢唱針和一些粗劣的紙張及油墨而辦起來”[35]。雖然油印報(bào)紙輕便,便于隨時(shí)遷移,但因小而簡陋,如何刻寫清晰、多量印刷就成為一個(gè)技術(shù)難題。也因此,初辦的報(bào)紙因缺乏經(jīng)驗(yàn),編排和印刷往往不甚美觀醒目,影響報(bào)紙的外觀、質(zhì)量和傳播效果。
《大眾報(bào)》是“平樂區(qū)首創(chuàng)的較優(yōu)秀的油印報(bào)”。工作人員因陋就簡,用留聲機(jī)的唱針在四號蠟紙上刻寫,“字體仿宋,頗秀麗整齊”;他們還別出心裁,用桐油或茶油與佛青按三比一的比例調(diào)制,自創(chuàng)油墨,將牛膠溶化鑄成印刷滾筒。[36]
表現(xiàn)較為突出的當(dāng)屬《曙光報(bào)》。《曙光報(bào)》從總編輯到一般編輯記者都參加了稿件的編寫、刻印工作。他們在蠟紙上刻寫的蠅頭小字,如五號字大小,端正整齊,一次印數(shù)從起初的幾百份達(dá)到一兩千份,版面美觀大方,有時(shí)還使用套紅,曾以優(yōu)良的編印技術(shù)在全國進(jìn)步油印報(bào)評比中獲得好評。[37]一個(gè)叫吳素馨的小姑娘,刻苦練習(xí)刻寫技術(shù),“不僅字寫得端正秀麗,而且每張蠟紙能油印兩千多份”[38]。有人說:“看了你們的油印技術(shù),即使不喜歡看報(bào)的人,也不能不拿起來貴報(bào)看一看。”[39]1940年底,《曙光報(bào)》隨學(xué)生軍團(tuán)遷到南寧,改為鉛印《曙光日報(bào)》,日發(fā)行量五六千份,最高達(dá)一萬余份,發(fā)行范圍覆蓋大半個(gè)廣西,時(shí)有“北有救亡(指《救亡日報(bào)》),南有曙光”之說。[40]
四、廣西學(xué)生軍報(bào)刊活動的影響
廣西學(xué)生軍的報(bào)刊活動,一是進(jìn)行政治教育,宣傳抗日救亡;二是抵近民眾,推動農(nóng)村地區(qū)文化的開展。以前者而言,懷集的《大眾報(bào)》一創(chuàng)辦很快就成為鄉(xiāng)村街長小學(xué)校和成人班師生、士紳和農(nóng)民的核心,“它組織了他們,推動督促訓(xùn)練了他們”[41]。陸川的學(xué)生軍創(chuàng)辦有《大眾之友》三日刊,有時(shí)學(xué)生軍把報(bào)紙當(dāng)作課本,教育民眾。[42]而《曙光報(bào)》散布到左右江每個(gè)偏僻的角落,報(bào)紙的社論和號召一經(jīng)發(fā)出,立刻引起了很大的關(guān)注。[43]
以后者而言,在抗戰(zhàn)初期就有人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鄉(xiāng)”的口號,“抱著書本的我們,既然沒有棄書從戈,但是能袖手旁觀嗎?救國不盡是拿槍桿的人干的,從事一點(diǎn)宣傳的工作,干一個(gè)‘跑到農(nóng)村去’的一員,也等(于)是救國責(zé)任之一”[44]。然而,盡管有人身體力行,但總體效果并不明顯;在軍隊(duì)和鄉(xiāng)村中“仍是看不到文章的影兒”,許多縣連一份報(bào)紙都看不到,如第一團(tuán)經(jīng)過的興業(yè)、貴縣、賓陽、上林、隆山、那馬、果德各縣(除了貴縣有大后方的報(bào)紙)就是如此。學(xué)生軍到來則煥然一新,很多鄉(xiāng)村和前線不但出現(xiàn)了壁報(bào)和新舊書籍、雜志,還出現(xiàn)了適應(yīng)當(dāng)?shù)氐钠毡榭械膸资N油印報(bào),“促進(jìn)了各地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45]。
郁林五縣原有《郁林日報(bào)》《陸川日報(bào)》、北流《建國日報(bào)》和一個(gè)三日刊共四家報(bào)紙,學(xué)生軍又創(chuàng)辦了四家油印報(bào)(如《好百姓》三日刊等),籌備出版《博白日報(bào)》。“鉛印的印刷工場,由四個(gè)而增到八個(gè),可見郁林文化工作的進(jìn)步。”[46]桂東南的信都和懷集兩個(gè)縣地處廣西邊陲,文化落后。“以文化而言,農(nóng)村里幾乎可說完全是未經(jīng)墾荒的處女地,他們過的差不多是原始社會的自供自給的經(jīng)濟(jì)生活。”三個(gè)中隊(duì)的學(xué)生軍創(chuàng)辦了《大眾報(bào)》和《火把》等報(bào)刊,“給他們帶來了新的文化、新的生活”[47]。
1939年廣西省政府發(fā)起和推行“成人教育年”,學(xué)生軍配合省政府辦起了大批各種形式的成人掃盲班和青年學(xué)習(xí)班,計(jì)有男女成人班2460個(gè),共173640人;高級成人班31個(gè),共1268人,還有讀書會升中補(bǔ)習(xí)班等。“這些學(xué)生和廣大農(nóng)村知識分子,無疑地也就是學(xué)生軍的報(bào)刊的讀者和支持者。通過他們,不僅宣傳了黨的政治主張,還把大批新文化種子撒到了這一帶廣大農(nóng)村。”[48]
總之,廣西學(xué)生軍分派到各縣,深入鄉(xiāng)村和前線,各大隊(duì)和不少的中隊(duì)以及軍民合作站出版油印小報(bào)、編印學(xué)習(xí)資料,對推動學(xué)習(xí)、宣傳抗戰(zhàn)、報(bào)道工作、交流經(jīng)驗(yàn)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學(xué)生軍編印的這些報(bào)刊在文化下鄉(xiāng)和文化上前線等工作中“做出了很好的貢獻(xiàn)和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49];同時(shí),通過辦報(bào)活動鍛煉出一批新聞工作者、編輯和文藝工作者。